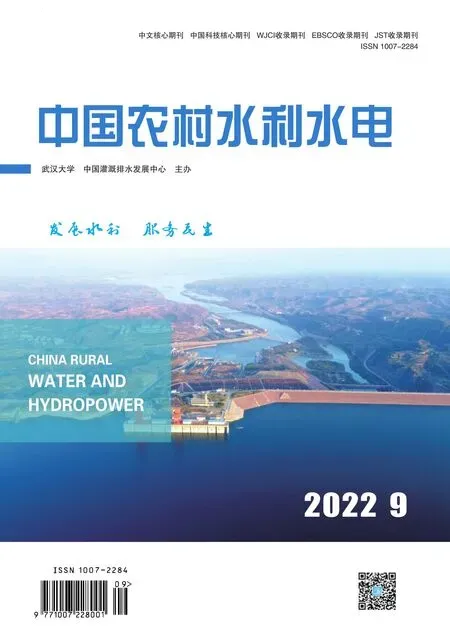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時(shí)空分布及其驅(qū)動(dòng)因子研究
易建州,李斯穎,付佳偉,王小笑
(江西省水利科學(xué)院,南昌 330029)
0 引 言
江西省山丘區(qū)占全省國(guó)土面積的78%,山洪災(zāi)害點(diǎn)多面廣、多發(fā)頻發(fā),每年因山洪災(zāi)害死亡人數(shù)占全省洪澇災(zāi)害死亡人數(shù)的80%以上,對(duì)基礎(chǔ)設(shè)施及環(huán)境資源造成了嚴(yán)重破壞。根據(jù)江西省2013-2015年度山洪災(zāi)害調(diào)查評(píng)價(jià)以及2017年度山洪災(zāi)害補(bǔ)充調(diào)查評(píng)價(jià)成果,全省94個(gè)山洪災(zāi)害防治縣有68.7萬人口受到山洪災(zāi)害嚴(yán)重威脅。
近年來,針對(duì)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的研究主要是在監(jiān)測(cè)預(yù)警、風(fēng)險(xiǎn)評(píng)估、防控等方面,如楊培生等[1]采用錐體法和風(fēng)險(xiǎn)潛勢(shì)關(guān)聯(lián)法,研究小流域山洪災(zāi)害監(jiān)測(cè)站網(wǎng)的布設(shè);雷聲等[2]分析了山洪災(zāi)害風(fēng)險(xiǎn)潛勢(shì)識(shí)別、監(jiān)測(cè)評(píng)估、預(yù)警及控制等4個(gè)主要環(huán)節(jié)的防控關(guān)鍵技術(shù),并在江西省進(jìn)行實(shí)踐;方秀琴等[3]通過觸發(fā)因子、孕災(zāi)環(huán)境和承災(zāi)體3個(gè)方面,構(gòu)建了山洪災(zāi)害風(fēng)險(xiǎn)評(píng)價(jià)指標(biāo)體系,對(duì)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風(fēng)險(xiǎn)進(jìn)行評(píng)估;徐慧茗等[4]、劉衛(wèi)林等[5]研究了山地景區(qū)的山洪災(zāi)害風(fēng)險(xiǎn)區(qū)劃。除此之外,對(duì)于山洪災(zāi)害驅(qū)動(dòng)因子、時(shí)空演變等方面的研究比較缺乏。
在山洪災(zāi)害驅(qū)動(dòng)因子的研究中,劉業(yè)森等[6]運(yùn)用空間聚類、熱點(diǎn)分析等時(shí)空分析方法,分析全國(guó)山洪災(zāi)害時(shí)空分布格局,利用地理探測(cè)器分析山洪災(zāi)害的驅(qū)動(dòng)因子,反映我國(guó)山洪災(zāi)害整體及各個(gè)分區(qū)的分異特征。熊俊楠等[7,8]采用空間分析和地理探測(cè)器對(duì)四川省和重慶市歷史山洪災(zāi)害時(shí)空格局和影響因子進(jìn)行研究。本研究整理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調(diào)查評(píng)價(jià)項(xiàng)目成果中的歷史山洪災(zāi)害數(shù)據(jù),利用空間分析方法研究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時(shí)空分布特征,同時(shí)利用地理探測(cè)器工具,進(jìn)一步探索降雨、自然環(huán)境、人類活動(dòng)等驅(qū)動(dòng)因子,對(duì)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時(shí)空分布的驅(qū)動(dòng)作用。
1 數(shù)據(jù)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shù)據(jù)來源
收集整理江西省歷史山洪災(zāi)害數(shù)據(jù)以及山洪災(zāi)害相關(guān)的人類活動(dòng)、自然環(huán)境、降雨等因素。各項(xiàng)數(shù)據(jù)及來源如下:
(1)基礎(chǔ)地理信息及歷史山洪災(zāi)害數(shù)據(jù)。來源于江西省2013-2015年度山洪災(zāi)害調(diào)查評(píng)價(jià)項(xiàng)目以及2017年度山洪災(zāi)害補(bǔ)充調(diào)查評(píng)價(jià)項(xiàng)目成果,基礎(chǔ)地理信息數(shù)據(jù)主要是江西省市縣三級(jí)行政區(qū)界、江西省12 546 個(gè)小流域單元矢量數(shù)據(jù)等,歷史山洪災(zāi)害數(shù)據(jù)為保證時(shí)間連續(xù)性,選取了1951年至2015年共2 978個(gè)歷史山洪災(zāi)害點(diǎn),歷史山洪災(zāi)害分布情況見圖1。

圖1 江西省1951-2015年歷史山洪災(zāi)害分布圖Fig.1 Historical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distribution map of Jiangxi Province from 1951 to 2015
(2)驅(qū)動(dòng)因子數(shù)據(jù)。根據(jù)山洪災(zāi)害發(fā)生機(jī)理,將山洪災(zāi)害驅(qū)動(dòng)因子數(shù)據(jù)分為自然地理、降雨、人類活動(dòng)3 類。選取高程、坡度、地貌類型、NDVI作為自然地理因子,土地利用、人口、GDP作為人類活動(dòng)因子,年最大10 min 暴雨均值、年最大1 h 暴雨均值、年最大6 h 暴雨均值、年降雨量作為降雨因子。其中自然地理、人類活動(dòng)以及年降雨量因子來源于中國(guó)科學(xué)院資源環(huán)境科學(xué)與數(shù)據(jù)中心(http://www.resdc.cn),年最大10 min 暴雨均值、年最大1 h 暴雨均值、年最大6 h 暴雨均值數(shù)據(jù)來自《江西省暴雨洪水查算手冊(cè)》(2010版)。
1.2 研究方法
采用標(biāo)準(zhǔn)差橢圓工具,分析各年代山洪災(zāi)害分布的方向及中心,通過Moran′I 函數(shù)探索縣域山洪災(zāi)害空間自相關(guān)性,利用聚類和異常值分析,識(shí)別歷次山洪災(zāi)害過程降雨量分布的局部聚類和突出值。基于降雨、自然地理、人類活動(dòng)三類影響因子數(shù)據(jù),利用地理探測(cè)器探測(cè)江西省歷史山洪災(zāi)害的主要驅(qū)動(dòng)因子以及各因子之間的交互關(guān)系;以十年為周期,選取山洪災(zāi)害記錄較為完整的1996-2005年以及2006-2015年兩個(gè)時(shí)間段,對(duì)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驅(qū)動(dòng)因子時(shí)空變化進(jìn)行研究。
1.2.1 空間分析方法
(1)中心及標(biāo)準(zhǔn)差橢圓分析。計(jì)算各年代山洪災(zāi)害分布的平均中心,即點(diǎn)集的質(zhì)心,平均中心計(jì)算公式如下:

在ArcGIS軟件中計(jì)算各年代山洪災(zāi)害的標(biāo)準(zhǔn)差橢圓,一級(jí)橢圓中包含總數(shù)68%的樣本數(shù),用來度量山洪災(zāi)害點(diǎn)的方向和分布的算法[9]。
(2)空間自相關(guān)。統(tǒng)計(jì)江西省各縣山洪災(zāi)害發(fā)生情況,以縣為單位,分析1950年以來各縣山洪災(zāi)害發(fā)生數(shù)量及相關(guān)屬性的全局自相關(guān)指數(shù)。全局自相關(guān)是通過計(jì)算數(shù)據(jù)集的Moran′sI指數(shù)值、z得分和p值,評(píng)估數(shù)據(jù)及相關(guān)屬性所表現(xiàn)的模式。Moran′sI>0 表示空間正相關(guān),值越大相關(guān)性越明顯,反之則為負(fù)相關(guān)。Moran′sI指數(shù)、z得分計(jì)算公式如下:

式中:其中zi是要素i的屬性與其平均值的偏差;wi,j是要素i和j之間的空間權(quán)重;n為要素總數(shù),S0為所有空間權(quán)重的聚合。
(3)聚類和異常值分析。利用聚類和異常值(Anselin Local Moran′s I)分析,分析江西省1951-2015年2978次歷史山洪災(zāi)害的過程降雨量分布,識(shí)別局部聚類和空間異常值。該算法對(duì)點(diǎn)集內(nèi)的每一個(gè)點(diǎn),都會(huì)計(jì)算Moran′sI指數(shù)和z得分。Moran′sI指數(shù)的算法如下:

式中:xi是要素i的屬性;Xˉ是該屬性的平均值;wi,j是要素i和j的空間關(guān)系權(quán)重;z得分的計(jì)算公式同(5)。
1.2.2 地理探測(cè)器
利用地理探測(cè)器研究山洪災(zāi)害空間分異的驅(qū)動(dòng)因子。將山洪災(zāi)害危險(xiǎn)程度作為地理探測(cè)器的因變量。在ArcGIS 平臺(tái)上對(duì)2 978個(gè)歷史山洪災(zāi)害點(diǎn)使用優(yōu)化的熱點(diǎn)分析工具,以z值作為山洪災(zāi)害危險(xiǎn)度,將山洪災(zāi)害危險(xiǎn)程度分為5 級(jí)。以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調(diào)查中劃分的12 546 個(gè)小流域?yàn)榉治鰡卧ㄟ^小流域的中心點(diǎn)提取山洪災(zāi)害危險(xiǎn)度和驅(qū)動(dòng)因子的數(shù)值。
地理探測(cè)器通過分析驅(qū)動(dòng)因子與因變量的空間分布,量化驅(qū)動(dòng)因子對(duì)因變量的影響程度即解釋力,還可以檢驗(yàn)不同驅(qū)動(dòng)因子空間分布的一致性,計(jì)算兩自變量交互后對(duì)因變量的解釋力,探測(cè)自變量之間的關(guān)系[10]。通過計(jì)算并比較各單因子q值及兩因子疊加后的q值,可以判斷兩個(gè)驅(qū)動(dòng)因子之間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及交互作用的強(qiáng)度、方向、線性或非線性等。q值計(jì)算方法如下:

式中:q為驅(qū)動(dòng)因子解釋力;h為驅(qū)動(dòng)因子;Nh和N分別為h影響因子的總數(shù)、研究區(qū)樣本量總數(shù);和σ為h影響因子的方差、研究區(qū)樣本總量的方差。q的取值在[0,1]之間,值越大說明驅(qū)動(dòng)因子對(duì)因變量空間分異的解釋能力越強(qiáng)。
2 江西省歷史山洪災(zāi)害空間分布特征分析
(1)中心及標(biāo)準(zhǔn)差橢圓年代變化。在ArcGIS平臺(tái)計(jì)算繪制江西省1951年以來各個(gè)年代歷史山洪災(zāi)害的1 級(jí)標(biāo)準(zhǔn)差橢圓(見圖2),可以看出江西省歷史山洪災(zāi)害總體分布呈東北-西南的態(tài)勢(shì)。各年代橢圓參數(shù)見表1,從1950年代到2010年代,橢圓的X軸相近,Y軸逐漸縮小,說明山洪災(zāi)害隨時(shí)間在南北方向上更向中心聚集。在1970年代,由于1973年在修河發(fā)生較大洪水,1975年在潦河發(fā)生較大洪水,引起江西省西北部修水縣、靖安縣多起山洪災(zāi)害,山洪災(zāi)害中心向西北方有較大的偏移。

圖2 各年代山洪災(zāi)害中心及標(biāo)準(zhǔn)差橢圓分布圖Fig.2 The elliptic distribution of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center and standard deviation in each decade

表1 各年代山洪災(zāi)害中心及標(biāo)準(zhǔn)差橢圓參數(shù)表Tab.1 Mountain torrent disaster center and standard deviation ellipse parameter table of each decade
(2)全局自相關(guān)。縣域全局空間自相關(guān)的計(jì)算結(jié)果見表2,其中縣內(nèi)山洪災(zāi)害數(shù)量和過程降雨量的Moran′sI指數(shù)為正數(shù),且p值小于0.05,通過顯著性檢驗(yàn),說明各縣歷史山洪災(zāi)害的發(fā)生數(shù)量和過程降雨量在空間上呈現(xiàn)顯著的正相關(guān),顯示出空間聚集性。死亡人數(shù)的Moran′sI指數(shù)為負(fù),經(jīng)濟(jì)損失的Moran′sI指數(shù)為正,但p值大于0.05,未通過顯著性檢驗(yàn),說明縣域內(nèi)死亡人數(shù)和經(jīng)濟(jì)損失沒有明顯的空間正相關(guān),呈現(xiàn)出隨機(jī)性。

表2 縣域內(nèi)各指標(biāo)全局自相關(guān)參數(shù)表Tab.2 Global Moran's I parameter table of each index in the county
(3)聚類和異常值分析。聚類和異常值分析結(jié)果如圖3(a),歷史山洪災(zāi)害過程降雨量在浮梁縣、婺源縣、資溪縣、石城縣、廣昌縣、崇仁縣、宜黃縣、尋烏縣形成了H-H型高值聚類,在宜春、贛州、九江市部分地區(qū)出現(xiàn)了H-L 型聚類。將結(jié)果與江西省暴雨區(qū)分布圖[圖3(b)]對(duì)比,可見這些區(qū)域大部分位于主暴雨區(qū),發(fā)生大暴雨的概率較大,容易引發(fā)山洪災(zāi)害。

圖3 過程降雨量聚類和異常值分析、江西省暴雨區(qū)分布圖Fig.3 Process precipitation clustering and outlier analysis,Jiangxi Province rainstorm classification map
3 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時(shí)空驅(qū)動(dòng)分析
3.1 驅(qū)動(dòng)因子選取與分布
結(jié)合山洪災(zāi)害發(fā)生機(jī)理和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調(diào)查評(píng)價(jià)成果,選取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的11 個(gè)驅(qū)動(dòng)因素。自然地理因子包括高程、坡度、地貌類型、NDVI,人類活動(dòng)因子包括土地利用、人口、GDP,降雨因子包括年最大10 min 暴雨、年最大1 h 暴雨、年最大6 h暴雨、年降雨量。其中,高程、坡度采用自然斷點(diǎn)法分為6級(jí),NDVI、降雨數(shù)據(jù)采用自然斷點(diǎn)法分為5 級(jí),人口、GDP 采用幾何斷點(diǎn)法分為5級(jí),地貌類型根據(jù)規(guī)范及江西省實(shí)際情況,分為平原、臺(tái)地、丘陵、低山、中山、高山6 類,坡度根據(jù)《水土保持綜合治理規(guī)劃》GB/T 15772-2008分為6類,土地利用根據(jù)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鄉(xiāng)、工礦、居民用地、未利用土地分為6 類。部分驅(qū)動(dòng)因子分布如圖4至圖11。是造成山洪災(zāi)害的主要因素,而最大6 h 降雨量對(duì)江西省歷史山洪災(zāi)害空間分布的解釋力最高。統(tǒng)計(jì)每個(gè)降雨因子內(nèi)部各個(gè)分區(qū),山洪災(zāi)害危險(xiǎn)度隨著雨量增強(qiáng)而提升。

圖4 高程等級(jí)分布Fig.4 Grading distribution of Elevation grade

圖5 坡度等級(jí)分布Fig.5 Grading distribution of Slope grade

圖6 地貌類型分布Fig.6 Distribution of geomorphic types

圖7 NDVI分布Fig.7 Grading distribution of NDVI

圖8 2015年降雨量等級(jí)分布Fig.8 Grading distribution of annual rainfall in 2015

圖9 土地利用類型分布Fig.9 Distribution of landuse types

圖10 2015年人口密度等級(jí)分布Fig.10 Grading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density in 2015

圖11 2015年GDP等級(jí)分布Fig.11 Grading distribution of GDP in 2015
人類活動(dòng)因子對(duì)山洪災(zāi)害的解釋力排名為土地利用(0.046)、人口(0.010)、GDP(0.005),土地利用和人口對(duì)山洪災(zāi)害發(fā)生的解釋力較強(qiáng),因?yàn)槿祟愂巧胶闉?zāi)害的主要承受者,土地利用是人類活動(dòng)的綜合體現(xiàn),對(duì)山洪災(zāi)害分布有一定的解釋作用。GDP 對(duì)山洪災(zāi)害分布有著微弱的解釋力,它雖然能影響到山洪災(zāi)害的分布,但不是主要的驅(qū)動(dòng)因子。
3.2 空間格局驅(qū)動(dòng)力
利用地理探測(cè)器對(duì)江西省1951年以來歷史山洪災(zāi)害空間分布的驅(qū)動(dòng)因子進(jìn)行分析,因子探測(cè)結(jié)果見表3。

表3 地理探測(cè)器因子探測(cè)結(jié)果Tab.3 Factor-detector results of Geodetector
由因子探測(cè)結(jié)果可知,對(duì)歷史山洪災(zāi)害解釋力最強(qiáng)的是降雨因子,解釋力大小依此為最大6 h 暴雨(0.488)、最大1 h 暴雨(0.45)、最大10 min 暴雨(0.446)和年降雨量(0.402),說明降雨
在自然地理因子中高程與坡度因子的解釋力較強(qiáng),分別為0.126 和0.104,表明地形起伏對(duì)山洪災(zāi)害有一定的影響。分析高程和坡度因子的風(fēng)險(xiǎn)區(qū)探測(cè)結(jié)果(見表4),由各分區(qū)內(nèi)山洪災(zāi)害強(qiáng)度平均值可知,在高程I 級(jí)分區(qū)(<123 m)山洪災(zāi)害危險(xiǎn)度最高,而在VI級(jí)分區(qū)(>968 m)山洪災(zāi)害危險(xiǎn)度最低,坡度I級(jí)分區(qū)(<5°)和VI 級(jí)分區(qū)(>35°)內(nèi)山洪災(zāi)害危險(xiǎn)度最高,原因是雖然高海拔高坡度地區(qū)易形成山洪,但這類地區(qū)人口密度較低,對(duì)人員和財(cái)產(chǎn)的損失較少,在地形高程低、坡度變化小的地方,人口密度高,山洪更容易成為威脅。

表4 高程及坡度因子風(fēng)險(xiǎn)區(qū)探測(cè)結(jié)果Tab.4 Risk-detector results of elevation
驅(qū)動(dòng)因子交互探測(cè)結(jié)果(表5)表明,最大6 h暴雨與其他驅(qū)動(dòng)因子的交互解釋力最強(qiáng),最高達(dá)到0.687,其他驅(qū)動(dòng)因子與其交互后,解釋力均大幅提高。探索驅(qū)動(dòng)因子兩兩交互后的結(jié)果(見圖12),降雨因子兩兩之間均為雙線性增強(qiáng)關(guān)系(Enhance,bi-),即P(A∩B)>max[P(A),P(B)],P(A)、P(B)分別是驅(qū)動(dòng)因子A、B對(duì)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分布的解釋力,P(A∩B)是A、B交互后的解釋力。最大6 h 暴雨、年降雨量與其他因子交互均為雙線性增強(qiáng)關(guān)系。

表5 驅(qū)動(dòng)因子交互探測(cè)結(jié)果Tab.5 Interaction_detector results of Geodetector

圖12 因子交互探測(cè)——雙線性增強(qiáng)結(jié)果(部分)Fig.12 Two-factor interactive detection——bilinear enhancement result(partial)
3.3 驅(qū)動(dòng)力時(shí)空變化
由于年代比較久遠(yuǎn)的山洪災(zāi)害,若無人員傷亡或失蹤,可能不會(huì)被記錄,導(dǎo)致數(shù)據(jù)不夠完整。江西省2013-2015年度山洪災(zāi)害調(diào)查評(píng)價(jià)項(xiàng)目數(shù)據(jù)截止至2015年,以十年為周期反推,選取江西省1996-2005年(Y1 時(shí)段)以及2006-2015年(Y2 時(shí)段)兩個(gè)近期時(shí)段,對(duì)山洪災(zāi)害驅(qū)動(dòng)因子時(shí)空變化進(jìn)行研究。對(duì)于人類活動(dòng)因子(人口、GDP、土地利用),分別采用2005年和2015年數(shù)據(jù),對(duì)于年降雨量,采用時(shí)間段內(nèi)的平均年降雨量進(jìn)行分析,地理探測(cè)器因子探測(cè)結(jié)果對(duì)比見表6。

表6 兩時(shí)間段地理探測(cè)器驅(qū)動(dòng)因子探測(cè)結(jié)果Tab.6 Factor-detector results of Geodetector in two time periods
對(duì)比Y1、Y2 兩個(gè)時(shí)間段各驅(qū)動(dòng)因子的解釋力,自然地理對(duì)時(shí)間段內(nèi)山洪災(zāi)害空間分布的解釋力保持穩(wěn)定,這是由于自然地理因子相對(duì)比較穩(wěn)定,對(duì)山洪災(zāi)害時(shí)空遷移的影響較小。
降雨因子在Y2 時(shí)段的山洪災(zāi)害空間分布的解釋力有著明顯增強(qiáng),說明降雨是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分布在Y1~Y2時(shí)段變化的重要驅(qū)動(dòng)因子,降雨因子中解釋力排名為年降雨量、最大6 h 暴雨、最大1 h暴雨、最大10 min暴雨。
人類活動(dòng)因子中,人口、GDP 的解釋力被削弱,可能隨著人類活動(dòng)的進(jìn)行,山洪災(zāi)害發(fā)生的原因更加復(fù)雜,單一的人類活動(dòng)因子解釋力有所下降。而土地利用是人類活動(dòng)綜合作用的結(jié)果,對(duì)山洪災(zāi)害的解釋力有所提高。
4 結(jié) 論
(1)江西省歷史山洪災(zāi)害重心集中在中部平原地區(qū),歷代標(biāo)準(zhǔn)差橢圓的X軸長(zhǎng)度相近,Y軸長(zhǎng)度呈現(xiàn)縮短的趨勢(shì),表明隨時(shí)間發(fā)展山洪災(zāi)害在南北方向上更加聚集。
(2)江西省縣內(nèi)山洪災(zāi)害的數(shù)量和平均過程降雨量在空間上呈現(xiàn)正相關(guān),顯示出空間聚集性。贛東北的浮梁縣、婺源縣,贛東石城縣、尋烏縣,贛中資溪縣、廣昌縣、崇仁縣、宜黃縣形成了高值聚類,為暴雨山洪多發(fā)區(qū)。
(3)江西省山洪災(zāi)害多分布在高程一級(jí)分區(qū)(<123 m)、坡度一級(jí)分區(qū)(<5°);降雨因子是山洪災(zāi)害分布的主要驅(qū)動(dòng)因子,最大6 h 降雨與其他因子交互后對(duì)山洪災(zāi)害分布的解釋力最強(qiáng),達(dá)到0.687;隨著社會(huì)發(fā)展,人類活動(dòng)造成的土地利用因子對(duì)山洪災(zāi)害的影響有所增強(qiáng)。
(4)雖選取了11 個(gè)較為代表性的影響因子,分析其對(duì)山洪災(zāi)害時(shí)空格局的驅(qū)動(dòng)力,但實(shí)際上山洪災(zāi)害的發(fā)生機(jī)理十分復(fù)雜,尤其是近年來人類活動(dòng)更加頻繁,引起了承災(zāi)體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承災(zāi)能力等方面變化,其對(duì)山洪災(zāi)害發(fā)生以及防治的影響,需要開展更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