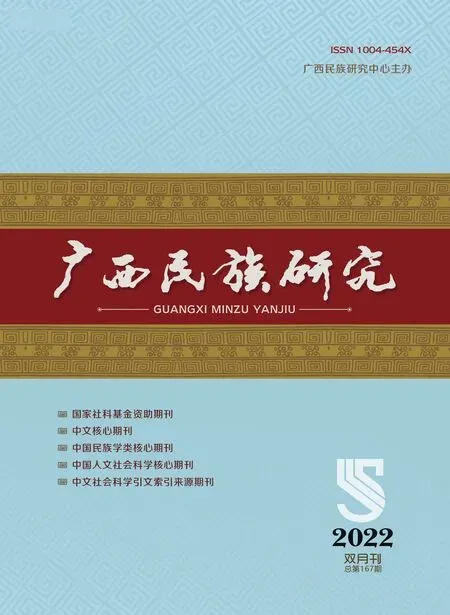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內涵、機理及路徑*
孟凡麗 王 靜 王國寧
2014 年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談會首次提出“牢固樹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著力點的關鍵表述歷經了“牢固樹立”—“積極培養”—“大力培育”—“鑄牢”的政策話語遞進過程,其演變是加強和改進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話語創新成果的集中體現。馬克思認為,“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1]11。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和國家意志的重要時代體現,只有融入各族群眾生活世界,才能日益彰顯出強大的理論說服力和實踐感召力,并獲得全面檢驗和實現理論“化大眾”。2022 年3 月,習近平同志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內蒙古代表團審議時著重指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要做看得見、摸得著的工作,也要做大量‘潤物細無聲’的事情”[2]。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需在政策、制度等宏觀設計上進行綜合考量,更要在“潤物細無聲”的落實落小落細上下功夫,其生活化正是立足各族群眾日常的學習、生活、工作而開展的命題闡發和微觀實踐探索。
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內涵解析
目前學界關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涵的研究集中于歷史形成、本體溯源、核心要素以及中國共產黨的主動形塑等方面:其一,基于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概念解析,如林意章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指中華民族共同體在新時代的社會經濟狀況、文化傳統、風俗習慣、地理環境等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綜合作用于中華民族精神生活的產物”[3]。其二,基于唯物論物質和意識辯證關系的內涵闡釋,重點從中華民族共同體實體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辯證關系進行了分析,如嚴慶認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人們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本體的認知和反映,既包括概念認知,也包括認同歸屬、理論解讀”[4]。其三,基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核心要素的有機協調而界定內涵,如陳瑛、郎維偉認為,“五個認同”則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內容[5]。其四,基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共同性內核的分析,如范君、詹小美認為,共建中華民族的命運與共意識、共享中華文化的共有精神家園意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心理認同意識等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價值內核[6]。其五,基于中國共產黨對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確立與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關系的分析,如張淑娟、陳憲章認為“中國共產黨全面文化自覺源于對傳統文化的正視、反思、重新敘述和劃定邊界,將傳統文化確立為凝聚中華民族共同體力量的基本素材”[7]。
生活化,顧名思義,是指通過人們生活中習以為常、細小甚微的方式融入其生活世界的過程,重在實現由生活世界向意義世界的有效建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生活化的相關論述以“現實的人”為邏輯起點,確立于“類本質”和“對象化”的概念之上,如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明確指出,“人們用以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的方式,首先取決于他們已有的和需要再生產的生活資料本身的特性。這種生產方式不應當只從它是個人肉體存在的再生產這方面加以考察。更確切地說,它是這些個人的一定的活動方式,是他們表現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們的一定的生活方式”[1]147,著重強調了社會生活的“實踐本質”——“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誘入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1]139~140,并提醒關注人們生產生活實踐的同時,要重視觀察和參與人們具體而細微的日常生活,主動追溯意識的“存在本源”,真正認識到“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1]152。此外,德國哲學家、二十世紀現象學學派創始人胡塞爾將生活世界定義為“作為唯一實在的,通過知覺實際地被給予的、被經驗到并能被經驗到的世界,即我們的日常生活世界”[8]58。素有西方學界公認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論之父”的法國思想家亨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則對“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作了基本區分,指出“日常生活就在我們身邊,從所有方面,從所有方向上,包圍著我們”[9]271。亨利·列斐伏爾的學生、匈牙利著名思想家阿格妮絲·赫勒(Agnes Heller)則將日常生活界定為“那些同時使社會再生產成為可能的個體再生產要素的集合”[10]3。西方學者對生活世界的界定和區分揭示了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范疇和能動性因素。我國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提出“生活即教育”的重要理論,認為“好生活就是好教育”“真正的教育作用是使生活與生活摩擦”。[11]381可以看出,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西方學者和我國人民教育家關于生活化的相關闡述各有側重,對于當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內涵厘定具有重要啟示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不是主張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消極地適應各族群眾的日常生活,也不是日常生活完全被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統攝,而是強調在各族群眾日常生活基礎上,發揮其對各族群眾生活世界的價值導引,在生活實踐中達到更高層次的精神圖景追求,并躍遷至提升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引領力、促進各族群眾自由全面發展的意義世界領域。總體來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具有人本性、體驗性、潛隱性、持續性、廣泛性的特點。
(一)“一個民族也不能少”的人本性
2019年,習近平在內蒙古考察時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一個民族也不能少”[12]。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內在要求是人民主體性,因此,必須堅持生活化的“人本性”理念,將維護各族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通過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各族群眾生產生活實際結合起來,以各族群眾“需要不需要”為出發點,以解決各族群眾關切的實際問題、現實需求為著力點,將各族群眾“滿意不滿意”作為落腳點,在各族群眾所思所想、所急所盼上下功夫;堅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問題導向、需求導向和結果導向有機結合,重點關注各族群眾業緣、趣緣等特點,根據各族群眾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體驗中的自我需求、認知困惑、行動偏好、未來愿景等進行靶向施策,引導各族群眾在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斷提升中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不斷增強“五個認同”,牢固樹立“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將實現好中華民族共同體整體利益始終放在首位。
(二)“看得見、摸得著”的體驗性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在理論層面重在理清各族群眾生活世界的基本范疇及向意義世界建構的內在邏輯,在實踐層面重在以有形有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引導各族群眾體驗和感悟生活世界,其本身就飽含著“接近生活,融入生活”的生活化氣息,更是對高高在上的理論說教的有力回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須落在有形的物質或活動載體上,以貼近各族群眾生活實際的中華文化形象和符號、標識性實物為切入點,使具體舉措“接地氣、暖人心、有特色、見實效”,如學校教育中思想政治理論課的課堂教學和“第二課堂”充分融入“五個認同”和“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的核心要素,社會教育中可融入娓娓道來的社區民族團結故事、以人為本的“微服務”體驗、城鄉公共文化實施建設、城市標志性建筑建設、旅游景觀陳列等,創造各族群眾“置身其中”的融入環境,使各族群眾“遠能識之,近則感之”,在耳濡目染和實際感觸中實現生活相依、情感相融、心靈相通,自覺形成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高度認同。
(三)“潤物細無聲”的潛隱性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是隱性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與各族群眾思想道德觀念的形成變化密切相關,直接受各族群眾日常生活環境、文化氛圍等直接影響。所以,可通過文化浸潤、輿論引導、風氣習染、精神支持與物質幫助等潛隱化方式,在落實落細中發揮著愛國主義情感陶冶、中華文化認同鑄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構筑、“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引導的功能,在潛移默化中不斷推進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例如,各族群眾勠力同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就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生動寫照,在我們黨的堅強領導下,各族群眾不分你我、并肩作戰,充分顯現出各民族相互依存、相互親近、共擔共享的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思維,以抗疫英雄的感人事跡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基本素材,通過榜樣示范等方式引導各族群眾增進對彰顯中華民族力量與擔當的偉大抗疫精神的敬畏與弘揚,形成“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的主動擔當感,在常態化抗疫中彰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新高度,使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將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團結互助傳統代代相傳。
(四)“宣傳教育常態化”的持續性
2021 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提出“要構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常態化機制”。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不可能一蹴而就,不是臨時性、短暫性、過場化的動員式活動,只有依靠穩定的、持續的宣傳教育常態化機制,融入經常性、習慣化的現實活動中,才能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無時不在”。在日常生活中,各族群眾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認識存在深淺不一、理解多樣的狀況,如何引導各族群眾準確全面把握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各民族意識的關系、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關系等,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完成的,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構筑更難以“畢其功于一役”,必須通過早期的“蹲苗”式生活化浸潤、初期的“育苗”式生活化融入、茁壯期“助苗”式生活化蓄力等方式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實現由生活世界重繪向意義世界建構的邁進,讓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各族群眾人心凝聚、團結奮進、共畫同心圓的強大精神支撐。
(五)“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的廣泛性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蘊含于各族群眾的實際生活狀態和各項工作開展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區資源稟賦、自然條件、人文環境等差別顯著,需要采取區域差別性的舉措,才能有的放矢地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作用于與各族群眾有關的各項具體實踐中,更好地體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人民主體性價值,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元素“像空氣一樣無處不在”;在生活化工作實踐中,準確全面地了解、把握和滿足各族群眾的基本需求,將文化浸潤與日常服務有機結合起來,不斷增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的親和力和感染力,使各族群眾由被動接受向主動參與轉變,調動各族群眾參與親身體驗、團結互助、共謀發展等,加深各族群眾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實踐價值的認識,才能激發各族群眾的心理共鳴,鞏固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文化上的團結統一,由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主觀認知上升到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踐期許和砥礪前行。
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發生機理
生活世界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起點和歸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本質上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與各族群眾生活世界的能動互構過程,二者內在貫通且相互支撐,形成自洽的內在邏輯圖式。
(一)以植根于生活為邏輯起點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層面的重要內容,在各族群眾生活世界的實踐活動中得以產生和發展。馬克思曾說,“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146,并指出,“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1]159。日常生活包含人對物質生活本身的能動效用,是人的有意識有目的的感性活動的縮影,是人的“現實的生活生產”和再生產活動的集合,是由物的依賴到在物的基礎之上追求人的獨立性的超越,以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為奮斗目標,因此,不斷變化的生活世界正是人類生存、發展、追求更高層次的意義世界的基本前提。
馬克思認為,“個人怎樣表現自己的生命,他們自己就是怎樣。因此,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怎樣生產是一致的”[1]147。毛澤東曾說,“你要有知識,你就得參加變革現實的實踐。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變革梨子,親口吃一吃”[13]287。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實踐基點是現實的人及其實踐活動,各族群眾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始終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現實基礎和動力源泉,教育引導各族群眾增強“五個認同”、牢固樹立“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等均是建立于各族群眾日常交往交流交融生活實踐基礎上的精神對話活動。植根于生活世界,就要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牽引相統一,在不同場域呈現出適合特定群體特點的融入方式,并根據不同群體的日常生活需求,結合各族群眾日常生活實際進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浸潤和微觀實踐探索,并融入各族群眾接受度高、參與性強的生活體驗中,不斷構筑各族群眾共建共享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使各族群眾在有感的融入活動中強化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生活化認知,內化為自身精神世界的時代渴求,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深深扎根于各族群眾生活實際中,為引導各族群眾由生活世界向意義世界的進階奠定了現實基礎。
(二)以升華于生活為意義探賾
馬克思指出,“光是思想力求成為現實是不夠的,現實本身應當力求趨向思想”[1]11。遵循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實踐相統一的邏輯理路,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抽象思維”過程是由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的基本途徑。“五個認同”與“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作為國家統一、社會穩定、民族團結的思想基石,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力量源泉和意義世界建構的核心內容。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世界的意義生成,是由各族群眾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感性認識上升到對“五個認同”“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的理性體悟過程,是在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基礎上,增強各族群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覺認同和歸屬。因此,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升華需以各族群眾的生活世界為現實基礎,以各族群眾生動、鮮活的交往世界為實踐場域,以形式多樣的社會實踐活動為依托,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經驗形態升華為科學樣態,促進各族群眾生活世界的意義建構與價值提升,實現由生活世界向意義世界的成功躍升。
各族群眾實際生產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新變化體現著各族群眾生活、學習、交往狀況中的經驗形態、內在發展規律與追求意義世界的努力,映射著各族群眾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認同狀況和向以“五個認同”“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為核心的意義世界的躍遷進度。應從各族群眾的實際生活體驗、實踐工作感性材料和生活經驗入手,通過對各族群眾生活世界的全面洞察,由各族群眾生活世界現象以及局部的生活世界認識上升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全面認識,由對各族群眾日常生活現象的描述深化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本質的透視,形成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規律的內在探尋,進而發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意義世界對各族群眾生活世界的積極推動作用,促進各族群眾在生活世界中和衷共濟、和諧發展、和睦相處,進一步維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的大團結局面,為不斷豐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內容,科學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具體工作提供理念指引。
(三)以回歸于生活為實踐指向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1]413,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從“現實運動”的角度闡發了“共產主義”的實踐性特質:“共產主義對我們來說不是應當確立的狀況,不是現實應當與之相適應的理想。我們所稱為共產主義的是那種消滅現存狀況的現實的運動。”[1]166毛澤東曾多次強調源于實踐的理論仍需回到實踐接受檢驗的必要性,指出“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13]284,“認識從實踐始,經過實踐得到了理論的認識,還須再回到實踐去”[13]292。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理論對各族群眾交往交流交融實踐提供了理論指導與價值引領,在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理論和實踐經驗進行歸納提煉的基礎上,明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核心內容和內在邏輯,形成了富有代表性、具有適用性的實踐經驗,這些實踐經驗是否符合各族群眾新的生活實踐要求,仍需再次回歸到各族群眾生活世界,在指導各族群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活化實踐中得到真正理解、有效檢驗和再次升華,以此循環往復,達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理論創新和實踐探索的良性互動。
馬克思認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1]140。從回歸各族群眾生活世界來看,通過參與體驗、自我教育、文化熏陶、典型經驗推廣等方式使各族群眾在生活化認識中確立了正確的中華民族觀和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高度認同,并將可以推廣的有益經驗、普遍模式和共有標準等因地制宜地打造成適用的“楓橋模式”,為更好地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提供了經驗支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社區實踐為例,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社區黨建、社區教育、社區管理、社區服務、社區環創、智慧社區建設等現實載體,充分發揮社區治理要素隱性施教的潛在優勢,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滲透到社區“法治、德治、自治”有機融合、公共精神培育等操作實踐中,使各族群眾在主動參與社區公共事務中自覺形成社區生活共同體意識;通過對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社區實踐材料進行整理、加工和凝練,以社區思政教育引導各族群眾由對社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感性認識上升到認同中國共產黨的全面領導、基層治理制度優勢,積極轉向和參與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
(四)以引領于生活為價值旨歸
馬克思指出,“理論一經掌握群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說服人,就能掌握群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1]9~10。毛澤東也引用他人語言指出,“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系起來,就會變成無對象的理論”[14]791。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進行了一脈相承的創新發展,與時俱進提出了中華民族大家庭、中華民族共同體等理念,明確了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進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思想、戰略目標、政策舉措以及重點任務,散發著馬克思主義真理的時代光芒,彰顯著新時代黨的民族理論創新的強大吸納力、巨大包容力和偉大實踐創造力,是指導各族群眾廣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行動指南。同時,伴隨著全球多元文化主義和西方蕪雜信息泛濫等帶來的思想困擾,受地緣政治因素裹挾的民族分離主義等悄然涌動,西方國家主導的披著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等“外衣”的文化霸權依舊虎視眈眈,企圖以隱秘化、科技化的形式向各族群眾日常生活滲透,各族群眾生活世界若缺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理論給養和精神引領,極易受到西方各類不良社會思潮的影響和占據。
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引領各族群眾生活世界的方方面面表現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各族群眾生產生活現代化發展的內在精神要求,指引著各族群眾在理想信念、價值理念、道德觀念上緊緊團結在一起,形成彼此“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日常生活思維,成為在生活中“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擰成一股繩”的“相親相愛一家人”,在精神情趣選擇上主動對標新時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要求,不斷提升與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相契合的道德素養;其內容和要求日益轉化為各族群眾的行為規范和實踐標準,能夠幫助各族群眾正確辨析和鑒別生活世界中遇到的各類錯誤思潮,自覺形成堅決劃清是非界限、抵制錯誤思想觀點的政治定力;引導各族群眾在向現代化生活方式邁進中緊跟時代發展步伐,將堅定“五個認同”、牢固樹立“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作為自身價值追求和精神歸屬的最高域,不斷夯實國家統一之基,鞏固民族團結之本,守護好精神力量之魂。此外,伴隨著全球多元文化主義和西方蕪雜信息泛濫等帶來的思想困擾,受地緣政治因素裹挾的民族分離主義等悄然涌動,西方國家主導的披著所謂“自由、民主、人權”等“外衣”的文化霸權依舊虎視眈眈,企圖以隱秘化、多樣化的形式向各族群眾的日常生活廣泛滲透,極易使各族群眾受到西方各類不良社會思潮的影響。通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宣傳教育給予各族群眾生活世界理論給養和精神引領,對于維護我國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安全具有重要意義。
三、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實踐路徑
遵循和運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發生機理,重在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作為多維度共同推進的系統工程,從內容、方式、機制、支持保障層面協同并舉,讓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觀則有形”“觸則有感”“行則有效”。
(一)打造“有形”的生活化內容
“有形”的生活化內容須以生活化呈現為抓手,以生活化的符號體系建構為支撐。一方面,重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活化呈現。習近平指出,“要讓文物說話,讓歷史說話,讓文化說話”[15]。“從多樣性的民族文化發展到統一性的中華文化是中華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邏輯。”[16]因此,應充分利用考古、歷史和文物研究成果,創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生活化呈現方式,如承載著非常豐富的歷史文化和藝術信息的敦煌莫高窟、云岡石窟、龍門石窟、古絲綢之路遺址,象征中華民族“和合”文化的紅山玉龍,中華民族歷史生動見證的茶馬古道等都蘊含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內涵。各地應依托當地豐厚的文物資源,挖掘館藏文物和文物遺址中蘊含的中華文化符號,如新疆民豐縣尼雅遺址的“五星出東方利中國”錦護膊,吐魯番市交河故城、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阿斯塔那古墓群、長城烽燧遺址等世界文化遺產都是各民族大融合的顯著標志和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技術化手段進行生活化形塑和處理,在街頭巷口、公共文娛場所多彩呈現,有助于各族群眾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形成全面了解和認知,增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理論的感染力、傳播力,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
另一方面,構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符號體系。圍繞自然山川、飲食生活、雕塑建筑、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等方面進行能動性符號建構,如在社區環境創設、公共街道、聚集性場合等圖繪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等建筑標識,增強各族群眾直觀的國家認同視覺感知;積極挖掘“長城”“長江”“黃河”等地理符號,打造“龍的傳人”“東方巨人”等書寫著中華民族集體記憶和價值情懷的文化標識,有力涵育中華民族認同生活化的內容;對“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像珍視自己的生命一樣珍視民族團結”等耳熟能詳的話語進行生活化符號表征,讓中華文化認同內容更“有形”;將作為中國共產黨象征和標志的黨徽黨旗充分展現在各族群眾生活中,以黨員公共場合正確佩戴黨徽、城市街道集中懸掛黨旗國旗等方式激發各族群眾愛黨愛國的真摯情感,結合當前時代境遇對一代代中國共產黨人團結帶領各族群眾共同鑄就的精神譜系進行生活化符號轉化,實現各族群眾對黨史的全面了解和對中國共產黨的高度認同;挖掘體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優勢的生活化符號,如作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生活化符號表現為各級人大代表,各族群眾可通過向各級人大代表反映自身的合理利益訴求等方式深化對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特征和優勢的認識,進而形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度認同。
(二)創新“有感”的生活化方式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作為落實落細的社會化工程,其方式創新需在不同實踐場域多維聯動和同構互塑。
就學校教育而言,積極推行系統性的生活化教育方式。一方面,無論是課堂教學還是“第二課堂”,都重視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容的“課堂滴灌”和日常生活教育的融會貫通,增強生活化內容的趣味性與吸引力,加強各族學生的融入性體驗,發揮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教育對各族學生日常行為的思想規約與價值引導。另一方面,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校園文化環境創設、大學生“三下鄉”實踐、“民族團結一家親”活動、互嵌式居住格局與“一站式”學生社區建設等,組織各族學生定期參觀革命紀念館、歷史博物館、紅色景區、中華文化藝術作品展等,引導各族學生在“有感”接觸中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建設與改革取得的輝煌成就,體會到革命先烈、英雄人物的偉大崇高,認識到“我是中華民族一份子”,在集體生活體驗和切身感受中形成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自覺認同。
就社會教育而言,多維融入社會范圍的“大生活”與各族群眾“與我有關”的“小生活”。一方面,廣泛開展中華文化浸潤社會主題宣傳活動,塑造富有特色的中華文化樣式,如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符號融入公共文化設施建設、城市標志性建筑建設、旅游景觀陳列等,設置中華民族精神特質視覺形象宣傳欄,在中華民族重要傳統節日創作體現中華文化的春聯、美繪本等喜聞樂見的文化作品,引導各族群眾感悟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樹立正確的中華民族歷史觀。另一方面,以通俗易懂的口袋書、社區廣播、公眾號等呈現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具象化內容,以“傳頌紅色家書”“文藝+宣講”方式激發各族群眾參與民族團結進步創建的熱情,營造富有時代特點和教育意義的濃郁文化氛圍。此外,滲透到各族群眾日常行為規范中,增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在價值要求對各族群眾日常行為的規約,使各族群眾在理論熏陶中養成維護各民族大團結的行為自覺,以生活化感知增進各族群眾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情誼。
就網絡空間而言,有力推進網絡空間傳播方式的優勢互補。一方面,推廣以“講好中國故事”等線上微視頻為主的生活化宣傳教育方式,在各類官方抖音、微博等設置有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內容的宣傳主題,有針對性地引導各族群眾參與網絡留言和線上互動,使各族群眾在“面對面”與“鍵對鍵”的多位適應中加深了解、交友交心。另一方面,加強網絡空間話語符號建構,通過對中華文化進行深耕、細描,塑造具有可視化特點的中華文化話語符號,如將“各民族要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等打造成具有標識性的“石榴”型網絡平臺符號,加深各族群眾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直觀認知。此外,鞏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網絡輿論紐帶,加強網絡輿情的引導和監管,營造良好的網絡輿論環境,提高對西方國家網絡文化生活化滲透的有效防范處理能力,凝聚網上網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思想共識,使網絡空間成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最大增量。
(三)建立常態化的“有效”落實機制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落實落細須以黨的組織領導機制為保證,以具體執行機制基礎,以評估激勵機制為動力。
首先,堅持和完善黨的組織領導機制。習近平指出,“加強和完善黨的全面領導,是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根本政治保證”[17]。各級黨委應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指導下,認真履行主體責任,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把黨的領導貫穿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全過程,充分發揮黨建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中政策統籌、方案設計、安排部署中的引領作用;在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過程中確保總體目標一致、各方有力協作,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核心要素和相關要求融入政策制定、分階段執行等各環節,重構各族群眾生活世界中“人心政治”治理實踐新樣式,通過以細化目標、確立標準、建立機構、完善機制等方式做好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宏觀設計,為推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工作提供堅強的政治保證。
其次,形成與時俱進的具體執行機制。應通過制定逐級、逐步、逐層的分階段生活化融入計劃和實施步驟,確立點、線、面相結合的生活化宣傳教育網絡;因時、因地、因人精準施策,探尋由宣傳教育者外顯展示、外部熏陶到各族群眾主動認知接受、內化吸收、外化踐行的生活化機理,激發各族群眾的自覺參與熱情,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宣傳教育走深走實;改進傳統剛性的工作方式方法,依靠情感體恤、情感共享等情感聯結紐帶,使各族群眾形成關系親密、困疾相扶的情感互惠期許;重視升國旗儀式、“國慶”節日等生活化內涵的挖掘,引導各族群眾在日常生活中時常感受到“愛國就在身邊”;將“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走向復興”等紅色經典歌曲融入各族群眾生活中,將對偉大建黨精神、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各族群眾進行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光榮歲月轉化為樸華無實的“身邊人、身邊事、身邊物”等,使各族群眾在切身體悟中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始終秉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最后,建立健全評估激勵機制。按照分級負責、權責統一的原則,當地黨政主管部門可擇機牽頭成立常態化評估機構,由具體負責的常態化評估機構組建熟悉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的專業評估隊伍;制定切合當地實際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評估方案,明確評估過程中按照“增進共同性”方向設計具體評估內容;搭建日常檢查和定期督導相結合的評估體系,逐步量化評估程序和操作步驟;培樹一批高質量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示范點,發揮示范點的模范效應和動員作用,對落實工作不到位或反復性問題提出整改建議,確保監督實效,力從機制上找原因、尋根源,對標糾偏,在深入整治中健全評估激勵機制,形成持續長效的責任落實格局,切實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工作往實里抓、往細里做。
(四)加強“有力”的支持保障
“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1]151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既要建立在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基礎上,也要為該工作的具體開展提供基本的物質條件支持與制度保障。
首先,多措并舉推動各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應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立足民族地區的資源稟賦、發展條件、比較優勢等,不斷完善差別化區域支持政策,積極貫徹新發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民族地區經濟高質量發展和融入新發展格局;適當向邊疆民族地區進行政策傾斜和人財物扶持,加大邊疆民族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產業結構調整支持力度,優化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實現民族地區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促進當地農牧業高質高效、鄉村宜居宜業、農牧民富裕富足,進而大力提升各族群眾自我發展能力,不斷提升各族群眾實際獲得感、幸福感,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奠定厚實的物質基礎。
其次,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工作提供基本的人財物保障。學校、社會以及網絡空間都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實體依托,因此,應著力確保學校、社會以及網絡空間開展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工作的人財物支持,使各場域的具體落實“有組織領導,有人員完成,有經費支持,有具體做法,有實踐成效”,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覆蓋全社會各層面、各方面、各角落,使各族群眾在日益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中感受到堅定“五個認同”、牢樹“四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的現實重要性,體驗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精神愉悅感,從而積極適應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實質要求相對應的生活環境,并在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中實現對美好生活的果敢追求和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合力構筑。
最后,通過具體制度規范的精準設計予以確認和保障。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憲法修正案將“中華民族”寫入《憲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在2019 年印發了《關于全面深入持久開展民族團結進步創建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意見》,2022 年1 月21 日,全國人大憲法法律委召開會議,進一步修改完善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織法(修正草案)》,在多數條款中充實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等內容,并完善了相關規定[18]。因此,有關部門應根據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對部門規章、地方性條例進行適用性調整、修訂,聚焦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工作中的基本要求、主要內容、落實舉措等,逐步細化具體操作方法和執行程序,注重制度完善過程中“增進共同性”的價值目標、價值取向、價值準則的內在統一,明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活化的指導性標準和評價性細則,使各族群眾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內心有尺度、行為有準則,切實提升制度保障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