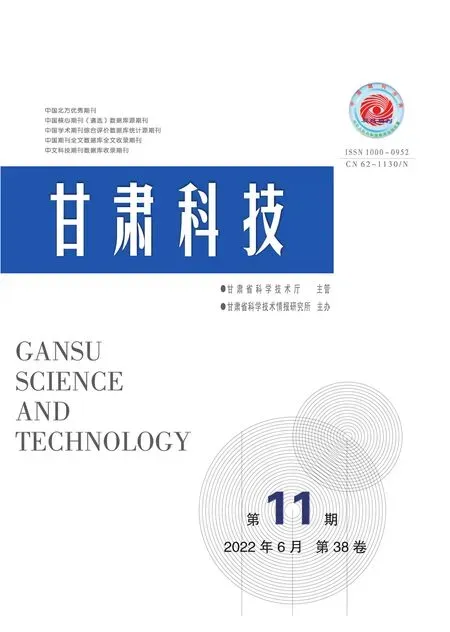隴東一次暴雨成因對比及預報偏差分析
向 軍,鄭 新,崔宇
(蘭州中心氣象臺,甘肅 蘭州 730020)
1 概述
我國西北地區地形地貌相對復雜,使得暴雨的時空分布特征與我國東部沿海地區有明顯差異,而甘肅省隴東地區又屬于西北地區暴雨發生較多的地區,且暴雨多以對流性強降水為主,因降水強度大、歷時短且局地性強,常常引發嚴重的洪澇災害和山體滑坡等次生自然災害,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極大危害。
丁一匯[1]總結了我國大部分地方暴雨形成的診斷條件,這些條件包括了大尺度環流背景、中小尺度系統特征、高低空系統的耦合、對流觸發機制、垂直上升運動、水汽輻合以及對流有效位能。其中高低空系統耦合主要體現在高低空急流形成的次級環流,高、低空急流形成的次級環流對于增強上升運動有著積極的作用,同時對于低空急流而言,偏南氣流提供了豐富的水汽,同時也是對流不穩定持續維持的重要保障與來源[2]。此時中高層冷空氣的干侵入對于增強低層大氣的不穩定能量,打破對流抑制有著積極主動的作用,這對于強對流中能量的維持以及不穩定觸發至關重要[3];中尺度輻合系統與地面輻合線觸發了強降水的發生[4],而天氣尺度的冷鋒對于觸發對流不穩定能量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眾所周知北京“7·21”特大暴雨造成了嚴重的災害,對其發生發展機理的研究不在少數[5],其中對于大尺度冷鋒在整個暴雨過程中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天氣尺度鋒面系統在東移的過程中,觸發不穩定能量的釋放,其攜帶的干冷空氣與暖空氣劇烈交匯是造成這次極端降水發生的重要原因,而其他的強降水個例研究也發現,天氣尺度的鋒面系統是對流觸發中極其重要的系統,同時鋒面兩側形成的鋒生垂直次級環流[6],會明顯增強上升運動,在傾斜上升運動的前側產生大范圍強降水,在大氣不穩定度高的情況下,地面冷鋒結合暖濕氣團在鋒面兩側形成抬升作用觸發對流不穩定能量釋放,產生強對流性暴雨天氣有時會伴有雷暴大風或者冰雹天氣。同時地形對于降水的影響也不容忽視,例如位于我國川陜甘交界處的秦嶺山脈,在其迎風坡的空氣遇到山體阻擋形成動力爬升效果,會在山前形成局地強降水[7]。隨著天氣預報手段的豐富,高分辨率數值模式已然在現代天氣預報中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但高分辨率數值模式對降水量的預報能力隨著時間增加而減弱,并與局部地形和降水量級的空間分布有密切關系,中國東部地區模式對于降水的預報能力強于西部,這主要受精細化地形的影響,特別對于地形地貌構造復雜的甘肅地區,同時對于量級而言,小量級降水預報準確率較高,對于突發性的對流性強降水預報能力是明顯不足的,因此針對地形復雜的甘肅地區對高分辨率數值模式的預報誤差進行研判和訂正,在短時臨近預報預警業務中十分必要。
2 資料
利用甘肅省加密自動站逐日降水數據和美國國家大氣環境中心的全球分銷系統(GDS)全球預報零場資料,水平分辨率0.25×0.25,垂直分辨率34層,時間分辨率為6 h,氣象要素包括風場、位勢高度場、溫度場、相對濕度場、垂直速度場等資料。
3 實況及降水量預報檢驗
如圖1所示甘肅省西部及隴東南出現區域性暴雨和局地大暴雨天氣,此次過程范圍廣、持續時間短、強度大。其中兩站大暴雨分別為:臨夏尹集111.8 mm和環縣曹旗村105.6 mm,暴雨86站,臨夏、慶陽、隴南、天水等市州共25站次短時強降水,強降水主要集中在8日晚上至9日凌晨,其中最強小時降水量出現在8日21—22時臨夏州尹集為56.3 mm。

圖1 2019年9月8日20時—9日20時甘肅24 h降水空間分布
歐洲中期天氣預報中心(ECMWF)等各家數值預報模式與此次強降水的落區及量級的預報都明顯偏小偏北,與實況降水出入較大。EC細網格(圖2左)8日8時起報的8日20時—9日20時24 h累積降水顯示隴中及隴東南有大雨出現,整體量級偏小,尤其對于臨夏州強降水完全沒有預報出來;GRAPES和NCEP兩家全球模式(圖2中)8日8時起報的8日20時—9日20時24 h累積降水則完全沒有預報出此次降水過程,只有局地中雨出現,偏差很大。可見主流數值模式降水落區偏北,降水量偏弱。天水-平涼-慶陽一帶的降水主要為穩定性的系統降水,主要由中尺度系統造成的,而出現在臨夏的降水對流特征明顯,雨強大,持續時間短,并伴有雷電。模式對于穩定性降水有一定的預報性,對于對流性降水明顯偏弱。以下將對2個地方暴雨的水汽、動力、熱力條件及中尺度對流系統進行對比分析。

圖2 2019年9月8日20時—9日20時EC(左)、GRAPES(中)、NCEP(右)8日08時起報的24h累積降水空間分布
4 環流形勢分析
500 hpa高空圖(圖3a)上呈現出“兩槽一脊”的大形勢,甘肅省剛好位于500 hpa高壓脊控制下,500 hpa大環境并不是十分有利,在青藏高原上不斷有短波小槽不斷東移為此次降水提供有利的環流形勢,反觀8日20時700 hpa(圖3c)低空急流從川東北一直延伸至臨夏、蘭州等地,受地形影響,低空急流進入臨夏州受太子山阻擋有明顯的抬升爬坡作用,加之西北冷空氣南下與低空急流相交匯造成此時臨夏開始出現降水,到9日8時(圖3b)隨著冷空繼續推移隴東南中尺度切變線明顯,切變線觸發不穩定能量的釋放,隴東南降水開始增強。

圖3 2019年9月9日8時500 hpa溫壓場(a)、700 hpa風場與地形(b)和2019年9月8日20時700 hpa風場與地形(c)
5 動力、熱力診斷
5.1 動力條件診斷

為了使得診斷分析具有代表性,選取2個降水大值中心臨夏尹集(103E,35.5N)和環縣曹旗村(107.5E,36.5N)進行對比分析。從圖4中可以看出尹集8日20時開始低層開始出現上升運動,到9日早晨達到最大,直到9日傍晚垂直上升運動減弱消失,降水結束,散度表現出低層輻合,中層輻散的節后,有利于降水的產生,其最強降水階段出現在9日凌晨對應深厚的上升運動,其上升運動出現原因與低空急流在山前受地形抬升密切相關;反觀曹旗村9日凌晨出現上升運動,上升運動較之深厚,開始逐漸加強,到9日14時達到最強,而中低層輻合較強,對應隴東南的降水出現時間。

圖4 2019年9月8日8時—9日20時尹集(a/c)和曹旗村(b/d)垂直速度、散度垂直分布(單位:pa/s)
從對流有效位能(CAPE)空間分布可以看出8日20時臨夏東部與定西交界地區為CAPE大值中心,中心值為200 J/kg,隨著時間推移到9日8時,CAPE大值區移動到天水西部地區,中心值也增大到了300 J/Kg,2個時次的CAPE分布與降水落區基本對應,如圖5所示。

圖5 2019年9月8日20時(a)、9日8時(b)CAPE分布
5.2 熱力條件診斷
假相當位溫是一種保守物理量,其綜合反應了溫度、壓力、濕度場的變化特點,可以較好地反應大氣的暖濕特征,假相當位溫的密集帶可以看成是鋒面,同時也可展現氣塊的不穩定能量。結合700 hpa風場,從圖6上可以看出隨時間推移攜帶干冷空氣的西北氣流經河西走廊向隴東移動,假相當位溫左端密集帶受高原邊坡高大地形影響停滯不前,與南來的低空暖濕氣流在高原邊坡地帶交匯,并由于大地形的動力抬升作用,在臨夏一帶形成強降水,右端在冷空氣推進下快速向東南方向移動,6 h時間從蘭州南部移動到隴南-天水-平涼-慶陽一帶,與西南低空暖濕氣流交匯,導致隴東南一帶的強降水天氣。

圖6 2019年9月9日2時(a)、8時(b)700 hpa假相當位溫空間分布
6 結論
利用甘肅省加密自動站逐日降水數據和美國國家大氣環境中心的GDS全球預報零場資料,使用天氣學診斷方法,對比分析了隴東暴雨不同降水影響系統的環流形式、動力特征、熱力條件等,得出以下結論:
(1)高空環流呈現出“兩槽一脊”的大形勢,甘肅省受高壓脊控制,高原上不斷有短波小槽不斷東移為此次降水提供有利的環流形勢;700 hpa低空急流進入臨夏州受太子山阻擋有明顯的抬升爬坡作用,加之西北冷空氣南下與低空急流相交匯造成此時臨夏開始出現降水,隴東南一線降水主要受鋒面觸發。
(2)臨夏與隴東南在9日傍晚低空輻合中層輻散明顯,同時垂直上升運動在8日夜晚至9日白天最為明顯,兩地區降水垂直結構層的分布受鋒面東南移動影響,上升運動及輻合輻散的時段表現不一致。
(3)熱力場方面假相當位溫左端密集帶受高原邊坡高大地形影響停滯不前,與南來的低空暖濕氣流在高原邊坡地帶交匯,并由于大地形的動力抬升作用,在臨夏一帶形成強降水,右端在冷空氣推進下快速向東南方向移動,與西南低空暖濕氣流交匯,導致隴東南一帶的強降水天氣。
(4)ECMWF等各家數值預報模式與此次強降水的落區及量級的預報都明顯偏小偏北,與實況降水出入較大。隴東南降水主要為穩定性的鋒面降水,而出現在臨夏的降水對流特征明顯,雨強大,持續時間短,并伴有雷電。模式對于局部地方的短時強降水預報能力明顯不足,這跟局部地形影響和中小尺度天氣系統的模擬能力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