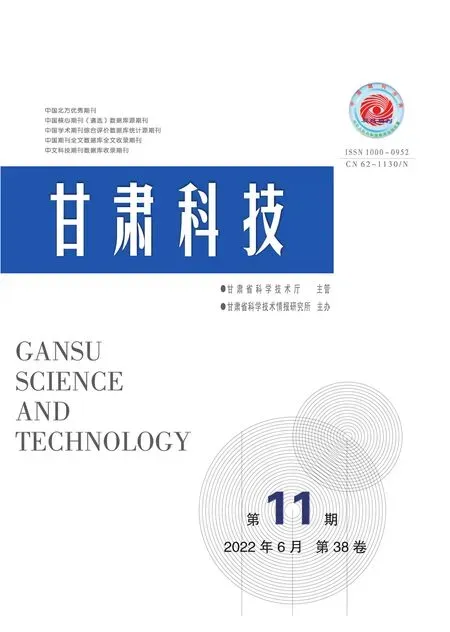“圍點打援”策略在惡性腫瘤治療中的應用初探
彭艷艷
(甘肅省人民醫院,甘肅 蘭州 730000)
1 引言
近年來,我國惡性腫瘤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呈上升趨勢[1],其西醫治療的主要方式有手術、放化療、分子靶向治療、免疫治療等。祖國醫學對惡性腫瘤的診療有悠久的歷史,其遵循整體審察、診法合參、病證結合的基本原則,并且在改善患者化、放療所產生的不良反應及患者生存質量方面的作用越來越受到重視。
應用“圍點打援”策略治療惡性腫瘤是導師裴正學教授在中西醫結合學術思想的基礎上,根據惡性腫瘤的病因、并發癥及治療過程中出現的不良反應、疾病的預后等特點,將腫瘤病灶看做“點”,把病因、并發癥、不良反應及影響預后的各因素看做“援兵”,將中醫宏觀辨證與西醫的微觀辨病、機體的反應性與病原的致病性、中醫的整體觀與現代醫學的局部觀有機結合。裴老將諸法并用,靈活運方遣藥,把藥物送到腫瘤靶點或靶器官的同時,對其并發癥或不良反應的治療也有一定作用,總體抗腫瘤臨床療效顯著。
2 從惡性腫瘤的病因病機探析
祖國醫學認為,惡性腫瘤是機體疾病的局部表現。其發病與內因、外因以及機體其他多種因素相關聯,這一認識與現代醫學理化刺激因素和機體內部基因突變產生腫瘤研究一致。腫瘤發生的機制,主要有正虛邪實、氣滯血瘀、臟腑失調、痰濕凝聚、毒熱內結幾個方面。裴老認為,其“虛”與“瘀”是最為主要的病因病機。虛是指正氣虛弱,不能抵御外邪侵犯而致病。《素問遺篇·刺法論》說:“正氣存內,邪不可干。”《素問·評熱病論》說:“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靈樞·口問》說:“故邪之所在,皆為不足。”當正氣相對虛弱,無論外感六淫,內傷七情,還是飲食勞傷,皆可導致機體臟腑功能失調,陰陽失和,氣血紊亂,或為痰凝,或為血瘀。氣血失調,常表現為氣滯血瘀。氣郁不舒,則血行不暢,導致氣滯血瘀,瘀結日久,必成癥瘕積聚。瘀血一旦形成,又會作為致病因素,在正虛的條件下,內合外邪,引起毒邪留滯,形成腫塊,致發惡性腫瘤。
裴老在“西醫診斷,中藥辨證,中藥為主,西藥為輔”中西醫結合十六字方針的指導下,根據藥物歸經理論選用靶向藥物治療腫瘤的同時,更主要的是從病因出發對機體的“虛”和“瘀”同時進行“補”和“化”,標本兼治,有的放矢,臨床療效滿意。尤其應用圍點打援策略在治療癌前病變、預防惡性腫瘤的進展方面具有良好的效果。張光霽和徐楚韻[2]進行了多次實驗研究,結論顯示“瘀毒同治”可以抑制惡性腫瘤轉移。研究已證實靜脈血栓栓塞是惡性腫瘤患者常見的并發癥之一,目前是惡性腫瘤患者死亡的第二原因[3]。在治療具有血瘀證型的惡性腫瘤時常聯用丹參酮等活血化瘀藥物以降解腫瘤細胞各種酶來誘導腫瘤細胞凋亡、抑制惡性腫瘤細胞生長,與伏杰等[4]用活血化瘀治療腫瘤研究一致。
3 從惡性腫瘤的并發癥探析
惡性腫瘤的發病部位不同則合并有不同的并發癥,乏力是消化系統、呼吸系統、神經系統等惡性腫瘤均可出現的并發癥。目前癌因性疲乏作為惡性腫瘤的并發癥之一已成為研究的熱點[5-6],其中醫學上屬于“虛勞”范疇,最早見于東漢·張仲景《金貴要略》。虛勞以氣血虧虛、臟腑功能失調為主要的病因病機。發病機制為正氣不足,氣血陰陽虧損、臟腑虛損,同時或夾雜痰、濕等。由于氣血同源,陰陽互根,五臟相關,故應同時注意氣血陰陽相兼為病及五臟之間的相互影響。
裴老在此時重用扶正固本方藥減輕惡性腫瘤患者并發癥的同時根據患者的體能狀況或輕或重選用抗腫瘤藥物,做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臨床療效滿意。對于長期口服比卡魯胺的前列腺癌患者仍伴有明顯夜尿頻、尿不盡、尿等待等癥候,老師在處方遣藥時多以補腎健脾、利尿通淋為首方,看似對其本病未使用一兵一卒,實則患者并發癥減輕的同時腫瘤病灶也得到了控制,患者二診時信心大增,不僅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而且提高了患者腫瘤治療的依從性。值得一提的是,裴老應用圍點打援策略,在肝癌并發癥的治療中通過經方加減已形成強肝湯、膽胰合癥方等多個經驗方。其中強肝湯[7]的組成為黨參、黃芪、郁金、柴胡、當歸、白芍、秦艽、板藍根、黃芩、半夏等,在肝硬化基礎上發生肝癌的治療中,對患者生存質量等的研究與張弛等[8]基于網絡藥理學研究白芍、柴胡對肝細胞癌抑制的報道相一致。對于胰腺癌患者在化療或放療的基礎上往往合并有梗阻性黃疸等并發癥,膽胰合癥方以柴胡疏肝散為主方加減能減輕患者梗阻癥狀,緩解患者腹脹、腹痛、飲食減少等并發癥,臨床療效明確。
4 從惡性腫瘤治療的不良反應探析
隨著人們對惡性腫瘤診療過程的不斷認知,患者的生存質量亦越來越受到更多學者的關注。目前,將評價新藥或治療方案的標準中有無不良反應的關注度遠高于總生存期、中位生存期、無病進展期等方面。無論何種惡性腫瘤,在化療中往往合并有骨髓抑制,這是每位腫瘤科醫生所關注的問題。當然,引起腫瘤相關性貧血的因素包括腫瘤本身因素,如腫瘤消耗、失血、溶血、腫瘤骨髓受侵等。西醫治療腫瘤相關性重度貧血以輸血聯合使用促紅細胞生成素治療為主要手段,存在易反復、價格昂貴等缺點。中醫認為貧血屬“血虛”“虛勞”等范疇,歷代醫家對治療“血虛”總結出了諸多經驗。現代醫家認為腫瘤相關性貧血為本虛標實,化療所致脾腎虧虛為本,瘀毒熱聚為標,其病位主要在脾腎,辨證多屬脾腎虧虛、氣血兩虛證。多遵《內經》“虛則補之”“勞則溫之”“損者益之”“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等治療原則,以健脾益腎、補氣養血為主要治療大法,將補脾氣、益腎精作為基本原則貫穿惡性腫瘤治療的整個過程中,從而達到增效減毒的目的[9-10]。
裴老在四十年前通過大量的臨床實踐自擬“蘭州方”[11-12],通過動物實驗及臨床對比研究其不僅對血液病療效明確[13-16],現已研制成裴氏升血顆粒成藥臨床使用。裴氏升血顆粒主要由六味地黃湯合生脈散加太子參、北沙參、潞黨參等組成,均屬扶正固本之品。方中太子參、潞黨參、北沙參重用以健脾,六味地黃湯以補腎,全方充分體現了“扶正固本”法則。研究證明,中醫的“脾”“腎”具有免疫系統、內分泌系統、代謝系統、植物神經系統、胃腸胰內分泌系統等諸方面的意義,“健脾補腎”具有改善上述各方面功能的作用[17]。“扶正固本”這一旨在發揮和動員人體免疫功能的觀點和現代腫瘤與免疫研究存在著很大的共同性。通俗論說“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患者因重度不良反應不能耐受進一步治療,化放療此時就顯得百無一用,而中醫看似在治療惡性腫瘤的不良反應,實則為抗腫瘤治療爭取時機。
5 從惡性腫瘤的預后探析
惡性腫瘤通過放化療、手術等個體化綜合治療后,患者仍面臨轉移與復發的可能,目前西醫的研究基于預防性放療或維持治療等措施。中醫“治未病”思想指導疾病防治的歷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周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云:“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祖國醫學對腫瘤的防治遵循“未病先防,已病防變”的原則[18]。《金匱要略·臟腑經絡先后病脈證》曰:“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又云:“實脾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肺與大腸相表里”的臟腑表里關系和大腸癌治療中“先安未受邪之地”均是指導醫師對大腸癌肝與肺常見轉移部位及時調理,預防腸癌肝、肺轉移。中醫通過陰陽辨證、表里傳變等理論在預防腫瘤復發轉移方面取得了顯著療效。
除此之外,裴老在惡性腫瘤患者的預后方面很關注患者的身心狀態,對于大腸癌造口的患者或乳腺癌術后的患者辨證多有肝氣郁結證,以行氣解郁、疏肝散結為治則,做到心中有數,防患于未然亦能延長患者的無病生存期,與原靜民[19]、安琳[20]等現代研究相一致。
綜上可見,裴正學教授在惡性腫瘤的治療中將宏觀與微觀、病原觀與機體反應觀、整體觀與局部觀相結合,病證結合貫穿于始終,充分掌握惡性腫瘤患者發病、治療及預后,在臨癥遣藥時將“圍點打援”策略融會貫通,得心應手,不僅能明顯減輕患者的并發癥、不良反應,而且更能很好的控制腫瘤病灶的生長,抑制腫瘤細胞的增殖,從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延長患者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