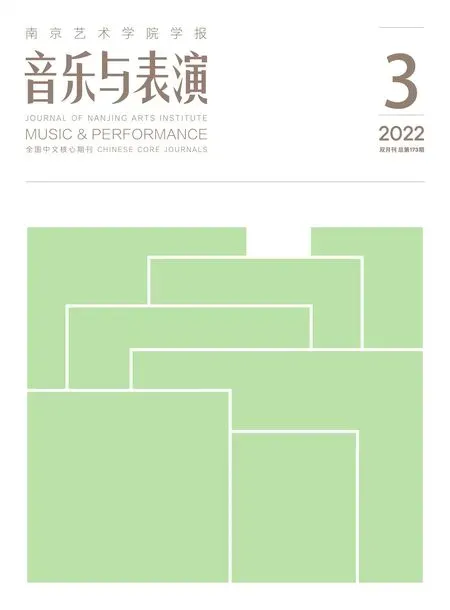意大利歌劇指導翁貝爾托·費納齊歌劇教學評析①
趙 明(中央戲劇學院 歌劇系,北京市 102209)
一、歌劇指導的職業特性及費納齊其人
近20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各大城市的古典音樂演出日益受到觀眾追捧。其中,歌劇作為古典音樂領域難度最高、耗資最大、最具綜合性的舞臺藝術,尤為引人矚目。歌劇演出,需要歌唱家、指揮家、樂隊、導演、舞美、舞臺監督等多個角色協同,每個環節必須緊密合作才能完美呈現。相比更受觀眾關注的歌劇演員、指揮家、樂隊以及歌劇導演,在歌劇制作中一個常常隱身幕后的關鍵角色近年來開始被人們逐漸重視,那就是歌劇指導。
歌劇是舶來的藝術,歌劇指導也是舶來的職業。追根溯源,歌劇指導英文為coach,我們在歌劇領域中翻譯為“歌劇指導”,在各大高校也被稱為“藝術指導”“音樂指導”或“歌劇音樂指導”。有關這個職業的具體命名,學術界也有著很多的爭論。這個職業的眾多名稱在語境上都稍顯籠統,有時甚至還會產生歧義,無法讓行業之外的人通過名稱直接了解這個工種的工作內容。在大眾更熟悉的足球、籃球等運動項目中,coach通常翻譯為“教練”。其實,歌劇指導在歌劇排練時所做的工作及其重要性與體育領域中的教練有些近似,只不過一般不會像體育教練那樣站在場邊,所以更容易被人忽視。
歌劇指導這一職業,需要極為豐富的理論知識和高超的技能儲備。首先,歌劇指導必須是鋼琴家,能流暢地演奏歌劇鋼琴伴奏縮譜是最基本的要求。他們還常常需要根據歌劇的樂隊總譜在演奏鋼琴縮譜時進行調整,以幫助歌手們更好地適應樂隊,因此歌劇指導還必須能夠看懂樂隊總譜。他們要指導歌手的演唱及糾正音樂和語言方面的問題,因此還要熟練掌握歌劇演唱所需要的各種語言。在歌劇排練階段,歌劇指導還要幫助指揮記錄歌手們在演唱時的錯誤,并在排練結束后提醒歌手改正。若指揮不在,歌劇指導有時還要臨時頂替指揮,所以很多歌劇指導本身就是助理指揮,成為真正的歌劇指揮也是很多歌劇指導的終極職業目標。演出時,有時歌劇指導會在樂池彈奏羽管鍵琴,為歌手演唱歌劇宣敘調伴奏,這也是歌劇指導在歌劇演出時僅有的登臺機會。總而言之,歌劇指導可以說是歌劇排練中的“萬能鑰匙”。正因為這項工作本身的高要求,雖然國內近些年來一直在著力培養,但歌劇指導人才至今仍處于極度匱乏的狀態。目前國內排練外國經典歌劇,一般還是要依賴國外的歌劇指導。
從1997年起,翁貝爾托·費納齊(Umberto Finazzi)大師開始與著名歌唱家米雷拉·弗雷妮(Mirella Freni)、雷娜塔·斯科托(Renata Scotto)、雷納托·布魯松(Renato Bruson)、路易吉·阿爾瓦(Luigi Alva)等大師在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青年歌唱家計劃任教,同時在米蘭威爾第音樂學院擔任教授。他還經常在意大利各大歌劇院擔任助理指揮、歌劇指導以及管弦樂團和合唱團的總監。
2016—2017年,筆者有幸連續兩年全程參與了費納齊大師在中央戲劇學院歌劇系講授的專家課程,受益良多。費納齊大師是意大利真正高水平的歌劇指導,能夠在國內近距離感受這位高級專家的講授,非常難得,加之國內對于專業歌劇指導的理論總結與研究也相對匱乏,故本人不揣愚陋,對費納齊大師的教學思路及特點作以下幾個方面的歸納和評析。
二、強調準確理解作品時代背景和譜面細節的重要性
費納齊大師在教學中常常從學生演唱作品的作曲家入手,先嘗試幫助學生分析作曲家的時代背景和創作風格。應該說,作為一名成熟的歌劇演員,在學習作品之初,首先就要了解作品背景以及作曲家的創作特點等,這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把握作品風格,為更好地演唱作品打下良好的基礎。但目前國內學習歌劇的年輕學生,少有能做好這一點的。要想真正好好把握與這樣世界一流的歌劇指導學習的機會,就一定要在課堂上善于體會大師對作品背景和內容的獨到見解和分析。例如,費納齊大師曾提到一個較為冷門的知識點,在歌劇《奧菲歐與尤利狄茜》的詠嘆調《世上沒有尤利狄茜我怎能活》中,最后富于張力的高音段落,其實并不是作曲家格魯克寫的。格魯克的原譜,在這一段之前就結束了,后面的高音段落,是后人為了更好地展現歌唱家的聲音而補寫的。所以,有的歌唱家就會選擇不唱詠嘆調最后的高音段落。這樣處理也是合理的,因為最后這部分的音樂與前面的段落風格區別很明顯,不是格魯克的音樂風格,甚至有些偏向另一位歌劇大師威爾第。這類新穎的知識點,有助于學生更生動地理解作品。
相信國內的歌劇領域不論聲樂教師還是鋼琴伴奏老師都會有同感,在國內歌劇專業的教學過程中,最無奈的一點,往往是最為基礎的作品譜面學習。譜面學習的內容既包含音準、節奏等譜面的基本構成元素,也包括強弱快慢等表情記號,甚至包括較專業的歌劇總譜才會有的舞臺行動提示,而這些都有可能成為學生出錯的“雷區”。應該說,作曲家對于作品的全部要求,幾乎都會嚴謹地體現在譜面上。準確演唱譜面,對年輕歌手是最基礎卻往往又是最嚴格的要求。做到這一點,其實甚至不需要老師的指導,而應該是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自己能夠做到的“性價比”最高的工作。費納齊大師在授課時,首先會糾正學生學習時的譜面錯誤。他還非常注重分析作品譜面的細節,而這往往是年輕學生在學習作品時容易遺漏的關鍵部分。比如費納齊指出,演唱莫扎特、羅西尼歌劇的宣敘調,經常會有一種約定俗成的做法——在唱某些音程時,改變原譜上的音符唱另一個“依附音”,(如譜例1)。

有些版本的譜子,還會把這種選擇用另一行標注在原譜邊上。這種做法,乍一看非常不符合古典音樂“一切尊重原譜”的原則,但實際上,這才是真正貫徹作曲家構思的做法。因為演唱這些“依附音”,才更能夠體現意大利語的語言重音,但這些音,放在當時的古典音樂和聲體系中卻會被視作錯誤,所以作曲家們就選擇不在樂譜上寫這些“依附音”。直到威爾第的創作中,這種情況才真正改變。可以說,威爾第才是第一位把所有構思都準確寫在樂譜上的作曲大師。歌劇指導的一項重要工作,就是要把樂譜中的這些隱藏要素傳達給演員們。
三、分析樂隊伴奏織體并提供高水平的鋼琴伴奏
費納齊大師教學中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通過分析歌劇鋼琴縮譜延伸至樂隊演奏,進而深入理解歌劇人物的角色特點。如前文所述,高水平的歌劇指導往往自身就具備作為歌劇指揮的實力,費納齊大師亦不例外。作為指揮,不能只關注歌手和鋼琴,還更需要全面掌控整個交響樂隊。而各院校的日常聲樂歌劇教學一般不具備樂隊伴奏的條件,通常都是依靠鋼琴縮譜伴奏。鋼琴縮譜的一個“縮”字,就體現出了鋼琴替代樂隊伴奏的不足。作為“樂器之王”,鋼琴是唯一能夠提供接近樂隊復雜程度和表現力的單件樂器,不可謂不強大,但終究還是不能完全展示樂隊的全部細節。而學習歌劇演唱的終極目標,必然是在舞臺上與樂池中的交響樂隊合作。基于此,費納齊大師在授課時,會盡可能地通過鋼琴譜面的和聲,講解樂隊的伴奏織體,向年輕學生展示歌劇樂隊的奧妙。這些經歷過數百年大浪淘沙的經典歌劇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往往也在于偉大作曲家們的匠心獨具。在他們筆下,聲樂、樂隊和鋼琴部分,幾乎沒有一個多余的和聲轉換、沒有一個莫名的速度或力度調整,音樂的一切變化都是服務于戲劇和角色的。
例如,費納齊大師曾專門對比了歌劇《費加羅的婚禮》中伯爵夫人和伯爵的音樂特征。他認為,伯爵夫人的人物性格整體來說比較冷靜,所以與伯爵夫人有關的音樂,相對和聲都比較規整。比如,伯爵夫人的第一首詠嘆調《求愛神給我安慰》全曲一直保持E大調,另一首詠嘆調《美好時光哪里去了》也是全曲保持C大調。而與之相反,伯爵的性格則較為沖動,所以他的音樂一直處于各種調性變化之中。比如,伯爵的詠嘆調《當你贏得了訴訟》之前宣敘調的開始。
這段樂隊的演奏就體現了伯爵內心的急躁和混亂,充滿力量。而唱完“la sentenza sara”之后的樂隊織體,則體現了伯爵內心的疑慮和不安,好像時鐘的鐘擺一樣,“咔嗒、咔嗒”在內心回蕩。
又例如《圖蘭朵》中柳兒的詠嘆調《你那顆冰冷的心》。大師講道,這是柳兒死前的詠嘆調,整首詠嘆調其實更像一首送葬曲,每一個音符都表達著柳兒誓死守護卡拉夫名字的決心。樂隊演奏要一直保持非常穩定的速度,就像送葬隊伍穩定的步伐,每一個明確的重音都代表著送葬的鐘聲。雖然這些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唱段,但大師結合曲式和聲、樂隊和鋼琴演奏技法以及劇中人物性格的綜合分析講解,讓人不僅“知其然”,還能“知其所以然”,耳目一新的同時還能夠讓人真正把握住作品要點。
如前文所述,歌劇指導首先是鋼琴家,對鋼琴演奏技術自然是有著較高的要求。但歌劇指導的演奏技巧不同于鋼琴獨奏,一方面是“伴奏”,一方面又是“樂隊”。因為在歌劇排練中,鋼琴的作用是模擬樂隊,即使是在音樂會舞臺上與歌手合作,也需要更靠近樂隊效果。費納齊大師的鋼琴演奏,師從于鋼琴大師阿圖洛·米開朗基利(Arturo Benedetti Michelangeli),鋼琴演奏水準不遜于任何鋼琴獨奏家。因此授課時,在鋼琴演奏技巧上,費納齊對鋼琴伴奏老師有著很多明確的要求。
例如,費納齊大師講解《唐璜》中采琳娜的詠嘆調《鞭打我吧》。他認為,鋼琴伴奏者在演奏莫扎特的作品時,一定要找到優雅的、“莫扎特”式的音色。在詠嘆調開始時,鋼琴伴奏譜右手的旋律與女高音的旋律相同,但這段旋律并不需要右手再去刻意強調,因為歌手已經在演唱同樣的旋律。需要注意的反而是左手的演奏,此時左手演奏的是樂隊中大提琴的部分,一定要演奏出大提琴般的連貫音色,不能彈得太斷,要格外注意觸鍵。而在講解《費加羅的婚禮》中的詠嘆調《你不要再去做情郎》時,大師則刻意強調鋼琴伴奏一定要彈出樂隊般的音色。比如詠嘆調尾奏中右手的旋律是樂隊中圓號的部分,一定要演奏得堅定有力,不能拖沓,觸鍵不能太軟。這里的和弦都要彈奏出樂隊的力度和氣勢,才能真正傳達出詠嘆調鼓舞士氣的作用。
四、著力糾正演員的發音及語感
音樂和語言是演唱的兩大基本構成要素。大多數歌劇經典作品都是用意、德、法、俄、英等外語原文演唱的。在當今國際歌劇界,優秀的中國歌唱家不斷地涌現在世界各大歌劇院的舞臺上。他們除了擁有精湛的歌唱技巧、迷人的音色和樂感之外,最重要的共同之處就是擁有如同母語般的外語發音和語感。而很多在國外發展受阻的中國歌唱家,語言往往也是最大的絆腳石。當然,近年來,國內的歌劇教學對學習外語的重視程度也一直在提升。畢竟,語言學習是演唱外國歌劇作品最重要的必修課之一。歌劇指導的一項重要工作內容,就是糾正演員們的語言問題。在歐美工作的歌劇指導大都能至少掌握意、德、法、英4種語言,這也是部分國內歌劇指導最為欠缺的一項素質。
作為一名意大利的歌劇指導,費納齊大師在歌劇教學的語言要求方面,除了基本的元音、輔音的發音準確性之外,還有著一些比較細致的要求。例如,在講解《費加羅的婚禮》中的詠嘆調《如果你要跳舞,我的小伯爵》時,費納齊大師專門強調了樂句“il chitarrino le suonero”的語言重音。如果“suo”是單獨出現的詞語,那么重音就在元音“u”上。但在詠嘆調中出現的“suonero”一詞中,重音就在詞尾的元音“o”上,不能混淆。“suonero”一詞,由于音樂節奏和之后高音小字二組f的干擾,很容易令歌手唱出并不存在的雙輔音“nn”,這是一定要避免的。同時,這個詞中出現的兩個元音“o”,還有開口閉口的區別。因為詞尾的“o”是重音所在,所以要發開口音“ò”,而前面的則要發閉口音“ó”。筆者認為,大師對歌劇語言的講解,最為獨到之處,就是能夠通過對某一個作品或某一個詞匯講解的展開和延伸,讓學生能夠舉一反三,更快地掌握更多的意大利語演唱要點。
五、力求將發聲技巧與作品處理完美融合
雖然費納齊大師是一名歌劇指導,并不是聲樂教師,但是多年的劇院實踐經驗,以及與眾多歌劇史上熠熠生輝的偉大歌唱家合作的經驗,都成就了他在發聲技巧方面準確而獨到的見解。事實上,在美國歌劇界,一直以來就有很多聲樂指導其實本身是歌劇指導,他們的本職工作是鋼琴家,自己并不會演唱,但卻能一針見血地指出歌手的發聲問題并予以指導。這一點,其實在歌劇界充滿爭議。對歌手發聲技術的指導,可以說是歌劇指導們的敏感區域。有些人選擇大膽突破,有些人選擇絕不逾越。很多美國歌劇指導就明確表示:幫助歌手在作品中找到正確的聲音,也在歌劇指導的工作范疇之內。而在較為傳統老派的意大利歌劇界,這種做法就不被推崇,他們更多的還是堅守著自己本職的細分工作領域。但這并不代表費納齊這種級別的大師不具備指導年輕歌手發聲技巧的能力,只不過他將相關建議,更巧妙地融入了作品處理之中。
比如,一位學生演唱一段較長的樂句,呼吸明顯較為吃力,在幫助歌手練習時,費納齊大師就臨時把這段樂句的柱式和弦伴奏調整為分解和弦,這樣一來,這段樂句整體就變得輕快了不少,歌手的呼吸增加了一些彈性,也就沒有那么僵硬了。另一位學生在演唱某花腔段落時明顯存在技術問題,大師就幫助學生把這段花腔的重音和氣口詳細地劃分了出來,明顯改善了這名學生整個花腔段落的演唱完整性。但即使是在類似情況下,費納齊大師也不會對歌手的發聲技巧做出評價,更不會對此進行具體指導,體現了一名高水平歌劇指導對待工作的嚴謹態度和深厚的藝術修養。
六、溫和謙遜的大師風范
通過跟費納齊大師上課學習以及觀摩授課,筆者收獲了很多以前不曾接觸過的歌劇專業知識,更感受到了一種建立在專業知識和舞臺經驗之上的、融會貫通的教學方法和理念。同時,費納齊大師的教學態度也令人欽敬。他在意大利授課時,指導的都是較為年輕的職業歌唱家,而在我校授課時,不可避免地會遇到學生專業能力參差不齊的情況。但在我校的授課過程中,費納齊大師始終保持著溫和耐心、不急不躁地面對每一位接受他指導的學生,這一點令我們所有師生由衷贊嘆。因為歌劇教學內容繁雜,學生的天賦、接受能力以及學習態度等,都時刻考驗著授課教師的心態。可以說,在教學過程中,出現情緒往往是難以避免的。費納齊大師在課堂上展現的修養和氣質,如同卓越藝術家在舞臺上一般,讓人切身感受到課堂其實也是藝術家的另一個舞臺。誠然,筆者作為一名普通的歌劇演員和聲樂教師,不論在學識還是舞臺實踐方面,都無法達到費納齊大師的高度。但我想,我可以在自身有限的能力之內,學習運用大師的教學理念和模式,更好地向學生展示我所能夠講述的教學內容,讓他們更加輕松而全面地理解和接受專業知識。在當下的國內聲樂歌劇課堂上,由于高水平歌劇指導的缺乏,很多音樂、語言等方面的內容需要由聲樂老師教授給學生,這也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客觀現實。同時,這也對我們的教學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斷激勵我們去學習演唱更多的角色和作品,以充實我們的歌劇教學。
希望通過對大師教學的研究和評析,包括列舉的部分作品實例,能夠給歌劇專業的師生們帶來一些較為實質性的幫助。雖然歌劇的奧秘永遠在舞臺上,但舞臺上完美的演唱,永遠源自舞臺下完美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