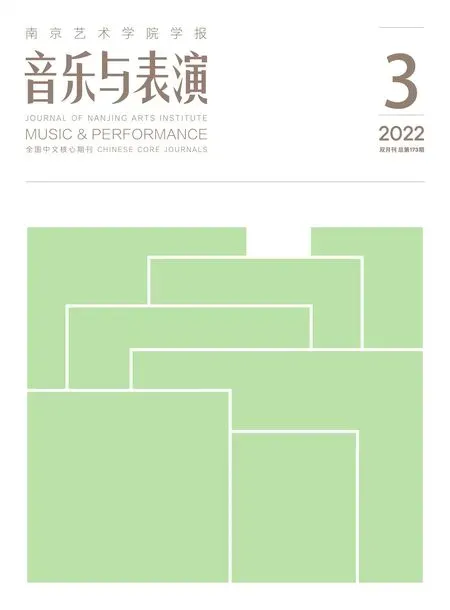城市民族音樂學①
談瀚鎂(長沙學院 音樂學院,湖南 長沙 410022)
趙書峰(湖南師范大學 音樂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城市民族音樂學,是近年來國內外音樂學術研究的關鍵詞之一。該術語直譯自英文“Urban Ethnomusicology”,1978年美國民族音樂學家布魯諾·內特爾在《八個城市音樂文化:傳統與變化》一書首次提出。作為一個興起不到50年的新興學科,其充分證明了民族音樂學研究對城市藝術文化的興趣與轉向。這個轉向是因為,面對日益加速的城市化進程以及城市與農村各族群日益受到的現代西方音樂文化的沖擊,民族音樂學家發現孤立的農村田野工作已然無法適應急速變化的環境。加上人類學與社會學的雙重作用,種種因素推動著民族音樂學家拓寬視野,跳出舒適圈,全力以赴奔赴城市環境展開研究。
一、城市民族音樂學的學科源流追溯
對城市民族音樂學的溯源要追尋到其母系學科民族音樂學的兩大上源學科:人類學和社會學。阿德萊達·賴斯·施拉姆(Adelaida Reyes Schramm)在《城市民族音樂學:一個理念的簡史》一文中提到,民族音樂學受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學派與其后的美國芝加哥學派對城市的定義以及相關研究的影響,是社會學與人類學兩大學科融合的結果。
現代社會學對城市和城市主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不過直到世紀之交,隨著德國城市研究學院的出現,這些努力才形成一個思想學派。理查德·塞納特(Richard Sennett)稱之為“城市研究的第一次現代努力”。德國學派以海德堡和柏林為基地,以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喬治·齊美爾(Georg Simmel)等社會學家為代表。韋伯認為,城市的主要定義特征是世界主義,這是不同生活方式、不同類型的個人共存并允許“最大程度的個性和獨特性”的結果。這個表述預示著一種對異質性特征承認,而這種特征將被嵌入到后續的城市描述或定義中。
音樂社會學的研究思路承襲于其母學科。筆者梳理20世紀以來音樂社會學發展脈絡,發現20世紀30年代,音樂社會學研究代表人物德國學者西伯爾曼(Alpho Silbermann)和恩格爾(Hans Engel)等就開始側重于對社會音樂生活、音樂商品的生產和消費等方面具體研究。法蘭克福學派代表人物阿多諾(Theodor W. Adorno)也從社會學角度來探討流行音樂與大眾傳媒,提出了“文化工業”對音樂產業的批評理論。可以看到,德國學派早期便頗為關注城市中的音樂,且始終將其與當時社會特定語境聯系起來揭示音樂的本質。此后20世紀60—70年代隨著美國戰后危機動蕩的社會與局勢影響到文化,搖滾樂、民間音樂和流行音樂各種發展形態密切地聯系起來,爵士樂也被當作可被研究的學術對象被接納。70年代,搖滾樂研究進入學院,這說明學校民族音樂學教育與研究開始接納流行音樂。這一現象標志著音樂社會學逐漸受到流行音樂形式的影響。80年代,在1987年勒珀爾特(Richard Leppert)和蘇珊·邁可克拉瑞(Susan McClary)合著的《音樂與社會》中有3篇重要的研究探討了城市音樂文化:芬那根(Ruth Finnegan)研究英國城市業余音樂家生活的《隱藏的音樂家:英國小鎮的音樂制作》,科恩(Sara Cohen)研究搖滾樂隊如何生成的《利物浦的搖滾文化:正在形成中的流行音樂》,以及威因斯坦(Deena Weinstein)為重金屬音樂正名的《重金屬:音樂及其文化》。
在許多方面,德國學派為美國芝加哥學派奠定了基礎,芝加哥學派在城市研究方面的影響力與德國學派不相上下。不得不提的是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帕克(Robert E. Park)。受到齊美爾和韋伯的影響,帕克與伯吉斯(Ernest W. Burgess)等其他社會學家共同創作了芝加哥學派一部重要的著作——《城市:有關城市環境中人類行為研究的一些建議》。帕克在這本書中強烈倡導人類學的民族志方法,采用系統的實證方法與定性數據進行城市研究,與德國學派學者的“扶手椅”方法截然不同。帕克從城市結構、工業化與城市組織、次級關系與社會控制、城市心理與環境四方面研究,借用大量生態學詞匯(競爭、適應、沖突、調節、入侵、同化等)闡述城市現象的變化。芝加哥學派還創建了城市擴張模型與區域劃分圖形:帕克和伯吉斯在生態演替理論與地理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提出城市同心圓增長理論,對分析城市結構形態起到了開創性作用。之后,亦有學者受此啟發,提出了扇形理論、多中心論、生態分布理論等,都為分析城市發展的人口與組織集中、分散與重新整合現象,為后人理解大都市、超大都市的結構和運轉有所裨益。在社區研究方面,帕克認為按一定秩序(人口、技術、習慣信念和自然資源)可以把城市劃分為若干社區,并認為區域劃分是某些機構或特定人口為獲得戰略空間相互競爭的結果。雖然“社區”概念隨著經濟文化全球化和城市的流動性在今天還值得商榷,但對“城市”這一空間與概念的研究有很大啟發。在此基礎上帕克還提出了種族關系周期理論、“社會距離”和“邊緣人”理論等,為后人研究城市空間結構、族裔——階級沖突、社區建設等問題提供了啟示。除此之外,帕克還通過調查認為,族群社區和外文報刊對外來移民與主流社會融合起著促進作用,這也拓寬了城市研究的視野。總之,20世紀二三十年代芝加哥學派的人文生態學方法是美國城市史研究中的一種理論模式,該理論模式直接催生了“城市化”理論的形成。該學派對城市史研究的發展起到了巨大推動作用,現在我們在城市民族音樂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中還可以感受到該學派搭建了城市研究理論框架。
對城市研究感興趣的不止社會學家。隨著城市的作用愈漸重要,時代的發展也促使人類學研究視域與研究對象逐漸轉向城市,促生了城市人類學研究的興起。
在20世紀中葉,英語世界中還沒有專門致力于發表城市研究的學術期刊。大部分主流學科期刊將城市研究作為一個分支。20世紀60年代,兩本期刊的創辦——《城市事務季刊》(Urban Aあairs Quarterly)和《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開始完全專注于發表城市研究的論文。這些研究的重點是跨學科的,其論文涵蓋了廣泛的不同研究。其他期刊也緊隨其后,如《國際城市和區域研究雜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專注于理論驅動,批判性導向的研究論文,同時對城市研究議程的廣度做出探索。更多的是圍繞特定分支的出現而確定的專業期刊,包括《城市地理學》《城市經濟學雜志》和《城市人類學》。20世紀末,在規劃和其他與城市發展相關的領域發表的專業期刊才越來越多。1972年,《都市人類學》(Urban Anthropology)雜志創刊。1979年,美國人類學會成立都市人類學會(SUA)。這些專著的問世、學術刊物的創辦和專業學術組織的出現,共同構建出都市人類學學科雛形。此后,都市人類學作為人類學的分支學科逐漸興起和形成,20世紀末,在全球化和城市化浪潮的推動下,都市人類學發展更為活躍,歐美國家很多大學里開始出現相關課程。阮西湖在梳理國外都市人類學理論時總結其研究內容包括:1.農村—城市人口流動;2.家庭結構和生活方式;3.文化上的適應和調整;4.社會階層和階級結構;5.民族志和民族學;6.城市歷史研究;7.城市與環境的研究;8.民族關系的研究。雖然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里,整個城市研究都受到芝加哥學派研究范式殘余的影響,但在世紀末,也有其他觀點開始嶄露頭角,得出了不同的分析方式。人類學家敏銳地意識到城市研究往往被普遍化的理論和論點所主導,范式城市和觀點在不斷變化的當代城市及城市多樣性下有害無利,進行城市研究需要多種視角。人們從乞靈于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生態學”模型的研究,從靜態模式轉向動態過程研究,不再將文化作為穩定的靜止現象,而是以文化中的變遷現象作為研究的主要內容,諸如西方文化接觸、跨國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等。人類學家為了補充20世紀早期研究僅關注鄉村民族志工作,主要集中于城市的人類學研究,強調“文化認同、文化身份、民族性、社會機構及其變遷,以及城市環境等問題”。其中吸引人類學家關注最多的一個問題就是:城市的定義,如何在變化中將其概念化。這是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在知識進化的不同階段,城市研究一直面臨著這個問題——什么是城市?如何定義?早期人類學家定義城市的嘗試傾向于關注它不是什么:農村。然而,由于現今城市和農村的模糊,以及人們日益認識到在一個由迅速出現的流動性所定義的世界中,以固定術語定義城市,這種觀念日益受到挑戰。這個問題也蔓延到之后城市民族音樂學的準確定義。“城市”冠以民族音樂學,有何特殊意義?
這就是城市民族音樂學從它的祖先那里繼承下來的歷史遺產。城市民族音樂學在音樂人類學與城市社會學的相互作用中汲取養分,是兩門學科“交叉受精”(Cross-fertilization)的果實,施拉姆將其稱為“遺傳物質”(genetic material)。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本質與它們的貢獻相結合時,城市民族音樂學在此社會文化背景中得以發展。
二、早期西方城市民族音樂學的生存環境
早期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主要研究歐洲和北美以外的音樂,研究范圍集中在鄉村語境,希望展現相對未受現代文明影響的音樂群體,民族音樂學的主題也一直圍繞著“所有的部落音樂和民間音樂以及各種非西方藝術音樂”,因此這兩門學科經常被描述為異域風情的學科。這種對“他性”(Otherness)的追求雖然吸引了一些音樂學家并引導他們創造性地探索人類學文獻,卻為民族音樂學家進行真正的研究對話設置了障礙。對“家門口的音樂”的研究最初并沒有受到積極的重視,而是被輕視或忽視。施拉姆表示,早期城市音樂發展進程緩慢的原因之一是對民族音樂學家長期持有的對部落和民間音樂以及所有非西方藝術音樂的界限劃分以及對所有舊的、不變的所謂“真實”觀點的過度關注,導致在當代城市環境中屏蔽了音樂的主要部分。受到人類學和民族音樂學研究范式的影響,早期城市民族音樂學家對文化同質性簡單且孤立的追求和對研究對象預設明確邊界的習慣使得他們即使搬到城市地區,進入一種截然不同的城市化社會,幾十年來根深蒂固的偏見仍對城市研究結果產生相當程度的偏差。所以,民族音樂學長期以來將音樂劃分為“西方音樂”和“世界音樂”的二元模式并沒有受到真正的挑戰,也沒有因為場地的簡單改變而消失。研究者們仍然希望在調查對象和自己的身份之間保持清晰的界限。這時民族音樂學家忽略了城市邊界的流動性、空間上的不斷變化,盲從于民族音樂學固有方法論思維,陷入一種孔斯特(Thomas Kuhn)所說的“范式誘導”。可以看到,早期民族音樂學研究面向封閉的系統,走向了相對自足和文化同質的死角。文化相對主義充斥著民族音樂學工作,許多研究的最終成果是用來表征來自特定文化或音樂領域的靜態特征,而非考慮變化的、多樣的、復雜因素的交互影響。在之后的一段時間,雖然民族音樂學家將目光轉向城市,但這僅僅只是地點的改變——從農村到城市,城市仍被當成一個舊封閉系統延伸,研究視角與研究習慣仍未改變。直到民間和傳統音樂的霸權受到有效的挑戰,直到各種流行的和西方的音樂真正被納入適當的民族音樂學研究的領域,城市地區的音樂才開始脫離作為一種簡單的、不尋常的鄉村音樂的待遇。
謝勒梅(Kay Kaufman Shelemay)在《走向早期音樂運動的民族音樂學》一文中通過對一個早期音樂運動的民族志研究,也對民族音樂學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崩潰的所謂“界限”和“邊界”提供了一些見解。作者引用了從紐約到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敘利亞猶太人創作的伴唱圣歌劇目,他們將神圣的希伯來文文本融入大量傳播的阿拉伯電影和錄音、北美流行歌曲以及貝多芬和拉赫瑪尼諾夫的作品中,來說明在城市民族音樂學視域下,“西方音樂”和“非西方音樂”的分類確實已經瓦解。理查德·G·福克斯(Richard G.Fox)呼吁根據對城市和社會之間的意識形態和行為聯系的調查,重新定義城市研究的目的,而不是強調“異國情調”。類似地,馬丁·拉巴(Martin Laba)研究了風俗習慣的行為模式,以描述從農村移植到城市的民俗項目。實際上,由于城市的發展,城市與農村的邊界日漸模糊,對清晰可見邊界概念的追求早已不是民族音樂學的追求。謝勒梅就表示:“在實地,無論學者們在哪里實踐音樂民族志,現在越來越難以辨別概念化和命名的邊界實際上可以在哪里繪制”,馬丁·斯托克斯(Martin Stokes)也將打破城市與農村邊界的趨勢視為“民族音樂學的成熟……證明了它能夠審問熟悉的和相似的東西,而不僅僅是異國情調和不同的東西。”謝勒梅進一步說,這樣的舉動是走向“去殖民化”民族音樂學的重要一步,這一步幫助該領域“從跨文化差異的面紗后面出現”。這時的民族音樂學家們基本達成共識,雖然城市音樂生活的研究方法起源于對民族社區的研究,并且經常繼續關注由血統團結起來的集體,但我們不斷變化的世界已經重塑了城市社區形成的過程,鼓勵了它們日益松散的邊界,并改變了它們賴以生存的網絡和媒體。
三、城市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屬性與特殊性
20世紀末后,學者們就城市民族音樂學的學科屬性、概念、界限、田野方法等問題展開研究,提出一系列研究模式及概念,力求建立一套完整的城市音樂人類學理論體系。
曾經有學者對民族音樂學之前加上“城市”二字的必要性提出質疑,因為他們認為城市民族音樂學是建立在其母學科功能重復的基礎之上的。對于“城市”二字是否冗余,施拉姆在《城市民族音樂學探索》中認為,前面加上“城市”二字的目的是為了強調這個詞,并讓它本身或它所代表的內容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即使“城市”是一種冗余,它提醒我們仍處于一個有待充分探索的領域,是一種有目的的冗余。但更重要的是,該理念作為一個概念和方法論,它解決了對多元文化主義、國家認同以及文化多樣性政策的同化與融合挑戰的問題。城市音樂研究作為一扇重要的窗口,能有效窺探復雜社會關系中音樂與人的能動性之間的緊密關系。城市主義研究揭示的這些社會關系的變化,必然會對由此產生的音樂生活產生影響。基于這些,城市民族音樂學的獨立存在就有了理由。城市民族音樂學研究的價值在于它能夠提供一個更普遍的民族音樂學目標:對音樂性和非音樂性的綜合解釋。作者解釋道,城市民族音樂學將研究對象和語境(context)視為一個整體共同研究,這種研究本身保障了民族音樂學對音樂和額外音樂之間內在聯系的興趣。城市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范圍方面,施拉姆討論了“存在于城市里的音樂”(in the city)和“屬于城市的音樂”(of the city)之間的細微差別。從平行的角度來看,關注“存在于城市里的現象”的民族音樂學將城市視為意外,也就是說,對研究對象和其解釋來說,城市是外在的。關注“屬于城市現象”的民族音樂學將城市視為本質,即城市是研究對象的本質,因此也是其解釋的本質。作者以美國紐約曼哈頓區1978—1981年期間免費公共音樂活動與事件而構建的一個紐約市音樂生活概覽的案例說明,正是由于這些音樂事件的平凡性,由于價值的廣泛使用和廣泛基礎的共識,城市這些現象才得以存在。正是這種平凡,在某種意義上,證明了它們不僅在城市中,而且屬于城市。
城市民族音樂學研究具有哪些特點?在這里,筆者借用桑德斯(Peter Saunders)的觀點。在桑德斯看來,一個本質上的城市問題需要的“不是一個城市理論(作為研究對象),而是一個社會關系基礎變化的理論”,這是城市生活的核心。這種張力是“關注在空間背景下運行的社會過程,以及關注空間單元本身”。桑德斯的表述強調了城市動態的內在張力的重要性,而這種張力實際上是城市動態的特征。正如城市歷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言:“在城市中,人類最具目的性的活動,通過相互沖突和合作的個性、事件、群體,得以形成和實現,并達到更有意義的高潮。這是一出通過群體活動的集中和強化而形成的社會劇,在這個城市里,沒有一種功能是無法發揮的——事實上,在這個開放的國家里,也沒有一種功能是無法發揮的。”桑德斯和芒福德的話強調了一點——對關系的關注。很多思想家都強調,考慮到城市社會有機體的活力和復雜性,對關系的關注變得更加迫切。
長期以來,城市民族音樂學強烈傾向于將注意力集中在不同的角度,例如在少數民族或少數民族群體上、在城市社區上、在城市體裁上(如嘻哈、搖滾音樂等)。人們一直在研究孤立的整體,這一趨勢阻礙了我們在城市背景下充分正視構成部分與整體關系這一復雜的方法論問題。這個問題需要特別注意,因為城市是一個新興的有機體。芒福德這樣說:“每一個群體、每一個社區、每一個職業、每一個棲息地……通過它們在城市的緊密媒介中的相互作用……為其所有成員提供了無盡的排列和組合。”無論主要的焦點是文化(如人類學)或社會生活(如社會學)或音樂生活(如民族音樂學),這都意味著城市生活,音樂或更廣泛的社會,其部分或調查者所認為的整體,最好被認為是一個開放的系統。雖然調查的對象可能是一個小單位,但它作為城市的身份不僅在其內部關系中,而且在其與其他單位的關系中。漢納茨(Ulf Hannerz)認為,萬花筒式的觀察才能更好地反映城市的社會生活,在那里“眾多的部分一次又一次地呈現出新的形態/整體”。
可以說,西方城市民族音樂學研究逐漸淡化且習慣了城市邊界的模糊特征,也不再執著于在清晰邊界空間里研究;學者們承認音樂流動與多變的特性,同時考慮到音樂周邊相關人事的關系與環境,特別是在城市空間里,關注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進行探索;雖然音樂學家們仍將注意力集中在城市音樂文化的各個部分,但也意識到在整體語境中考慮音樂的重要性,城市音樂亦應當作為一個單元或一個整體研究。
四、城市民族音樂“新”的田野方法
馬林諾夫斯基在田野調查基礎上構建的民族志范式對后來人類學民族志研究方法具有極為深遠的影響,然而早期民族志范式中田野調查主要是基于部落社會的研究語境實現的。馬氏選定的這類群體或部落聚集緊湊,居住在相對封閉和隔絕的空間,群體內部多為親戚關系,少與外界聯絡,文化構成較為單一,正符合人類學家理想的具有明確族群和文化邊界的異文化部落。正是在這種語境下,馬氏才可能通過多年的居住式田野,以一己之力全面掌握當地的社會文化體系。這種對有清晰邊界體系的研究后來轉換為對村落或社區的研究,并被人類學家熟練運用。這樣的民族志方便人類學家展開田野調查,更加清晰地掌控一個研究單位,然而卻在城市研究的語境中面臨著巨大的挑戰。早期人類學仍習慣于將研究對象鎖定于城市中的少數和邊緣群體(如貧困人口、少數族裔、亞文化群體等)。這些群體在城市中的聚集同樣具有封閉和排他的特點,從而為人類學者提供了一個類似具有清晰邊界的“封閉社區”的研究對象,這就導致人類學對城市的研究仍未逃脫類似于“部落研究”的思維范式。一些學者甚至抨擊人類學家偏愛人為界定調查對象,簡化城市復雜和交錯的社會現實,致使對城市的研究僅是地點的改變,而非研究概念和對象上的改變。
現在,人類學家意識到在以開放性和流動性為主要特點的城市中,那種有邊界且內部功能完備的整體幾乎不復存在。城市語境下復雜的人口遷移與流動,多種文化交織糅雜,以及科技與媒介的影響,都使得設定明確邊界的理想難以實現。人類學家發現在城市中他們常常面臨著人員流動快、人群規模大、文化變遷、對象與范圍難以界定等實際困難,并發現再難以一個人的力量掌控這一復雜局面。于是人類學家學著適應城市文化環境節奏,對城市民族音樂學所需“新”的田野調查方法展開思考。謝勒梅在《聲音景觀:探索變化中的世界的音樂》中嘗試逃離民間音樂的研究范圍,概述了波士頓、休斯敦、朱諾等多個城市綜合、互動的聲音景觀,包括當地少數族裔社區、街頭音樂家、夜總會、小酒館、飯店及各種正式與非正式音樂群體的音樂。在《民族音樂研究:31個論題和概念》一書中,內特爾認為:“城市音樂研究的新方面主要是城市環境、成為現代都市特點的文化與音樂的匯聚,以及都市作為研究音樂文化的獨特的、綜合的環境。”他指出,現在民族音樂學家可能將田野地點選在自己生長或熟悉的城市環境,研究內容則建立在城市與鄉村音樂與社會文化過去與當今的差異之上,如被社會、經濟、大眾媒介等影響下出現的不同階層、族裔多元化等等。以上說明,1980年代后,民族音樂學界對城市音樂的研究在認識框架上有了很大的轉變,即認識到傳統音樂在現代都市文化背景中發生了時間背景和空間背景,以及民族音樂學家自身背景的多重轉換。
近年來,面對城市音樂環境,人類學家們推薦以團隊的方式進行田野調查。事實上,20世紀后期越來越少的人在偏遠甚至不熟悉的地方學習。內特爾也表示,許多民族音樂學家都培養和依賴于具有相似地理、學科背景或理論興趣的同事,有時在該領域分享經驗。他承認他們的“線人”大多是同事和老師。謝勒梅在《一起實地考察:紐約布魯克林敘利亞猶太人的團隊研究》一文中介紹了城市民族音樂學田野調查的方法和過程,闡述了現今團隊田野的現實與優勢。筆者認為這是對民族音樂學一直以來單槍匹馬進行田野工作的反思。這篇論文以布魯克林敘利亞猶太人音樂田野為例,反映了城市音樂民族志研究的過程。作者認為,隨著越來越多的民族音樂學家在復雜的環境中進行研究,作為進入新學科和新社區的一種手段,個人在建立和利用親密的人際關系進行研究方面可能具有的優勢往往遠不如以前那么強大。特別是城市地區,經常給偶然的參與者觀察帶來相當大的障礙。城市來源的多樣性和范圍也顯示出數據的范圍和數量往往超出了個人收集、處理和吸收的能力。作者站在哈佛大學音樂系教授的立場,認為在城市地區進行團隊研究除了能夠提高效率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優勢,就是它為培養學生提供了理想的環境。學生們以新手的身份進入該領域,而團隊項目能為其提供一個環境,在這個環境中,學生可以進行實地考察。謝勒梅認為團隊研究項目為民族音樂學的實地工作訓練提供一個實驗室,能為學生日后進入民族音樂學田野考察奠定穩健的基礎。
五、城市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實踐
中國城市民族音樂學的起步在21世紀初。上海音樂學院洛秦教授與湯亞汀教授等人通過翻譯與介紹內特爾、謝勒梅等西方學者有關論文與著作,以及對西方城市民族音樂學理論進行綜述,逐步將該概念引進國內。洛秦教授在《城市音樂文化與音樂產業化》一文首次從概念上對城市音樂進行界定:“城市音樂文化就是在城市這個特定的地域、社會和經濟范圍內,人們將精神、思想和感情物化為聲音載體,并把這個載體體現為教化的、審美的、商業的功能作為手段,通過組織化、職業化、經營化的方式,來實現對人類文明的繼承和發展的一個文化現象。”自此,國內民族音樂學家也逐漸“將目光投向城市”。據筆者不完全統計,21世紀以來論及城市音樂相關內容的文章多達500余篇。由洛秦教授帶領的上海高校音樂人類學E—研究院建設計劃項目(2005年1月成立)是國內城市音樂研究比較突出的成果,主要研究的是上海音樂歷史和文化。洛教授將他與學生們數十篇碩士與博士學位論文研究成果匯集成“城市音樂的文化闡釋”“城市音樂的歷史敘事”“城市音樂的社會表達”三輯。這些研究成果涵蓋內容廣泛豐富,從古代上海古琴文化、評彈流派、京劇琴師,到民國時期上海唱片業發展、《申報》音樂資料研究、近代上海電影歌曲研究,到現代音樂劇場、社會音樂文化演出、爵士音樂文化品牌研究等,包含了上海上百年來種種音樂人物、事件與活動,以及涉及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問題,勾勒出上海城市歷時與共時縱橫交錯的概貌。這些研究大多以個案來呈現,卻都遵循洛教授對上海音樂研究的核心理念:結合音樂人類學、歷史文化語境與世界主義宏觀視角三重視界來看待上海這個既具有悠久歷史,懷抱濃厚滬上特色,又身處國家經濟金融中心兼具國際視野的雙重特質的超大城市。筆者認為,謝勒梅所說的“團隊考察”的優勢在構建“音樂上海學”的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正是通過以洛教授為負責人的各位教師與相關專業碩博士們對中國本土的個案研究進行研究積累,才逐漸發展對中國民族音樂學者對國內城市民族音樂學的獨特解釋,將西方理論和思想實施安放在中國實踐中。洛教授還陸續發表了數篇文章,通過對“音樂上海學”建構的理論與實踐、所面對的問題及其思考、其范疇與特質、價值與意義等方面的探討,力圖打造“音樂上海學”的學術理念。
洛教授及其團隊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與討論。隨后國內逐漸出現了“音樂北京學”“音樂哈爾濱學”,以及“區域音樂研究”“音樂地方學”等相關論域的專門研究群體及成果。也有不少學者在借鑒西方理論的基礎上,對國內城市民族音樂學研究所取得的階段性成果進行梳理總結,以便推動該學科日后的理論建設。如陳波《我國城市民族音樂學研究綜述》一文從歷史與當代兩個視域總結了國內城市音樂文化研究的個案,對個案進行了內容總結與細致分類;趙書峰在《城市音樂人類學研究新思考》中以“媒體藝術之都”長沙為例,提出對城市空間聲音景觀、娛樂空間的音樂與舞蹈、城市音樂節、城市生活史等新學術熱點的考察與展望。
可以看到,國內城市音樂研究與國際學界的城市音樂人類學研究熱點既有一致之處,如流行音樂與文化產業,音樂中的女性意識、跨界族群現象、少數族群的社區音樂空間等,也有聚焦于中國當地城市特有音樂現象的論題。筆者認為,這是因為中國城市民族音樂學有其特殊性。中國城市,在歷史淵源、城市規模、族群交融、意識形態等方面更為復雜,這些因素直接影響了中國城市音樂的生存環境與樣態呈現。我國許多城市保留著上千年深厚的歷史文化遺產;也有一些城市在近代歷經了強烈的中西方文化碰撞融合而成;有的城市與周邊鄰國接壤,相互吸收了周邊異國文化;有的城市是少數民族聚集區,保留了豐富的民間藝術文化遺產。這就要求國內學者進行研究時充分考慮研究對象的生成語境,充分結合實際對其進行針對性和本土化的思考。因此,用生硬的“拿來主義”將西方理論套用于中國的城市音樂文化研究并非可行的方法,我們應考慮西方城市民族音樂學術話語的“中國實踐”問題。
筆者發現,國內城市音樂研究有兩個本土化實踐值得關注,也有仍待優化之處。一是在城市音樂研究中對歷史語境的觀照。只有在尊重歷史書寫史實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對“以往人類的全部活動”進行整體觀照,突破閾限的思維模式。洛教授以上海城市音樂研究為例,提出將人類學、社會學和歷史學融為一體是“新史學”研究方法,“以上海音樂文化觀照整個上海城市歷史文化,通過音樂的小文化來透視整個城市的大歷史,來探討音樂在其中的作用和大歷史對小文化的影響”。我們看到,雖然現下國內城市音樂文化的研究中有不少歷史的內容,但仍缺乏歷史的意識。對于音樂作品、音樂創造的主體與歷史事件的勾連仍然是孤立的,“缺乏將音樂的人事關系置于歷史場域中進行結構性思考”。二是重視考量民間音樂文化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城市的生存與發展。內特爾曾提出,西方學術傳統中一個重要的理念,就是將“城市視為傳統延續的組成部分”。歐美民族音樂學家對城市傳統,特別是被稱為“家門口的民族音樂學”的研究越來越感興趣,這種與熟悉事物的接觸導致了內特爾對城市空間里的音樂給予了更多關注——在對美國中西部一所典型音樂學校的研究中,他將其描述為“未經研究的音樂文化的最后堡壘”。也就是說,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西方古典音樂沒有被研究過。于是人類學家轉而以民族音樂學的研究方法研究“家門口的音樂”——西方藝術音樂。如謝勒梅的《早期音樂運動的民族音樂學》,勞丹(Laudan Nooshin)的《對特殊問題的導論:西方藝術音樂的民族音樂學》等,都闡明“西方藝術音樂”和“非西方音樂”之間的界限早已土崩瓦解,變得模糊不清。相較之下,我國從古至今幾千年的歷史更是源遠流長,積淀豐富是我們城市獨有的特征。國內學者沿襲西方理論思路,又在國內強調非遺保護的特殊語境下,不再以地理空間劃分界限,也不再認為鄉村與城市之間存在涇渭分明界限并以此來區分研究對象的屬性,而是關注文化對象本身及其環境,即國內傳統民間音樂與藝術形式在城市的生存現狀,于是如《……之城市化研究》《……之(生存)現狀研究》《城市民族音樂學視野下……的研究》的主題如雨后春筍,重點關注傳統音樂的城市化過程,或在城市化格局中其生存環境與表演形態受到的嚴峻考驗,以此來呼吁地方政府與社會各界的重視,使其能夠得到更好的傳承與保護。結合國內文化環境,正如張伯瑜教授所說:“在西方,村落基本上不存在了,城鎮是西方社會的基本結構單元。中國則不同,村落還大量存在,農村與城鎮共同構成現實的中國社會結構……所以,中國的民族音樂學必然會與西方的民族音樂研究不同,中國學者仍然會把大量的精力花在農村的音樂品種之上。”最后,西方城市民族音樂學理論的本土化實踐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不過國內學者更多的是通過個案形式探討音樂人事關系及其價值和意義,對城市的整體缺乏觀照。雖然已經有學者意識到這一點,如洛秦教授所說,城市音樂研究可以“以某特定城市為單位,對其音樂的歷史發展及其整體音樂風格特征的研究”,然而或許是對該學科脈絡梳理與學科建構方面還比較薄弱,所以從整體觀出發的研究還比較欠缺。
結 語
本文通過對城市民族音樂學的母學科民族音樂學及其上源學科都市人類學和城市社會學的“血統”追溯,闡釋了該學科產生的環境,發現早期該學科在研究模式、思維理念、田野考察等方面都帶有其“祖先”的遺傳影響。而后民族音樂學家在對“家門口的音樂”研究過程中逐漸放棄“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對立思想和對文化同質性的偏執,在不斷流動和變化的邊界松散的城市空間中摸索出對多元城市音樂文化之間互動關系的新的研究模式,強調城市整體與元素部分的關系,關注城市環境的作用力,并呼吁采用團隊田野的模式對復雜城市語境進行應用實踐型考察。通過城市民族音樂學的中國實踐,可以看到中國學者身上對傳統文化/民間文化特別是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城市生存現狀的文化擔當。通過豐富的個案研究案例,也通過學者對以“音樂上海學”為典型的城市研究模式的構建反映了中國城市民族音樂學的發展動向,體現了學者們立足中國文化本位的研究立場。筆者通過對民族音樂學關鍵詞——“城市民族音樂學”提供探源和反思性的討論,闡釋了該學科生成環境與學科屬性,展示了在城市空間中考慮多元主義、流動性與融合的重要性,呼吁學界在借鑒西方跨學科、跨文化的理論意義的基礎上努力構建國內城市民族音樂學研究學科建設與研究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