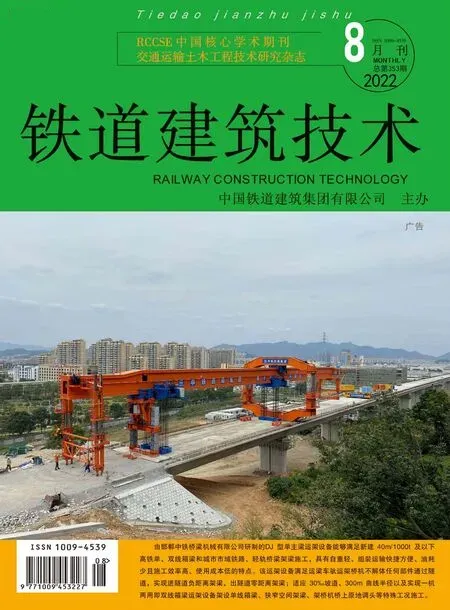梅家溝隧道支護變形分析及加固方案優化研究
郭傳臣
(1.中鐵十四局集團有限公司 山東濟南 250014;2.鐵正檢測科技有限公司 山東濟南 250014)
1 緒論
近年來隨著全球化經濟影響,極大刺激了我國道路交通行業。隧道作為山嶺地區常用道路載體,正形成“長、深、大、雜、群”總體建設格局,也成為本世紀隧道發展的總趨勢[1]。
對于隧道工程軟巖大變形問題,國內外學者做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多種突破思路與理論體系,主要有理論計算方法、數值分析方法、監控量測研究方法、物理模型試驗分析方法、工程地質判別法和工程類比法[2]。其中數值分析方法又衍生出基于有限元法、有限差分法、離散元法、不連續變形分析法和混合有限元-離散法等[3]。李術才[4]等采用有限元數值模擬方法,對處于高地應力和圍巖較差的軟巖隧道進行圍巖與支護結構受力變形狀態、開挖工法與支護之間的耦合性和相關性進行分析,并得出系列重要結論;王洪峰[5]等采用大型有限元軟件對隧道變形進行模擬,分析了隧道周圍巖體的應力、支護結構內力和應變以及巖體塑性區發展規律。
本文基于現有研究成果,針對梅家溝隧道現場軟巖工程特性,結合現場情況及監控量測結果對支護效果進行評價。現場監控表明,不同加固方案對于軟巖地質具有不同的變形抑制作用。對現有初支二次加固方案進行優化,通過數值模擬計算確定初支施作二次加固的必要性以及施作時機。
2 工程地質概況
梅家溝隧道隧址區位于綿陽市平武縣白馬鄉祥述家寨東側,S205省道從隧址區通過,交通便利。隧道全長2.38 km,Ⅴ級圍巖,圍巖主要為強-中風化千枚巖、炭質板巖、炭質板巖夾薄層千枚巖,裂隙發育,多為泥質充填,巖體破碎,巖質軟,遇水易軟化;局部斷層破碎帶地段有涌突水;工程區斷裂和褶皺均較發育,主要有大橋復向斜、木皮倒轉復背斜、白馬弧形構造帶等大型褶皺。
3 現場監控變形概況
3.1 現場監控量測
根據九綿高速隧道監控量測數據平臺導出的監控量測數據,繪制斷面變形速率極值和累計值如圖1、圖2所示。

圖1 梅家溝隧道斷面變形速率極值

圖2 梅家溝隧道斷面累計變形量
分析可知,梅家溝隧道左洞周邊收斂速率極值普遍在20 mm/d以上,左、右洞拱頂下沉速率極值分布規律相似;左、右洞周邊收斂累計值普遍在150 mm以上,而拱頂下沉量累計值普遍在50 mm以上,可知該隧道以收斂大變形為主,拱頂下沉較小,其量值比率在2~6之間。現場拱架連接位置受剪切和擠壓較為明顯,邊墻大面積剝落,而初支拱頂狀態較為完整,一定程度上驗證了監測結果的正確性。
3.2 支護變形情況
隧道開挖施作初期支護后,其變形主要體現為:噴射砼開裂掉塊、鋼拱架扭曲、鋼拱架折斷、鋼拱架剪斷、初期支護侵限,如圖3所示。

圖3 軟巖大變形現場
4 支護方案嘗試及效果
4.1 支護方案
針對原方案支護效果不良問題,項目參建方研討了多種支護方案,匯總如表1所示。

表1 抑制大變形方案匯總
4.2 各支護方案試驗段效果分析
根據超前地質預報結果,結合地勘設計資料,選取地質巖性相近的里程作為試驗段,進行不同支護類型條件下效果分析。左洞試驗段為ZK67+980~ZK68+685,右洞為K68+015~K68+658。
提取梅家溝隧道左右線 Da、Db、Dc、Z5af、Dc-1(襯砌類型預留變形量均為300 mm)襯砌類型監測斷面共16組的拱頂下沉及周邊收斂時程數據,分別對左右線不同襯砌類型下的監測斷面進行變形速率及累計值統計。各方案斷面數量、各斷面支護類型、各支護方案具體里程及變形量統計如圖4所示。


圖4 不同支護類型下變形量分布(縱坐標單位:mm)
(1)相同支護類型下,不同監測斷面拱頂下沉量基本可以與支護結構較好匹配;不同支護類型下,78~99號、55~67號斷面控制較好。
(2)相同支護類型下,不同監測斷面拱頂下沉量相差無幾,需結合周邊收斂情況進行雙控;66~79號斷面,拱頂下沉控制效果較好。
(3)相同支護類型下,不同監測斷面周邊收斂量基本可以較好匹配;不同支護類型下,周邊收斂量值變化不明顯,82~99號、55~62號斷面控制效果較好。
不同支護類型下,梅家溝隧道收斂大變形累計值占預留量的60%~100%;拱頂下沉量較小,累計值占預留量的20%~40%。上臺階開挖并支護后,圍巖壓力(松散圍巖壓力、變形圍巖壓力、膨脹圍巖壓力)作用在支護結構上,引起支護結構變形,此時變形速率較大,量值為10~20 mm/d,持續時間為2~4 d;隨后速率有所下降,約為5 mm/d,累計變形量持續上升。受下臺階開挖擾動,圍巖內部應力再次重新分布,收斂變形速率出現突增,量值達到20 mm/d以上的概率極大,局部斷面達到40 mm/d以上,初支全斷面出現不同程度的開裂,拱頂下沉量值突變不明顯。大變形速率持續時間受制于拱架連接作業時間和仰拱施作時間的長短。仰拱施作完成后,變形速率明顯減小,穩定跡象有所不同,局部斷面以低速率(1~2 mm/d左右)持續變形。
僅根據監控量測變形值評價支護結構的有效性并不合理:首先,不同工隊施工技術層次高低不齊,難以界定施作質量;其次,不同支護類型下對應的圍巖地質條件也不盡相同,盡管試驗段盡可能選擇了地質巖性相近的里程,但地層的各向異性和巖層分布的不規則性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最后,支護強度的提高,不一定造就小變形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變結構受力狀態,使整體能夠保證在正常使用極限狀態下工作,而不會達到承載能力極限狀態。
5 初支現狀及二次加固方案優化
5.1 支護現狀
如表2所示,經過現場監控斷面數據分析,下臺階開挖時往往會發生突變變形,伴隨支護承受壓力急劇增大,支護結構大概率會發生變形、侵限甚至失穩。為確保支護質量及工程安全,應施作二次加固,并合理確定加固方案的施作時機和施作方式。

表2 不同支護結構下監控量測結果
5.2 加固方案優化
5.2.1 數值計算結果
建立三維數值模型,模型尺寸為100×80×30 m,如圖5所示。邊界條件為:固定前后左右和下部界面,上部邊界為自由面。偏壓模擬方式采用簡化的重力模式,即在模型上邊界施加不同量值的重力場[6]。為簡化試算步數,將隧道中線作為重力場分界線,采用Mohr-Coulomb本構模型,大應變變形模式,開挖循環進尺為1 m,按照臺階法施工步驟進行計算,所選取的圍巖力學參數如表3所示。

圖5 數值計算模型

表3 巖體物力力學參數
數值分析做如下假設:
(1)實際工程中隧道雙洞凈距為25 m,即2.5B,尚滿足小凈距隧道條件,模擬過程只建立單洞模型,將雙洞開挖的擾動效應等效成圍巖體力學參數的弱化程度[8]。
(2)為簡化循環計算時間、提高結果準確率,采用位移控制的摩爾-庫倫本構模型代替時效控制的應變-軟化本構模型。
(3)計算模型尚未考慮地下水對施工過程的不利影響,該影響可簡化為對應力和位移的不利影響,影響因子根據現有文獻資料[7-9]查得分別為0.05和0.015。
(4)整個計算過程不考慮二襯作用,即圍巖對支護的作用力均由初支和仰拱承擔。
5.2.2 初支二次加固時效性優化
數值計算結果表明:初支施作完成后,淺層圍巖在深部巖體作用下產生松散變形,導致初支隨之變形,在初支變形至某一時刻時進行二次加固,會改變初支和圍巖的受力狀態,進而改變初支結構的位移軌跡。由圖6可知,當初支不進行二次加固時,變形至378 mm時仍未出現收斂趨勢;進行二次加固運算至1 000步時,結構變形有減弱效果,但運算到5 000步時,仍然呈現持續性變形趨勢,且變形值較大,達到348 mm,相比無二次加固降低30 mm,仍尚處于預留變形量邊緣。數值計算至2 000步時,相應結構變形有減弱效果且較前者更為明顯;運算到5 000步時,累計變形達284 mm;隨著二次加固的施作,改變了圍巖受力狀態,優化了應力分布形態,初支結構開始呈現收斂趨勢,變化速率明顯降低。數值運算3 000步時,收斂速率大幅降低且趨于穩定,在規定計算步內累計變形達273 mm,這表明支護結構的受力分配和巖體膨脹力、松散力相耦合,達到優化目標。在數值計算過程中運算4 000步時,即初支變形至288 mm時施作二次加固后,初支結構超過正常使用狀態,臨近極限狀態,結構瀕臨破壞,表明二次加固施作不能有效支撐破壞區內圍巖,且淺層破壞區巖體向深部發展,結構變形曲線斜率有增大趨勢,二次加固作用微弱。


圖6 周邊收斂值隨計算步變化曲線
6 結束語
(1)梅家溝軟巖隧道現場監控量測數據表明,該隧道具有明顯的偏壓特性,且隧道整體以水平變形為主,豎向變形相對較弱。
(2)現場所嘗試的初期支護結構對于抑制圍巖變形所貢獻的強度、剛度不足以確保支護結構處于正常穩定狀態,表明了二次加固的必要性。
(3)數值模擬計算結果表明,二次加固的時機選擇對于有效抑制圍巖變形、改善巖體作用狀態、優化結構受力分配、保障結構整體安全有效具有決定性作用;建議經過試驗研究與理論驗證確定施作時機,切不可盲目操作,以至于導致安全和質量事故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