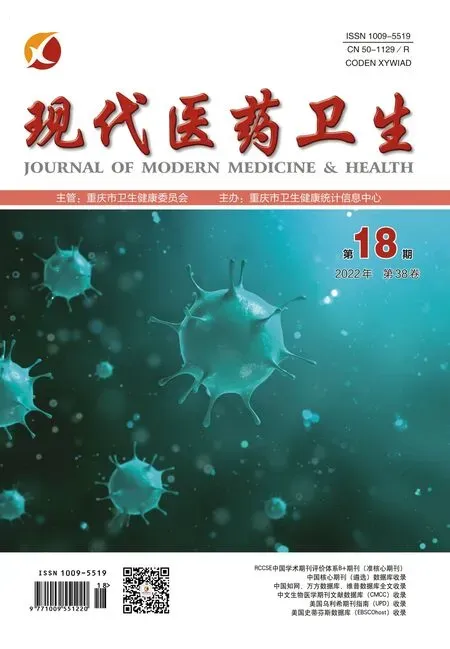脾臟硬化性血管瘤樣結節性轉化2例臨床病理特征*
林海月,楊聰穎,張春芳,聶艷紅,賀艷玲,齊冬雪,陳 昊
(徐州醫科大學附屬連云港醫院病理科,江蘇 連云港 222002)
脾臟實體瘤很少見,手術和尸檢標本中的發生率僅為0.007%[1]。脾臟硬化性血管瘤樣結節性轉化(SANT)是一種罕見的非腫瘤性血管病變,于1993年首次被報道,學者稱其為“索狀毛細血管瘤”,MARTEL等[2]于2004年將其正式命名為“硬化性血管瘤樣結節性轉化”,并得到廣泛認可。自2004年以來,相關報道僅200余例[3]。臨床對于SANT的發病機制尚不清楚,而SANT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但其病理形態及免疫組織化學表型具有一定特征。作者報道了2例SANT,結合相關文獻探討其臨床病理特征,以期提高該病的診斷水平。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一般資料 收集本院病理科脾臟切除標本中的2例SANT。其中女性1例(病例1),年齡36歲;男性1例(病例2),年齡44歲。2例患者臨床均無癥狀,為體檢時發現,其中男性患者2年間腫物增大至5.0 cm×4.5 cm×4.0 cm。均行腹部計算機斷層掃描(CT)+增強掃描,病例1顯示脾臟孤立性腫塊,早期及門靜脈期腫物邊界清楚,密度低于脾臟,延遲期與脾臟等密度;病例2脾臟內見一類圓形低密度影,增強呈漸進性不均勻強化。見表1、圖1。

表1 SANT患者的臨床資料
1.2標本結果 10%中性甲醛固定手術標本,經石蠟包埋,4 μm連續切片后蘇木精-伊紅染色(HE染色),顯微鏡下觀察。免疫組織化學染色采用EnVision兩步法,DAB顯色,用磷酸緩沖鹽溶液(PBS)代替一抗行空白對照,抗體CKpan、CD31、CD34、CD8、CD68、SMA、CD30由廣州安必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購入。術后對2例患者進行電話隨訪,以了解患者的預后情況。
1.3眼觀結果 病例1,脾臟大小17.0 cm×8.0 cm×6.5 cm,剖面一側見一灰紅灰白腫塊,大小為8.0 cm×7.0 cm×6.0 cm,邊界清楚,灰褐色,分葉狀,灰白色星芒狀瘢痕明顯,其余脾臟組織灰紅、實性、質較軟,見圖2。病例2,脾臟大小11.0 cm×8.0 cm×6.0 cm,剖開見灰白腫塊,大小為5.0 cm×4.5 cm×4.0 cm,實性質韌,灰褐色,邊界清楚,分葉狀,灰白色星芒狀瘢痕明顯。
1.4鏡檢結果 低倍鏡下腫物呈大小不一的血管瘤樣多結節生長模式(圖3a),部分結節相互融合,結節周圍被梭形細胞呈同心圓狀包繞,結節間為纖維硬化間質。高倍鏡下血管瘤樣結節由裂隙樣、圓形或不規則形的血管腔構成,管腔內襯肥胖內皮細胞,部分血管腔見紅細胞,血管腔隙見散布梭形及卵圓形細胞,缺乏核異性及核分裂活性,無壞死,結節內散在淋巴細胞、漿細胞;間質由致密纖維組織構成,散在胖梭形細胞、淋巴細胞、漿細胞和組織細胞,結節周圍及間質中見少量含鐵血黃素沉著。
1.5免疫表型 血管瘤樣結節內含3種不同類型的血管:毛細血管、竇狀隙、小靜脈,CD31在3種血管類型中的內皮細胞均彌漫陽性(圖3b),毛細血管CD34陽性(圖3c)、CD8陰性,竇狀隙CD8陽性(圖3d)、CD34陰性,小靜脈CD34及CD8均陰性。2例中,1例CD8陽性的竇狀隙表達較少,1例CD8陰性表達。結節內梭形及卵圓形細胞混合表達CD31、CD68(圖3e)、SMA(圖3f),表明其可能由內皮細胞、組織細胞及血管周細胞混合組成。結節周圍同心圓狀排列梭形、卵圓形細胞及間質細胞SMA均彌漫表達、CD68散在表達,CD30均陰性。
1.6隨訪情況 2例患者術后隨訪5和8個月,均未見復發及轉移。
2 討 論
2.1發病機制 SANT的發病機制尚不明確,MARTEL等[2]提出,SANT可能是起源于紅髓的血管病變,因小血管流出道破壞,引起近端血管床的結節性改變或增生。血管瘤樣結節最終可能發生纖維性閉塞,某些病變也可能開始于炎性假瘤或組織血腫。有學者提出,SANT可能與免疫球蛋白G(IgG)4相關硬化性疾病[4]或Epstein-Barr病毒(EBV)相關[5]。PELIZZO等[6]報道了1例9周大的女嬰發生SANT的病例,認為其發病機制不能排除遺傳或妊娠危險因素(如妊娠糖尿病)的作用。有學者研究表明,SANT是一種多克隆反應性病變而非腫瘤[7]。
2.2臨床特征 SANT好發于成年女性,男女患者比例為1.00∶1.63。SANT直徑3.83~175.00 mm,中位直徑為49.5 mm,多為孤立性結節,罕見多發結節[8],偶見嬰兒及兒童病例報道[9]。患者通常無癥狀,通過體檢或者因其他疾病就診發現,少數患者可表現為腹痛,而兒童比成人更常出現癥狀,原因為兒童腹部空間較小,可能表現腹部腫塊、疼痛、紅細胞沉降率升高、血細胞減少、白細胞增多和發熱[9]。影像學上,SANT表現為實性、孤立、橢圓形或小葉狀界限清楚的結節病灶,伴有纖維性瘢痕,偶爾伴有鈣化,增強CT和核磁共振成像(MRI)典型強化特征包括漸進向心性強化、“輪輻”狀強化、結節狀強化及中央纖維瘢痕延遲強化[10]。SANT具有逐漸生長的潛能,NOMURA等[8]根據數據推測,其增長速度估計為每月0.75 mm。DUTTA等[11]報道了1例早期乳腺癌并發脾臟SANT患者,兩年半內脾臟病灶由14 mm×8 mm增加至38.3 mm×30.3 mm,而本研究男性患者2年間病灶生長速度與其報道大致相同。
2.3病理學特征 SANT具有特征性的病理形態學特征,大體多為單發腫塊,少見多發,邊界清楚無包膜,質韌,中央見白色星芒狀瘢痕,伴有出血灶。鏡下呈類似肉芽腫表現的多結節血管瘤樣結構,單個結節具有模糊分葉狀結構,結節由裂隙樣、圓形或不規則形的血管腔構成,管腔內襯肥胖內皮細胞,血管腔之間散在分布梭形及卵圓形細胞,缺乏核異型及核分裂活性,無壞死。梭形細胞呈同心圓狀包繞結節,有紅細胞外滲,散在炎癥細胞。結節間質由黏液樣到致密纖維組織構成,散在胖梭形肌成纖維細胞、淋巴細胞、漿細胞和含鐵血黃素吞噬細胞。
SANT的免疫表型在多數報告的病例中基本相似,結節內包含3種不同類型的血管:毛細血管(CD34+/CD8-/CD31+)、竇狀隙(CD34-/CD8+/CD31+)、小靜脈(CD34-/CD8-/CD31+),似乎模仿紅髓的結構,結節內梭形或卵圓形細胞不同程度表達CD31、CD68及SMA。本研究中2例病例稍有不同的是,1例CD8陽性的竇狀隙表達較少,1例CD8陰性表達,這與MARTEL[2]等研究中“隨著血管阻塞時間延長,部分竇狀隙CD8可能失表達或消退”的結論相符合,SAID等[12]的報道中,患者結節CD8為陰性表達。WEINREB等[5]及ZHOU等[13]研究中,血管瘤樣結節中血管內皮出現CD30表達上調,而本研究中2例患者CD30均為陰性。
2.4鑒別診斷 SANT需要與以下疾病相鑒別。(1)血管瘤:常為海綿狀或毛細血管瘤,同時表達CD34、CD31,不表達CD8。(2)竇岸細胞血管瘤:由類似脾竇的交錯血管網構成,同時有乳頭狀突起和囊腔,被覆細胞表達CD31及Ⅷ因子相關抗原,不表達CD34及正常脾竇內襯細胞的標志物CD8,另表達CD68等組織細胞標記。(3)血管內皮瘤:為一種中間型血管腫瘤,內皮細胞有一定的非典型性,腫瘤細胞表達CD31、CD34,亦可以出現組織細胞標記陽性,但不表達CD8。(4)血管肉瘤:CD31陽性,偶爾CD34、CD8也可以陽性,但其血管腔相互吻合,內皮細胞異型性顯著,核分裂多見。(5)脾臟錯構瘤:由被覆內皮型相互溝通錯亂的血管網組成,CD31、CD34、CD8的表達與SANT有重疊,但缺乏SANT病灶境界清楚、多結節血管瘤樣結構及硬化性間質的形態。(6)炎性假瘤:由增生的梭形細胞和炎性細胞混合組成,血管內皮細胞標記陰性。(7)惡性腫瘤脾臟轉移:罕見,常來源于乳腺癌、肺癌、結腸直腸癌、卵巢癌及惡性黑色素瘤[8]。惡性腫瘤患者出現脾臟占位時與SANT鑒別診斷困難,DUTTA等[11]報道了1例具有乳腺癌病史患者,通過脾臟活檢確診SANT從而避免脾臟切除。
2.5治療與預后 由于SANT臨床表現無特異性,且術前通過影像學無法與其他脾臟良惡性腫瘤鑒別,一般行脾臟切除達到通過組織病理學診斷與治療的目的,手術方式包括開腹脾切除、腹腔鏡下脾切除及腹腔鏡脾部分切除。JIN等[14]對比了3種手術方式的療效,其中,腹腔鏡脾部分切除術保留了功能性脾實質的同時去除了局灶性病變,術后患者血小板計數峰值顯著降低,推薦在術前影像學檢查提示非惡性病變,且病變不靠近脾門、未侵犯脾臟大血管時,選擇腹腔鏡脾部分切除術,同時進行術中冰凍切片排除惡性腫瘤。SANT預后良好,文獻中未見復發及轉移報道。本研究2例術前診斷不明確,病例1腫瘤體積較大,病例2隨診觀察兩年期間腫瘤明顯增大,均行腹腔鏡下脾臟切除術,隨訪5、8個月,均未見復發及轉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