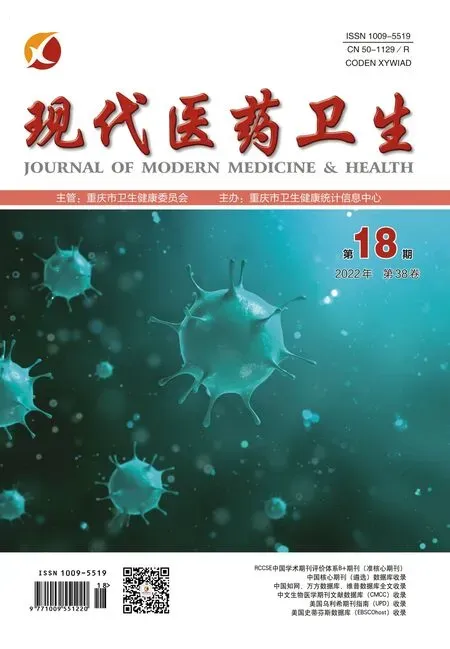可視內鏡聯(lián)合椎間孔鏡技術治療脫出游離型椎間盤突出癥的近期臨床效果研究
李光旭,周 榮,馬 健,李德勝,廖文潔,楊影楓,吳久松
(重慶市永川區(qū)人民醫(yī)院骨科,重慶 402160)
與開放手術比較,經皮內鏡下腰椎間盤切除術(PELD)在椎間孔入路治療腰椎間盤源性疾病具有創(chuàng)傷更小、恢復更快的優(yōu)勢[1]。HOOGLAND等[2]改進了Yeung脊柱內鏡系統(tǒng)(YESS)技術,形成了經典的TESSYS技術,切除上關節(jié)突腹側部分骨質行椎間孔成形,在治療各類腰椎間盤突出癥、側隱窩狹窄等疾病中療效確切。在TESSYS基礎上發(fā)展起來的偏心環(huán)鋸技術和可視內鏡下多次成型技術則為某些較為復雜的疾病治療提供了內鏡下技術支持。
脫出游離型在腰椎間盤突出中占35%~72%[3],以往常采取后路開放手術解決,切口較大,也會對脊柱后部的穩(wěn)定結構造成破壞,術后易出現(xiàn)腰背痛等并發(fā)癥[4-5]。采取傳統(tǒng)的椎間孔鏡技術,重度脫垂的髓核會受到關節(jié)突、椎弓根及椎體后緣的阻擋,建立通道困難、骨塊或髓核殘留及神經脊膜損傷等問題使其仍然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6-7]。本研究回顧性分析了本院2018年8月至2020年7月脫垂游離型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56例,針對Lee分區(qū)法[8]分型,采取偏心環(huán)鋸結合可視內鏡多次成型技術治療,取得良好的臨床效果。
1 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 選取本院2018年8月至2020年7月脫垂游離型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56例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26例,女30例;年齡23~78歲,中位年齡37歲;突出節(jié)段L3/4者12例,L4/5者27例,L5S1者17例。按照Lee脫出分類法[8],5例為Ⅰ型,脫出在矢狀位上超過上位椎弓根下緣以下3 mm,為重度頭端脫出;8例為Ⅱ型,脫出位于上位椎弓根下緣以下3 mm至上位椎體下終板之間,為輕度頭端脫出;25例為Ⅲ型,脫出位于下位椎體上終板與下位椎弓根中部之間,為輕度尾端脫出;18例為Ⅳ型,脫出位于下位椎弓根中部以下,為重度尾端脫出。所有病例均經門診復診并完成隨訪,本研究經醫(y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納入標準:患者腰臀疼痛伴單側下肢放射性疼痛;出現(xiàn)跛行、對應神經支配區(qū)下肢肌力異常、感覺麻木等明顯影響生活的癥狀,患肢直腿抬高試驗陽性;影像學計算機斷層掃描(CT)和核磁共振成像(MRI)證實為單節(jié)段椎間盤脫出游離,與臨床癥狀、查體相符;經正規(guī)保守治療6周以上癥狀無改善或進行性加重。排除標準:(1)多節(jié)段腰椎間盤突出;(2)患有脊柱不穩(wěn)、滑脫、感染、結核、腫瘤等疾病;(3)合并廣泛的椎管發(fā)育性狹窄或中央型狹窄;(4)患有嚴重的全身系統(tǒng)性疾病;(5)同一節(jié)段存在既往手術史。
1.2方法
1.2.1治療方法 采用德國Joimax THESSYS Ⅰ SEE 脊柱椎間孔鏡手術系統(tǒng),手術均由同一組醫(yī)生完成。患者取常規(guī)俯臥位,標記棘突連線及患側髂嵴在皮膚的投影線,根據不同節(jié)段和髓核脫出方向確定穿刺線指向對應上關節(jié)突肩部,旁開距離L4/5通常為背部平面和側平面交匯線,節(jié)段向上靠棘突線內移,穿刺方向越平,節(jié)段向下外移,穿刺方向稍大,標記穿刺點。同時,根據腰椎前弓、髂脊高低、髓核脫垂方向調整穿刺方向和旁開距離。在透視引導下將穿刺針送達關節(jié)突關節(jié),并用1%利多卡因在關節(jié)囊內外局部浸潤麻醉,再從上關節(jié)突腹側劃入椎間孔。穿刺成功后,拔出針芯,插入導絲,并做8 mm左右的皮膚切口。逐級置入擴張?zhí)坠芎螅先氚臊X套管和環(huán)鋸,余留一級導桿保持軸心,根據脫垂游離方向,利用偏心環(huán)鋸的向背側及脫垂方向切除骨質擴大椎間孔,取出骨塊。根據脫垂的方向和范圍,在內鏡直視下按需行多次成型,盡量減少對關節(jié)面的影響,然后置入工作套管。切除黃韌帶,取出脫垂游離髓核,探查椎管和神經根管減壓徹底后,最后用射頻電極行纖維環(huán)破口和隆起的皺縮成形,縫合皮膚切口,無菌小敷貼覆蓋傷口,手術結束。術后次日可佩戴腰圍下地活動如廁,指導下肢功能鍛煉;術后1周開始腰背肌功能鍛煉,但2周內以多臥床休息為主,出院前復查CT、MRI以了解減壓情況;佩戴腰圍1個月,術后3個月內避免久坐、彎腰或搬重物等活動。
1.2.2觀察指標 分別記錄比較術前、術后2 d、術后3個月、術后1年患者的視覺模擬評分法(VAS)、日本骨科學會(JOA)評分,術后1年采用改良MacNab療效[9]評估病情恢復情況。改良MacNab療效評定標準:優(yōu),癥狀完全消失,恢復原來工作及生活;良,有輕微癥狀,活動輕度受限,對工作生活無影響;可,癥狀減輕,活動受限,影響正常工作和生活;差,手術治療前后無差別,甚至加重。JOA評分共29分,主觀癥狀0~9分,臨床體征0~6分,日常活動受限度(ADL)0~14分,膀胱功能0~6分,分數(shù)低表明功能障礙越明顯。

2 結 果
2.1手術前后患者VAS及JOA評分比較 本組56例脫出游離椎間盤患者手術均在局部麻醉+靜脈輔助麻醉下順利完成,手術時間為45~105 min,中位手術時間為65 min;術后住院時間3~6 d,中位住院時間為4.2 d。與術前比較,本組病例術后復查MRI見脫出椎間盤均取出完全。術后各隨訪時間點的VAS、JOA評分均較術前明顯改善,差異均有統(tǒng)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手術前后患者VAS及JOA評分比較分)
2.2術后不良反應及隨訪情況 術后患者下肢放射痛明顯緩解,即刻患肢直腿抬高試驗陰性。有1例硬膜輕度撕裂致術后出現(xiàn)雙下肢麻木感,1 h后麻木消失,逐出現(xiàn)患下肢刺痛感,1周治療后逐步消失。有3例出現(xiàn)下肢短暫性神經感覺異常或痛覺過敏,給予保守治療2周后好轉。1例術后半年出現(xiàn)間盤復發(fā),因年齡大選擇保守治療后任存留患肢疼痛。按照改良MacNab標準,術后1年隨訪時:優(yōu)占69.6%(39/56),良占23.2%(13/56),可占5.4%(3/56),差占1.8%(1/56),優(yōu)良率為92.8%。見表2。

表2 改良MacNab標準下術后1年隨訪情況(n)
2.3典型案例 案例1,患者,男,77歲,L4/5椎間盤重度向頭端脫出,行PELD治療。術前腰椎MRI示L4/5椎間盤向頭端重度脫出,達到上位椎體椎弓根內緣,游離髓核呈淚滴狀,尾部與L4/5椎間隙相延(見圖1a、1b)。術中稍平建立工作通道(正、側位見圖1c、d)。術中脫出髓核位于上位椎弓根內側緣(見圖1e)。多次環(huán)鋸后取出骨塊(見圖1f)。術后復查CT不影響關節(jié)突關節(jié)面(見圖1g)。案例2,患者,女,75歲,L3/4椎間盤重度尾端脫出,行PELD治療。術前腰椎矢狀位MRI示L3/4椎間盤向尾端重度脫出,接近下位椎體椎弓根下緣(見圖2a、2b)。術中偏心環(huán)鋸建立工作通道,環(huán)鋸遠端位于下位椎體椎弓根的上緣(正、側位見圖2c、2d)。術中鏡下見脫出的松散髓核(見圖2e)。術中鏡下取出髓核后探查脊膜和神經減壓充分(見圖2f)。術后復查腰椎MRI示脫出髓核組織完全取出(見圖2g、2h)。
3 討 論
腰椎間盤脫出游離型是指游離髓核組織突破后縱韌帶和纖維環(huán)進入椎管的硬膜外間隙,壓迫硬膜囊和神經根管,可引起出行根和走行根神經癥狀,也可出現(xiàn)馬尾神經癥狀。其游離髓核組織多呈淚滴狀,尾部常與椎間隙相延,臨床常以此來確認責任間盤(如圖1a)。經典的后路開窗行椎間盤髓核摘除術,手術療效確切,但存在手術廣泛剝離腰背部肌肉、瘢痕粘連、骨質切除較多及住院時間長等缺點[10-11],復發(fā)率為5%~18%[12]。早期PELD采取經椎間孔逐級上關節(jié)突成形的TESSYS技術,直視下能安全有效地摘除壓迫神經根和硬膜囊的髓核組織,具有局部麻醉、創(chuàng)傷小、出血少、恢復快,對椎旁肌肉和韌帶干擾小,對脊柱的穩(wěn)定性影響較少等特點[13-14];同時對于在椎間孔區(qū)的神經壓迫和極外側椎間盤突出具有后側入路所不能比擬的優(yōu)勢;但其逐級成形操作常出現(xiàn)通道滑移偏離、損傷脊膜神經和骨塊存留等問題[15-16]。
由TESSYS發(fā)展而來的可視環(huán)踞經椎間孔關節(jié)突的一鋸成形和再次成形,既能減少放射暴露,又能更好、更安全地為解除壓迫的脫出游離髓核創(chuàng)造條件,減少神經損傷和骨塊殘留等問題[17-18]。李海音等[19]首先提出,偏心環(huán)踞在腰椎側隱窩狹窄癥中能有效完成上關節(jié)突增生、黃韌帶肥厚和椎間盤突出的減壓,減少通道滑移和過多切除骨質的問題,且不會影響關節(jié)突的穩(wěn)定性。作者將2種方式相結合,在本組病例中采取一級導棒從上關節(jié)突腹側滑入,逐級導棒擴充后留下一級導棒、半齒外套筒和環(huán)鋸,再采取偏心環(huán)鋸,可以向背側、遠側或頭側偏斜,將成形減壓的空間偏向髓核脫出的方向,然后在可視下根據術中需要再行二次或多次成形。這樣既能避免行環(huán)鋸時滑移過大導致減壓目標偏移,又能按需成形,避免過多切除破壞關節(jié)面骨質進而影響脊柱的穩(wěn)定性,同時還能安全取出髓核,并充分減壓。
針對不同脫出游離到達的分區(qū),做好詳細的術前計劃非常重要。首先,通過術前癥狀、查體和仔細閱讀影像資料明確需要探查的重點區(qū)域,然后根據需要探查的范圍設計關節(jié)突成形的范圍和手術技巧要求,最終進入通道完成鏡下操作。實踐中,大部分脫出游離的分區(qū)為Ⅲ區(qū),即游離髓核從椎間盤層面向椎體后上部分和上關節(jié)突、椎弓根上部分形成的側隱窩區(qū)域脫出,這時上關節(jié)突成形按Kambin三角基底方向建立通道,完成椎間盤和側隱窩層面顯露探查,摘除髓核進行椎管和神經根管的減壓;脫出游離的分區(qū)為Ⅱ區(qū),只需上關節(jié)突成形后向椎間盤頭側調整通道或少許再次關節(jié)突成形就可以顯露。而Ⅰ區(qū)和Ⅳ區(qū)壓迫為高度脫出游離型,需要可視環(huán)鋸多次成形才能完成通道的建立。向Ⅰ區(qū)脫出游離時,部分有時也會向上至Ⅳ區(qū)(如圖1a、圖1b),這時首先應該向Kambin三角底邊穿刺,避免環(huán)鋸損傷出口根,但穿刺角度要稍平進行初次環(huán)鋸,然后在可視下向頭側進行二次或多次成形,以滿足通道向上位椎的椎弓根下,即出口根處和椎弓根骨性內側層面,特別對于行走根和出行根交匯處和椎間孔上份區(qū)域顯露充分,進而完成該區(qū)域的髓核摘除和減壓。對來自Ⅲ區(qū)脫出至Ⅳ區(qū)的情況(如圖2a、圖2b),這時在上關節(jié)突成形時加大向側隱窩的穿刺角度,可通過二次或多次成形,或者切除部分椎弓根上份骨質,建立向椎弓根內側通道,取出壓迫髓核并減壓,需要完成椎間盤層面、側隱窩和椎弓根內側骨性層面整個區(qū)域的探查。針對不同分區(qū)確認探查范圍時,如脫出的髓核組織壓迫脊膜和側隱窩區(qū)域時,重點探查在脫出層面的中央椎管和側隱窩;如脫出髓核壓迫椎間孔區(qū)導致出口神經根壓迫時,需要在椎間孔區(qū)解除對出口神經根的壓迫;對于極外側椎間盤壓迫出口根時,可在椎間孔鏡直接面對此區(qū)域進行減壓;如果波及椎間孔內外區(qū)域,則需對受壓整個神經根管進行探查減壓。
本研究病例均在局部麻醉+靜脈輔助麻醉下完成,脫出髓核組織均完全取出,整體優(yōu)良率達92.8%。除了偏心環(huán)鋸成形范圍的可控顯露外,詳細術前計劃和術中可視內鏡操作避免了術中髓核組織的殘留。偏心環(huán)鋸結合可視內鏡下成形具有如下優(yōu)勢:(1)內鏡創(chuàng)傷小,不損傷椎旁肌,從上關節(jié)突腹側成形,不破壞關節(jié)穩(wěn)定性,不影響腰椎生物力學穩(wěn)定;(2)避免了行環(huán)鋸時滑移偏離靶向區(qū)域,且直視下髓核脫出和減壓區(qū)域按需成形,避免了過多切除破壞關節(jié)面骨質進而影響脊柱的穩(wěn)定性,減少了骨質過多破壞和骨塊殘留[20];(3)術中直視下逐層操作進入,安全、完整取出髓核,并充分減壓,有效減少了對硬膜及神經根的干擾損傷,降低出血、神經損傷、腦脊液漏等發(fā)生率[21];(4)局部麻醉下操作,減少了其他麻醉對機體的干擾風險,能與患者實時溝通,預判手術效果;(5)恢復快,早期可下地活動。但是該技術具有一定的學習曲線,比較陡峭,尤其是高度脫出游離型椎間盤的摘除更加困難。本研究中有1例硬膜輕度撕裂,有3例出現(xiàn)下肢短暫性神經感覺異常或痛覺過敏,考慮是術中牽拉脫出髓核組織時對神經和脊膜干擾損傷;1例患者術后半年腰部用力后出現(xiàn)間盤突出復發(fā),因年齡大選擇保守治療后存留部分患肢疼痛,考慮是髓核脫水退變致再突出壓迫神經。因此,要取得良好效果,首先要熟悉椎間孔可視內鏡的2種操作技術;其次要清楚腰椎的局部解剖結構和患者的病例壓迫因素,制定比較詳盡的術前計劃;最后鏡下操作要輕柔,仔細探查壓迫區(qū)域的脊膜、神經根,術中同患者有效溝通,避免損傷神經和脊膜,清理取出髓核組織完全,減壓充分、反復探查,并同術前影像相互印證,避免遺漏。
綜上所述,經皮椎間孔鏡采取偏心環(huán)鋸技術和可視內鏡下椎間孔成形結合技術治療脫出游離型腰椎間盤突出癥的療效突出,具有創(chuàng)傷小、恢復快、安全有效的特點,近期臨床療效滿意,但需要醫(yī)生把握適應證,做好詳細術前計劃,熟練掌握手術操作的技術要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