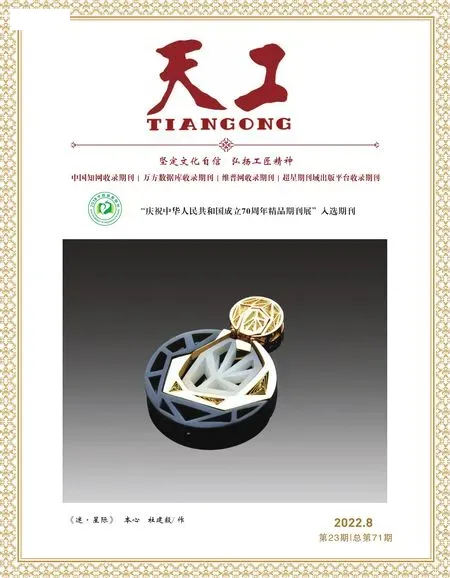明式家具工藝在當代仙游古典家具制作中的傳承發展
陳銘洲
中國古典家具工藝有著悠久的歷史,從先秦時期就獨樹一幟,等到明代開始形成更為獨特的風格,因而被后人稱為明式家具。明式家具有造型優美、簡練素雅,選材考究,制作精細三大特點,是家具文化風格的代表,裝飾精微,雕飾精美,將傳統文化的精氣神體現得淋漓盡致。
一、明式家具的藝術特色:造型優美、簡潔素雅,極具文人美學
明式家具是我國古典家具工藝的一項藝術成就,被世人冠以“東方藝術的一顆明珠”的雅號,在世界家具體系中頗負盛名。明式家具在工藝制作和造型藝術上的成就,也是中國數千年來智慧和人文的杰出代表。明式家具是獨具特色的傳統家具,大體指自明代中葉以來,技藝精湛的能工巧匠所制作的硬木家具,材料以紫檀木、花梨木、酸枝木等居多。
明式家具最早由文人參與設計,極具文人美學,也被稱為文人家具。設計者大多是文化氣息濃郁的明代文人雅士,由他們對家具圖樣進行設計,再由經驗豐富的能工巧匠制作而成。設計家具之時,作為文人的設計者會在設計中融入自己對整個世界的理解以及對人文元素的運用,使家具的造型典雅、沉穩、簡潔,各組件的比例考究,既實用又精美,裝飾雖少但精、雖淡卻雅。
明式家具,乍看之下,毫不起眼,感覺就是普通家具,但細細品味,卻能從中品出獨特的魅力,欣賞、推敲每一處細節,都有獨到的韻味。明式家具好比一杯好茶,剛入口時味道恬淡,再三品嘗則回味無窮。甚至有設計師認為,明式家具是用來觀賞的文物而不是用來使用的器物。
明式硬木家具深受國人喜愛,在全國都有廣泛的生產。但尋其根源,還是以蘇州為中心的長江一帶的江南地區,當地匠工制作的家具得到了文人雅士的認可。因此,蘇州附近制作的家具常被人們稱為“蘇州明式家具”,簡稱“蘇式”。
隨著時間的推移,如今的工匠們更是融匯古今、貫通中外,結合區域特點生產不同特性的作品,除了“蘇作”以外,另有“京作、廣作、仙作”等三種風格,和蘇作一起,撐起當代明式家具的一片天空。
其中,京作家具因為地域因素,明清時期接近權力中樞,對用料比較講究,結構寬宏,氣勢雄渾,裝飾紋樣以上古青銅器紋樣和龍鳳麒麟紋等祥瑞神獸居多,更具有象征意義。
廣作家具,因為珠三角一帶較早接觸西方世界,受西方文化影響較深,它的裝飾紋樣多帶有西方元素,線條分明,棱角干脆,和國內的圓潤中庸不同,裝飾感很強。
仙作家具,是近年來在福建莆田仙游一帶興起的家具制作,有強烈的地域風格,結合古時中原和閩南一帶的特點,款式典雅,結構嚴謹,用料考究。
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中,勤勞智慧的仙游人將代表中國古典家具藝術的“仙作”工藝發揮到極致。福建省仙游縣,歷史上是“海濱鄒魯、文獻名邦”,有濃厚的古典家具藝術傳統。2014年11月,仙游古典家具制作技藝列入第四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名錄擴展項目名錄,2018年還入選第一批國家傳統工藝振興目錄。

圖1 仙游古典家具《四出頭雕龍官帽椅》 陳銘洲/作
仙游古典家具制作技藝,簡稱為“仙作”,產于中國古典工藝家具之都——福建省仙游縣,意取仙人之作,源于唐宋,興于明清,盛于當代,是一個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古老工藝流派,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項目,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征和仙游地方文化特色,成為中國古典家具的代表作之一。“仙作”以其造型簡練、結構嚴謹、裝飾適度、紋理優美而著稱,是傳統國畫藝術、雕刻藝術與家具制作技藝的巧妙融合,是明清家具經典款式的傳承和創新,蘊含著一代代仙游人的文化理念與審美情趣,被譽為“東方藝術家具”。仙作與京作、蘇作、廣作并稱為中國古典家具的“四大流派”。在制作工藝上,仙作家具主要是建立在工藝學和美學兩門基本學科的基礎上,以探討工藝領域審美問題為主。
仙游古典家具的形成與家具的歷史積淀、城市和市鎮的繁榮、私人建筑的興盛、文人的倡導和直接參與有非常密切的關系。明式家具受明代文人的影響更深,文人躬身力行參與設計,無疑增添了明式家具的文人氣韻,而文人更是將前人“守虛靜,順天時”的審美傾向發揮到了極致。
二、仙游古典家具《四出頭雕龍官帽椅》:與時俱進,大膽創新,追求淡雅情趣
筆者身處毓秀靈動的閩地東南——福建省仙游縣,深受當地文化影響,于作品中加入現代思想,融合古人智慧,力求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作品追求化繁為簡,大巧不工,每一刀一筆無不沁入自身的專注與汗水,融匯古今,再創新品。
以筆者設計的《四出頭雕龍官帽椅》(如圖1)為例。四出頭官帽椅是明式家具的最經典器型之一。何謂“四出頭”?是指椅子的靠背搭腦兩端與扶手兩側前端與普通的閉合圓潤造型不同,均采用出頭的形式,合為四個出頭,所以得名。雖然稱為出頭,但卻沒有“出頭”詞語本身帶有的銳氣,令觀者感到柔潤、舒適。何謂官帽?因為搭腦部分出頭,就像是古代官員的帽子,所以稱之為官帽椅。
四出頭官帽椅之美,看似毫不經意,實則皆為匠心獨具,于每一構件中蘊藏有深刻內涵。
首先,看其搭腦,微微翹起,兩端出頭宛若官帽的展腳,神似古代官吏所戴的帽子。藏鋒卻露意,蘊藏“出人頭地”的美好期望。同時,筆者對椅子搭腦的設計也略做修改,映照傳統建筑,參考古建筑中的屋脊大梁。搭腦、屋脊兩者皆位于所處器物的頂端,且舒展的形態極為相似,都是中部略微隆起,兩邊些許回落,到了末梢,又逐漸向上。暗藏人生起落的哲理,卻又不刻意追尋風光大起,猶如儒家中庸思想。四出頭官帽椅的搭腦的向外延伸之勢,與普通座椅的直角收口相比,整體造型更為流暢、委婉,更顯得氣韻生動。
其次,觀其靠背板,形態與其他椅具保持一致。古人講究坐相,通過椅子靠背板與扶手曲線的造型語言來展現坐者的威儀。官帽椅的靠背有“C”形與“ S”形兩種款式,筆者所選為S形曲線,更貼合人體脊柱,讓坐上去之人更為舒適。
大部分官帽椅的靠背裝飾相對簡約,追求自然氣韻,不事雕琢,直接展現木料紋理的天然秀美,也有追求淡雅情趣,只是在上部簡單開光,作一普通云紋或者花鳥。筆者結合古人思想和當代追求,大膽創新,隨著靠背的曲線,雕刻一條五爪金龍。金龍從山川之巔騰飛而起,直沖云霄,身旁云霧繚繞,祥云匯集,爪下一顆龍珠熠熠生輝。金龍雕刻,寓意吉祥如意,幸福安康。同時凹凸感也能帶給坐椅之人以摩擦穴位達到按摩的效果,一舉多得。
觀察兩側扶手,尾端亦出頭,并開口向外,整體造型婉轉自如,就像游龍戲水,又似深巷小道,猶如流水小橋,通體線條流暢,簡直渾然天成。
扶手下方鵝脖、聯幫棍亦微微彎曲,與扶手互相呼應,在弧度上融為一體,更具有自然文韻。 扶手與鵝脖相接之處,筆者亦添加一份角牙,支撐扶手的同時,給椅子增添一點點綴,更具有情趣。
官帽椅的坐面,一般分為兩種,分別是軟屜與硬屜,前者多由藤料精細編織而成,透氣、柔軟、舒適;后者一般采用落堂踩鼓作為面板,支撐性強。
坐面四周,對面框,筆者采用上舒下斂的冰盤沿造法,將硬屜收斂其中,堅固耐用,拋光上蠟,令椅子更加細膩,同時更富有人文觀賞氣息。
椅子四腿和普通椅子的直行站立不同,筆者設計椅腿略帶側腳收分,實用與審美的雙重功用在其中交匯融通,在腿足部位將線條的威嚴與張力表現得淋漓盡致。
兩個椅腿之間或設有“步步高”趕棖,前端最低,兩側略高,后部最高。古時科舉之風盛行,匠人為了迎合學子步步高升的愿望,特地設立此名字。如今雖然時過境遷,但是步步高升的愿望在任何時代都是所有人的愿望之一,既附和古時意境,也接洽當代風貌。同時,趕棖可以讓坐者將腳部置于其上,提高腿部的舒適度。這些部件的設置也是筆者一直追求的滿足世人倚坐的基本需求,皆為以人為本的設計典范。
官帽椅采用軸對稱形式,以正面中心為軸,搭腦、靠背板、扶手、座面、牙子等各個部件均位于同一條軸線上,視覺上擁有平衡感,結構上更是堅定穩固。這種嚴謹、對稱、工整的整體結構,正是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修身養性”和“中和之美”的平衡、和諧。
而在制作過程中,筆者更是不用任何膠水、釘子,僅憑古人創造的榫卯結構相互咬合,就搭建了穩健的椅子結構。少事雕琢,充分顯露木材自然生長所成的俊秀,可以說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不過,官帽椅因為多處構件擯棄常見的直來直去結構,皆采用弧形曲線,不僅在原材料的挑選使用上需要更加費心費力,對所用木材的質地和紋理也有更高的要求,相比于普通座椅,制作工藝難度更大,故而此家具在古時候多為王公貴胄所專享。筆者所作雕龍官帽椅,也是經過多方查找資料后,歷經數月辛勤雕琢才完成的作品。
此官帽椅優雅大氣,既可單獨陳設于書齋之中,與書桌相組合,人倚坐其上,可閱覽古今、揮毫作畫、俯首工作等;亦可成套出現,與茶桌相搭配,以組合的形式放置在大廳明間的左右,用來接待賓客。

圖2 仙游古典家具《知書達理博古架》 陳銘洲/作
三、仙游古典家具《知書達理博古架》:造型簡約,線條流暢
古人追求君君臣臣,相互輔佐,主次分明,詳略得當。廳堂內若面積相對較大,則需要其余家具作分隔,起到畫龍點睛的作用。博古架就是明式家具中具有這項功能的家具之一。
例如筆者設計制作的古典家具《知書達理博古架》(如圖2),為四件五層橫列博古架,造型簡約。四件博古架,兩寬兩瘦,互為補充,相得益彰。左側三層處,設有三個抽屜,充實空間的同時,也具有更好的收納功能。右側兩件,在底層和三層處,筆者設置兩個雙開門柜子,鏤空柵欄設計,隱約可見其中隱藏器物,深得古人“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朦朧感。博古架上通體直線,線條硬朗分明,與古人每日三省吾身、行止端方相對應,故取名曰:知書達理。
四、結語
不論是四出頭官帽椅,還是博古通今的博古架,明式家具在現代生活中越來越受到社會各界人士的喜愛,也借著當代的優秀工藝從王謝堂前進入了尋常百姓家。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對家居生活的追求也越來越高,相信明式家具一定能在未來持續綻放靚麗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