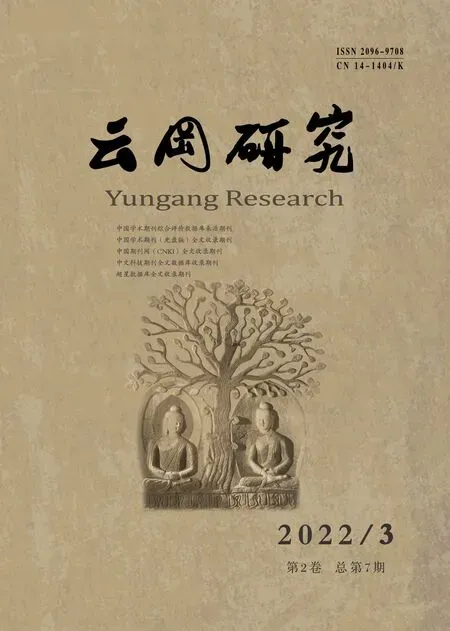均田制與北魏女性經濟地位的構建
苗霖霖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黑龍江哈爾濱 150028)
均田制是北魏孝文帝時期創設的對國內平民進行計口授田的土地制度。該制度自太和九年(485年)孝文帝頒布均田令開始,至唐德宗時期創立兩稅法,徹底廢除均田制為止,前后實行了近300年的時間。作為我國古代社會中最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均田制的創立和實施不僅對北魏王朝,甚至對整個中國歷史的發展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學者對于均田制的關注和研究較多,張金龍先生在《北魏均田制頒發行時間再議》[1]《北魏均田制實施考論》[2]和《北魏均田制研究史》[3]中對均田制的實施狀況進行了分析,認為均田制擴大了北魏的納稅人口數量,防止了土地過度集中,也增加了國家的稅收,筆者同意這一觀點。此外,還應注意到均田制對婦女受田的規定,直接造成了北魏婦女在國家中經濟地位的提升,對后世的婦女社會地位的改善,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筆者試從此角度出發,對均田制女北魏女性經濟地位的影響進行考察,以期能夠對相關研究有所助益。
一、女性授田的創舉
在我國古代社會經濟生活和社會生活中,由于生理原因的制約,使女性在社會生產和生活中無法發揮與男性相同的作用,這也直接造成了女性無法獲取與男性相同的家庭和社會地位。尤其是由于女性無法擁有獨立的經濟收入,使她們不可避免的成為男性的附庸,進而導致她們社會地位的不斷下降。
在農業經濟占據主導地位的古代社會中,男性承擔著主要的生產任務,他們也成為農業生產資料的主要占有者,更成為家庭經濟收入的主要獲取者,女性則由于無法獲得獨立的土地,也就隨之失去了獨立進行生產、生活的資本,根本無法獲得獨立的經濟收入,她們只能被迫依附于男性生存,無法獲得相應的家庭和社會地位。直至西晉時期占田課田制推行后,這一狀況才有所改變。占田課田制:
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4](卷26《食貨志》,P790)
戶調制推行的目的在于增加國家的賦稅收入,但卻是我國古代國家對女性作為獨立的納稅者身份的首次認可,使女性不再依托男性,而是直接與國家建立起聯系。作為戶調制的配合,西晉還通過占田課田制,對女性占有的土地,給予法律層面的認可,進而有助于她們社會地位的提升。只是由于此時處于土地私有制的發展時期,國家無法限制豪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的現象,也就導致占田課田制未能得到很好的貫徹和實施。高敏先生指出:占田不是授田,而是私田。占田課田制中也只是規定了女性可以占有土地的數量,國家卻并未直接給予女性土地,也無法保障女性可以占有足夠數量的土地。[5]可以說,占田制課田制對女性占田和課田的規定只是停留在制度層面,也并未獲得實際的嚴格執行,但該制度卻開了古代國家給予女性土地、征收相應稅賦的先河,仍有著一定的積極意義。西晉占田課田制中對女性占有土地的規定,還被北魏統治者所借鑒,成為北魏均田制對女性授田的先聲。
東晉十六國以來的戰爭,打亂了當時的社會秩序。鮮卑族拓跋部則在此間隙乘勢而起,在北方地區建立起了勢力強大的北魏政權。由于鮮卑族本屬我國古代北方地區的游牧民族,其生活方式多是“隨水草放牧,居無常處。以穹廬為舍,東開向日”。[6](卷90《烏桓傳》,P2979)受此影響,鮮卑族在經濟上也以畜牧和狩獵經濟為主,并無農業耕種的傳統和經驗。在北魏建立后,由于其國內并無系統化的舊制可以因循,北魏統治者便廣泛吸納漢族士人參與國家建設。在他們的極力倡導下,北魏上承魏晉舊制,兼才南朝規范,開啟了對鮮卑族政權的封建化變革,實現了由行國政權向封建王權國家的轉變,為了配合這一轉變,北魏還在經濟領域內推行了富有創新意義的均田制,不僅推動了本國的農業生產發展,也為后世的土地制度變革打下了基礎。
北魏建立初期,北方地區政權林立,國家的重心一度放在了對外開拓疆域、對內鞏固統治,但是由于國家長期進行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在擴展了本國領土的同時,也造成了北魏國內的人口銳減、土地荒蕪。與此同時,國家掌握了大量的無主土地,加之其“時民困饑流散,豪右多有占奪”。[7](卷53《李安世傳》,P1176)為了實現對土地的開墾和耕種,解決土地和人口分離的狀況,北魏建國后也曾嘗試對京都附近地區的居民“各給耕牛,計口授田。”[7](卷110《食貨志》,P2850)但由于此時豪族地主仍然占據大量的土地、隱秘人口,使該制度并未徹底改變國內土地過度集中的狀況,由于土地問題引發的社會矛盾和居民糾紛也層出不窮。
東晉十六國以來,由于戰亂導致普通居民被迫變賣田宅、漂泊異鄉,在國內安定以后,這些離鄉背井的人們也慢慢返回故土,但是由于他們離開故土時間較長,造成土地、房產所屬權認定的困難,加之“年載稍久,鄉老所惑,郡證雖多,莫可取據。”[7](卷53《李安世傳》,P1176)也導致了國內的爭端不斷。有鑒于此,漢臣李安世上書孝文帝,就國內的民間土地歸屬爭議問題,提出了“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7](卷53《李安世傳》,P1176)的主張。他的這一主張不僅快速解決了愈演愈烈的土地爭端,更便于國家對土地進行重新的丈量,為推行均田制打下基礎。
在國家明確了掌握的土地和人口數量以后,孝文帝便開始著手在全國范圍內推行均田制。唐長孺先生指出:均田制的推行,在拓跋族政權看來,乃畿內計口受田等部族舊制的推廣;而在李安世等漢族臣僚看來,卻是對漢代限田以及西晉占田課田制的沿襲。[8](P126)其時,北魏已經實現了皇權的高度集中,有能力也有實力推行新的土地變革。當時北魏朝廷中的真正掌權者是文明太后馮氏,他對于進行土地改革的意志非常堅決,在她的強烈支持下,均田制得以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的開展,均田制計口授田的方式也顧及了鮮卑貴族和漢人世族雙方的既得利益,贏得了他們的支持,但國內不明就里的“百姓咸以為不若循常,豪富并兼者尤弗愿也。”[7](卷110《食貨志》,P2856)因而,均田制最初沒有得到豪族乃至百姓的擁護。但均田令中有關奴婢、耕牛受田的規定,也保證了強宗豪族的利益不會受到過大的侵害,也給予無立錐之地的平民以土地,保證了國家農業的有序開展,因而均田制并沒有遭到劇烈的反對。
二、婦女受田產生的原因
北魏均田制“施行后,計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內安之。”[7](卷110《食貨志》,P2857)均田制授田規定中最具特色的便是明確了對國內婦女的受田的種類和數量。國家通過計口受田的方式給予了女性屬于她們自己的土地,不僅使她們擁有了獨立的生產資料和經濟收入,同時也使她們不再經由男性與才國家建立聯系,而是成為國家的直接納稅人。他們通過繳納賦稅與國家建立起直接的隸屬關系,不僅增加了她們的可支配經濟收入,更在客觀上提升了她們的家庭和社會地位。
北魏均田制中有關婦女受田的規定不是憑空出現的,這種現象的出現與鮮卑族長期以來男女平等的民族歷史和國家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的現實需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從民族歷史上看,北魏是由鮮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權,由于女性在鮮卑族歷史上一直都有著較高的家庭和社會地位。在部落制時代,鮮卑族普遍實行族外婚制,為了保證來自其他部落女性的生命安全,避免因為她們受到的人身傷害,而造成其母家部落的復仇,進而引發部落間戰爭,導致部落被吞并或是部民傷亡,性格悍驁的鮮卑部民,逐漸形成了“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9](卷30《烏桓傳》注引《魏書》,P832)的民族傳統,其部落約法更直接規定“其自殺父兄則無罪”,[6](卷90《烏桓傳》,P2979)這也為鮮卑女性的生命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
北魏建立后,鮮卑傳統習俗在當時社會中的影響仍然十分顯著,主要表現為鮮卑婦女在家庭和社會政治、經濟生活中起到了較為重要的作用,并形成了“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為夫訴屈。”[10](卷1《治家篇》,P48)同時,由于鮮卑女性沒有受到儒家傳統的束縛,根深蒂固的民族傳統對她們的性格和行為也產生了重要影響,鮮卑女性在意識形態中也表現出追求與男子地位平等的心理需求。
從經濟因素上看,鮮卑族男性與女性社會地位的平等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游牧經濟中社會分工的影響。在我國古代的游牧民族中,畜牧經濟在民族中一直占據著主導地位,在畜牧業的生產方式下,男性主要承擔著畜牧、狩獵、作戰等工作,而女性則負責飼養牲畜、制作皮貨,甚至家庭的日常生活也一般由女性進行照料,這也造成了鮮卑婦女既要充當母親、妻子,承擔起家庭的服務性勞動,又是社會性生產活動的重勞動力,參加家庭和社會的物質生產。鮮卑女性在長時間的生活中,將“服務性勞動與生產性勞動集于一身,家務勞動與社會勞動合為一體。”[11]這也造成鮮卑社會中男性與女性在財富創造中趨于等同,相同的社會和家庭貢獻,也為女性擁有與男性相同的家庭和社會地位奠定了基礎。
從社會原因上看,北魏是在十六國時期混戰中新興起的國家。鮮卑族男性大都有著勇武善戰的傳統,在與中原漢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政權的戰爭中,鮮卑領袖屢次率部取勝,不僅擴展了本國的領土和疆域,更掠奪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另一方面,戰爭也造成了東晉十六國以來,北方地區人民受到戰爭的波及而流離失所,甚至出現了大量的“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7](卷53《李安世傳》,P1176)在北魏建立并統一北方后,這些由于戰亂而漂流異鄉者逐漸回歸家鄉。這樣就在北魏國內一方面出現了很多無主的土地,這些荒蕪的土地由國家直接控制,可以直接進行使用和分配;另一方面又有很多無地耕種的農民,他們沒有屬于自己的土地,也就沒有了生存的資本,在無形中對于國家的安定產生了影響。此外,當時國內的豪族家庭更是占據著極多的土地,這也引起了無地貧民的不滿,階級矛盾在國內愈演愈烈。有鑒于此,北魏統治者需要在顧及各方面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通過合理的分配方式,將國家掌握的無主土地合理的分配給無地耕種土地的農民,從而達到“使土不曠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7](卷53《李安世傳》,P1176)這樣既能保證幾近荒蕪的土地能夠得到有效耕種,使國家的農業生產得到有序的開展;又能使無地的貧民有地可耕,保證了他們家庭的生存和繁衍。此外,國家還也可以通過對領取國家土地的流民征收賦稅,擴充國家的財政收入。可謂是一舉而三得。
從政治原因上看,北魏建國后,由于受到鮮卑族傳統的影響,女性有著極強的參政意愿,更多次出現了太后參政或干政現象,無論是道武帝的生母、獻明皇后賀氏,還是太武帝保母、惠太后竇氏,以及文成帝乳母、昭太后常氏,她們都曾或多或少的干預過北魏的朝政。特別是在文成帝逝世后,其皇后馮氏更是在獻文帝、孝文帝兩朝都曾臨朝聽證,將女主政治推向了新的高潮。尤其是在馮太后與孝文帝祖孫二人共同臨朝主政時期,社會中對他們稱以“二圣”,開鑿于這一時期的云岡石窟中的一龕二佛造像,便是“二圣”臨朝社會現狀的直接反映。與此同時,男女平等的思想也在此時北魏社會中盛行。均田制中對婦女授田的規定,正適應了當時的北魏社會中,女性追求與男性平等地位的心理需求。
從思想狀態上看,北魏是鮮卑族建立的封建政權,在進入中原以前,他們一直處于部落制時代,其基層社會組織是邑落,“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9](卷30《烏桓傳》注引《魏書》,P831)由部落大人進行管理。部落大人由全體部民共同選舉產生,當選者不僅要求“有勇健能理決斗訟”,[9](卷30《烏桓傳》注引《魏書》,P831)更要善于“斷法平端,不貪財物”。[9](卷30《烏桓傳》注引《魏書》,P838)部落大人一旦失去了這些特質,出現“性貪淫,斷法不平”[6](卷90《烏桓傳》,P2994)的行為,便會遭到部民的拋棄,甚至有時還會導致邑落的脫離,進而造成整個部落的潰散。集體選舉領袖的體制也直接造成了鮮卑族落制時代中平均主義盛行,這種平均主義思想的影響更一直延續到王權時代。
北魏在建國初期由于外部政權環伺,其國家的重心便放在了開拓疆土和穩定統治上。隨著與中原漢族政權接觸的日益增多,北魏皇帝也注意吸收漢族士人為國家建設服務,并在他們的幫助下逐步完成了國家的封建化進程。
北魏建立前,鮮卑族仍然處于部落體制之下,在國家建立后,他們便隨著國家的封建化變革,迅速進入到了王權社會,不進造成北魏部分制度中留有的部落制時代的印記,無法短時間內徹底磨滅;傳統鮮卑社會中的平均主義思想在此時也仍然還有一定的影響。
在鮮卑傳統的平均主義思想的影響和需要開墾荒地現實需求下,[7](卷110《食貨志》,P2850)為了促進其都平城(今山西大同)的繁盛,北魏建國后便在京畿地區遷入居民十萬余人,“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7](卷110《食貨志》,P2850)北魏的這項政策不僅直接促進了當地的農業生產發展,還對維系當時社會穩定、緩和民族矛盾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此外,“計口授田”也是我國古代歷史上,首次按照家庭人口數量進行的土地分配,也為日后均田制在全國范圍內的推行埋下了伏筆。
此后,北魏皇帝更通過頻繁的對外征戰,吞并了周邊政權,統一了我國北方地區。隨著國家版圖的不斷擴張、人口的不斷增加,北魏不僅掌握了較多的無主荒地,也出現了較多的無立錐之地的流民,這種狀況的長期存在將不僅無益于農業生產的發展,流民的無序移動還會對國內安定存在著隱患。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亟需將流動的人口和無主的土地進行重新組合,以迅速提升國內的農業生產能力,并解決流民的生存問題。受傳統平均主義思想影響的均田制,便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
綜上所述,鮮卑族在建國前過著游牧遷徙的生活,畜牧業在國家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在北魏建立后,國家版圖不斷擴大、土地和人口也日益增加,出于改變鮮卑居民游牧生活習慣和解決流民生存問題的現實需要,需要迅速實現農業生產的復興和發展,此時大量涌入的漢族人口帶來了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解決了鮮卑族不善農耕的困境。在漢族和鮮卑等民族的共同努力下,北魏國內的農業經濟的比重不斷增加,并逐步取代了傳統的畜牧業在國家中的統治地位,成為國家的主要經濟形式。
三、均田制對婦女受田的內容與影響
在北魏統計了國家掌握的無主荒地后,為了安置國內的流民,促進農業生產快速發展,太和九年(485 年),孝文帝采納了漢臣李安世的主張,正式頒布了均田令,并“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還受以生死為斷,勸課農桑,興富民 之本。”[7](卷7 上《孝文紀上》,P156)北魏均田制具體內容包括:
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
諸麻布之土,男夫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依良。
諸有舉戶老小癃殘無授田者,年十一已上及癃者各授以半夫田,年逾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
諸民有新居者,三口給地一畝,以為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7](卷110《食貨志》,P2853-2854)
通過這些記載可知,在均田制之下,北魏男性可以獲得的土地數量為:露田40 畝,麻田10 畝,共計50畝;婦女獲得的土地數量為:露田20 畝、麻田5 畝,共計25畝。
從受田數目上看,北魏對婦女受田的數目只是男性的一半,這種男女授田數目的差異,不僅與漢族家庭中女性地位低于男性、女性需依附男性生存的傳統認知有關,更主要的是考慮到農業生產需要更多的體力,而女性在這方面明顯不如男性,對她們授予與男性相同數量的土地,也無法達到完全耕種、實現土地有效利用的目的。
此外,在對女性的授田中,北魏還特別關注到了守節寡婦這一特殊的群體。守節的寡婦在丈夫去世后,主要承擔起了撫養老人和教育子女的責任,但是由于她們生產能力有限,家庭普遍比較貧困。國家在授田中也對她們給予了特殊的優待,不僅授予守節寡婦與普通婦女相同數目的土地,更減免了她們的稅賦,使她們獲得的土地上所有的收益都成為她們的個人財富,以此增加其家庭的經濟收入,降低經濟負擔,客觀上保障了她們的基本生活質量。
北魏在授田時,為了使流民最大程度的獲得安置,保障他們的日常生活所需,還按照家庭人口的數量,賜予他們建設房屋的土地。均田制中規定:北魏家庭中每三口人可以獲得一畝土地,作為建設房屋的宅基地。國家對宅基地的授田中,并不分區分性別和年齡。也就是說,這些宅基地中不僅有男性的份額,也有女性的份額,這也在客觀上實現了對婦女的居所的保障,避免她們由于家庭內的種種原因而被迫流離失所,不僅保障了家庭結構的穩定,更提升了整個社會的生產力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使國內“百姓殷阜,年登俗樂。鰥寡不聞犬豕之食,煢獨不見牛馬之衣”。[12](卷4《城西》,P178)
北魏均田制對婦女受田的做法,使婦女在家庭中能夠擁有一定數目的個人財產,確保了婦女在經濟領域占有一席之地。在均田制之下,女性獲得的土地來自國家,這些土地作為女性的個人財產,受到了國家的法律保護,不能隨便為他人所侵占。女性在掌握了土地這一重要的生產資源后,通過農業生產獲取收益,用以作為她們的生活資料。她們只需將土地收益中的一部分交給國家,而剩余的部分便可作為她們個人的經濟收入,并可依照個人意愿進行支配。
女性也由此成為國家的直接納稅人,她們無需通過依附男人與國家建立起聯系,而是以租調的形式直接與國家建立起了隸屬關系,其土地的收益扣除續交繳納給國家的稅賦,剩下部分的便是女性的個人收入,這也保證了女性在家庭經濟中的經濟獨立,從而確保了她們家庭地位的穩固,并成為北魏婦女自我意識提升的重要因素。可以說,均田制開了我國封建社會中對婦女受田的先河,是封建國家在夫權社會中承認婦女經濟獨立性的表現。
由于經濟上的獨立,使她們不再完全依附于男人,成為男人的附庸。均田制對女性的授田規定,不僅提升了北魏女性的社會地位,也在客觀上造成女性擁有參與政治的能力和愿望。如果說北魏婦女參與政治、從事社交與當時鮮卑族婦女在意識上要求與男人品等的要求有關。那么,我們也有理由認為,婦女這種平等意識的長期存在也是與北魏時期婦女經濟上的獨立也密不可分。尤其是北魏在前期的對外戰爭中,過多的消耗了國家的物力和財力,為了彌補財政的不足,征收賦稅就成為了此時的當務之急,而對婦女授田則擴大了國家賦稅的征收范圍,有助于國家稅收的增加。因此,均田制對婦女受田規定的創立正是北魏男女平等的社會需求與擴大稅源的客觀要求共同造就的結果。
結語
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4 年)頒布的均田令,標志著均田制開始在北魏施行。均田制歷經整個北朝、隋代,直至唐德宗時期創立兩稅法之后,才被徹底廢除,前后實施了近三百年的時間。作為我國古代重要的土地制度之一,它不僅對北魏王朝本身的農業生產發展,乃至漢化變革都有著重要影響,甚至對整個中國古代歷史的發展、演進都產生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從女性史研究的角度上看,均田制的制定和實施將北魏婦女的社會地位又向上推進了一大步,不僅造就了女性的經濟和人格方面的獨立,更直接提升了她們的持家和參政熱情。也正是因為這種特殊的社會地位和特定的社會背景,北魏數度出現女主臨朝稱制局面。更重要的是,均田制的規定一直延續了整個北朝時代,從而使北朝時期的社會中存在著與當時漢族社會明顯的區別——婦女在社會、家庭生活中地位相對較高,并成為“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10](卷1《治家篇》,P48)的經濟保障。
北朝女性相對較高的家庭和社會地位的影響一直延伸到了唐代,并成為唐代女性普遍擁有較高家庭和社會地位的重要淵源,更成為唐朝女皇臨朝的社會根源之一。可以說,均田制不僅促進了我國古代社會農業的發展,也對古代社會的演進有著同樣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