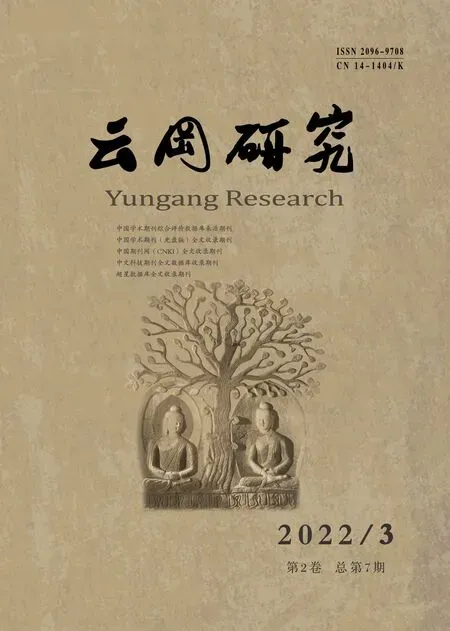《張玄墓志》的美學意蘊及價值
謝千欣,王新利
(1.成都大學美術與設計學院,四川成都 610106;2.新鄉學院商學院,河南新鄉 453003)
魏碑又稱北碑,是廣泛流行于我國南北朝時期北方廣大地域的一種書體。而以北魏時期的作品最典型,最精到,也最能代表這一時期的書風特征。具體而言,魏碑是秦漢隸書與隋唐楷書之間的一種過渡性楷書體系。魏碑通常包括碑碣、墓志銘、摩崖石刻、造像題記等文字刻石形式。由于其書刻精美細膩,用筆方正端嚴,結體古雅多姿,而受到世人的高度關注,同時,它的美學價值與意蘊也逐漸得到發現,并引起世人的極大興趣。筆者不揣淺陋,嘗試以《張玄墓志》為例,透過刀鋒看筆鋒,探討其中的美學意蘊及價值,體味與領悟其背后的藝術魅力。
一、《張玄墓志》產生的時代背景
《張玄墓志》全稱《魏故南陽太守張玄墓志銘》(圖1)。張玄,字黑女,因避清康熙帝玄燁之諱,故該墓志又稱作《張黑女墓志》。此碑刻于北魏后期普泰元平(531 年)年間。碑刻為正書,計20 行,滿行20字,共367 字。此志出土的時間地點未詳,從志文中“葬于蒲坂(今山西永濟)城東原之上”一句推斷,此墓志應在今山西省永濟市境內。原石久佚不存,今僅存清何紹基剪裱舊拓孤本,現藏于上海博物館。

圖1 《張玄墓志》
北魏是鮮卑族建立的少數民族政權。自立國伊始,北魏諸帝王就雅好詩書,崇尚漢文化,注重刻碑勒石以宣揚功業。尤其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年)執政時期更加重視漢文化的推行,北朝文化獲得迅速發展。孝文帝大力倡導民間刻碑紀事,推行厚葬之風,厚葬導致墓志鐫刻風行,當時北魏貴族上層隨葬者多有墓志,一般平民百姓效法刊刻墓志者亦屢見不鮮。特別是孝文帝太和十八年(494 年)遷都洛陽后,魏碑書體的發展更是趨向規范化、精美化。魏碑書風以京城洛陽為中心,不斷蔓延全國各地。僅《魏書》一書中就記載了大量與帝王相關的刻石活動。這些碑文書寫水平高超,刻工精良。一般而言,魏碑書體的發展以遷都洛陽為界限分為前后兩個階段。而《張玄墓志》則是北魏后期魏碑書法藝術的典范之作。值得一提的是,北方游牧民族樸拙粗獷的性格與漢人儒雅尚禮的特征相結合是北碑鮮明藝術風格形成的基礎。或者說,“魏碑”體是鮮卑草原文化和中原農耕文化相互碰撞的產物。由于《張玄墓志》出現于北魏后期,正值南朝書風北漸之時。此時,“魏碑”書體已漸趨成熟,筆法趨向規范化,書風趨于典雅秀美。與北碑初期質樸渾厚、粗獷豪放之風明顯拉開了距離,反映了北碑的最高成就。《張玄墓志》既有北碑的爽朗俊邁,又不乏南帖的婉約含蓄,可謂集南北朝楷書雍容典麗、秀勁挺拔之大成,因而成為后世楷書流美一派之始。清代中晚期,大興碑學之風,受何紹基等人的推動,《張玄墓志》相繼被錄入金石學著作,其拓本問世后即受到眾多文人、書家的推重。取法者日漸增多,與其相關的品評文字也不斷出現。因此,它的誕生為中國書法史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二、《張玄墓志》的書法審美特征
《張玄墓志》的書法審美特征可以從用筆、結構、章法等數方面進行分析。
(一)用筆特征
《張玄墓志》刻工精美,用筆精巧,技法高妙。第一,《張玄墓志》的用筆以方筆為主,圓筆為輔;中鋒為主、側鋒為輔。具體表現為,起筆與捺腳處多以方筆為主,轉折處卻時方時圓。但橫畫多見方起圓收或圓起方收。中鋒筆法以長橫、長豎與長撇、長捺居多,得厚重含蓄之意;側鋒筆法多見于短撇、短橫與方折處,取飄逸妍美之趣。筆鋒藏多露少,藏鋒、露鋒并用使得筆意圓潤含蓄,筆畫豐富多樣,張力表現增強。第二,融入隸書與行書筆意是此墓志用筆最為明顯的特征,也是最大亮點之一。隸書筆意多見于字之撇捺與鉤畫處,如“吏”“太”二字撇畫向左伸展,尾部上翹,略含隸意,古趣盎然。何紹基在《張玄墓志》題跋中有“化篆分入楷,遂爾無種不妙,無妙不臻,然遒厚精古,未有可比肩《玄》者。”[1](P77)可見評價之高。行書筆意的加入使字形增添了些許靈活之趣,規整端莊中富含節奏感。如“其”“然”等字點的寫法,“復”“河”二字偏旁的寫法,“無”字的完全行書寫法,都運用了行書的筆意。第三,《張玄墓志》通過巧用外拓法弱化了轉折處刀斧刻畫的痕跡,這樣每個字給人以既圓融又不失遒勁之感。如“南”“圖”“褐”等字。第四,筆畫處理較為奇崛,如直硬且修長的平捺,顯得剛健、質樸;大弧度的斜鉤,顯得抒情飄逸。為使作品厚重、簡潔與明快,故意增強“點”“提”“短撇”等筆畫的寬肥、短促;為增強作品的奔放、舒展與悠揚,“橫”“撇”“捺”等筆畫非但悠長,而且平直中富有柔緩的弧度。如“茂”“昏”“之”“光”等字即是。第五,“口”框處理十分巧妙,故意打破左右對稱,增強“左豎”下收的幅度,這樣處理筆畫起初給人以怪誕之感,細觀又顯得趣味橫生。
(二)結構特征
《張玄墓志》承接兩晉余緒,結字寬綽有余,字形左右開張,強調橫勢,于灑脫多變中呈現出平衡的自然美感,與鐘元常(繇)古拙相通。正是因為這種動態變化,《張玄墓志》才呈現出飄逸瀟灑的儀態。《張玄墓志》結體的基本格局可以概括為兩點:一是伸展橫向筆畫,收縮縱向筆畫,斜向筆畫或收縮或伸展。其中以橫勢字為主體,縱勢字作為靈活調節。橫勢字力求穩健質樸,縱勢字追求挺拔險峻,如“翼”“義”“貫”“戶”等。這就改變了北碑“斜畫緊結”的慣常體勢,是對隸書“古雅質樸”風格的回歸。或許這是該碑與其他北碑的最大區別。具體地講,《張玄墓志》字形結構的靈活處理主要表現在以下數方面。
第一,《張玄墓志》靈活處理重心位置的高低。重心低的字增加沉穩氣質,如“氣”“祿”等字;重心高的字則更顯挺拔偉岸,如“具”“其”“守”“魚”等字。《張玄墓志》的中宮處理以寬博疏朗為基調,松緊結合,自由靈活,這樣就避免了作品整體上的單調乏味。第二,《張玄墓志》的結構多呈寬博扁方,但為保持整體結構的一致性,有時又會對各個筆畫作相應調整。同時,根據單字情況,或橫勢增強或縱勢夸張,尤其是極橫與極縱之間的處理,往往高低參差、層次分明。縱橫對比既起到章法調節之作用,又顯秀逸峻拔之姿。除此,為避免寬扁的字結構呆板,有時故意使結體上寬下窄,以制造險絕生動的藝術效果。第三,行書筆意既使字形結構活潑靈動,顧盼生姿,也使意境更顯醇厚高古。如“純”字的絞絲旁、“靈”(靈)字的雪字頭、“然”“爲”(為)字的四點底等,部分字還使運用了草書的寫法如“無”(無)字等。第四,《張玄墓志》的結構以風骨內斂,精氣內涵為特征。既有北魏樸茂雄強之勢,又有南帖秀雅溫婉之韻,可謂集輕靈、秀逸、雄健、含蓄數美于一體。第五,疏密處理恰到好處。密處豐滿,疏處空靈。圓轉委婉,顧盼有情。正如清代鄧石如所言:“字畫疏處可以走馬,密處不使透氣,常計白以當黑,奇趣乃出。”[2](P641)
(三)章法特征
《張玄墓志》章法布局橫成行豎成列,字間距大于行間距。疏密變化明顯,行列曠達舒朗,但因字之結構取橫向平勢,字形扁寬,左右開張,因此章法橫勢稍緊,縱勢更顯疏朗。這種承接漢碑的章法使整幅作品顯得空靈蕭散,疏密有致,更顯字之古雅雋秀。這種章法與五代楊凝式《韭花帖》頗為相似。蘇東坡論書云:“大字雄于法密而無間,小字難于寬綽而有余。”此墓志雖為小楷,則顯雄闊疏宕,氣象雍容,氣勢磅礴。值得注意的是,此碑最后幾行“映,瓊玉參差。俱以普泰元年,歲次辛亥,十月丁酉,朔”,錯落有致的章法布局為整篇墓志增加了些許靈動之氣。《張玄墓志》通過收放對比,更凸顯通篇的節奏感與空間感。強烈的行氣使整篇具有連貫性與呼應感。真可謂“星辰麗天,皆有奇致。”[3](P775)
章法與字法是整體與部分的關系。大章法指整幅作品的謀篇布局,小章法指一字之內的點畫安排。《張玄墓志》不受楷書界格限制,錯落有致連綴成篇,通過筆畫粗細、字形大小、姿態奇正、結體長扁變化、結構收放之調節,使作品整體顯得生機勃勃、韻味無窮。因此,與其它北碑相較,《張玄墓志》更透著一股濃郁的文化氣息。
三、《張玄墓志》的價值
(一)和諧的觀念與隸楷技法
一幅作品如不講求變化,則顯得呆板單調,如缺乏統一,則顯得雜亂無章。《張玄墓志》講究方圓結合、剛柔相濟、虛實相生、收放自如等書法觀念即是和諧統一的反映。《張玄墓志》點畫錯落有致,節奏感強,富于韻律美,變化中尋求和諧統一。這與中華傳統文化中陰陽對立統一的美學觀念相一致。正如蔡邕所言:“夫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勢出矣。”[4](P4)
作為北魏的墓志書法,《張玄墓志》既是漢文化“中和”美學觀念的體現,同時也是鮮卑民族崇尚武力美學觀念的體現。《張玄墓志》中方圓兼備、收放自如、渾厚質樸的審美特征是漢文化與鮮卑文化相互激蕩融合的結果。作為北魏墓志中的精品,《張玄墓志》無論是從用筆還是結字均可窺見歷史傳承與南北交融的痕跡,它是南北文化融合在書法風格上的反映,而《張玄墓志》又站在了融合的起點上。其次,經清代何紹基的推廣越發影響深遠,成為后代書家學習研究北魏楷書極好的范本。
《張玄墓志》書刻俱佳,既是隸、楷技法高度融合的典范,也是集北碑俊邁爽朗與南帖含蓄婉約優點于一體的經典之作。康有為評價此墓志:“如駿馬越澗,偏面嬌嘶。”此言極是。《張玄墓志》承繼秦漢書風之余緒,融南北書風為一體而別具一格,既有魏晉小楷的寬綽舒展、古雅大氣,又有唐楷的雄強茂密與渾穆典雅。因此,它開啟隋唐一代書風之先河,并為唐楷的形成奠基。
(二)文獻與書法史價值
《張玄墓志》為后人研究南北朝歷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獻資料。此墓志追述了張玄先祖及張玄本人的任職情況,贊美了其惠及百姓的高雅出眾之品行,并詳述了張玄去世以及與妻子陳氏合葬的時間和地點。為后人了解墓主人的家族狀況、個人身世及當時的社會背景等均具有一定的歷史意義。
《張玄墓志》書刻于北魏末期,此時正值魏碑書體的成熟期,是當之無愧的魏楷精品。它是北方游牧民族樸拙粗獷的性格與漢文化含蓄深邃特點相融合的產物,書法藝術風格極其鮮明。從作品中充滿隸意的筆法中可以窺見北碑初期的雄健古樸漸向南方圓潤遒麗變化之軌跡。有人甚至把它稱之為書中“蘭亭”是不無道理的。《張玄墓志》代表北魏墓志書法的最高成就,在中國書法史上留下了燦爛輝煌的一頁。
(三)藝術價值
作為北魏墓志中的精品,《張玄墓志》本身蘊含極高的美學價值與欣賞價值。通常情況下,魏碑楷書點畫多為方起方收,棱角分明,書法審美角度單一。而《張玄墓志》卻破方為圓,以方為主,或左方右圓或外方內圓,審美含量增加。章法關系不斷得到調整,和諧中求生動,多變中求統一。雖單個筆畫或單個字獨立存在,但精神契合,血脈相通。為追求美的藝術效果,此碑在各個構成方面總是做到匠心獨運,因此取得了辯證統一、豐富而和諧的整體效果與美學高度。
《張玄墓志》的文學藝術價值也不容忽視。它敘事真切,文筆精煉,是一篇難得的文學珍品。
結語
《張玄墓志》自清代被發現以來,一直受到學界的推崇。康有為說:“凡魏碑,隨取一家,皆足成體。盡合諸家,則為具美。”特別是《張玄墓志》“厚、奇、峻、樸”的穩健古雅之風不但給清代書學者帶來了新的視覺體驗,而且為清末書壇注入了一股新的生機與活力。它進一步豐富了魏碑的美學元素,開創了書法美學的新境界與審美新趣味,為后人提供了更多可取的藝術精華,其高情閑雅的美學情趣也給人以回味無窮的境地。啟功先生主張學習魏碑應“透過刀鋒看筆鋒。”意即魏碑學習者要將刻石還原成鐫刻前的墨跡書丹效果,用心體會書寫者的狀態,才能發現其用筆真諦。自然美是藝術家追尋的目標,追求道法自然是學書的終極境界,《張玄墓志》天真爛漫、珠圓玉潤而又清新雋永的特征正是值得后人取法的精髓,也給后人留下了諸多尚待探索的審美空間。從美學角度看,傾向風格多變是現代書壇追求的審美目標,而《張玄墓志》正好與這一審美要求相契合。同時,《張玄墓志》力去蒼勁渾厚、古拙樸茂,追求精美古雅、婉約含蓄面貌之改革精神,為后人的魏碑書法創作提供了更為寬闊的思路與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