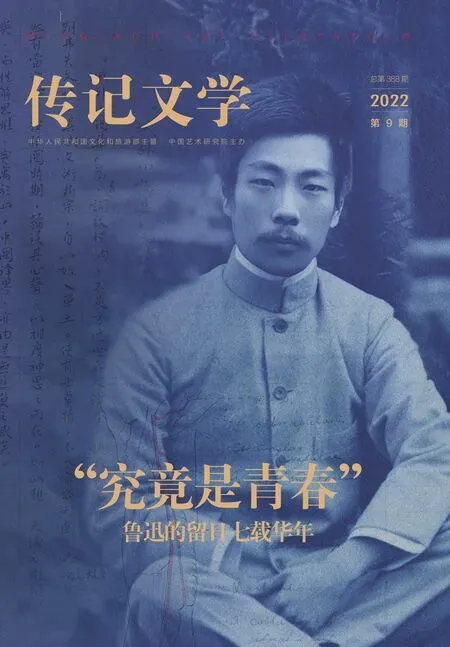“透光的裂縫”:現代文人自傳中的成長教育書寫
——以沈從文、胡適為例
黃紅春
20世紀30年代,中國文壇出現《廬隱自傳》《巴金自傳》《欽文自傳》等自傳作品,形成前所未有的文人自傳熱。當然,古代也有文人自傳,如司馬遷的《史記·太史公自序》、陸羽的《陸文學自傳》等,但數量少,且多缺乏獨立意識觀照下的思想性格的變化發展書寫。現代文人自傳熱是在知識分子遭遇文化取舍矛盾和自我認同焦慮,需要重新審視自己、建構自己的背景下,由胡適等人的提倡和現代出版業的推動所致。胡適動筆寫《四十自述》時,還勸梁啟超、林長民、陳獨秀、蔡元培等人寫自傳,原因之一是他“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二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現代出版機制在30年代也逐漸完善,書籍出版、報刊連載等多種渠道有利于文人自傳的面世。1934年,上海第一出版社推出“自傳叢書”,《從文自傳》就是其中的一部。此外,《宇宙風》《人間世》等雜志也熱衷于刊載文人自傳。胡適的《四十自述》最初刊登在《新月》月刊上,1933年由亞東圖書館出版單行本。沈從文和胡適的自傳雖然都不是寫完整的一生,卻充分反映了他們如何成長、如何培養將來寫作或者做研究的素養。從現代成長教育理念來看,不良的成長環境、不科學的教育手段和不健康的教育目的等,皆不利于一個人的成長。現代文人自傳如果從成長教育視角來看,最有價值的地方就在于它展示了本來也是很普通的人,甚至是不幸的人,卻因為能夠化解不幸、超越不幸而走向成功,而對這種轉化和超越的展示,筆者稱之為“透光的裂縫”書寫。目前學界對于現代文人自傳已經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尚未見專門研究這種“透光的裂縫”書寫。因此,本文以沈從文和胡適的自傳為例,對此展開研究。
一本“大書”以認識自然和社會
逃學曠課在學校教育中是一種病理現象。逃學的原因雖然很多,但歸結起來,不外乎三種:一是學校的過失,課堂教育本身枯燥無味,沒有吸引力,或者學校管理不科學不人性化,讓學生無法接受;二是社會的引誘,校園外的世界豐富多彩卻也誘惑叢生,如吃喝玩樂,尤其一個“玩”字就可以讓人沉迷其中,不思進取;三是家庭的影響,如遇父母離異或者親人故去等突發事件,或者家庭氣氛不和諧、父母教育方法不得當等,孩子因此精神萎靡,失去上進心。健康的成長教育本該防止逃學現象發生,如果防止不了發生了,它就是教育的“裂縫”,也是成長的“裂縫”。
作家沈從文少年時逃學,而且不止一兩次,幾乎常態化。《從文自傳》不僅沒有回避這一點,反而用了很多筆墨來書寫,發人深思。導致少年沈從文逃學主要是學校(那時上的是私塾)的原因,他用了兩個詞來形容學校的情形:一個是“虐待”,一個是“頑固”。他說:“凡是私塾中給予小孩子的虐待,我照樣也得到了一分。”很快,他跟從幾個較大的學生,“學會了頑劣孩子抵抗頑固塾師的方法,逃避那些書本去同一切自然相親近”。這說明老師對學生沒有親和力,不懂得教育方法,教的內容也簡單乏味。老師讓學生死記硬背那些奧古難懂的經書,還動不動就體罰學生,嚴重缺乏所謂引導性教育和個性化教育。魯迅在自傳性散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里也反映了類似的問題,比如,他本來很想弄清楚“怪哉”一蟲是怎么回事,便求教于私塾里的先生,哪知道先生除了一句“不知道”,“似乎很不高興,臉上還有怒色了”。這“怒”從何來,其答案反映了老師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態度。學生畢竟是孩子,見老師一怒,感覺莫名其妙還十分害怕,求知欲立馬減弱,下次再也不敢隨便請教了。健康的教學當貫徹以教師為主導、以學生為主體的教學理念,引導、啟發、激勵學生,而不是打擊和壓抑學生,如《禮記·學記》所謂“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少年魯迅離開百草園去上學,感覺不是獎賞,而是責罰:“我不知道為什么家里的人要將我送進書塾里去了,而且還是全城中稱為最嚴厲的書塾。也許是因為拔何首烏毀了泥墻罷,也許是因為將磚頭拋到間壁的梁家去了罷,也許是因為站在石井欄上跳了下來罷……”暗示了他對書塾教育的不滿。胡適則在自傳里回憶他上私塾時,老師上課一般不“講書”,學生不懂得書中講的是什么,結果學無興趣,常常“賴學”。賴學即逃課,逃課的人被捉回來,“總得挨一頓毒打”。
缺乏溫情與耐心的教學態度,沒有生動有趣的教學內容,少年沈從文盡管遭遇了這樣的教育“裂縫”,卻能在“裂縫”中尋找“光明”。他逃離枯燥乏味的課堂,去到一個更大的世界觀察生活,學習知識。那時的他和眾多少年一樣,叛逆心強,而且被蔥蘢生長的好奇心牽引著,喜歡新鮮有趣的事物。他說:“我的心總得為一種新鮮聲音、新鮮顏色、新鮮氣味而跳。”他偷偷地跟著張表哥下河洗澡,在洗澡時凝視清波,感受水性,居然得了水的啟發。這啟發還深刻影響了他日后的創作。他喜歡寫水,水樣的女子、水樣的溫情,人離不開水,水載幸福,也含憂愁。如其小說《邊城》里,翠翠水樣靈氣而柔順;翠翠和爺爺生活在水邊,靠擺渡為生;翠翠的母親為愛情投水自殺;翠翠的爺爺去世后河水猛漲;大佬天寶因為得不到翠翠而傷心,出排時意外淹死水中;翠翠喜歡的二佬儺送從水里走來又順著水遠走,等等。回顧少年生活,沈從文說:“一派清波給予我的影響實在不小。”“我認識美,學會思索,水對我有極大的關系。”除了認識大自然,他還去坊間觀察,在針鋪、傘鋪、剃頭鋪、染坊、豆腐坊、皮鞋店等地方溜達,琢磨諸如為何騾子推磨時得把眼睛遮上、刀要等燒紅時在水里一淬方能堅硬、雕佛像的會把木頭雕成人形,所貼的金那么薄又用什么方法做成等古怪的問題。他說:“我就喜歡看那些東西,一面看一面明白了許多事情。”無論傳統教育還是現代教育,都不鼓勵逃學,也不應該鼓勵,但如果真逃學了而沒有去做損人害己的事情,還能虔誠地向自然和社會學習,培養觀察力和想象力,這便成了一件變害為利的事情。
少年沈從文在逃學中“學會了用自己眼睛看世界一切”,看見了平常書本上所看不到的山水美、人情美和人性美,培養了對家鄉的感情,積累了小說創作素材,更塑造了影響他一生的品性。正如他自己所言:“二十年后我‘不安于當前事務,卻傾心于現世光色,對于一切成例與觀念皆十分懷疑,卻常常為人生遠景而凝眸’,這分性格的形成,便應當溯源于小時在私塾中的逃學習慣。”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其逃學不過是闖進了另一個課堂,讀另一本書,即他所謂的“大書”。這本“大書”是校園外的自然和社會。后來轉學進了新式小學,上了許多課,他仍然放不下這本“大書”。《從文自傳》獨特的價值,就在于對這本“大書”的肯定。沈從文這種觀點與陶行知的“社會是大的學校”的教育思想有共通之處,可我們的成長教育常常忽略這本“大書”,只重視課堂上那本小書,不僅造成書本知識和現實生活脫節、知大于行的缺陷,還束縛了人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然而,好的教育需要留白,需要“跑野馬”,給學生時間和空間去分辨自然的美丑,去懂得人間的是非。
直面現實社會,悟人生窺世情
陶行知說:“壞的社會,我們也要認識,也要有所準備,才能生出抵抗力,否則一入社會,便現出手慌足亂的情狀來。”殺人若隨處可見,那也是壞的社會表征之一。從科學的成長教育來看,不管出于什么原因的殺人都是血腥的、暴力的,參與或者目睹殺人,均不利于身心健康。沈從文出身軍人家庭,自己又曾側身行伍,《從文自傳》多處寫他親眼看到殺人的慘狀,這不能不說是他少年生活的不幸,更是成長教育的“裂縫”,幸而他能思考,還從中獲得了對生命和社會的認識。
例如,《辛亥革命的一課》講述了湘西辛亥暴動,沈從文的父親和表哥等人均參加了“殺仗”,小小年紀的他起初以為殺仗是好看的熱鬧,等殺完了看到道尹衙門口平地上、鹿角上、轅門上滿是一大堆骯臟血污的人頭和一串串被割下來的耳朵,他這才明白這種“熱鬧”是要人命的。這要命的事情讓他惶惑不解:“為什么他們被砍,砍他們的人又為什么?”他拿這些疑問去請教參與殺人的父親,可父親只說那是“造反”,并不能給他一個明確的、令人滿意的答復。革命失敗后,政府到處搜捕革命黨員,但是到底誰是革命黨呢?城防軍派兵下鄉捉“造反”的人,捉到就放北門河灘上殺戮,“每天必殺一百左右”,其中有不少是為了充人頭數而被捉去的普通農民。
沈從文寫殺人的筆調冷靜客觀,但字里行間透露了他的思想態度,比如,他用了“胡胡涂涂”“無辜”這樣的詞語來形容被殺的人,像“被殺的差不多全從鄉下捉來,胡胡涂涂不知道是些什么事”,“但革命印象在我記憶中不能忘記的,卻只是關于殺戮那幾千無辜農民的幾幅顏色鮮明的圖畫”,體現了他對無辜被殺農民的深切同情。同時,他用了“愚蠢”一詞來形容這種殺人行為,如“這愚蠢的殺戮繼續了約一個月”,反映了他對于殺人行為的憤怒。殺戮看多了,少年沈從文表面波瀾不驚,內心卻如刀子刻印,開始思考生命、感悟人生。因為被捉的無辜的人太多,只好選擇性地殺,選擇的辦法是委托本地人所敬信的天王,把犯人牽到天王廟,在神前擲竹筊,一仰一覆的順筊和雙仰的陽筊被開釋,雙覆的陰筊則被殺頭。“生死取決于一擲,應死的自己向左走去,該活的自己向右走去。”他親眼看到那些被開釋的人嚇得不敢睜開眼睛,那些必須死又還惦念家中的人則無比頹喪,那些表情讓他永生難忘。他說:“我剛好知道‘人生’時,我知道的原來就是這些事情。”什么是“人生”,沈從文沒有展開說,但是這生和死的問題已經觸及人生的要義,卑微的人沒有生死的自由,他們走過這個世界,不過就像被擲的竹筊,只是一個偶然。
同時,在殺戮背后,少年沈從文也窺見了復雜的世情。比如,在《清鄉所見》里,他所在的隊伍沿路每到一個寨堡,就享受那堡中有錢地主的蒸鵝、肥臘肉的款待,他們要殺的犯人,也多數由各鄉區團總地主送來,當他們走過山中小路時,受到的卻是當地人無數冷槍的襲擊。可見,部隊與當地有錢有權階級勾結,無錢無勢的百姓才是清鄉的對象。當地人殺死他們部隊兵三個,他們就殺死當地人近兩千。老實的鄉下人被用繩子縛來過堂問罪,“無力繳納捐款,或仇家鄉紳方面已花了些錢運動必需殺頭的,就隨隨便便列上一款罪案,一到相當時日,牽出市外砍掉”。同樣可悲的還有那些看客,“人殺過后,大家欣賞一會兒,或用腳踢那死尸兩下,踹踹他的肚子,仿佛做完了一件正經工作,有別的事情的,便散開做事去了”。看客們那種欣賞的態度反映了國民素質低下,分不清是非,沒有人道主義同情心,更談不上對生命的尊重。沈從文雖然在敘述中不動聲色,就像魯迅在《示眾》《阿Q正傳》等小說里用白描的手法寫看客一樣,字里行間卻透露出對看客麻木不仁的批判和諷刺。
當然,除了悲憫和批判,面對殺人,面對他人的死亡,少年沈從文也有感動和欽佩的時候。比如,在他們部隊執行清鄉任務的東鄉榆樹灣,他看到兩個鄉下人因仇決斗,卻遵循著古風習俗,用同一分量同一形色的刀互砍,直到一人躺下為止。這種決斗法讓他感覺決斗的人不但是勇敢的,而且很講公平。還有一個打豆腐的年輕男子,因為奸尸被正法。臨刑前他不但不害怕死,而且還兀自沉浸在美好的回憶中,這男子被人罵為“瘋子”“癲子”,可在沈從文眼里,他愛得癡狂、率性,有獨特的個性。所以,他寫道:“我記得這個微笑,十余年來在我印象中還異常明朗。”這種印象也許潛在地影響了他的愛情觀和創作,因為他后來在小說里塑造了不少任情率性的人,尤其是為了愛情可以不顧生死或者不惜逾越道德規范的人。比如《媚金、豹子與那羊》里,男女雙方都為愛而自殺,其中媚金以死來證明自己對豹子的愛,豹子亦以死來證明自己并不曾失信于媚金;而《一個多情水手與一個多情婦人》里,吊腳樓的妓女和水手相愛,雖然不甚合乎文明世界的禮儀風化,卻愛得真誠、率性。
總之,少年沈從文親眼看見反動的當權者濫殺無辜、草菅人命,地方軍閥借清鄉剿匪之名敲詐百姓,搜刮錢財,當權者之間互相傾軋,為排除異己而不惜展開爭斗和屠殺等種種亂象,看見人性的惡、世情的惡。這種遭遇對于任何一個孩子的成長心理都是有百害而無一益的,因為從心理學來看,它有可能對孩子的言行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使之模仿暴力行為,或者它可能讓孩子對生命和社會的認識發生偏差,建立錯誤的價值觀。所幸的是少年沈從文善于思考且心性溫厚,所以,他反而從這些成長的“裂縫”中,獲得了對生命的感悟和對世情的認識。
因服從與感恩而發奮讀書
現代教育強調“以人為本”,培養孩子“為自己而讀書”的自覺意識和獨立意識。為自己讀書并不排斥有家國情懷,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讀書修身,增長才干,方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實現人生價值。但如果把讀書的目的完全放在為國家、為家庭上而忽略讀書者自身的主體性,就難以激發求知欲,不利于發揮讀書者的主觀能動性。
例如,胡適作為現代著名學者,其當年的成長教育卻并不健全和科學。他還沒有進學校不識得讀書的滋味更不懂得謀劃未來的時候,就已經被父親指定了將來必走讀書這條路。他三歲時父親去世,臨終前父親留話,說他天資聰明,應該令他讀書。于是,胡適的母親遵了遺囑,全心全意督促他學習,竭其所能供他上學。同時,她自己也認為胡適應該走讀書成才的道路,她是胡適父親第三次婚姻的妻子,只生了胡適一個孩子,前任的孩子多,有的孩子年紀比她還大。丈夫去世后,年輕的她要在那個大家庭里安身立命,除了自己待人做事要通達,還要能管教好她親生的孩子。未必每一個母親都指望著享受兒子的榮華富貴,但望子成龍的心理是普遍的、必有的。因此,胡適的母親在管教他時超乎尋常地嚴格。回憶九年的家鄉教育,胡適說每天天剛亮,母親就把他叫醒,然后對他說前一天他做錯了什么事說錯了什么話,要他認錯,督他用功讀書。他犯錯時,她從不在別人面前打罵他,只用嚴厲的目光看他。犯的事小,她會留到第二天清晨來教訓他;犯的事大,她就在當天晚上關門休息時,重重地責罰他,包括罰跪或者擰他的肉。她總提醒他要向已故的父親學習,“不要跌他的股”,意即不要給他父親丟臉。可見,少年胡適成長教育的出發點,不是以他自身為主體,要將他培養成一個健全的人,而是以父母的期望為主體,要讓他為父母爭氣、爭光。拿今天的話來說,少年胡適的未來不是由自己做主,而是由父母來“包辦”。被早早限定了未來發展的方向,他的生活因此非常單調,性格氣質自然也受影響。正如他自己所說:“小時不曾養成活潑游戲的習慣,無論在什么地方,我總是文縐縐地。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兒童愛玩的、活潑的天性被壓抑,除了讀書,其他的興趣、愛好全被看做非正道而被限制發展,這顯然是極為不健康的成長教育。“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游戲的生活。”“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這些話細讀來讓人心疼,因為它反映了胡適的成長教育有道很深的“裂縫”,但人們往往以胡適最后成才成名的結果來忽略它,由此也忽略了胡適如何從這些“裂縫”中找尋光明。
少年胡適雖然處在“裂縫”中,但他沒有叛逆,沒有逃學,反而從母親的言行中看出她的良苦用心,懂得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的原因。所以,即便有時遭到母親嚴重的體罰,他也會默默地承受。他不僅不反感讀書,而且在這方面有所鉆研和發現,使得學業日益精進。首先,他發現了“講書”的好處,講書是讓人知其所以然,認一個字、讀一篇文章,不解其意,是難以記住和發生興趣的。進學堂前,他已經認得近千個字,每個字經父母的講解,他都知其意。進了學堂,母親比別人多給先生幾倍的學金,為的是讓先生單獨給他講書,讓他學得通透。后來,他自己將看過的小說變成故事,講給本家姊妹聽。這樣的講書,不單鍛煉口才,還提高了理解能力和寫作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說:“這樣的講書,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譯成績溪土話,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十四歲來上海開始作古文時,就能做很像樣的文字了。”其次,他發現讀書要會看注釋,注釋中別有天地。當時他有同學看《幼學瓊林》,讓他教認上面的生字,他便也借了該書來看。他最愛看的是書中的小注,“因為注文中有許多神話和故事,比《四書》《五經》有趣味多了”。還有,他善于抓住自己學習中的興趣點,由此順藤摸瓜,擴大閱讀面,獲得更多的知識。比如,有一天他在叔父的廢紙箱里發現了一本《水滸傳》殘本,站在箱子邊一口氣讀完后,馬上尋思它前面寫什么、后面寫什么。他跑遍全村,終于得到全本,并因為讀了這本《水滸傳》,而迷上了小說,之后他讀盡他們村和鄰村所知的小說。那些小說均是用白話或口語寫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勝的趣味。它們教他懂得人生的復雜性,也讓他逐漸掌握了可以作為一件文藝工具的“白話”,這也使他若干年后能成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之一。
少年胡適服從父母的旨意發奮讀書,在讀書中善于思考,摸索出做學問的方法,也得到讀小說的樂趣。同時,他學會體諒母親的難處,從其威嚴中讀出慈愛,剛強中讀出溫柔。比如,有一次母親責罰他時,他哭著用手揉眼睛,導致感染細菌,久治未愈。她又悔又急,為了治療眼翳,她竟用舌頭舔他的病眼。他明白她的愛心,因此稱之為“嚴師”和“慈母”。回憶過往,他充滿感恩之情,說:“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深刻的影響。”“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這也是胡適成長的非凡之處,在知識和做人方面都超越局限獲得升華。
結語
1900年,梁啟超寫下《少年中國說》,疾呼“少年強則國強”。青少年是國家的未來民族的希望,青少年的成長教育直接關系到國民素質。當下,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對人才的需要不只是知識的占有者,更要有高素質的勞動者,尤其是專業性強的創造性人才。這便需要改變傳統理念和方法,建構讓青少年健康發展的新的成長教育。沈從文和胡適的自傳盡管是20世紀現代中國知識分子成長的自我書寫,但反映了成長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并在世情教育、生命教育和情感教育等方面提供了個人突圍經驗。今天的教育條件、教育理念總體上有了很大的改進,但如何將觀念和理論落到實處見成效,需要廣借鑒深反思,現代文人自傳中的成長書寫是很好的一面鏡子。
注釋:
[1][2]胡適:《四十自述·自序》,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第7頁。
[3][4][9][10][11][12][13][16][17][18][19][20][21][22][23][24][25]沈從文:《從文自傳》,《沈從文全集》第13卷,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50—251頁,第251頁,第253頁,第252頁,第256頁,第251頁,第253頁,第269頁,第270頁,第270頁,第272頁,第270頁,第270—271頁,第271頁,第303頁,第304頁,第305頁。
[5][7]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林非主編:《魯迅著作全編》第1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564頁,第563頁。
[6]楊天宇: 《禮記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575頁。
[8][27][28][29][30][31][32]胡適:《四十自述·九年的家鄉教育》,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頁,第36頁,第34頁,第35頁,第34頁,第30頁,第39頁。
[14]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1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15頁。
[15]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06頁。
[26]孟子:《離婁上》,柳俊林、李樹永主編:《孟子》,重慶出版社2014年版,第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