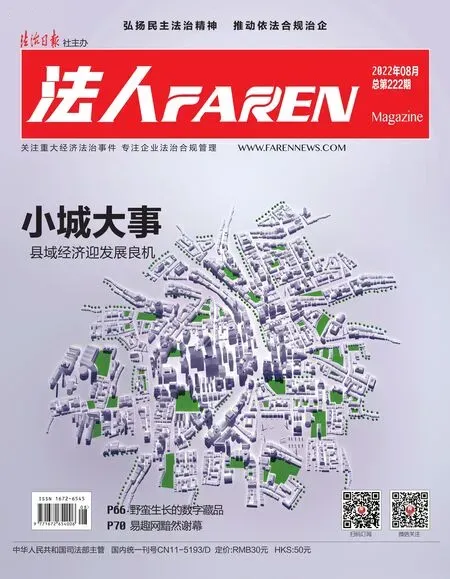縣域經濟加速奔跑
◎ 文 《法人》全媒體記者 李遼
2021年,縣域經濟獲得突破性發展,“百強縣”以占全國不到2%的土地和7%的人口,創造了中國9.94%的GDP。同時,越來越多的縣市GDP突破千億,“千億縣”梯隊已增至43個。
縣域經濟頭部,“百強縣”“千億縣”蒸蒸日上,但更多的縣域則顯得默默無聞。工信部“賽迪顧問”發布的2021年“百強縣”名單中,東部地區占65席,中部地區占22席,西部和東北地區僅分別占10席和3席。同時,全國有近11個省(區、市)的縣域無緣“百強”。
如今,縣域經濟迎來發展良機,但前路風險與光明并存,在新的發展格局下,縣域經濟該如何走上一條適宜的發展之路?

擁有“八閩首邑”之稱的閩侯縣,是中國縣域經濟百強縣,及第一批沿海開放縣
國家政治經濟的“穩定器”
在中國,縣域以縣城為中心,以鄉鎮為紐帶,以廣大農村為腹地,是解決城鄉二元問題的落腳點,是國家政治經濟的“穩定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群的發展吸引了更多目光。一些觀點認為,發展縣域經濟并不“經濟”,其投資收益與大城市相差甚遠。然而,不及城市經濟光鮮亮麗的縣域經濟,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縣域面積廣、人口多、經濟體量大,在中國的滲透程度比大都市更為深入。根據國家發改委宏觀院國土所國土經濟研究室主任黃征學的研究,2019年全國縣市(含自治縣、縣級市、旗、自治旗)總面積853萬平方公里,縣域GDP總量接近全國40%。第七次人口普查顯示,全國縣市常住人口總數約為7.48億人。因此,當提到縣域時,更多的是關注中國1869個縣域單位、占全國土地面積88%的區域和占全國人口總數52.8%的人群的生存現狀。
甘肅省委省政府專家顧問團顧問、蘭州財經大學原校長蔡文浩長期致力于區域經濟的研究,他在8月4日接受《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中國一直重視縣域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是‘兩條腿’走路,一是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按照規模經濟、產業鏈的思路,朝著現代化、工業化、產業集聚和城市間協作方向發展;二是縣域按照特色經濟、現代農業的思路發展。”
2021年,縣域經濟踏上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趕考”之路。8月4日,黃征學在接收《法人》記者采訪時表示,如今,縣域經濟成為推動鄉村振興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重要動力,是國家高質量發展的支撐。
根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021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為2 . 5:1,有所縮小,但仍存在一定差距。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縮小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收入差距,扎實推進共同富裕。
僅僅就鄉村解決鄉村問題難度較大,而縣域作為城鄉緩沖帶,擔負著銜接二者鴻溝的重任。用縣域經濟的發展帶動鄉村經濟發展是可行性路徑。蔡文浩稱,“通過發展縣域,一方面從供給側改革增加農產品供給;另一方面,待縣域經濟發展成熟后,涵蓋的7億多人口是市場的消費主體,未來將釋放巨大消費潛力,有助于內循環構建。”
值得一提的是,縣域經濟對構建外循環同樣重要。“小商品之都”浙江義烏、“世界鞋都”福建晉江、“眼鏡之都”江蘇丹陽、“酒店用品之都”江蘇杭集、“紐扣之都”浙江永嘉等已與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密不可分,潛移默化中扼住了全球細分領域的咽喉。
中國縣域尤其是在經濟欠發達地區,農業集中度高、產業集中度低,更偏向于鄉村化。黃征學介紹,2021年在1866個縣市中,產糧大縣和重點生態縣占比較大,分別為1039個和819個。對此,他表示,糧食安全是“國之大者”,發展縣域經濟,有助于維護國家的糧食安全和生態安全,與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到的“兩個安全”緊密吻合。
同時,作為中國城鎮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縣城近日迎來了中央文件的支持。中辦和國辦印發了《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為不同類型的縣城提供了新型城鎮化的發展轉型方向。

CFP
縣域產業顯露“代差”
“百強縣”“千億縣”創造了巨大的經濟價值,終歸只是上千縣城中的少數。中國縣域的情況千差萬別。人口最多的縣域江蘇昆山與人口最少的縣域西藏自治區札達縣,人口數量相差約260倍;江蘇縣域的平均人口規模最大,為97.1萬人,西藏縣域的平均人口規模最小,僅3.7萬人,而很多邊境縣域,人口則不到1萬人。
蔡文浩以他熟悉的甘肅地區為例:“甘肅省面積為45萬平方公里,相當于兩個英國的面積。但人口只有2400萬,是英國的1/3。該省人口分布極其不均,主要分布在黃河以東地區,而黃河以西的酒泉雖擁有17萬平方公里的面積,人口卻不足200萬。”
在一些縣域,不少農村成為“空心村”,僅剩“老弱小”。黃征學與其團隊做過測算,中國68%的縣域呈現出人口凈流出的狀態。而缺少人的要素會造成縣域經濟發展的三大困難。蔡文浩認為,首先是經濟協作沒法形成,其次是公共財政投入成本高,最后是難以形成具備一定規模的消費市場。
縣域經濟發展呈現出離散性。“‘千億縣’不論是城鎮規模還是特色產業,均邁入良性循環軌道,昆山和江陰甚至以一縣之域超過寧夏、青海、西藏的GDP。但從區域分布來看,‘百強縣’‘千億縣’中,除資源大縣外,大多集聚在城市群和都市圈范圍內,而原國家級貧困縣基本集中在省際交界地區,人口規模偏小,產業結構相對單一,經濟發展動力不足。”黃征學說。
2019年,GDP總量在100億元以下的縣市占比超過四成,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低于10億元的縣市接近六成。盡管過去10年,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呈現增長趨勢,但不同縣域間的“財力”差異也在拉大。與2011年相比,2020年東中西部地區縣域GDP都獲得了正向增長,但東北地區縣域的GDP卻下降了0.4萬億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2011年相比減少了3.7%。
黃征學團隊曾對1866個縣市的金融機構的存貸款做了測算比較,結果顯示,全國60%的縣域存款大于貸款,“這意味著很多資金流到了大城市。”缺乏資金,產業技術得不到改進,產品不能升級,企業缺乏研發能力,使這些縣域的產業層次較低。
此外,產業布局也已顯露出“代差”。當昆山、江陰等頭部縣域上市公司云集、高端制造業廣泛布局時,一些偏遠縣域還在依賴石油、煤炭等自然資源發展經濟。同時,黃征學提到,縣城與城市間的數字鴻溝正在拉大,“如今很多大城市、中心城市在大力發展數字經濟,很多偏遠縣域卻對數字經濟了解不夠”。
在現有的縣域單位中,原國家級貧困縣占了近五成,其中多數是革命老區、重點生態功能區和產糧大縣。“這些縣肩負著維護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的重任,但由于經濟發展滯后,保護和發展的矛盾相對突出。”黃征學說。
發揮比較優勢找出路
中國幅員遼闊,歷史、文化、地理條件、交通狀況、生活習慣不盡相同。縣域經濟的發展模式,也不能一刀切,應該因地制宜,發揮比較優勢,尋找最適合自己的道路。
今年兩會,中央提出要形成同市場需求相適應、同資源環境承載力相匹配的現代農業生產結構和區域布局,宜糧則糧、宜經則經、宜牧則牧、宜漁則漁、宜林則林,為縣域經濟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黃征學表示,縱觀“百強縣”“千億縣”的發展,除少數資源型地區外,均在市場融合、產業融合、人口融合等方面下足功夫,形成了較為鮮明的發展模式。
部分縣域的發展屬于城市輻射帶動型,憑借毗鄰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優勢,形成專業化配套或專業化服務,如山東萊州發展汽車零部件產業融入山東半島汽車產業集群;一些縣市距離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較遠,通過創造市場,推動貿工聯動,實現“買全國、賣全國”,這是市場加工互動型,以浙江義烏和江蘇江陰為代表;外資外貿推動型縣域則集中在沿海地區,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經濟發展,江蘇昆山和福建晉江是典型代表;農產品主產區的部分縣市,依托農業資源優勢,推動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以“中國蔬菜之鄉”山東壽光為代表,屬于農副產品加工型;陜西神木和內蒙古準格爾是礦產資源開發型的代表,圍繞資源開發,完善產業鏈條;還有部分重點生態功能縣,如浙江桐鄉以旅游文化為突破口,推進縣域經濟綠色轉型發展。
黃征學提到,部分縣域之所以“不經濟”,主要是人口規模和市場規模“不經濟”,因此,“融合”至關重要。“如果縣域地處大型城市群,應該主動融入,借勢發展,積極推動便捷交通圈、高效經濟圈、美麗生活圈建設。”
內地縣域離大城市和超大城市較遠,則需要加強縣之間的合作,打破固有邊界。黃征學曾到重慶、貴州、湖南、湖北4個省份交界的幾個縣域考察,這些地區資源特色不明顯、產業規模較小,單獨一個縣要想向上延伸任何產業鏈都很難。但各縣統一規劃,加強合作,分別將生豬養殖、黃牛養殖、牲畜屠宰和飼料加工作為主要發展方向,抱團形成產業鏈,實現了規模經濟。
重點生態功能縣和產糧大縣可采取與社會整體發展相協調的步調。黃征學說:“這些縣大多為人口凈流出縣,應該按照‘內聚外遷’的思路,鼓勵人口向縣城和經濟大鎮集中,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加快發展‘紅、綠、古’三色文化旅游產業,重點規劃對環境和生態較為友好的生物醫藥和大數據產業,發展綠色生態有機農業。”他表示,還可以加快推進碳排放權、碳匯交易等,將資源直接轉化為資產。
針對西部偏遠地區,蔡文浩認為,首先要解決人口集聚問題,將人們搬遷到水資源豐富、自然承載力較強的地方。他介紹,在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過程中,甘肅很多扶貧項目也正是通過易地搬遷來實現:“一旦某地出現了自然災害,原有家園被毀,就不在原地重建,而是把這些人搬遷到蘭州新區,國家給予補貼。同樣,有些地方自然條件惡劣,不適宜人類生存,也可采用易地搬遷的辦法。另外,甘肅酒泉一帶人口較少,則需要把多民族融合在一起,和睦相處,帶動民族地區的經濟發展。”
其次則是村村通。蔡文浩說,通過改善基礎設施如道路、電信網絡來解決交通和貿易的問題。“過去,由于交通不便,缺少消費人群,甘肅的核桃產能過剩,當地老百姓用核桃油點燈,將核桃皮當柴燒。如今交通和電信條件改善后,身處大山深處的老百姓與外界開始有了交流,既輸出了物品,又輸入了觀念。”
縣域經濟是當今中國新發展格局網絡上的重要節點。黃征學認為,發展縣域經濟,應與自身資源稟賦相協調,與社會整體發展相協調。其無窮價值,將隨著中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持續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