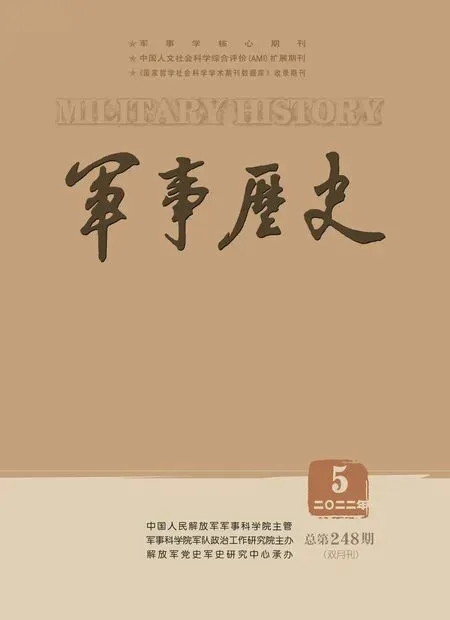《紹興辛巳親征詔》的形成及其后世意義
★ 黃昌付
學界關涉《紹興辛巳親征詔》(以下簡稱《親征詔》)的研究較少,主要集中于討論《親征詔》的作者及其抵抗完顏亮南侵的作用。如,李菁認為《親征詔》作者是洪邁;楊青燁認為《親征詔》由陳康伯所草,《親征詔》在紹興末年抵抗金軍侵略中發揮著振奮人心、提升士氣的作用;楊高崴亦是如此。①李菁:《〈紹興辛巳親征詔〉作者考》,《湖北社會科學》2015 年第8 期;楊青燁:《陳康伯與南宋前期政局研究》,西北師范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7 年;楊高崴:《陳康伯〈親征詔草〉與紹興辛巳宋金大戰》,《江西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 年第5 期。曾棗莊、陳琳主編的《全宋文》(2006 年出版)對《親征詔》歸屬問題未作考辨,將《親征詔》歸于洪邁的同時,又歸于陳康伯。②[宋]洪邁:《親征詔》,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21 冊,卷4911,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年,第339 頁;[宋]陳康伯:《親征詔草》,《全宋文》第188 冊,卷4142,第227 頁。曾棗莊與吳洪澤合著《宋代文學編年史》(2010 年出版),將《親征詔》作者斷為洪邁。③曾棗莊、吳洪澤:《宋代文學編年史》第3 卷,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 年,第1646 頁。這一轉變說明史學界對《親征詔》的作者問題有了進一步認識。為研究《親征詔》的演變,本文擬將《陳文正公集》④[宋]陳康伯:《陳文正公集》卷2《紹興辛巳親征詔草》,《續修四庫全書》第131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324 頁。《建炎以來系年要錄》⑤[宋]李心傳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93,紹興三十一年十月庚子,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第3747 頁。(以下簡稱《要錄》)和《全宋文》所載《親征詔》的內容進行對比,提出一些新的認識。
一、《陳文正公集》《要錄》《全宋文》所載《紹興辛巳親征詔》內容比較
《親征詔》作為南宋應對金海陵王完顏亮南侵頒布的詔書,它的內容很大程度上是號召全民皆兵同仇敵愾地應對金兵。《陳文正公集》《要錄》《全宋文》記載的《親征詔》內容有細微差別,透過這些差別,不僅可以發現《陳文正公集》中《親征詔》的作偽情況,還能體會出其強烈的恢復國是的主張。現將《全宋文》中《親征詔》引述如下:
朕履運中微,遭家多難。八陵廢祀,可勝懷土之悲?二帝蒙塵,莫贖終天之痛。皇族尚淪于沙漠,神京猶污于腥膻。銜恨荷窮,待時而動。未免屈身而事小,庶期通好以弭兵。屬戎虜之無厭,曾信盟之弗顧。怙其篡奪之惡,濟以貪殘之兇。流毒徧于華夷,視民幾于草芥。赤地千里,謂殘暴而無傷;蒼天九重,以高明為可侮。頃因賀使,公肆嫚言。指求將相之臣,坐索淮漢之壤。吠堯之犬,謂秦無人。朕姑務于含容,彼尚飾其奸詐。嘯厥丑類,驅吾善良。妖氛寖及于中原,烽火遂交于近甸。皆朕威不足以震疊,德不足以綏懷。負爾萬邦,于今三紀。撫心自悼,流涕無從。方將躬縞素以啟行,率貔貅而薄伐。取細柳勞軍之制,考澶淵卻敵之規。詔旨未頒,歡聲四起。歲星臨于吳分,冀成淝水之勛;斗士倍于晉師,當決韓原之勝。尚賴股肱爪牙之士,文武大小之臣,戮力一心,捐軀報國,共雪侵凌之恥,各肩恢復之圖。播告邇遐,明知朕意。①[宋]洪邁:《親征詔》,曾棗莊、劉琳主編:《全宋文》第221 冊,卷4911,第339 頁。
詔書表達了南宋政府動員全國人民上下一心,共同對抗金兵侵略的強大決心,但與《陳文正公集》中詔書的內容對比后,不難發現《陳文正公集》中的詔書比《要錄》《全宋文》中詔書表達對痛失北方之地的惋惜之情更加強烈。現以《陳文正公集》《要錄》等書所載詔書的內容與之進行對比,制表如下:
《陳文正公集》與《要錄》《全宋文》記載《親征詔》的內容基本相同,但細致比對后,卻能發現三者在修辭手法等方面有明顯不同,并可證明《陳文正公集》的《親征詔》乃是后人篡改所為。理由如下:
序號1 中的“抷土”和“懷土”與序號3 中的“荷窮”和“何窮”兩處的差異,應是版本流傳所致;序號6、7、8、9 的差異并不能引起文本含義的差異,亦屬版本流傳所致。
由序號2 中“裂”與“污”二字相比來看,后者的修辭手法較前者更加突出,但前者平白的直述卻強烈地表達了對痛失開封故地的憤恨和恢復舊疆的強烈意向。另外序號5 中的“不”改成“弗”,說明《全宋文》《要錄》的《親征詔》比《陳文正公集》的《親征詔》修辭性更強,更加符合四六駢文的官方詔書體例,這也說明陳氏后人有篡改《親征詔》,繼而坐實為陳康伯所撰的現象。雖然序號10 中記載表明《全宋文》《陳文正公集》的修辭均不如《要錄》,但也不排除陳氏后人作偽的存在。要知道洪邁的《親征詔》和《要錄》中《親征詔》的成書,均早于陳氏后人在自家發現《親征詔》的時間,洪邁的《親征詔》成書于紹興三十一年(1161),而陳氏后人自言于慶元六年(1200)于家中發現此稿:“(陳康伯)受命摛詞,人莫得聞,公亦未嘗一語告于家,迄今四十年,始得遺稿于中表何氏。”①[宋]陳康伯:《陳文正公集》卷13《讀親征詔草跋》,《續修四庫全書》第1317 冊,第371 頁。實際上清代編纂《四庫全書》時,便有人認為《陳文正公集》中存在大量偽作:“末大于本,殊非體例,且遺文亦多偽作。”②[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卷174《集部·別集類存目·陳文恭公集》,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第1540 頁。
序號11 中,《陳文正公集》為“詔旨一頒,歡聲四起”,而《要錄》《全宋文》均為“詔旨未頒,歡聲四起”,可以看出二者之間有明顯的時間差距。前者由于詔旨沒有頒布,所以希望頒布詔旨,達到民心振奮的效果,才有“詔旨一頒,歡聲四起”的書寫,亦或是后人回憶當時詔書頒布后的情形;而“詔旨未頒,歡聲四起”,則顯然是對詔旨頒布前民心已悅的表述。因此,陳版詔書雖然在修辭等方面下足功夫,但在時間的設置上卻存在疑點。序號12 的對比也可說明此點,“朕以正月十五日親臨軍前,撫勞士卒,播告中外,咸使聞之”是表達皇帝親征的愿望,而“播告邇遐,明知朕意”則對皇帝親征的愿望完全沒有表達,只是表達皇帝希望全國上下,君臣一心,共雪靖康之恥。雖然《宋史》載,紹興三十一年(1161)九月,“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朝臣有遣家豫避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入浙,且下令臨安諸城門扃鐍率遲常時,人恃以安”③《宋史》卷385《陳康伯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第11809 頁。,此時陳康伯可能已經下定讓皇帝御駕親征的決心,但到是年十月丁巳,高宗才正式決定親征:“丁巳,得報王權果敗歸,中外大震……存中言:‘虜空國遠來,已犯淮甸,此正賢智馳騖不足之時。臣愿率先將士,北首死敵。’上喜,遂定親征之議。”④[宋]李心傳撰,胡坤點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93,紹興三十一年十月丁巳,第3763 頁。而官方詔書早已于決定親征之前頒布,⑤《宋史》卷32《高宗本紀九》:“冬十月庚子朔,詔將親征。……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同宰執議于內殿,陳康伯贊帝定議親征。”何來“詔旨一頒,歡聲四起”?
綜合來看,《陳文正公集》中《親征詔草》應為陳康伯后人改作,內容中飽含恢復舊疆的意向,這點可從慶元、嘉泰之際士大夫為其所作題跋看出。如嘉泰四年(1204),辛棄疾題跋曰:“使此詔出于紹興之初,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于隆興之后,可以卒不世之大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⑥[宋]辛棄疾著,辛更儒箋注:《辛棄疾集編年箋注》卷5《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北京:中華書局,2015 年,第446 ~447 頁。另外,陳氏后人為將《親征詔》坐實為陳康伯所撰,他們相繼請何澹、陸游、葉適等人題跋。⑦李菁:《〈紹興辛巳親征詔〉作者考》,《湖北社會科學》2015 年第8 期。而這一舉動,應與慶元、嘉泰時期的政治背景有密切關系。
二、慶元黨禁的弛解與韓侂胄的困境
(一)慶元黨禁弛解的困境。慶元(1195—1200)黨禁,以紹熙五年(1194)趙汝愚等人廢光宗、擁立寧宗的內禪為導火線。⑧沈松勤:《南宋文人與黨爭》,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113 頁。道學人士與反道學人士開啟了長達數年的黨爭,最終反道學人士占據朝廷主要職位。但到慶元末期,反道學人士對黨爭有了較為清醒的認識。嘉泰二年(1202),“言者論近歲習偽之徒唱為攻偽之說,今陰陽已分,真偽已別,人之趨向已定,望播告中外,專事忠恪”⑨[宋]佚名編,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7,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124 頁。,就連黨禁的發動者韓侂胄,也開始認識到必須弛解黨禁:“一時善類悉罹黨禍,雖本侂胄意,而謀實始京鏜。逮鏜死,侂胄亦稍厭前事,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后恐不免報復之禍。侂胄以為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后復官。偽黨之禁寖解。”①《宋史》卷474《韓侂胄傳》,第13774 頁。此時,反道學人士已經出現弛解黨禁的跡象,但道學人士中還是存在對反道學人士的抨擊,甚至有對弛解黨禁的質疑。如,呂祖泰將矛頭直指韓侂胄,上疏曰:“愿陛下亟誅侂胄及蘇師旦、周筠,而罷逐陳自強之徒。故大臣在者,獨周必大可用,宜以代其任,不然事將不測。”②[宋]佚名編,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6,第104 頁。另外,恢復周必大等人官職一事,也沒能得到這些人的積極回應,或未見回復,或以疾請辭。“嘉泰元年,有以布衣上書及公(周必大)姓名者,言者論公,降一官,次年復少傅”③[宋]周必大撰,王蓉貴、[日]白井順點校:《周必大全集·附錄》卷3《行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7 年,第1928 頁。,卻未見到周本人的任何回復;陳傅良于“嘉泰二年,敘復元官,再畀祠祿,遂除泉州。以病力辭,除集英殿修撰”④[宋]樓鑰:《樓鑰集》卷101《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杭州:杭州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1761 頁。;王藺則“起帥閫,易鎮蜀,皆不就”⑤《宋史》卷386《王藺傳》,第11854 頁。。因此,恢復受黨禁牽連士人的職官進行得并不順利。要想打開弛解黨禁的困境,還需從其他方面努力,消弭與道學人士的矛盾。
(二)韓侂胄的困境與恢復國是。同時,韓侂胄欲完成從外戚擅權向宰相執政的轉變,亦面臨困境。慶元六年(1200),韓皇后去世,韓侂胄的勢力大為削弱。他出任平章軍國事一事,沒能得到其集團核心成員謝深甫的支持。他若想順利總攬朝政,只有通過不斷制造輿論,為其北伐做足準備,這樣才能完成從外戚擅權向宰相執政的轉變。⑥李超:《南宋寧宗朝前期政治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第222 頁。
淳熙時期,孝宗將內政治理作為主要施政方向,但遭到部分士大夫的質疑。淳熙十年(1183),李燾言:“前兩入朝,適虞允文暨趙雄當路,士大夫爭談兵……前日紛紛,今日默默,俱非自治。”⑦[宋]周必大撰,王蓉貴、[日]白井順點校:《周必大全集》卷66《敷文閣學士李文簡公燾神道碑》,第618 頁。淳熙十一年(1184),羅點上疏言:“臣聞虛誕之風勝……陛下初載,急于事功,小人乘時,以才自進。久之,皆以虛誕,紛然擾敗,圣意厭之。由是韜晦斂縮,日趨偷惰頹靡之域,其失等爾。臣愿陛下復振起之。”⑧[宋]袁燮:《絜齋集》卷12《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崇仁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累贈太保羅公行狀》,《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57 冊,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 年,第156 頁。但是這種恢復國是的聲潮,并沒有幫助他們進行北伐。孝宗禪位后,國是基本圍繞緩解孝宗與光宗的關系。寧宗施政前期基本圍繞黨禁,這種恢復國是的主張基本沒有立足之地。也許韓侂胄正是看中這一點,遂開始在恢復國是上做文章。黨禁結束后,恢復國是的主張逐漸抬頭,“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于是恢復之議興”⑨《宋史》卷474《韓侂胄傳》,第13774 頁。。韓侂胄的北伐盡管帶有個人目的,但更主要是受孝宗朝以來盛行的恢復國是主張影響的結果。⑩參見吳雪濤:《略論辛棄疾的一樁公案——兼及韓侂胄與開禧北伐》,《河北師范大學學報》1982 年第1 期,第34 頁;張維玲:《從南宋中期反近習政爭看道學型士大夫對“恢復”態度的轉變(1163—1207)》,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碩士學位論文,2009 年,第121 頁。
韓侂胄為北伐做了一些準備工作。嘉泰四年(1204),以張嗣古為賀金主生辰正使,“入敵中,因伺虛實”?[宋]葉紹翁撰,沈錫麟、馮惠民點校:《四朝聞見錄·乙集·開禧兵端》,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第87 頁。;同年九月,“鄧友龍使金,有賂驛吏夜半求見者,具言虜為韃之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宋]羅大經撰,王瑞來點校:《鶴林玉露·甲編》卷4《鄧友龍使虜》,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第62 頁。。然而,其北伐主張并未得到大多數朝臣的支持。嘉泰三年,金人在邊境囤積糧草,韓侂胄認為這是金人的挑釁行為,遂在人事任用上進行調整,但一些士大夫以各種理由推辭:“時武帥鄭挺在襄陽,邊釁開,懼不能任,力求去……于是文臣無肯行者,遂以李奕為荊、鄂副都統制兼知襄陽……時東老父喪未免,力辭,改命廣帥薛象先侍郎,而象先不行,留提舉祐神觀,遂命宇文挺臣侍郎代之。辟置參機,皆非常制。”①[宋]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9《嘉泰開邊事始》,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第651 ~652 頁。于是,韓侂胄不得不在其他途徑上為北伐制造輿論,以求獲得更多的支持。
三、陳本《紹興辛巳親征詔》的作用
慶元黨禁的弛解得不到道學士人的信任,而韓侂胄力圖通過北伐實現其從外戚擅權向宰相執政的轉變。因此調和與道學人士之間的矛盾,成了一項重要任務,而能完成這項重任的非陳景思莫屬。
(一)陳景思與道學人士的關系。幫助韓侂胄解決恢復國是的困境,號召更多的士大夫參與進來,需要一個不僅與韓侂胄關系密切,而且與其他人士保持親密聯系的人物。慶元、嘉泰之際,韓侂胄集團核心成員主要有何澹、謝深甫等人。黨禁期間,何澹上疏抨擊道學曰:“專門之學,流而為偽。愿風厲學者,專師孔、孟,不得自相標榜。”②《宋史》卷394《何澹傳》,第12026 頁。謝深甫雖曾力贊朱熹關于宗廟之事,“宗廟重事,未宜遽革。朱熹考訂有據,宜從熹議”③《宋史》卷394《謝深甫傳》,第12040 頁。,但他與道學人士的關系亦不融洽。
陳景思,字思誠,“故相康伯之孫也,與侂胄有姻連”④《宋史》卷429《朱熹傳》,第12768 頁。,并與道學人士保持著往來,并向朱熹請教,朱答其關于治世之道的提問時曰:“但其所為者,要當真實有用力處;所不為者,要當深自省察。”⑤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59《答陳思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2842 頁。葉適居于錢塘期間,與陳曾多有學問的討論:“余客錢塘,不擇晨暮過,疑難填臆。至其舍,論辯從橫,僮御必旰食而返。”⑥[宋]葉適:《葉適集·水心文集》卷18《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侍郞陳公墓志銘》,北京:中華書局,1961 年,第360 頁。因此,陳景思可在道學人士和反道學人士之間充當調解、緩和雙方矛盾的重要角色。“時攻偽日峻……先生每為所親正說不忌。與文公書,具言其無他。”⑦[清]黃宗羲撰,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49《侍郎陳先生景思》,北京:中華書局,1986 年,第1590 頁。朱熹則回答陳景思:“其然其然!韓丈于我本無怨惡,我于韓丈亦何嫌猜乎!”⑧[宋]葉適:《葉適集·水心文集》卷18《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侍郞陳公墓志銘》,第360 頁。反道學人士攻擊朱熹時,陳景思“勸侂胄勿為已甚,侂胄意亦漸悔”⑨《宋史》卷429《朱熹傳》,第12768 頁。。因此,陳景思在慶元黨禁時期起到緩解雙方矛盾的重要作用。葉適稱贊道:“道學不遂廢,思誠力最多。”⑩[宋]葉適:《葉適集·水心文集》卷18《朝請大夫主管沖佑觀煥章侍郞陳公墓志銘》,第360 頁。當陳景思拿出草詔后,“一時王公大人爭相是正”?[宋]陳康伯:《陳文正公集》卷13《讀親征草詔跋》,《續修四庫全書》第1317 冊,第371 頁。,這其中就有葉適、辛棄疾等人。
(二)后人題跋意向與仕宦晉升。《親征詔》的頒布是為了提升士氣、安定民心,希望全國上下與皇帝同心同德,共同抵抗金兵南下。但通過后人為改寫后的《親征詔》所作的題跋,可以發現其中所蘊含的強烈的北伐愿望。
慶元六年(1200),何澹為《親征詔》題跋,作為韓侂胄一派的核心成員,何的題跋無外乎證明草詔作者是陳康伯。?[宋]陳康伯:《陳文正公集》卷8《讀親征草詔跋》,《續修四庫全書》第1317 冊,第352 頁。而同年謝深甫的題跋則傳達出不尋常的意味:“中興以來咫尺之書,為攘夷狄立華夏者多矣,惟親征之詔垂四十余年,凡稍有知識者,皆尚能傳誦,而聞思舊言之入人深,未有若是者,端由思陵恢復之志,窹寐弗忘。”①[宋]陳康伯:《陳文正公集》卷8《讀親征草詔跋》,《續修四庫全書》第1317 冊,第352 頁。這明顯是在為韓侂胄恢復國是造聲勢,并影響到葉適與辛棄疾等人。葉適步入仕途后,潛心將有關為國之論合在一起,希望達到尊華攘夷的目的。他于嘉泰三年(1203)的題跋中寫道:“適從士大夫之后,竊聞為國者之論合之。上規殷周,下軼漢唐,復仇、正名、尊華賤夷,本末宏大,未易名舉。”②[宋]陳康伯:《陳文正公集》卷8《讀親征草詔跋》,《續修四庫全書》第1317 冊,第353 頁。將他多年的心愿和盤托出。嘉泰四年(1204)辛棄疾的題跋,認為此草詔可建不世之功勛,但草詔與金人仍俱在,不禁發出悲憤之音(見前文所棄語)。
在這份草詔恢復國是的號召下,一些士大夫成為韓侂胄北伐的支持者。③李超:《南宋寧宗朝前期政治研究》,第211 頁。嘉泰三年(1203),就在為草詔題跋的后一月,葉適“除權兵部侍郞”④《宋史》卷434《葉適傳》,第12892 頁。,建議韓侂胄“先擇瀕淮沿漢數十州郡,牢作家計”⑤[清]黃宗羲撰,陳金生、梁運華點校:《宋元學案》卷54《忠定葉水心先生適》,第1739 頁。;同年,辛棄疾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使,第二年,“言夷狄必亂必亡,愿付之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之計”⑥[宋]李心傳撰,徐規點校:《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18《丙寅淮漢蜀口用兵事目》,第825 頁。,韓侂胄聞之大喜,很快召之入朝。北伐失敗,韓侂胄伏誅,中丞雷孝友彈劾葉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⑦《宋史》卷434《葉適傳》,第12894 頁。;辛棄疾亦受到牽連,嘉定元年(1208),“攝給事中倪思劾稼軒迎合開邊,請追削爵秩,奪從官恤典”⑧鄧廣銘:《辛棄疾傳·辛稼軒年譜》,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年,第271 頁。。
可以看出,紹興三十一年(1161)《親征詔》經過陳氏后人的改寫和宣傳,其意向已悄然由軍民一心抵抗金人侵略轉變為收復北方失地的愿望,獲得了辛棄疾、葉適等人的歡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韓侂胄與部分道學人士之間的矛盾,同時也為韓侂胄的北伐助長了聲勢。伴隨著黨禁進一步的弛解,韓的北伐主張進一步獲得道學人士支持,這些長期遭受黨禁的道學人士“或憤于久郁,樂于乍伸,輒動其彈冠經世之念,則其思猶未熟也。復仇,開下之大義也”⑨[宋]佚名編,汝企和點校:《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卷7,第125 頁。。由此,雙方有了共同的目標。
結語
《紹興辛巳親征詔》在紹興三十一年(1161)由洪邁撰寫,它鼓舞了南宋軍民,從而一舉抵御了完顏亮的南侵。但在嘉泰年間,由于陳景思與韓侂胄的特殊關系,《親征詔》再次出世,作者也由洪邁變成了陳康伯,且內容上則顯得更具對金人的仇恨。《親征詔》重現后,獲得了辛棄疾等人的青睞,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韓侂胄與道學人士的矛盾,為韓侂胄發動北伐戰爭做了一定的動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