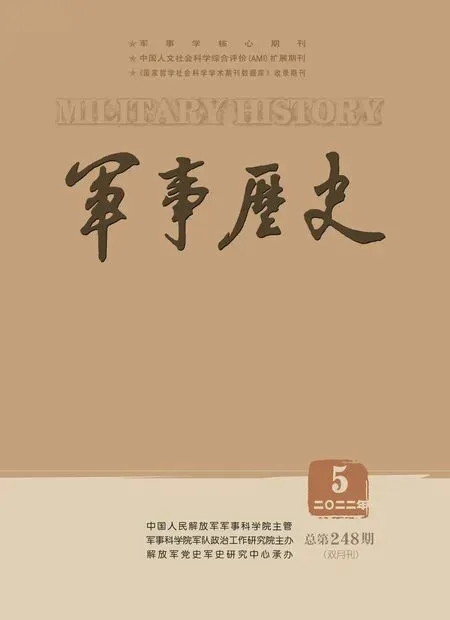論陜北三戰三捷的戰略意義
★ 徐 艷
解放戰爭時期,為粉碎國民黨軍對陜北的重點進攻,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部隊在極端劣勢的條件下,于1947 年3 月25 日至5 月4 日,在延安東北地區相繼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戰役的勝利,合稱陜北三戰三捷,共殲滅國民黨軍胡宗南集團1.4 萬余人,挫敗了其速戰速決的戰略企圖,穩定了陜北戰局,奠定了西北戰場內線防御作戰的勝利基礎,也有力配合了全國各解放區戰場的作戰,在全國解放戰爭史上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一、勝利揭開西北戰場成為解放戰爭重要主戰場之一的序幕
從1946 年6 月至1947 年2 月,在解放戰爭前8 個月的作戰中,相較于其他解放區戰場,西北戰場無論從作戰規模、作戰頻次上看,都略顯沉寂。其主要原因在于:政治上,內戰雖然已經全面爆發,但國共關系并未完全破裂,國民黨當局仍在表面上維持著繼續國共和談的假象,以應對國際國內的反對聲浪。在此期間,如貿然對中共中央所在的陜甘寧邊區進行大規模軍事進攻,需要冒極大政治風險;軍事上,陜甘寧地區山地、溝壑縱橫,交通不便,對國民黨軍來說,不利于其機械化半機械化兵團機動,也難以充分發揮其重型武器多的優勢;經濟上,土地貧瘠,物產不豐,難以就地以戰養戰,后勤物資嚴重依賴長途運輸,難以支持大兵團持久作戰。據統計,從1945 年9 月抗日戰爭勝利到1947 年2 月,陜甘寧邊區人民解放軍連同民兵、游擊隊作戰250 余次,殲滅國民黨軍1 萬余人,爭取起義5000 余人。①參見《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戰史》編委會編:《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第3 ~4 頁。由此也能看出,這一時期國民黨軍雖在陜甘寧邊區周邊屯駐重兵,但其軍事行動主要是小規模的襲擾作戰。情況到1947 年初發生了變化。此時,政治上國民黨召開了偽國大,制訂了偽憲法,驅逐中國共產黨和談代表,宣布國共關系已經破裂;軍事上經過解放戰爭前8 個月的作戰,國民黨軍雖然占領解放區105 座城市,但總兵力損失了71 萬人。由于占領區擴大,戰線延長,又不得不以重兵來守護交通線和要點城市,這樣,盡管其進攻解放區的總兵力不斷增加,但能用于第一線的機動兵力反而由1946 年10 月最高峰時的117 個旅銳減到85 個旅,其機動兵力不足和戰線過長這一矛盾日益突出。在此情況下,國民黨軍不得不放棄全面進攻,改取重點進攻,在晉冀魯豫、晉察冀、東北等戰場轉取守勢,集中主力重點進攻陜北、山東兩解放區,企圖在消滅這兩區的人民解放軍后,再轉兵其他戰場。
與此相應,在陜甘寧邊區及周邊的晉綏解放區,人民解放軍野戰部隊的規模一直比較小。1945 年8 月,晉綏軍區成立了晉綏野戰軍,下轄第358 旅及獨立第1、第2、第3 旅。1946 年7 月,為遂行晉北戰役,晉綏軍區成立晉北野戰軍指揮部,統一指揮晉綏和晉察冀兩軍區在晉北的部隊。9 月,從中原解放區突圍的第359 旅回到陜甘寧邊區,轉隸晉綏軍區建制。11 月,為應對國民黨軍對陜甘寧邊區可能發動的進攻,中央軍委決定撤銷晉綏野戰軍、晉北野戰軍番號,將部隊統一整編為晉綏軍區第1、第2、第3 縱隊,并將第1 縱隊調駐陜甘寧邊區。1947 年2 月,根據國民黨軍準備向陜甘寧解放區發動重點進攻的局勢,中央軍委決定將晉綏軍區第1 縱隊和陜甘寧邊區部隊新編第4 旅、教導旅、警備第1 旅、警備第3 旅,組成陜甘寧野戰集團軍,張宗遜任司令員,習仲勛任政治委員。3 月13 日,國民黨軍向陜北發動重點進攻后,中央軍委除組織部隊于延安以南進行陣地防御,阻擊國民黨軍進攻外,從全國戰局著眼,決心主動放棄延安,同時將胡宗南集團牽制在陜甘寧并大量消滅其有生力量,以利其他戰區的作戰。為加強陜北戰場的作戰指揮,16 日,中央軍委決定,以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總參謀長彭德懷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統一指揮所有駐陜甘寧解放區的野戰部隊和地方武裝,即西北野戰部隊(又稱西北野戰兵團),下轄第1 縱隊、第2 縱隊(3 月17 日由晉入陜)、教導旅、新編第4 旅等部共2.6 萬余人,擔負保衛陜甘寧解放區的任務。19日,西北野戰部隊勝利完成掩護中共中央機關、人民解放軍總部安全轉移的任務后,主動撤離延安。3 月25 日至5 月4 日,西北野戰部隊取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給胡宗南集團以沉重打擊,穩住了陜北戰局,并策應了晉冀魯豫軍區部隊在晉南地區的反攻作戰。5 月下旬至7 月上旬,西北野戰部隊揮師隴東,北進三邊,收復環縣、定邊、安邊、靖邊等地,沉重打擊了國民黨軍馬步芳、馬鴻逵部。7 月31 日,中共中央軍委決定,西北野戰兵團定名為西北人民解放軍野戰軍,簡稱西北野戰軍,彭德懷兼任司令員和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成軍后,很快由內線防御轉入內線反攻、外線進攻,部隊越打越強,由初建時的不到3 萬人最多時發展到35 萬人①包括改隸第一野戰軍的第18、第19 兵團在內。,至1949 年底解放了西北廣大地區。可以說,正是陜北三戰三捷奠定了西北野戰軍(1949 年2 月改稱第一野戰軍)發展壯大的基礎,使西北戰場逐漸上升成為全國解放戰爭的重要主戰場之一。
二、摸索形成符合西北戰場實際的戰役指揮和戰略戰術原則
解放戰爭西北戰場的基本特點是,敵我兵力對比異常懸殊,敵強我弱的基本態勢持續時間較長。解放戰爭開始時,全國敵我兵力之比為3.4 ∶1,而西北戰場敵我兵力之比為10 ∶1。國民黨軍控制著西北的陜西、甘肅、青海、寧夏、新疆五省廣大地區,且有四川等省為后方,兵源補充及物資供應條件均比較優越。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解放區只有10.4 萬余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積和162 萬人口,兵源補充和物資供應均比較困難。西北人民解放軍兵力少、裝備差,糧彈皆缺,而且在三戰三捷之前,西北人民解放軍也缺少大兵團作戰的歷練,稍具規模的作戰行動僅有榆(林)橫(山)戰役、西華池戰斗、延安保衛戰等。通過三戰三捷,西北野戰部隊積累了大兵團作戰指揮的經驗,熟練了特殊戰場條件和特定戰場環境下的戰略戰術運用,奠定了西北戰局順利發展的堅實基礎。
(一)采取“蘑菇”戰術的作戰方針。“蘑菇”戰術,名為戰術,實則是作戰方針。1947 年4 月15 日,毛澤東在給西北野戰部隊的電報中,提出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我之方針是繼續過去辦法,同敵在現地區再周旋一時期(一個月左右),目的在使敵達到十分疲勞和十分缺糧之程度,然后尋機殲擊之”,“此種辦法是最后戰勝敵人必經之路。如不使敵十分疲勞和完全餓飯,是不能最后獲勝的。這種辦法叫‘蘑菇’戰術,將敵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滅之”。②《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 年,第37 頁。這一作戰方針的提出,正是基于對青化砭、羊馬河戰役的經驗總結。此前3 月25 日,西北野戰部隊在撤出延安后,利用國民黨軍急于尋求決戰的心理而行之以分兵追擊部署之缺點,成功伏擊了孤軍冒進的國民黨軍整編第31 旅,取得首戰青化砭的勝利。此役之后,胡宗南吸取教訓,采取所謂“方形戰術”,以主力兩個整編軍排成數十里寬的方陣,穩扎穩打。3 月29日和31 日,西北野戰軍曾計劃在蟠龍、永坪設伏,殲擊整編第135 旅,因無有利戰機而放棄。4 月2 日晚,彭德懷、習仲勛致電中央軍委:“敵自青化砭戰斗后,異常謹慎……以致三面伏擊已不可能,任何單面擊敵均變成正面攻擊。敵人此種小米磙子式戰法,減少我各個殲敵機會,必須耐心長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尋找弱點。”①《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 年,第220 ~221 頁。在這一方針的指導下,西北野戰部隊隱蔽待機,致胡宗南部“武裝游行”了400 余里路,到處撲空,兵疲糧缺后不得已將整編第135 旅留守瓦窯堡,大部主力返回永坪、蟠龍地區休整補充。其后,當整編第135 旅由瓦窯堡南下時,西北野戰部隊以逸待勞,于4 月14 日一舉將其殲滅,取得二戰羊馬河的勝利。半個月之后,西北野戰部隊再次運用“蘑菇”戰術,先拖后打、拖打結合,在拖動胡宗南部主力北上綏德后,于5 月2 日至4 日,乘虛殲滅其留守蹯龍的整編第167 旅等部,取得三戰蟠龍的勝利。
(二)實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作戰指導。當時,國民黨軍用于進攻陜甘寧邊區的部隊共有34 個旅25 萬人,其中進攻主力胡宗南集團是國民黨軍最大的一支戰略預備隊,擁有20 個旅17 萬余人的兵力,其裝備精良,彈藥充足,且配備有飛機和坦克。而西北野戰部隊所轄部隊為總計只有6 個旅2.6 萬余人,全軍僅有少量山炮和迫擊炮,彈藥奇缺,平均每支槍不到30 發子彈,機槍不足500 發子彈,炮彈更是缺乏。在雙方力量對比極其懸殊的情況下,只有在每一個局部上、每一個具體的戰場上,集中絕對優勢的兵力才有可能保證戰役戰斗的勝利。西北野戰部隊撤出延安后,面對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巧妙避開其主力,力避同其打消耗,在青化砭、羊馬河、蟠龍三戰三捷中,每戰都選擇孤立薄弱之敵為攻殲目標,集中優勢兵力,將全局上的絕對劣勢轉化為局部的絕對優勢。首戰青化砭,以6 個旅伏擊國民黨軍1 個旅(欠1 個團),兵力7 倍優勢于敵,確保了首戰勝利。二戰羊馬河,以2 個旅阻誘國民黨軍主力,以4 個旅伏擊國民黨軍1 個旅,戰役進行中又實行集中兵力分割逐次殲敵辦法,先以3 個旅殲滅其1 個團,繼而轉兵合力殲滅其旅部和另1 個團。三戰蟠龍,以主力4 個旅,攻擊國民黨軍1 個旅(欠1 個團)及地方部隊一部,由于兵力上占有絕對優勢,西北野戰部隊在裝備極端簡陋的條件下,僅用2 天3 夜就取得這次攻堅作戰的勝利,
(三)運用機動靈活的戰法。在陜北三戰三捷中,西北野戰部隊根據國民黨軍急于尋我主力決戰的企圖,采取以一部兵力誘阻其主力、而以大部殲其一路的戰法。青化砭戰役,是利用國民黨軍占領延安后不明情況又急于尋求決戰的心理,以一部兵力公開示形迷惑,誘其主力5 個旅北上安塞,使掩護其側翼安全的整編第31 旅遠離主力,造成其孤軍深入之勢后予以殲滅。羊馬河戰役,是利用國民黨軍要圍殲西北野戰軍于蟠龍、青化砭西北地區的企圖,先以一部兵力節節抗擊并疲憊其主力9 個旅,并將其誘至蟠龍、青化砭西北地區,使由瓦窯堡南下的整編第135 旅陷入孤立后予以殲滅。蟠龍戰役,是利用國民黨軍要殲滅解放軍于綏德附近地區或趕過黃河以東的企圖,以一部兵力迷惑敵人,將其主力誘牽至綏德,使守備蟠龍的整編第167旅陷入孤立,從而一舉殲滅并奪取了蟠龍這個國民黨軍的重要后勤補給基地。
三、有力支持中共中央做出轉戰陜北的重大戰略決策
解放戰爭經過前8個月的作戰,國民黨軍被迫由全面進攻改為重點進攻,這一戰略轉變的背景和目標,都在于解決機動兵力不足這個癥結。當時延安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所在地,極具政治象征意義,陜甘寧邊區的存在牽制了國民黨軍大量機動兵力。可以說,國民黨軍以陜北為重點進攻方向之一,其軍事上的直接動因就是要用上并用好在這一地區的機動兵力。在國民黨軍重點進攻陜北的部署中,以南線胡宗南集團實力最強、威脅最大,其整編第29 軍、整編第1 軍分別組成左、右兩路兵團直接向延安發起進攻;西線、北線的二馬(馬鴻逵、馬步芳)集團及鄧寶珊集團,實力較弱,主要負責配合胡宗南集團的進攻行動。國民黨軍的目的是打擊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軍首腦機關,消滅西北人民解放軍,或迫使中共中央和駐陜部隊東渡黃河,爾后將胡宗南集團這個戰略總預備隊投入到華北或其他戰場作戰。中共中央洞察國民黨軍的戰略企圖,毛澤東一針見血地指出,其目的是“妄圖首先解決西北問題,割斷我黨右臂,并且驅逐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出西北,然后調動兵力出華北,達到其各個擊破之目的”①《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35 頁。。
針對國民黨軍對陜甘寧邊區的重點進攻,中共中央最初的決策是全力保衛延安。3 月2 日,中央軍委在給保衛延安各部隊發出的指示中,強調“要取得外線有效配合,內線防御須有二十天堅決抗擊,才能粉碎敵人,保衛延安”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 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第105 頁。。3 月10 日,胡宗南集團進攻延安的15 個旅共14 萬人在洛川、宜川地區集結完畢。次日,中央軍委再次分析了形勢,認為胡宗南集團大舉進攻已迫在眉睫,兵力裝備均占有絕對優勢,西北野戰軍正面防御作戰處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鑒于西北野戰軍在陜北作戰的目的是鉗制胡宗南集團,其實現關鍵不在于是否守住延安,而在于讓胡宗南集團進入陜北后無法脫身。據此,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決定從長期戰爭著眼,在當前應誘敵深入,必要時主動放棄延安,同胡宗南部主力在延安地區周旋,陷其于十分疲憊、十分缺糧的困境,然后集中兵力逐次加以殲擊,以達到鉗制并逐步削弱胡宗南部,從戰略上配合其他戰略區作戰,最終奪取西北解放戰爭勝利的目的。當日,毛澤東在發給劉伯承、鄧小平等的電報中,提出“延安準備暫時讓敵占去”③《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7 頁。。3 月13 日,胡宗南集團向延安大舉進犯。在彭德懷、習仲勛指揮下,陜甘寧邊區部隊采取運動防御,節節抗擊,遲滯進犯之敵,經6 天激戰,勝利完成了掩護中共中央、人民解放軍總部安全轉移和疏散人民群眾的任務,于3 月19 日上午主動撤出延安。
在暫時放棄延安后,中共中央是留在陜北還是離開陜北,是當時面臨的一個艱難選擇。留下來,有利于牽制胡宗南集團深陷陜北,減輕其他戰場壓力,戰略上利益極大。對此,中共中央高層有著共識。3 月17 日,周恩來指出:“即使延安不守,胡敵也將消耗甚大,而我反得以從容各個殲滅之。倘以邊區現有力量能鉗制與削弱胡宗南主力于此,則對爭取全國勝利將幫助甚大。故現時邊區正以全力進行此長期戰爭,并不望敵人退出。”④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7 年,第745 頁。18 日,在中共中央在決定撤出延安的同時即指出:“以邊區地域之廣,地形之險,人民之好,有把握鉗制胡軍并逐漸削弱之,保持廣大地區于我手,以利他區作戰取得勝利。”⑤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2 年,第425 頁。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發出關于撤出延安解釋工作的指示,又指出,“我們若能將胡敵大部吸引在陜甘寧而加以打擊消滅,這正便利于其他解放區打擊和消滅敵人”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檔案館編:《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24 冊,第115 頁。。
但是,留下來同時意味著極高的安全風險。盡管毛澤東本人從一開始就堅持要留在陜北,他在離開延安前就談到準備留在陜北,他說:“我們在延安住了十幾年,都一直是處在和平環境之中,現在一有戰爭就走,怎么對得起老百姓?所以,我決定和陜北老百姓一起,什么時候打敗胡宗南,什么時候再過黃河。”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 年,第794 頁。但當時黨內高層、軍隊高層出于安全考慮,對于是留是走意見并不一致,多數主張中共中央應盡快東渡黃河,將中央遷至晉西北。3 月20 日,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在發給賀龍、李井泉的電報中,就表達了中共中央渡河進入晉綏的初步想法。3 月25 日,任弼時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兩份電文中,均提出了進入晉綏的意見。但就在3 月25 日這一天,戰場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西北野戰部隊取得了青化砭戰役的勝利。這一勝利,有力地證明了西北野戰部隊有能力保衛黨中央的安全,也使毛澤東更加確認了留在陜北的戰略決心。26 日,毛澤東致電彭德懷、習仲勛:“慶祝你們殲滅三十一旅主力之勝利。此戰意義甚大,望對全體指戰員傳令嘉獎。”27 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的電報中明確提出:“現在不怕胡軍北進,只怕他不北進……中央決定在陜北不走。”同日,毛澤東在給賀龍、李井泉并轉彭德懷、習仲勛的電報中再次指出:“中央率數百人在陜北不動,這里人民、地勢均好,甚為安全。目前主要敵人是胡宗南,只要打破此敵即可改變局面,而打破此敵是有可能的。”①《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11、13、15 頁。28 日,中共中央在王家坪開會,初步決定中央主要領導人留在陜北。29 日,中共中央機關轉移到清澗縣棗林溝村,當晚政治局會議再次討論中共中央去留問題時,會上又發生了激烈爭論。毛澤東闡述了中共中央留在陜北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他說:“我不能走,黨中央最好也不走。我走了,黨中央走了,蔣介石就會把胡宗南投到其他戰場,其他戰場就要增加壓力。我留在陜北,拖住胡宗南,別的地方能好好地打勝仗。”②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二),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 年,第758 頁。最終在毛澤東的堅持下,會議正式形成了中共中央留在陜北的決策,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率中央前委和解放軍總部留在陜北,從此開始了偉大的轉戰陜北的歷程。同時,由劉少奇、朱德、董必武組成中央工作委員會,前往晉西北或其他適當地點,進行中央委托的工作。4 月9 日,毛澤東在《關于保衛陜甘寧邊區的通知》中指出:“必須用堅決戰斗精神保衛和發展陜甘寧邊區和西北解放區,而此項目的是完全能夠實現的”,“我黨中央和人民解放軍總部必須繼續留在陜甘寧邊區”。③《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35 頁。在這個黨內通知發出后不久,西北野戰部隊于4月14 日、5 月4 日接連取得羊馬河戰役、蟠龍戰役的勝利,強有力證明了西北野戰部隊完全有能力保衛中共中央安全,有實力實現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目的。
5 月14 日,西北野戰部隊召開了三戰三捷慶祝大會。會上,習仲勛講道:“今天這個大會完全揭穿了兩個月來敵人的造謠。他們說什么‘中共中央走了,西北局走了,邊區政府也走了’。這只是敵人說夢話……毛主席和中共中央仍然在邊區領導著我們。”④《習仲勛文集》上卷,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 年,第64 頁。周恩來受中共中央委托參加了慶祝大會,公開宣布: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同志自從撤出延安后,一直留在陜北,同邊區的全體軍民共同奮斗。⑤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二),第763 頁。這一宣示,不僅進一步鼓舞了軍心民心,而且為抑留胡宗南集團于陜北添置了極重的籌碼。
四、客觀促成解放戰爭戰略進攻布局的完善
棗林溝會議雖然做出了中共中央留在陜北的決策,但能否只依靠西北野戰部隊獨立支撐西北戰局,在當時還是未知數。此前,中共中央關于西北戰場的作戰方針,一直強調從外線解圍。在相關戰略布局中,尤其倚重在晉南一帶活動的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 縱隊(司令員陳賡、政治委員謝富治)。1946 年11 月3 日,面對國民黨軍可能進攻延安的態勢,中央軍委要求“陳謝縱隊迅即攻占隰縣、蒲縣、大寧、吉縣、鄉寧,控制馬斗關渡口,開辟到延安之道路”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 卷,第550 頁。,是為中央軍委賦予陳謝集團保衛延安任務的開始。此后10 多天的時間內,毛澤東曾連續起草了十幾份電報,就陳賡等部保衛陜甘寧做出具體部署。
在國民黨軍發動重點進攻前夕,中共中央對陜北局勢的設想是主要依靠外線作戰。1947 年3 月6 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的給劉伯承、鄧小平的電報中指出:“陳謝率五個旅寅皓渡河襲占隴海潼洛線,為調動胡軍、保衛延安最好辦法”,“我現布置內線縱深防御可能遲滯十天時間,主要依靠陳謝從外線解圍。”⑦《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4 頁。17 日,中央軍委又專門電告:“為援助陜北作戰之目的,陳謝集團決心使用于同蒲線。”⑧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6 冊,第425 頁。
3 月25 日,青化砭戰役勝利后,從中共中央到西北野戰部隊均信心大增,彭德懷提出力爭停止敵人于蟠龍、永坪、延川線以南,并要求陳謝縱隊應開始向同蒲路南段進攻,進行戰略上的配合。毛澤東則認為“現在不怕胡軍北進,只怕他不北進,故陳謝遲幾天行動未為不利”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13 頁。。28 日,毛澤東就陳謝集團晉西南作戰做出指示,要求由陳謝統一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第4 縱隊和太岳軍區部隊,在晉西南三角地帶作戰主要目的不在占地而在殲敵有生力量,主力要隨時準備使用于他處(陜北)。①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17 頁。此時,依靠西北野戰部隊獨力支撐陜北戰局的決心雖然尚未形成,但較此前主要依靠外線解圍的看法已經有了轉變。
4 月14 日,羊馬河戰役勝利后,中共中央的看法又向前進了一步。4 月15 日,毛澤東在致彭德懷、習仲勛并其他戰略區領導人的電報中指出:“這一勝利給胡宗南進犯軍以重大打擊,奠定了徹底粉碎胡軍的基礎。這一勝利證明僅用邊區現有兵力(六個野戰旅及地方部隊),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決胡軍。”②《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39 頁。5 月4 日,西北野戰部隊運用“蘑菇”戰術再次取得蟠龍戰役的勝利,用實踐證明了毛澤東這一判斷的正確性。也是從這一天開始,對陳賡部如何使用,開始發生重要變化。在當天的一份電文中,毛澤東對劉鄧、陳粟、陳謝部的作戰任務進行了部署,明確“晉南(陳謝)陜北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胡宗南系統”,陳謝主力“隨時準備從下流或從上流渡河,受彭習指揮,殲滅胡宗南及其他雜頑,收復延安,保衛陜甘寧,奪取大西北”。③《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50 頁。由此可見,此時中央雖仍有調陳賡部西渡黃河入陜的考慮,但其主要任務已經發生變化,即由保衛陜北轉變為協同西北野戰部隊“擊破胡宗南系統”。
陜北三戰三捷之后,胡宗南集團因迭遭重創,被迫戰略收縮、整補軍隊,西北野戰部隊主動轉向北線作戰,陜北戰局出現明顯好轉。中央軍委開始進一步思考如何使用陳謝集團的問題。6 月20 日,毛澤東在給彭德懷、習仲勛并轉陳賡、謝富治的電報中征詢意見:“依西北之敵情、地形、補給等條件來看,邊區野戰軍與陳謝集團在數個月內似宜分開行動,而不宜集中行動。”④《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109 頁。進入6 月底,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發起魯西南戰役,揭開了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序幕。7 月4 日,毛澤東就陳謝集團如何使用致電彭德懷、習仲勛,又提出兩個方案征詢意見:一案是陳賡所部按原計劃入陜作戰;另一案是陳賡所部到鄂豫陜邊開辟新場。電報并告知陳賡到陜北靖邊小河村,彭德懷、習仲勛也可來小河一起會商。⑤參見《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125 頁。7 月19 日,毛澤東在為中央軍委起草的電文中,專門提出改變陳謝所部使用方向的問題,指出:“為著協助陜甘寧擊破胡宗南系統,同時協助劉鄧經略中原,決將陳謝縱隊使用方向改為渡河南進,首先攻占潼洛鄭段,殲滅該區敵人,并調動胡軍相機殲滅之。爾后向豫西、陜南、鄂北進擊,創建鄂豫陜邊區根據地,作為奪取大西北之一翼。”⑥《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 卷,第143 頁。21 日,在中共中央小河會議上,毛澤東又對陳謝縱隊使用方向問題進行了重點說明,指出:原計劃陳賡率部西渡黃河,集中在陜北打擊胡宗南,現在決定陳賡南渡黃河挺進豫西、加入中原作戰。南征以后,他們還要協助西北我軍打胡宗南。⑦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203 頁。至此,徹底解除了陳賡所部入陜的任務,轉為南下挺進豫西,與劉鄧、陳粟大軍,在江淮河漢之間構成品字型布勢,為形成“三軍配合、兩翼牽制、內外線密切配合”的戰略進攻態勢提供了重要條件。中共中央改變陳謝集團使用方向,是一次重大的戰略性調整,而支持這一調整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從3 月至7 月西北野戰部隊的作戰,特別是陜北的三戰三捷,證明了西北野戰部隊有能力獨立承擔本戰略區的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