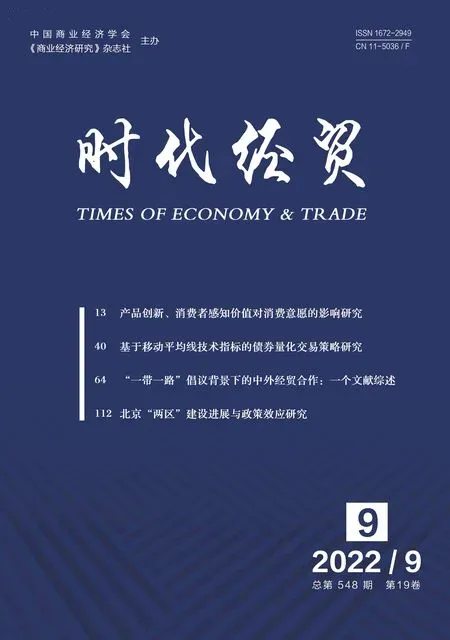基于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的遼寧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評價
張嘉昕 王鶴春 戰(zhàn) 帥 劉子寧 楊 洋
(沈陽師范大學管理學院 遼寧沈陽 110034)
相關(guān)文獻綜述
國內(nèi)外有很多關(guān)于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研究,但相關(guān)概念還沒有明確的官方定義,涉及的科技成果權(quán)屬、運用與保護等領(lǐng)域都需要進一步明確。因此,很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對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進行定義。如李修全(2015)從“創(chuàng)新鏈”的角度,認為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需要經(jīng)歷理論驗證、技術(shù)研發(fā)、實際應用這三個環(huán)節(jié),這三個環(huán)節(jié)將科技與經(jīng)濟緊密結(jié)合,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創(chuàng)新鏈;郭英遠等(2015)從知識的角度,認為科技成果是隱藏在科技人員體內(nèi)的隱性知識和專利等顯性知識相結(jié)合的“知識包”,二者的比例決定了成果轉(zhuǎn)化的具體方式。
國內(nèi)很多學者在設計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指標體系時,也盡可能從不同方面進行構(gòu)建,使其更完整、更全面。從轉(zhuǎn)化條件、轉(zhuǎn)化實力和轉(zhuǎn)化效果三方面構(gòu)建指標體系的學者較多。如柴國榮等(2010)對西部地區(qū)2004-2007年十一省市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進行了綜合性評價;郭俊華和徐倪妮(2016)對2015年全國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qū)的高等學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能力進行實證分析,發(fā)現(xiàn)不同地區(qū)的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存在較大差異;陳輝和林超輝等(2019)選取7所全國代表性的理工科高校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作為樣本,對其進行實證分析,發(fā)現(xiàn)影響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能力的因素多種多樣;林超輝和楊堅偉等(2020)從創(chuàng)新實力指數(shù)、研發(fā)實力指數(shù)、轉(zhuǎn)化實力指數(shù)三個方面構(gòu)建指標體系,采用東、中、西三大區(qū)域中具有代表性的12所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數(shù)據(jù)對這三個區(qū)域的高校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能力進行整體分析。還有一些學者從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投入和產(chǎn)出來進行綜合評價。鐘衛(wèi)(2018)從投入和產(chǎn)出兩方面測算了2010-2012年50所高校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率;孫濤(2020)選取了2004-2017年東三省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相關(guān)數(shù)據(jù),從科研投入和產(chǎn)出比來分析我國老工業(yè)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由此看來,我國大多數(shù)學者傾向于從經(jīng)濟效益的角度建立指標體系,多維度進行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評價的研究較少。因此,本文從經(jīng)濟、社會、技術(shù)三方面對遼寧省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進行綜合評價分析。
目前,運用定量分析方法對科技成果轉(zhuǎn)化進行研究的文獻較多且成熟,運用案例分析等定性分析方法則較少。如張明喜(2013)、羅彪(2018)、王趙琛(2020)、孫濤(2020)等都選擇運用數(shù)據(jù)包絡分析方法(DEA)對高校或區(qū)域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進行評價;一些學者運用多準則VIKOR法、層次分析法(AHP)、灰色關(guān)聯(lián)度分析法、脈沖響應函數(shù)等方法對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評價進行分析;還有一些學者運用案例分析、田野調(diào)查、扎根理論等方法進行分析。
研究設計
數(shù)據(jù)來源與指標體系。為保證數(shù)據(jù)的權(quán)威性和可復制性,本文所使用的數(shù)據(jù)均來源于2019年遼寧省及14個地區(qū)的統(tǒng)計年鑒、《科技統(tǒng)計年鑒》、統(tǒng)計公報、人民政府網(wǎng)、市科技局。為了能夠更加全面地對遼寧省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情況進行評價,本文選取了經(jīng)濟、社會、技術(shù)三個指標作為一級指標。在設計評價指標體系時,要堅持系統(tǒng)性、科學性、可操作性等原則,同時要考慮數(shù)據(jù)的可獲得性,論文結(jié)合了遼寧省科技成果的實際情況,并借鑒了現(xiàn)有的相關(guān)研究,設計了4個二級指標和12個三級指標,如表1所示。

表1 遼寧省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遼寧省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實證分析
(一)因子分析
論文選擇SPSS23.0軟件中的因子分析方法進行分析,具體分析過程如下:
1.KMO和Bartlett球形度檢驗。經(jīng)檢驗,論文的KMO值為0.816,接近1,說明變量的相關(guān)度較高,適合做因子分析。而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近似卡方值為371.913,顯著性概率為0.000,小于0.05,說明變量之間存在相關(guān)性,數(shù)據(jù)呈球形分布,適合做因子分析。
2.特征值和方差貢獻分析。通過數(shù)據(jù)分析,本文發(fā)現(xiàn):論文所提取的第一個因子的特征值為10.208,第二個因子的特征值為1.047,二者都大于1,且這兩個公共因子的特征值累計貢獻率為93.792%,說明這兩個公共因子可以解釋大部分信息。因此,論文提取這兩個因子為公共因子,分別為第一公共因子(F1)和第二公共因子(F2)。對因子進行旋轉(zhuǎn)之后,各個因子所解釋的方差比例重新分配,第一個公共因子(F1)的方差貢獻率降為68.728%,第二公共因子(F2)的方差貢獻率升為25.064%,但兩個公共因子的累計貢獻率仍為93.792%,使得因子結(jié)構(gòu)變得更加簡單,更容易解釋。
3.因子載荷矩陣。將旋轉(zhuǎn)后的成分矩陣與表1結(jié)合起來,可以發(fā)現(xiàn),第一公共因子(F1)主要解釋了技術(shù)合同交易額、科研及技術(shù)服務人員、專利申請數(shù)、專利授權(quán)數(shù)四個指標,第二個公共因子(F2)主要解釋了規(guī)模以上工業(yè)戰(zhàn)略性新興產(chǎn)業(yè)增加值增長率、R&D經(jīng)費投入強度兩個指標,它們相互補充,增強了各個指標之間的聯(lián)系,對遼寧省14個地區(qū)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評價具有更大的影響。
4.綜合得分排名。兩個公共因子的計算模型,分別為:
其中,X1-X12代表各個指標。
第一公共因子(F 1)的方差貢獻比例為R1=68.728/93.792=0.7328,第二公共因子(F2)的方差貢獻比例為R2=25.064/93.792=0.2672。據(jù)此,本文建立遼寧省各地區(qū)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綜合評價模型:W=0.7328F1+0.2672F2。根據(jù)這個公式,可以計算出14個地區(qū)的因子得分和綜合得分,并進行排序,如表2所示,大連兩個公共因子的得分排名接近,發(fā)展較為穩(wěn)定;沈陽為第二公共因子,雖然得分排名較低,但是由于第一公共因子得分高并沒有拉低綜合得分排名,說明沈陽的R&D經(jīng)費投入強度不是很低;朝陽的第一公共因子得分排名第5,但第二公共因子的得分卻很低,拉低了朝陽地區(qū)的綜合排名。這充分說明有些地區(qū)在各公共因子代表的因素上發(fā)展不平衡,影響科技成果轉(zhuǎn)化的綜合排名。

表2 遼寧省各地區(qū)科技成果轉(zhuǎn)化各因子得分與綜合得分
(二)聚類分析
為了更直觀地了解遼寧省各地區(qū)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的差異,論文運用K-均值的方法對各因子得分與綜合得分進行聚類分析,如表3所示,可以將14個地區(qū)的科技成果和鉆花效率分為四個類別:

表3 聚類結(jié)果
第一類: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高。沈陽第一公共因子(F1)方面的得分為3.06288,遠遠超過其他地區(qū),這說明沈陽的科技成果多,資金支持也較多。但第二公共因子(F2)得分僅為-0.33044,說明沈陽科技成果在產(chǎn)業(yè)應用方面不足,未能打通“最后一公里”,真正實現(xiàn)科技成果轉(zhuǎn)化。但是跟其他13個地區(qū)相比,由于第一公共因子(F1)所占比重較大,所以不影響沈陽的綜合得分。
第二類: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較高。大連第一公共因子(F1)與第二公共因子(F2)得分差距不大,且都為正,這說明與其他地區(qū)相比,大連在各公共因子代表的因素上發(fā)展較平衡,科技成果效率較高。
第三類: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較低。該類別包括鞍山、錦州、盤錦三個地區(qū)。這三個地區(qū)第一公共因子(F1)與第二公共因子(F2)得分差距不大,第二公共因子(F2)較高,說明這三個地區(qū)試驗與發(fā)展經(jīng)費投入較高,但科技成果較少,轉(zhuǎn)化效率也較低。
第四類:科技成果轉(zhuǎn)化能力低。該類別的9個地區(qū)第一公共因子(F1)與第二公共因子(F2)得分都很低且為負,這說明這9個地區(qū)的科技成果轉(zhuǎn)化效率度有待提高。而且,除營口經(jīng)濟實力較強之外,其他地區(qū)經(jīng)濟實力都較弱,導致科技人才流失嚴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