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9例上海市孕產婦對產前診斷的認知及其影響因素研究
許厚琴,樊志磊,何麗蕓,馬 鳳,范崇純,朱麗萍,陳英耀
(1.上海市婦幼保健中心,上海 200062;2.復旦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衛生技術評估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032)
我國孕產婦和適齡女性數量龐大,其醫療需求和就診體驗存在一定特殊性[1];如何為其提供優質便捷的產前診斷服務以保障婦女兒童健康水平,是衛生服務提供者和決策者關心的問題[2]。需方滿意度作為衡量衛生系統反應性的重要指標之一,可以從孕產婦的視角評價現有產前診斷(篩查)服務的提供質量,發現當前服務過程中的問題,從而更好地改善孕產婦的就醫體驗。目前,已有一些針對孕產婦人群就醫滿意度的研究[3],但關注于產前診斷環節的國內研究相對較少,且存在樣本量較少、研究內容較單一的局限性。本研究旨在分析在上海市10家產前診斷中心就診的孕產婦對產前診斷(篩查)服務的滿意度、認知及其影響因素,為改善孕產婦的就醫體驗、提升產前診斷機構技術服務能力提供針對性建議。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課題組于2018年12月至2020年3月,對在上海市10家產前診斷相關機構就診的孕產婦開展問卷調查,調查方式以手機掃碼填寫在線問卷為主,共收集到699份問卷,經過對問卷的復合和邏輯性檢查,最終納入有效問卷689份,有效率98.57%。所有研究對象均知情同意自愿參與研究。
1.2 研究方法
根據文獻分析和研究目的,擬定調查問卷。調查的主要內容:孕產婦基本人口學信息(年齡、孕周、胎次、戶籍地、受教育程度、職業、參保情況、不良孕產史),孕產婦對產前診斷服務認知情況、使用情況(包括接受產前超聲、唐氏篩查、染色體核型分析、遺傳咨詢及無創產前基因檢測等),孕產婦對產前診斷服務的需求和滿意度(包括對醫生診療技術、服務態度和收費水平的滿意程度)。與孕產婦認知、意愿和滿意度相關的問題采用Likert 5級計分進行測量,其中很滿意5分、比較滿意4分、基本滿意3分、不太滿意2分、不滿意1分。
1.3 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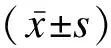
2 結果
2.1 受訪孕產婦的基本人口學信息
本研究689名就診的孕產婦中,平均年齡為(31.95±4.93)歲,大于35歲的孕產婦占比為25.25%,75.91%孕產婦處于孕中期,59.65%的孕產婦來自外地,59.50%的孕產婦接受過本科及以上教育,商業、服務業人員占32.37%,商業保險參保率為12.48%,有過不良孕產史的(包括自然流產、人工流產、引產、死胎、死產等)孕產婦占比達到57.47%,見表1。

表1 受調查的孕產婦基本人口學特征[n(%)]
2.2 受訪孕產婦對產前診斷服務的認知與利用情況
在對產前診斷技術的認知方面,認為產前診斷風險較低的孕產婦占大多數(65.67%),66.24%的受訪者傾向于選擇超聲檢查等無創方式進行產前診斷。對于選擇產前診斷技術的側重因素,相較于“費用低”(0.29%)、“疼痛少”(1.43%),多數孕產婦更為看重“安全性高”(71.24%)和“確診早”(27.04%)兩個因素。孕產婦獲得產前診斷相關信息的渠道以醫務人員介紹為主(75.11%),26.47%的孕產婦認為獲取產前診斷的信息有點困難或非常困難;大多數孕產婦表示愿意收到更多產前診斷相關信息。在對產前診斷中心進行選擇的考量因素方面,技術水平高(59.66%)和醫療設備完備(50.07%)是孕產婦考慮的主要方面。
產前診斷服務利用方面,受訪者接受過的服務包括產前超聲篩查(78.83%)、唐氏篩查(40.06%)、染色體核型分析(22.46%)等,也有7.73%的受訪者表示不清楚服務所屬類型。在產前篩查后由醫生推薦接受產前診斷服務的占大多數(49.07%);82.69%是在聽取醫生建議后自主選擇接受產前診斷技術服務。在接受產前診斷服務的過程當中,95.85%的醫生對相關問題進行過解釋,86.86%的受訪者認為醫生的解釋通俗易懂,86.12%的孕產婦在治療過程中向醫生表達過自己的主觀訴求,其中80.73%的訴求得到了部分或完全解決,見表2。

表2 受訪孕產婦對產前診斷服務的認知與利用情況[n(%)]
2.3 受訪孕產婦對產前診斷服務的滿意度情況
本研究孕產婦對醫生診療技術的滿意度為(4.20±0.77)分,對醫生服務態度的滿意度為(4.26±0.73)分,對產前診斷服務收費的滿意度為(2.44±0.64)分。三者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且孕產婦對于服務收費的滿意度低于對醫生診療技術和服務態度的滿意度(F=1 510.50,P<0.001);受訪者中對收費情況很滿意的為0人,見圖1。

圖1 孕產婦對產前診斷過程不同方面的滿意程度
2.4 影響孕產婦對產前診斷服務滿意度的因素
以診療技術滿意度、服務態度滿意度、服務收費滿意度分別作為因變量,以孕產婦的基本人口學特征、對產前診斷的認知情況和服務利用情況三個層面的信息作為自變量,構建初步的多分類有序Logistic模型,對模型進行平行線檢驗以確定是否滿足比例優勢假定。最終分析時將診療技術滿意度和服務態度滿意度原有五點計分中的“1、2”合并為“不滿意”、“3”為“基本滿意”,“4、5”為“很滿意”構建三分類有序Logistic模型。結果顯示相對于26~30歲的孕產婦,35歲以上的孕產婦對服務收費的滿意度更高,其OR值及95%CI為1.92(1.26~2.93),P<0.001;與大專學歷的孕產婦比較,碩士及以上學歷的孕產婦對醫生診療技術和服務態度的滿意度均更低,其OR值及95%CI分別為0.31(0.15~0.67)、0.35(0.16~0.77),P<0.01;孕產婦認為獲取產前診斷相關信息越難,對醫生診療技術和服務態度的滿意度越低,其OR值及95%CI分別為0.58(0.43~0.77)、0.54(0.39~0.74),P<0.001;醫生解釋過相關問題、解釋的通俗易懂、孕產婦向醫生表達過主觀訴求、訴求得到解決,均會提高醫生診療技術、醫生服務態度、服務收費的滿意度(OR值介于1.42~7.01之間,P<0.05),見表3。

表3 孕產婦對產前診斷服務滿意度的Logistic回歸模型結果
3 討論
預防和減少出生缺陷,把好人生健康第一關,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質、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要舉措。通過廣泛開展產前篩查、普及產前篩查適宜技術,推廣高通量基因測序等無創產前檢測新技術能夠減少嚴重出生缺陷兒出生[4]。近年來產前診斷(篩查)的方法越來越多,除了傳統的血清學篩查、影像學檢查、羊水穿刺染色體核型分析等,涌現出了一批如NIPT、基因芯片等新技術[5-6],它們準確率高、假陽性及假陰性率低,但是價格較為昂貴,往往會影響孕產婦的支付意愿及滿意度[7]。自2016年國家衛健委發布《規范有序開展孕婦外周血胎兒游離DNA產前篩查與診斷工作的通知》以來,NIPT在國內臨床中得到較好開展[8]。
3.1 孕產婦對上海市產前診斷服務的滿意度總體較高,但需關注對服務收費的滿意度
本研究針對醫護人員診療技術、服務態度及服務收費情況三個方面的孕產婦滿意度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孕產婦總體滿意度較高,但對于服務收費的滿意度低于對醫生診療技術和服務態度的滿意度。多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顯示年齡是影響服務收費滿意度的關鍵因素,可能與35歲以上的孕產婦收入基礎較好有關。另外,西南地區的研究發現產婦對NIPT費用滿意度最低,但是隨著價格的下降,產婦個人支付的意愿隨之上升[9]。醫療服務尤其是孕產婦、嬰幼兒相關的醫療服務具有極小的價格彈性,幾乎是“剛需”,不應讓收費價格成為阻礙孕產婦獲得產前診斷服務可及性的因素。建議有關部門可以在全成本核算的基礎上合理制定產前診斷(篩查)的收費標準,或采取其他相應措施緩解目前孕產婦認為收費過高的現象,以提高新技術應用推廣的可及性。
3.2 醫生應對產前診斷技術的安全性進行充分解釋,并注意對患者訴求的及時回應
本研究結果顯示,多數孕產婦(71.24%)在選擇產前診斷技術時更看重“安全性高”,并且孕產婦獲取相關信息的難易程度、醫生是否解釋過相關問題、孕產婦是否表達過主觀訴求、訴求的解決程度等均是影響孕產婦就醫滿意度的重要因素。研究報道NIPT檢測及報告解讀等待時間會使服務對象增加焦慮[10]。醫務人員介紹為孕產婦獲取產前診斷信息的最主要途徑,因而加強醫務人員對產前診斷服務的宣教意識至關重要,尤其是在進行一些相對較新技術的檢查結果解讀時更要有耐心[11]。有研究報道,女性有積極的選擇性、對選擇的信任程度能有助于她們做出產前篩查的選擇,外界影響、認知度低反而會影響她們做決定[12]。因此,及時有效的溝通可以發揮重大作用,尤其需引導醫生對患者最為關切的問題如安全性、風險性和必要性等進行詳盡的解釋,可提高孕產婦良好的認知度和就診滿意度。
3.3 拓展宣傳渠道、利用多種平臺提高孕產婦對產前診斷的認知度,從而改善其就醫體驗
本研究調研顯示,65.67%的對象認為產前診斷的風險較低,75.11%孕產婦獲得產前診斷相關信息的渠道為醫務人員介紹,26.47%孕產婦認為獲取產前診斷的信息困難,79.40%的孕產婦表示愿意收到更多產前診斷相關信息,與相關報道相似[13]。多元素、個性化健康宣教可以提高孕婦對唐氏綜合征篩查的認知度及依從性。在當今信息傳播日益便捷的年代,可更多運用微信、微博、短視頻等平臺,也可依托孕婦學校、優生咨詢門診、主題宣傳日等廣泛開展形式多樣的產前診斷(篩查)知識宣教。另外,66.24%的受訪者傾向于選擇超聲檢查等無創方式進行產前診斷。相比傳統的篩查和診斷項目,新技術的知曉度更低,健康宣教時應側重于不為大眾所熟知的新技術,并且需注意對技術的副作用和潛在風險加以解釋,同時引導其規范就醫的流程,避免商業機構繞過產前診斷機構從中牟利。此外,在對信息系統的利用上,除完善診斷結果傳遞和疾病信息管理,也應善于利用信息平臺加強醫生與孕產婦之間的溝通交流,提升孕產婦就醫滿意度和就醫體驗。
孕產婦年齡、學歷、獲取產前診斷相關信息、醫生的詳細解釋說明等均是影響孕產婦滿意度的因素,提升產前診斷機構的服務能力及拓展孕產婦產前診斷的宣傳渠道對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至關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