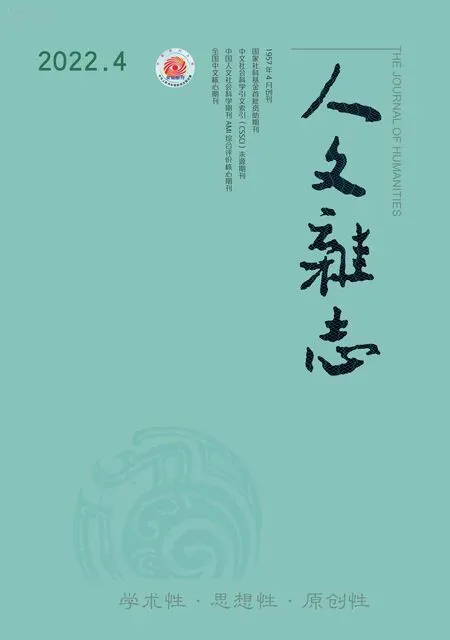政治視域下的道德因素考量
——荀韓哲學(xué)思想之比較
先秦時(shí)期的諸子關(guān)系是目前學(xué)界研究的熱點(diǎn)與重點(diǎn),這主要包括對(duì)儒道關(guān)系、儒法關(guān)系、道法關(guān)系等的研究。在儒法關(guān)系研究方面,荀韓關(guān)系是當(dāng)前研究當(dāng)中較為薄弱、需要積極發(fā)掘的論題。就荀韓關(guān)系而言,在天人關(guān)系、人性論、政治哲學(xué)等方面都是可以加以比較與集中討論的。
一、天人關(guān)系:天人相分與對(duì)道的政治化處理
春秋晚期與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禮樂(lè)崩壞、天下失序,這一歷史時(shí)期諸子學(xué)的興起與諸子對(duì)于天人關(guān)系問(wèn)題的思考不無(wú)關(guān)系。
肖健告訴《中國(guó)名牌》記者:“百姓如今的生活水平上去了、經(jīng)濟(jì)條件好了,自然會(huì)選擇更安全、更健康的食物。”
所謂天人關(guān)系,實(shí)際上是指人在天地之間的位置以及人與天的關(guān)系等問(wèn)題。與強(qiáng)調(diào)“盡心”“知性”“知天”的《孟子·盡心上》,強(qiáng)調(diào)“與天地參”的《禮記·中庸》,強(qiáng)調(diào)“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shí)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的《周易·乾卦·文言》具有天人合一式的思維理路不同,荀子更注重發(fā)掘人的主體理性精神,
在天人相分的基礎(chǔ)上,將天的功能主要限定在了生物的范圍內(nèi)。《荀子·禮論》即云:“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合而萬(wàn)物生”。《荀子·大略》亦云:“天之生民”。在天人之間劃定了界限,從而為天人關(guān)系構(gòu)架中人的主體精神的充分發(fā)揮做了理論上的廓清,故而《荀子·天論》言謂:“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應(yīng)之以治則吉,應(yīng)之以亂則兇。強(qiáng)本而節(jié)用,則天不能貧;養(yǎng)備而動(dòng)時(shí),則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貳,則天不能禍。故水旱不能使之饑,寒暑不能使之疾,祅怪不能使之兇。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養(yǎng)略而動(dòng)罕,則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則天不能使之吉。”“天不為人之惡寒也輟冬,地不為人之惡遼遠(yuǎn)也輟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也輟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數(shù)矣,君子有常體矣。”此意在強(qiáng)調(diào)君子治世不要違背天時(shí)和規(guī)律,這是對(duì)三代固有觀念的沿襲與吸收,同時(shí)更強(qiáng)調(diào)要充分發(fā)揮人的主觀能動(dòng)性,不應(yīng)把人間的治亂與否完全歸結(jié)于天地鬼神。這就與其他先秦諸子所強(qiáng)調(diào)的“人事應(yīng)當(dāng)順應(yīng)天道權(quán)威,社會(huì)治理應(yīng)該遵守天道秩序”
的政治思維方式有所不同,從而為先秦諸子政治治理思維方式與政治治理智慧的多元性與多樣化貢獻(xiàn)了自己的力量。
大豆出苗后進(jìn)行查苗、缺苗補(bǔ)苗,確保苗全,并及時(shí)間苗剔除疙瘩苗。達(dá)到苗全、苗壯是栽培中一個(gè)重要環(huán)節(jié)。補(bǔ)苗時(shí)可以補(bǔ)種或芽苗移栽。
可以說(shuō),荀子對(duì)于天人關(guān)系的獨(dú)特性理解,首先是基于對(duì)三代時(shí)期天的宗教神秘色彩的弱化,相應(yīng)地便是對(duì)天功能的縮小與限定,天不再是人間吉兇禍福與人類命運(yùn)的完全決定者:“天地合而萬(wàn)物生,陰陽(yáng)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wàn)物、生人之屬,待圣人然后分也。”(《荀子·禮論》)在這里,天能生物,卻不能辨物;地能載人,卻不能治人。原來(lái)高高在上,幾乎無(wú)所不能的天,在荀子這里卻變成了功能有限的天。因而,人主體能動(dòng)性的發(fā)揮正是在天所不能及的地方——辨物和治人。人能辨物,能治人,卻不能生物,這正是荀子提出天人相分理論的現(xiàn)實(shí)基礎(chǔ),也為其化性起偽、師法教化圣人治國(guó)理念的提出做了理論上的準(zhǔn)備。
戰(zhàn)爭(zhēng)年代早已遠(yuǎn)去,和平時(shí)期的軍隊(duì)沒有經(jīng)歷過(guò)戰(zhàn)場(chǎng),沒有經(jīng)受過(guò)戰(zhàn)火洗禮的軍隊(duì),很難在突然發(fā)生的戰(zhàn)爭(zhēng)中發(fā)揮應(yīng)有的實(shí)力。而全息投影則很好地解決了這個(gè)問(wèn)題,利用全息投影模擬戰(zhàn)場(chǎng)環(huán)境,為軍事行動(dòng)提供高空間感的仿真環(huán)境支持。這在陸軍方面或許作用不是非常顯著,但是在海空軍中用來(lái)模擬飛機(jī)飛行,艦隊(duì)行駛,不僅訓(xùn)練了參戰(zhàn)人員的實(shí)際操作能力,還節(jié)省了使用真實(shí)裝備進(jìn)行演練的經(jīng)費(fèi),減少了設(shè)備的損耗。
需要注意的是,采用上述計(jì)算得到泄壓板面積為有效面積。在實(shí)際的工程應(yīng)用中,由于泄壓板多為方形開口,需根據(jù)泄壓板形狀將有效泄壓面積轉(zhuǎn)化為幾何面積進(jìn)行設(shè)計(jì)。
正因?yàn)檎J(rèn)為人性不可化,所以韓非在考量各種社會(huì)關(guān)系時(shí)并沒有如孔孟那樣為其蒙上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而是主張用利益因素來(lái)分析和解釋人們的日常行為,并認(rèn)為人與人之間從根本上說(shuō)只是利害算計(jì)、利益得失的關(guān)系。在利害得失面前,所有的關(guān)系都經(jīng)受不住考驗(yàn),無(wú)論是君主和臣下、醫(yī)生和病人還是做車和做棺材的匠人之間,甚至父母與子女之間都是以算計(jì)之心相待的,故而《韓非子·六反》有云:“故父母之于子也,猶用計(jì)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wú)父子之澤乎?”既然如此,世界上便不可能真正存在超脫利益算計(jì)的君子,即便是在儒家眼中德行高尚的曾子、史鰌也非常值得懷疑:“夫陳輕貨于幽隱,雖曾、史可疑也;懸百金于市,雖大盜不取也。”(《韓非子·六反》)與其勞心費(fèi)力地考驗(yàn)可能心懷利害算計(jì)的君子,倒不如刑名律法來(lái)得理性與可靠。退一步講,即使世上確實(shí)存在不計(jì)名利得失的君子,但這樣的君子相對(duì)于天下民眾而言仍占極少數(shù),按照韓非的治國(guó)立場(chǎng),君主治國(guó)面對(duì)的是全體民眾,而非如儒家那樣以君子的標(biāo)準(zhǔn)來(lái)要求世人,后者顯然是一種迂闊而難以實(shí)現(xiàn)的政治思想。
在老子看來(lái),天道的運(yùn)行,無(wú)意識(shí)、無(wú)目的、自然無(wú)為,因而天道的本質(zhì)特征是“自然”和“無(wú)為”,楊慶中將其稱為“自然主義的天道觀”。
這種天道觀與孔孟對(duì)天所作的道德化理解有著很大不同,自然也就無(wú)法通過(guò)道德修養(yǎng)的方式將人與天真正貫通起來(lái)。從荀子所處的歷史階段和《荀子》文本所呈現(xiàn)出的集大成特點(diǎn)來(lái)看,荀子對(duì)天自然主義式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老子的影響。關(guān)于老子的“道”,楊慶中認(rèn)為,“從‘實(shí)證’的立場(chǎng)說(shuō),老子提出‘道’,是為了超越傳統(tǒng)天命論中的上帝主宰論(老子視道為‘象帝之先’),克服春秋時(shí)期天道自然觀的局限(老子又視道為‘可以為天地母’),進(jìn)而塑造一個(gè)無(wú)知、無(wú)欲,具有自然性特征(相對(duì)于上帝的人格特征而言)和超感覺、超形象、無(wú)始無(wú)終,具有普遍性特征(相對(duì)于天道自然觀的局限性而言)的實(shí)體,以反映宇宙間最普遍的規(guī)律。”
按照他的這種理解,既然老子提出“道”是為了超越傳統(tǒng)天命論中的上帝主宰論,那么老子所理解的道與天道便不再具有濃厚的宗教神秘色彩,這也為荀子對(duì)天的自然式理解在理論資源上創(chuàng)造了條件。同時(shí),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四庫(kù)全書總目提要·經(jīng)部·易類序》)的思維理路也對(duì)荀子在人性上的認(rèn)知產(chǎn)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荀子·性惡》曰:“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xué),不可事。”這就為荀子后來(lái)在性偽二分的基礎(chǔ)上,以化性起偽的方式發(fā)掘與確立人的主體性奠定了理論基礎(chǔ)。
在對(duì)天人關(guān)系的理解上,韓非在荀子天人相分的理論基礎(chǔ)上更進(jìn)了一步,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放在了如何治世與強(qiáng)國(guó)上。受老子的影響,荀子對(duì)天往往持自然式的理解,并無(wú)顯著的道德色彩。與此類似,韓非對(duì)道也持有這樣的認(rèn)知方式,而有所不同的是,他雖然借鑒了老子的道,但主要采用了道的規(guī)律義和法則義,并將其與治國(guó)之術(shù)相結(jié)合,以切實(shí)服務(wù)于強(qiáng)國(guó)的政治目標(biāo)。韓非對(duì)道的這種理論建構(gòu),我們不妨稱之為對(duì)道的政治化處理,這其實(shí)在老子那里已露端倪。在《道德經(jīng)》文本中,屢次出現(xiàn)“圣人”一語(yǔ),圣人不仁、不自生,無(wú)為、無(wú)執(zhí),是道的自然性質(zhì)在圣人身上無(wú)為的體現(xiàn),
對(duì)此白奚也說(shuō):“老子是為最高統(tǒng)治者(‘侯王’)建言,不關(guān)注‘臣’的層面,‘無(wú)為’和‘無(wú)不為’的主體始終都是‘道’和法‘道’而行的‘圣人’。”
依此來(lái)看,《道德經(jīng)》文本確實(shí)有將圣人作政治化處理的一面,并以道化了的圣人形象來(lái)要求和規(guī)范在世侯王,從而將道與圣人以政治言說(shuō)的方式有意進(jìn)行了鉤聯(lián)。有所不同的是,韓非雖然借鑒了老子的道,但實(shí)際上更加重視由“道”所衍生出的理、法、刑、名這一類彰顯“道用”的思想理念,以及道在馭臣、治國(guó)上的實(shí)踐與運(yùn)用,張岱年將此理路稱為“以理解釋道”。
故而與老子言說(shuō)道的時(shí)候,主要指向最高統(tǒng)治者并為其建言有所不同,韓非言說(shuō)道和道用的對(duì)象則有所擴(kuò)大,不僅指向了最高統(tǒng)治者,而且還包括臣僚百官在內(nèi)的一般治國(guó)者。當(dāng)然,由于韓非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并不在天人關(guān)系本身,他對(duì)人的本質(zhì)、人存在的價(jià)值及合理性等問(wèn)題也沒有多少理論興趣,再加上他同荀子一樣對(duì)天作了自然主義式的理解,故而韓非關(guān)注更多的是如何治世(治世的手段與方式)、為何如此治世(治世的依據(jù)及合理性)以及治世的有效性等問(wèn)題,彰顯了其務(wù)實(shí)理性的特點(diǎn)。
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歷經(jīng)春秋晚期與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這樣大的時(shí)間跨度,整個(gè)天下在政治體制上逐漸呈現(xiàn)出從貴族政治向君主集權(quán)政治過(guò)渡的趨勢(shì)。這反映在政治文化上的建構(gòu)方面便是在以道和道用為討論中心的時(shí)候,其言說(shuō)對(duì)象已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在走向君主集權(quán)政治的過(guò)程中,地域性國(guó)家新形成的統(tǒng)治集團(tuán)顯然已逐步打破了過(guò)去那種貴族世卿世祿的人員構(gòu)成模式,韓非在政治文化建構(gòu)上言說(shuō)對(duì)象的擴(kuò)大便是對(duì)這種現(xiàn)實(shí)政治權(quán)力發(fā)生變化的真實(shí)反映。
二、人性理論:性樸欲趨惡論與治世工具
荀子對(duì)于天人關(guān)系的理解,并不似孔孟那樣具有濃厚的“天人合一”式的思維理路與特點(diǎn),諸如“下學(xué)上達(dá)”(《論語(yǔ)·憲問(wèn)》)、“與天地參”(《禮記·中庸》)、“盡心,知性,知天”(《孟子·盡心上》)此類思想都體現(xiàn)出了這樣的特點(diǎn),而是以對(duì)天、人各自功能進(jìn)行限定的方式對(duì)于天人之間的關(guān)系加以處理,是謂“天人相分”(《荀子·天論》)。由于荀子對(duì)天作了自然主義式的理解,故而其視野下的天自然無(wú)法像人格神那樣對(duì)于人事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yù),其對(duì)世間的影響主要集中在生物以及在生物的過(guò)程中對(duì)物的性質(zhì)與特點(diǎn)的賦予等方面。在傳統(tǒng)語(yǔ)境下,物既包括萬(wàn)物,還包括人和事。所以,生物也包括人的生成以及人性的成就,故而荀子言謂:“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xué),不可事。”(《荀子·性惡》)依荀子對(duì)天人關(guān)系的新建構(gòu),以及對(duì)人性的自然式理解,我們首先可以承認(rèn)荀子對(duì)人性的判斷確實(shí)有自然人性論的一面,也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對(duì)于荀子人性理論所產(chǎn)生的影響,故而筆者對(duì)于學(xué)界有些學(xué)者對(duì)荀子人性理論作出“性樸”的詮釋
是認(rèn)同的。
性樸是基于荀子整體思想結(jié)構(gòu)(包括天人關(guān)系、性偽之分與性欲之別等方面)與運(yùn)思理路作出的判斷;性惡則出自《性惡》篇,實(shí)指情惡、欲惡。依《性惡》篇的整體思路來(lái)看,性惡并非是說(shuō)性本身為惡,而實(shí)指情惡、欲惡,故而筆者將荀子的人性理論整體特征判定為“性樸欲趨惡論”。
由于情、欲處于性物之間,是性由樸的狀態(tài)發(fā)動(dòng)起來(lái)呈現(xiàn)為或善或惡樣態(tài)的中間橋梁與環(huán)節(jié),而在性發(fā)動(dòng)起來(lái)的過(guò)程當(dāng)中具有理性思維功能與道德辨知能力的心也會(huì)參與進(jìn)來(lái),是故這樣的心參與程度的深淺便是人不偽、少偽或能偽的具體表現(xiàn)。對(duì)于具有大清明之心的圣人而言,其心的參與程度自然是最深的,但這樣的人對(duì)于整個(gè)社會(huì)而言是少數(shù);就大多數(shù)人而言,“偽”的程度比較低,往往沒有多少自覺性與主動(dòng)性,故而禮義法度與師法教化的作用便在民眾教化與社會(huì)治理方面得到了很好的體現(xiàn)。
《荀子·性惡》對(duì)此多有陳說(shuō):“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后出于辭讓,合于文理,而歸于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惡,以為偏險(xiǎn)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dǎo)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故圣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圣人之所生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圣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后始出于治,合于善也。”可以說(shuō),荀子對(duì)于禮義法度與師法教化的重視首先與其對(duì)戰(zhàn)國(guó)晚期社會(huì)現(xiàn)狀、對(duì)于人的欲情的認(rèn)知有關(guān)。在荀子看來(lái),當(dāng)時(shí)社會(huì)上的大多數(shù)人在面對(duì)名利地位的時(shí)候,并不能很好地操持自己的欲情,反而在外物的誘導(dǎo)下容易喪失自我,這自然不符合儒家的立場(chǎng)。同時(shí),荀子又對(duì)孔孟的道德優(yōu)先立場(chǎng)并不完全認(rèn)同,故而對(duì)禮儀法度和師法教化更為重視,并試圖以此來(lái)矯正人的欲情,從而使天下政治重回清平盛世。
不可否認(rèn),荀子對(duì)政治社會(huì)治理的認(rèn)知,脫離不了其在天人關(guān)系新構(gòu)架下對(duì)人性作出的創(chuàng)造性理解。荀子一方面受到老莊道家的影響,對(duì)于人性的理解持有一定的自然主義立場(chǎng),故而我們沿用學(xué)界所謂的“性樸”;另一方面,基于對(duì)人的欲情容易流于惡的境地的判斷,荀子不相信僅憑德性修為或者柔弱謙下的品質(zhì)就可以使人們變得良善不爭(zhēng),故而他在“性偽二分”的基礎(chǔ)上,強(qiáng)調(diào)相較于“性”,“偽”才是人的本質(zhì),并以經(jīng)由“解蔽”實(shí)現(xiàn)了“大清明”之境地的圣人所制定的禮義法度來(lái)作為民眾教化與社會(huì)治理的依據(jù)與手段。可以說(shuō),荀子對(duì)于人性的理解,既受到道家的影響,同時(shí)還摻雜了一定的法家化特征,彰顯了荀子所具有的集大成特點(diǎn)和諸子文化在經(jīng)歷了春秋晚期與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不斷交流、碰撞以后所逐漸形成的融合互補(bǔ)的特點(diǎn)。
(3)水旺莊礦區(qū)控礦深度超過(guò)-2200m,而長(zhǎng)達(dá)110km的招平斷裂其他區(qū)域勘查深度多在-1500m左右,水旺莊深部找礦突破進(jìn)一步拓展了招平斷裂深部找礦的空間。
與荀子有所不同,韓非對(duì)于人性的理解往往出于現(xiàn)實(shí)政治的需要,從國(guó)家治理的角度來(lái)討論人的問(wèn)題,并沒有完全如孔孟、老莊那樣將人置于天地關(guān)系當(dāng)中去認(rèn)知與把握。這是因?yàn)轫n非處于戰(zhàn)國(guó)晚期,統(tǒng)一趨勢(shì)愈加明朗化,隨著自然科學(xué)知識(shí)的進(jìn)一步豐富,人文理性精神得到了進(jìn)一步發(fā)展。韓非在討論人的時(shí)候,并沒有接續(xù)三代以來(lái)天人關(guān)系的思維框架,反而脫離了天人關(guān)系的約束來(lái)談?wù)撆c人有關(guān)的一系列問(wèn)題。這樣的處理方式,可以使他能夠更加從容、理性地談?wù)撜我曇跋碌娜耍M(jìn)而更好地挖掘、闡述人的特點(diǎn)、人的政治行為以及人與政治的關(guān)系等內(nèi)容。
不僅如此,歷經(jīng)春秋晚期到戰(zhàn)國(guó)中期的發(fā)展,諸子對(duì)天人關(guān)系以及人的本質(zhì)、人存在的價(jià)值與合理性等帶有哲學(xué)意蘊(yùn)的思想命題已經(jīng)進(jìn)行了較為充分的探討,再加上統(tǒng)一戰(zhàn)爭(zhēng)形勢(shì)的愈加激烈與殘酷,使身處天下統(tǒng)一前夜的韓非將理論視野與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如何運(yùn)用人性的特點(diǎn)來(lái)更好地治世上,而上述帶有哲學(xué)意蘊(yùn)命題的討論雖然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政治主張的價(jià)值根源與形上依據(jù)的問(wèn)題,但無(wú)法迅速切中時(shí)務(wù)。
正如上文所言,人性生來(lái)如此,“欲利之心”(《韓非子·解老》)不可去,計(jì)較利害便是人之常情,故韓非對(duì)人性并不作善或惡的價(jià)值判斷。基于此,韓非強(qiáng)調(diào)“凡治天下,必因人情”(《韓非子·八經(jīng)》),所謂的“因人情”即是依據(jù)人的趨利避害之心來(lái)治國(guó)理政,如此通過(guò)刑德(賞罰)二柄便足以達(dá)到富國(guó)強(qiáng)兵、稱霸天下的目的,從而形成了自然之性(強(qiáng)調(diào)生來(lái)如此)—不免于欲利之心(強(qiáng)調(diào)趨利避害)—刑德二柄(強(qiáng)調(diào)刑名法術(shù)之用)—富國(guó)強(qiáng)兵(維護(hù)君權(quán))的政治哲學(xué)邏輯鏈條。這樣的政治哲學(xué)鏈條通往的是對(duì)君國(guó)利益的極端維護(hù),而對(duì)民眾利益則采取了相對(duì)漠視的態(tài)度,如此實(shí)現(xiàn)國(guó)富兵強(qiáng)的目標(biāo)卻是以民貧為代價(jià)的,這既不合乎孔孟的仁政王道理想,也不合乎荀子所言的“重法愛民”的霸道標(biāo)準(zhǔn)。余治平認(rèn)為,依法家精神治國(guó)的秦國(guó),“近百年來(lái)的政治道路和發(fā)展模式選擇既不合王道,因?yàn)樗挥萌逍g(shù),只注重以力服人;也不合霸道,因?yàn)樗鼑?guó)強(qiáng)民弱,依然國(guó)富民窮,百姓過(guò)得很苦逼。”
結(jié)合我們上文的分析來(lái)看,這種論斷是成立的。
現(xiàn)實(shí)的政治目標(biāo)使韓非雖然認(rèn)識(shí)到人性生來(lái)是自為自利的,并由此導(dǎo)致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呈現(xiàn)出利害化的一面,但他并沒有對(duì)人性進(jìn)行善、惡的價(jià)值判斷。一方面,他明確反對(duì)儒家以人性中的道德因素(或曰內(nèi)圣)作為政治制度設(shè)計(jì)和政治治理依據(jù)的思維理路,從而將人的道德修養(yǎng)與政治價(jià)值的實(shí)現(xiàn)相剝離,在人的道德修養(yǎng)之外尋求政治價(jià)值實(shí)現(xiàn)的手段與途徑;另一方面,人性變成韓非視野中政治理論建構(gòu)和政治治理可資利用的工具,由此人性便被俗化為功利性的治世工具,使人的主體性在現(xiàn)實(shí)政治面前最終被弱化不少,人隨之也被有意地窄化成了政治權(quán)威的附庸。
三、政治哲學(xué):道德于政治領(lǐng)域的弱化與政治的去道德化
與荀子在人性論上所持的“性樸欲趨惡論”相比,韓非在這方面走得更遠(yuǎn)。雖然荀子強(qiáng)調(diào)性樸和欲趨惡,但他畢竟還認(rèn)為人性可化、欲可節(jié)可導(dǎo),而且《荀子》文本所言的“心”還具有一定的理性思維功能與道德辨知能力。與此不同,韓非對(duì)人性并未作善惡的性質(zhì)判定,他不僅認(rèn)為人性生來(lái)如此,而且認(rèn)為人性是不可化的,所以他并不像孔孟那樣分別強(qiáng)調(diào)“推及”工夫和“擴(kuò)充”工夫,也不似荀子那樣十分重視師法教化,而是提倡“以吏為師,以法為教”。《韓非子·五蠹》云:“故明主之國(guó),無(wú)書簡(jiǎn)之文,以法為教;無(wú)先王之語(yǔ),以吏為師;無(wú)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所謂的“無(wú)書簡(jiǎn)之文”和“無(wú)先王之語(yǔ)”,實(shí)際上是說(shuō)道德訓(xùn)誡和師法教化對(duì)于好利惡害、皆挾自為心的百姓而言并無(wú)多少實(shí)際效果,力主將律法內(nèi)容和法吏權(quán)威滲透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以此來(lái)約束和規(guī)范百姓的言談舉止與行為方式。
既然欲望對(duì)于每個(gè)人而言是普遍的,那么如何對(duì)待欲望便是所有人都需要面對(duì)的問(wèn)題,而對(duì)待欲望的方式之不同又成為圣賢與涂之人的重要區(qū)別。對(duì)于涂之人而言,由于深陷生存與生活的諸多困境之中而對(duì)欲望所可能產(chǎn)生的消極性影響缺少基本認(rèn)知與必要警覺,從而在個(gè)人自覺能動(dòng)性方面就顯得沒有那么強(qiáng)烈,所呈現(xiàn)出來(lái)的狀態(tài)是難偽或不偽,如此便無(wú)法充分應(yīng)對(duì)欲望因受外界的誘惑而在民眾中間出現(xiàn)的爭(zhēng)斗現(xiàn)象,在這種情況下便可能導(dǎo)致政治失序、社會(huì)混亂局面的出現(xiàn)。如此,禮義法度與師法教化的價(jià)值與作用便體現(xiàn)了出來(lái)。
誠(chéng)如上文所言,天能生物,卻不能辨物;地能載人,卻不能治人;人能辨物、能治人,卻不能生物:由此來(lái)看,天、地、人三者在荀子眼中是各有功用又各有局限與不足的。細(xì)而言之,荀子視域中的天與傳統(tǒng)意義上的天已有了很大不同,在使天原來(lái)所具有的宗教神秘色彩被弱化的同時(shí),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天從人事領(lǐng)域被剝離了出來(lái),除了能夠生物、賦予物的性質(zhì)與特點(diǎn)以外,對(duì)于人事領(lǐng)域的干預(yù)與影響已大為弱化。與天有所不同的是,地能載人,此說(shuō)與《坤卦·彖辭》“至哉坤元,萬(wàn)物資生,乃順承天”相應(yīng)。可見,地載物之性能是上承天而來(lái)的,故《正義》云:“‘坤’是陰柔以和順承奉于天”,“以其廣厚,故能載物”;
《本義》又云:“順承天施,地之道也。”
對(duì)此,楊慶中也說(shuō)“‘順承天’,喻天施地生之義”,
所言非虛。盡管地因其廣厚而能載物,但其既不能如天那樣可以生物,也不能如人那樣能夠治人,故而在這里荀子實(shí)際上對(duì)天和地的職能有意進(jìn)行了區(qū)分與限定,這就為人主體性的顯發(fā)在天人關(guān)系方面做了必要的清理。
對(duì)于身處戰(zhàn)國(guó)晚期的荀子而言,其對(duì)政治哲學(xué)的建構(gòu)主要著眼于兩點(diǎn):一是“性樸欲趨惡論”的人性理論;二是吸納道、法兩家思想形成的新型圣人觀。就后者而言,《荀子》文本中的圣人呈現(xiàn)出了復(fù)雜性的一面。首先,《荀子》文本中的圣人仍然延續(xù)了孔孟對(duì)于圣人道德性一面的重視,進(jìn)一步強(qiáng)調(diào)圣人不同于涂之人的重要之處在于能偽、善偽、自覺能動(dòng)性強(qiáng),即“圣人之所以同于眾,其不異于眾者,性也;所以異而過(guò)眾者,偽也。”(《荀子·性惡》)荀子認(rèn)為,圣人經(jīng)由“偽”的工夫可以達(dá)致“大清明”的境地,而這種境地按照《荀子》文本提供的語(yǔ)境來(lái)看顯然不是惡的,最起碼是破除了對(duì)心的種種遮蔽之后所呈現(xiàn)出的理性狀態(tài),而這種理性狀態(tài)又是可以知善辨惡的。如此便與善不相違背,這也是荀子為何被歸入儒家而非法家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身處風(fēng)云際會(huì)的戰(zhàn)國(guó)晚期,政治社會(huì)發(fā)生劇變前的時(shí)勢(shì)讓荀子對(duì)于圣人的認(rèn)知又有著適應(yīng)于時(shí)代新形勢(shì)而不同于孔孟立場(chǎng)的一面,即增強(qiáng)了圣人創(chuàng)制禮儀法度方面的職能,如《荀子·儒效》即云:“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應(yīng)當(dāng)時(shí)之變?nèi)魯?shù)一二;行禮要節(jié)而安之,若生四枝;要時(shí)立功之巧若詔四時(shí);平正和民之善,億萬(wàn)之眾而博若一人;如是,則可謂圣人矣。”可以說(shuō),荀子對(duì)于圣人形象的改造,不只關(guān)注圣人之德,而且更為推崇圣人的外王之功,這自然體現(xiàn)了儒家對(duì)于現(xiàn)世侯王建功立業(yè)、解救民眾于水火的理想期許。
可以說(shuō),荀子對(duì)于圣人新形象的建構(gòu),既沒有放棄孔孟重視德性的一貫立場(chǎng),又在此基礎(chǔ)上對(duì)于圣人創(chuàng)制禮義法度的理性實(shí)踐功能給予了相當(dāng)程度的重視。荀子在圣人觀上的這種創(chuàng)建,正與舊制衰微尚未退場(chǎng)、新制開啟而未完全確立的時(shí)代特點(diǎn)及社會(huì)要求相適應(yīng)。在新舊制度交替的春秋晚期與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從對(duì)人的本質(zhì)及存在合理性的反思到轉(zhuǎn)向政治制度的設(shè)計(jì)是諸子從哲學(xué)思考向政治實(shí)踐的回落,而這一時(shí)期的政治實(shí)踐又受到長(zhǎng)于治世理論與制度設(shè)計(jì)的法家的影響,荀子雖守持基本的儒家立場(chǎng),但道德于政治領(lǐng)域的弱化也是其政治哲學(xué)理論的顯著特點(diǎn)。當(dāng)然,荀子建構(gòu)的新型圣人觀雖然弱化了道德在政治領(lǐng)域所起的作用,但并沒有完全放棄道德對(duì)于個(gè)體的積極影響,尤其是圣人經(jīng)由“虛壹而靜”而達(dá)致的“大清明”境地,這種境地經(jīng)過(guò)辨善知惡、好善惡惡以后完全可以視之為善的:“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焉”(《荀子·勸學(xué)》)。與此同時(shí),荀子強(qiáng)調(diào)圣人制禮義法度,重視師法教化,著重挖掘與闡述圣人的外王之功,而外王之功的實(shí)現(xiàn)又離不開位勢(shì)的支持,這實(shí)際上是強(qiáng)調(diào)在戰(zhàn)國(guó)晚期要想實(shí)現(xiàn)平治天下的理想目標(biāo),一味依賴圣人之德并不可靠,更要依憑圣人所擁有的位勢(shì),故而在《荀子》文本中不僅出現(xiàn)了“圣人”一語(yǔ),更是高頻次地出現(xiàn)了“圣王”這一詞匯,即“圣”與“王”的結(jié)合體,是“融合了道德權(quán)威與政治權(quán)威(權(quán)力)于一體的人”。
如此來(lái)看,荀子政治哲學(xué)思想既具有理性務(wù)實(shí)的一面,同時(shí)又沒有如韓非“將道德因素排除于政治之外”那樣極端,
而是在注重治國(guó)主張務(wù)實(shí)有效的同時(shí),也為民眾化性起偽成為圣人保留了一絲希望。
韓非政治哲學(xué)有著消解宗法倫理與宗族力量的現(xiàn)實(shí)用意,故而與荀子有意弱化道德在政治領(lǐng)域所起的作用相比,前者更為自覺地將道德從政治領(lǐng)域剝離出來(lái):“君通于不仁,臣通于不忠,則可以王矣。”(《韓非子·外儲(chǔ)說(shuō)右下》)“君不仁,臣不忠,則可以霸王矣。”(《韓非子·六反》)與孔孟思想理論的泛道德化傾向相比,韓非在理論建構(gòu)的過(guò)程中試圖將道德因素從政治領(lǐng)域清除出去的同時(shí),力主憑借客觀理性特點(diǎn)顯著的刑名法術(shù)來(lái)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治理與富國(guó)強(qiáng)兵。由于韓非急于建構(gòu)一套切實(shí)有效的政治理論,而這套政治理論又是建立在對(duì)儒家道德哲學(xué)反思基礎(chǔ)之上的,故而韓非摒棄了孔孟對(duì)于道德所持的泛化立場(chǎng),彰顯了其政治哲學(xué)的務(wù)實(shí)理性特點(diǎn),所以有學(xué)者將其稱為“不講原則、只求效用”。
在韓非的思想立場(chǎng)之下,甚至有張公門弱私家、以公代私的傾向,故而荀子入秦時(shí)曾看到如下景象并不奇怪:
2008—2017年招收的常州市第一人民醫(yī)院血液凈化專科護(hù)士培訓(xùn)基地的學(xué)員,總計(jì)89人,均為女性。其中2008年7人,2009年8人,2010年8人,2011年9人,2013年10人,2014年11人,2015年12人,2016年12人,2017年12人(2012年學(xué)員與其他培訓(xùn)中心合并,未列在觀察范圍內(nèi))。
2.2.2 母根栽植方式 為了研究母根栽植方式對(duì)種條生長(zhǎng)的影響,開展了先栽植后灌溉和先灌溉后栽植再灌水兩種方式進(jìn)行區(qū)組試驗(yàn)。試驗(yàn)采用一年生根樁,栽植株行距30cm×60cm。栽植后進(jìn)行常規(guī)撫育管理。進(jìn)行萌芽、生根及生長(zhǎng)量觀測(cè)。
入其國(guó),觀其士大夫,出于其門,入于公門;出于公門,歸于其家,無(wú)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黨,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荀子·強(qiáng)國(guó)》)
在荀子眼中,秦國(guó)官員做事高效干練,平時(shí)出入的皆為私家與公門,并無(wú)結(jié)黨營(yíng)私之心,常常將君國(guó)利益置于個(gè)人私利之上。很顯然,此時(shí)的秦國(guó)官員已深受法家理性務(wù)實(shí)精神的影響,正與韓非所強(qiáng)調(diào)的“凡人主之國(guó)小而家大,權(quán)輕而臣重者,可亡也。”(《韓非子·亡征》)“自環(huán)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韓非子·五蠹》)之公利高于私行的原則相應(yīng)。于此可知,君國(guó)具有價(jià)值上的優(yōu)先性,而個(gè)人利益則逐漸具有了很強(qiáng)的依附性,或者說(shuō),個(gè)人利益的實(shí)現(xiàn)有賴于君國(guó)在價(jià)值上的優(yōu)先滿足與實(shí)現(xiàn)。
整體上看,荀子在人性論上持有“性樸欲趨惡論”的立場(chǎng)與觀點(diǎn),而這樣的立場(chǎng)與觀點(diǎn)使其對(duì)孔孟修己仁愛、為政以德的主張并不認(rèn)同,反而認(rèn)為以道德介入政治的理路并不可靠。這是因?yàn)椋谲髯涌磥?lái),道德修養(yǎng)固然可貴,但現(xiàn)實(shí)情況卻是圣賢少涂人眾,敬慎修己并不見得對(duì)每一個(gè)人都是有效的,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如孔孟那樣自覺地去追求道德修養(yǎng)與品格提升。就荀子的思想理論來(lái)說(shuō),欲望在其思想體系當(dāng)中是一個(gè)非常特殊而重要的概念。一方面,荀子說(shuō)“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欲不可去,性之具也”(《荀子·正名》),“人生而有欲”(《荀子·禮論》),特別強(qiáng)調(diào)欲望是普遍的,在每個(gè)人身上都會(huì)存在,需要給予基本的滿足;另一方面,他又對(duì)于人欲易流于惡的境地深有警惕,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荀子·性惡》),名義上是說(shuō)人性的問(wèn)題,實(shí)際上集中針對(duì)的是人欲的問(wèn)題,兩者并不完全一致。
需要指出的是,荀子并沒有完全排斥天、地對(duì)人的影響,或者說(shuō)荀子在探究人的主體性的時(shí)候并沒有完全舍棄天人關(guān)系的整體架構(gòu)與思維框架,《荀子·禮論》即云“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王制》亦云“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wàn)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
這種思維理路在《易傳》那里也有體現(xiàn)。《易傳》屢言“君子以”,實(shí)際上強(qiáng)調(diào)人對(duì)天地的效仿,
這雖然不能說(shuō)對(duì)荀子在天人關(guān)系的認(rèn)知上毫無(wú)啟發(fā)的可能性,但老子對(duì)天自然化的理解顯然對(duì)荀子在天人關(guān)系的建構(gòu)上產(chǎn)生的影響更大。
與老子對(duì)人性的認(rèn)知相似,韓非對(duì)于人性同樣也沒有做善、惡的判斷。
雖然他們都認(rèn)為人是有欲望的,欲望太熾對(duì)于國(guó)家治理和社會(huì)發(fā)展會(huì)造成不良影響,但如何對(duì)待欲望,老子和韓非卻有著不同的認(rèn)知。老子主張懷素抱樸,以反向復(fù)道的方式化解欲望對(duì)于人素樸狀態(tài)的損害,進(jìn)而要求圣人以減少干預(yù)的方式治國(guó),如“不仁”(《老子》第五章),“無(wú)為”“無(wú)執(zhí)”(《老子》第二十九章),“無(wú)常心”(《老子》第四十九章),“不爭(zhēng)”(《老子》第八十一章)等等,希冀百姓以自化、自正、自富、自樸的方式生活:“我無(wú)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wú)事,而民自富;我無(wú)欲,而民自樸。”(《老子》第五十七章)與老子主張對(duì)人的欲望加以消解不同,韓非接續(xù)了荀子“欲不可去”(《荀子·正名》)的基本立場(chǎng),將人的欲望、趨利避害的人情視為制度設(shè)計(jì)與國(guó)家治理的重要依據(jù):“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韓非子·八經(jīng)》)欲望何以會(huì)成為韓非政治理論建構(gòu)的重要依據(jù)?這是因?yàn)橛哂酗@著的外在指向性,能夠與外界發(fā)生直接的聯(lián)系,所謂的趨利避害、自為心和計(jì)算之心無(wú)不與他人及社會(huì)相關(guān)聯(lián),而這種種的關(guān)聯(lián)便會(huì)產(chǎn)生實(shí)際行為后果,這在韓非的政治視域中便可以以政治與法律的手段來(lái)調(diào)節(jié)與控制。可以說(shuō),關(guān)于人性善惡的價(jià)值評(píng)判問(wèn)題并非韓非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他所關(guān)心的是如何以政治與法律的手段、措施來(lái)調(diào)控人的欲望,以使人的欲望與君主統(tǒng)一天下的意志相適應(yīng),
故而他政治理論創(chuàng)建的重心在于如何利用人的欲望來(lái)達(dá)到國(guó)家治理、富國(guó)強(qiáng)兵的現(xiàn)實(shí)目的。換句話說(shuō),韓非并不關(guān)心人性本身是什么、人性如何的問(wèn)題,他所關(guān)注的是人性在現(xiàn)實(shí)世界中如何投放的問(wèn)題——往往以欲情的形式展現(xiàn),進(jìn)而將其表現(xiàn)內(nèi)容經(jīng)驗(yàn)性地歸納,直陳趨利避害、皆挾自為心是欲情的本質(zhì)性特點(diǎn)。不可否認(rèn),人性本身確實(shí)有著復(fù)雜的一面,這從韓非之前的諸子對(duì)人性的闡述便可略知一二。對(duì)此,韓非并非毫不知曉,只是說(shuō)他重點(diǎn)關(guān)注的是與現(xiàn)實(shí)政治關(guān)聯(lián)度比較緊密的人性內(nèi)容,而這部分內(nèi)容在韓非看來(lái)正是人的欲與情。
與法家不喜儒術(shù),更注重以力服人相比,荀子畢竟還是主張王霸并重、王霸兼用的:“故用國(guó)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荀子·王霸》)“故尊圣者王,尊賢者霸。”(《荀子·君子》)“人君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荀子·強(qiáng)國(guó)》)“上可以王,下可以霸。”(《荀子·君道》)可見,荀子雖然重視具有信、尊賢和重法愛民特點(diǎn)的“霸”,但也沒有排斥具有義、尊圣和隆禮尊賢特點(diǎn)的“王”,雖然與孔孟相比已具有顯著的理性務(wù)實(shí)特點(diǎn),但并沒有偏離儒家一貫的立場(chǎng)。與荀子不同的是,韓非由于堅(jiān)持公利高于私行的立場(chǎng),其政治哲學(xué)不僅將道德與政治做了一定程度上的切割與剝離,而且還充分彰顯了他維護(hù)君權(quán)和君國(guó)利益的理論旨?xì)w。
硒是仔豬生長(zhǎng)發(fā)育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仔豬缺硒時(shí)突然發(fā)病,食欲下降,精神不振,關(guān)節(jié)腫大,癱瘓,嚴(yán)重者突然死亡,剖檢時(shí)可見肝壞死,肌肉蒼白、萎縮,心包積水等病變。發(fā)病特點(diǎn)是營(yíng)養(yǎng)狀況良好、生長(zhǎng)發(fā)育快的仔豬最先發(fā)病。仔豬3~5日齡肌注亞硒酸鈉0.5 ml,斷奶時(shí)再注射1 ml。
四、結(jié)語(yǔ)
我們主要從天人關(guān)系、人性論和政治哲學(xué)三方面對(duì)荀韓哲學(xué)思想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比較研究。關(guān)于荀子,學(xué)界主要從人性理論、禮法關(guān)系、孟荀關(guān)系以及荀學(xué)對(duì)漢代經(jīng)學(xué)的影響等方面展開了持續(xù)、深入的研究,而對(duì)于儒法關(guān)系尤其是荀韓關(guān)系而言,與前述其他方面相比研究得還比較薄弱,需要發(fā)掘的空間也很大。不可否認(rèn),諸子之間的關(guān)系是學(xué)界研究先秦哲學(xué)的重要問(wèn)題與學(xué)術(shù)熱點(diǎn),而對(duì)于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政治文化與政治哲學(xué)的研究又離不開對(duì)儒法關(guān)系當(dāng)中的荀韓關(guān)系進(jìn)行重點(diǎn)考察。
春秋晚期與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是中國(guó)古代政治制度發(fā)生轉(zhuǎn)型、新舊制度交替的重要?dú)v史時(shí)期,舊制度衰退尚未退出歷史舞臺(tái),新制度產(chǎn)生還未完全確立,諸子文化的產(chǎn)生與發(fā)展均離不開這一重要?dú)v史背景,諸子對(duì)現(xiàn)實(shí)政治的反思也是新舊制度交替在文化層面的投射。與春秋晚期思想文化形態(tài)有所不同的是,到了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儒道法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一步呈現(xiàn)出交流與互補(bǔ)的發(fā)展趨勢(shì),這既與其時(shí)日益嚴(yán)峻、復(fù)雜的社會(huì)歷史情形要求綜合、多元治國(guó)理論的出現(xiàn)相關(guān),也與自春秋晚期文化下移以后諸子文化之間不斷進(jìn)行交流、碰撞及相互吸收關(guān)系密切。
荀子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集大成者,這種集大成地位的確立離不開其對(duì)道、法、墨、陰陽(yáng)等派別思想的借鑒與吸收,以及在這種借鑒、吸收基礎(chǔ)之上的轉(zhuǎn)化與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經(jīng)由《荀子》文本,我們可以看到他在理論闡述過(guò)程中所顯示出的集大成特點(diǎn),以及他在應(yīng)對(duì)現(xiàn)實(shí)政治局面時(shí)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和所貢獻(xiàn)的政治智慧。與孔孟過(guò)于依賴政治權(quán)威與道德力量相比,荀子則采取了審慎的態(tài)度來(lái)應(yīng)對(duì)現(xiàn)實(shí)政治,既沒有完全舍棄儒家對(duì)于道德所持的肯定性立場(chǎng),同時(shí)又在反思道德泛化傾向的基礎(chǔ)上弱化了道德在政治領(lǐng)域的作用,強(qiáng)調(diào)和突出了禮義法度、師法教化等制度化建設(shè)在現(xiàn)實(shí)政治治理中的價(jià)值與意義。
與荀子相類,處于天下統(tǒng)一前夜的韓非的思想理論也同樣具有集大成的特點(diǎn)。與荀子有意弱化道德在政治領(lǐng)域的作用相比,韓非在這方面則走得更遠(yuǎn):“用法的客觀性來(lái)說(shuō)明執(zhí)法過(guò)程中應(yīng)盡量排除外在因素的影響和內(nèi)心情感的驅(qū)使,從而使客觀性的法既能夠與無(wú)私己性的道相合,也能在理論建構(gòu)過(guò)程中呈現(xiàn)出去道德化的個(gè)人主觀性努力。”
可以說(shuō),與荀子思想理論相比,韓非哲學(xué)思想的理性務(wù)實(shí)特點(diǎn)更為顯著,不僅在張公門弱私家的立場(chǎng)之下對(duì)于政治領(lǐng)域與私家私門進(jìn)行了有意區(qū)分,而且還依據(jù)人生來(lái)就有的趨利避害之心來(lái)治國(guó)理政,如此通過(guò)刑德(賞罰)二柄便足以達(dá)到富國(guó)強(qiáng)兵、稱霸天下的目的,從而形成了自然之性(強(qiáng)調(diào)生來(lái)如此)—不免于欲利之心(強(qiáng)調(diào)趨利避害)—刑德二柄(強(qiáng)調(diào)刑名法術(shù)之用)—富國(guó)強(qiáng)兵(維護(hù)君權(quán))的政治哲學(xué)邏輯鏈條。
可以說(shuō),荀韓在哲學(xué)思想上呈現(xiàn)出的這種既有繼承又有推進(jìn)的復(fù)雜關(guān)系,正反映了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政治制度由周制向秦制嬗變過(guò)程中所呈現(xiàn)出的復(fù)雜歷史面相。反過(guò)來(lái)說(shuō),這種復(fù)雜的歷史面相單純依靠儒家或法家的治國(guó)主張與政治智慧都不足以從容應(yīng)對(duì),惟有交流、互補(bǔ)與相互吸收甚至儒道法加以融合才會(huì)形成新型的并帶有一定綜合意義的思想理論,來(lái)順應(yīng)和助力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政治制度的嬗變。不僅如此,荀韓思想理論的互補(bǔ)與融合,到了秦漢時(shí)期依然在為中央集權(quán)政治制度的確立與穩(wěn)定發(fā)揮重要的價(jià)值與作用,無(wú)論是“以法治國(guó)”“陽(yáng)儒陰法”
等命題的提出,還是官制的設(shè)置與政治制度的具體運(yùn)行都說(shuō)明了這一點(diǎn)。
1.3 統(tǒng)計(jì)分析 將患者病理結(jié)果、隨訪結(jié)果與當(dāng)初CT 室、PET/CT 和多科(CT 室、PET/CT、呼吸內(nèi)科、胸外科醫(yī)生)MDT討論后的結(jié)果進(jìn)行對(duì)照,采用SPSS 19.0統(tǒng)計(jì)軟件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計(jì)數(shù)資料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yàn),以P<0.05為有統(tǒng)計(jì)學(xué)意義。計(jì)算HRCT、PET/CT、及二者聯(lián)合診斷SPN良惡性準(zhǔn)確率。準(zhǔn)確性(%)=(真陽(yáng)性人數(shù)+真陰性人數(shù))/總?cè)藬?shù)×100。
在新時(shí)代的國(guó)家治理體系建設(shè)與完善方面,我們應(yīng)充分借鑒先秦時(shí)期儒道法融合、荀韓思想理論互補(bǔ)的文化發(fā)展格局與經(jīng)驗(yàn),既充分重視制度規(guī)范建設(shè)又不放棄對(duì)于文明風(fēng)尚、道德素養(yǎng)的積極倡導(dǎo),從而使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政治文化重新煥發(fā)活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新征程貢獻(xiàn)應(yīng)有的智慧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