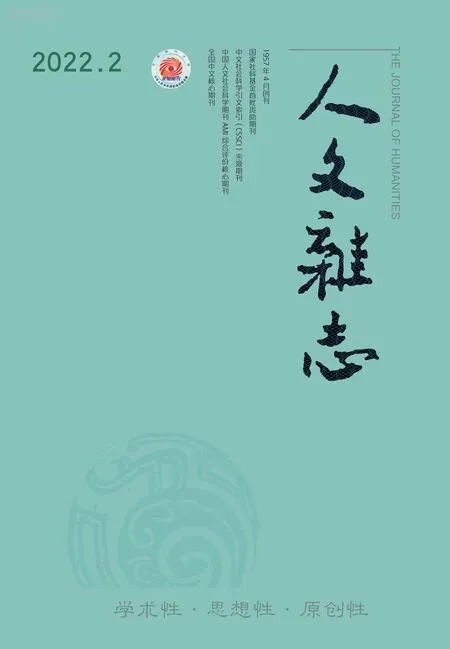從歷史真實到藝術創造性真實
——論宮廷劇的創造性路徑
宮廷歷史題材與現實生活題材的電視劇本來只是藝術創造的不同材料,并不存在價值高低的問題。但宮廷劇以曲折的宮斗為主要內容并持續熱播的現象,使得本來作為題材的宮廷歷史劇成為一種難以對權力爭斗文化的異化問題進行審視性思考的藝術,而宮廷劇在立意上的大同小異使受眾產生了“宮廷劇即宮斗劇”之錯位的理解。一方面,宮廷斗爭與中國先秦哲學在大利小利問題上思考善惡問題的哲學關系從未被編導作當代哲學的審視,使得眾多宮廷劇只能迎合當代觀眾趨利避害的趣味而淡化了超功利的哲學啟示意義,是宮廷劇缺乏藝術創造性動力的原因;另一方面,愛情、友情、親情和生命關愛之情的復雜關系又常常被納入皇權文化框架中充當犧牲品,這不僅放逐了中國遠古生命神力呵護百姓生命尊嚴的生命力之信仰,使皇帝和皇妃們復雜的生命世界難以得到展示而隱遁,你死我活的斗爭快感助長了觀眾非現代性藝術趣味,也是宮廷劇雖然熱播但不能在文化上影響現代世界之原因。雖然國內近幾十年宮廷劇熱播是一種依附傳統權爭文化的弱創造性藝術現象,但是其中的一些亮點作品卻也值得我們在創造性問題上探究一二,故本文提出的“創造性路徑”問題,或許可以使宮廷劇創作從市場化效應考量走向經典化弱市場之考量。
蒜瓣特別脆嫩且沒有外殼保護層, 排種時, 蒜瓣既不能擠壓也不能排絞, 針對該狀況以及大蒜的不規則外形,研制出一種圓盤轉勺式大蒜取種盤。該播種機的排種盤上固定了多個取種窩,取種窩根據大蒜的形狀來設計;排種盤的直徑是根據大蒜株距、排種盤上的取種窩數、大蒜播種機的行走速度而確定的,從而設計出帶有取種勺的圓盤,如圖3所示。
一、怎樣理解“創造性路徑”
在對文學藝術作品的評價中常常會有這樣的現象:評價者有什么樣的文化價值觀念,便容易看到與這種價值觀念相匹配的文化性內容,比如用中國文化中負面性的“追名逐利”“勾心斗角”等觀念去創作和鑒賞,相應地,設計的“逐”“斗”情節就越驚險越好,至于編導要表現什么樣的哲學思考則不得而知。如果用正向的價值觀念,便容易設計或看到“清廉無私”“純潔天真”的形象和內容,不符合這些觀念的生命內容就會被忽略。中國近年拍攝的宮廷劇,壞人不是爭寵爭位就是嫉妒暗算,好人不是犯傻倒霉就是命運悲慘,“無私”和“純真”后面是否有編導批判創造性的審視意味,“勾心斗角”后面是否會有復雜的動因及其行為的自我消解,
自然都不會被追問。所以“宮斗”是一個典型的非藝術性非創造性的文化類型概念——從《金枝玉葉》到《甄嬛傳》再到《步步驚心》,從《延禧攻略》到《如懿傳》,如果缺乏藝術穿越文化的批判創造性思維,我們就會忽略對這些表面似乎大同小異的宮廷劇情“后面還有什么特殊內容和意味”的思考,上述作品的創造性內容之差異就會被遮蔽。“宮斗”的消極性不在其對爭利智謀文化之宣揚,而在其缺失了如何被批判、被審視的藝術創造性。
這種評價模式在文學經典研究中由來已久,某種意義上已形成文學批評的通約性文化。諸如《水滸傳》是“忠孝節義”,《金瓶梅》是“權色合謀”,《西游記》是“斬妖除魔”,《三國演義》是“權謀斗智”……這些作品顯在的情節、故事和人物內容上與儒道佛文化內容相輔相成,也與中國的權力和利益文化的追逐相輔相成,教化影響讀者的同時又被讀者的價值取向所支撐。這種“文化決定文學”的思維方式會將“藝術的創造性問題”限定在“表達”層面上,所謂的文學性藝術性就化為性格鮮明、人物傳神、故事跌宕、情感豐沛等表征,文學性和藝術性似乎淪為更好地接受文化教化和啟蒙的手段。文學有沒有突破文化思維,顯示出藝術家對世界獨特的哲學性理解,這種獨特理解會派生怎樣的情節故事與人物的復雜關系并突破既定的創作方法?這個問題在文藝評論中一直沒有受到重視。于是,上述文學經典是因為這些文化性內容的生動展現成為可能,還是因為作家的獨特理解與文化性內容形成批判性的張力?這些問題也就成為文藝評論中的一個盲點性議題。
“創造性路徑”是由“創造性”和“路徑”組成的復合性概念。“創造性”是極其個體化的,一般包含創造程度較高的“獨創”和創造程度較低的“弱創”,
是一個內涵寬泛的概念。在經驗的意義上使用這個概念,評論家往往不會深究“創造程度高低”的問題,從而在創造性問題上容易似是而非。“獨創”是指藝術家對世界有獨特的哲學性理解,形成獨特的人物形象和意味,給人以突破既有文化觀念的啟示,把握以哲學化的方式投射在人物及情節的能力,自然就成為藝術性較高的評價尺度;而“弱創”是指藝術家依附某種文化觀念進行再闡釋,其闡釋可以被既定的文化所概括而具有觀念教化的功能。比如電影《血戰鋼鋸嶺》建立了“戰爭的本質是拯救生命”的藝術性理解,海明威《永別了,武器》建立了“戰爭即罪惡”的文學性理解,均突破了“正義戰爭”的常識性文化觀念,這就比《戰狼2》在“正義對抗邪惡”的文化框架內書寫拯救海外僑胞的故事更具有創造性。同樣,韓國宮廷劇《大長今》以“推倒眾人之墻的自我創造性實現”賦予長今獨特的人生信念,不僅突破了儒家的“眾怒難犯”的倫理哲學,而且以“大長今”身份離開宮廷去關懷百姓生命為宗旨,這就比韓國宮廷劇《皇后的品格》通過權力斗爭獲得個人愛情幸福的內容更具有創造性。
3.將0.5片氟哌酸(含量0.125 g)與3~5 ml蜂膠酊混合后給仔豬灌服,一般連服2~3劑即可。蜂膠酊可用蜂膠溶解在95%的酒精中制成,濃度以20%為宜。
二、路徑一:呵護被權力爭斗輕視的生命與生命力
在藝術創造的內容上,尊重生命的愛欲、情欲、個性、意志并予以關愛,是突破儒道文化規范使藝術獲得創造性的根基;而捍衛生命上述內容之尊嚴展開的抗爭,則顯示出生命和中國儒道文化互動的生命力。文化以強大的觀念力量消除生命與文化的矛盾張力,使得生命文化化,藝術則通過放大這樣的矛盾張力去突出藝術穿越文化的品格,呵護生命和生命力的藝術性,這是藝術創造的基本內容。所以寶玉的嬉戲,豬八戒的食色,周瑜的狂傲,分別與孱弱道化的黛玉、輕欲殺生的悟空、愚孝無愛的李逵、智謀無敵的諸葛亮構成的藝術張力,才是作品復雜關系產生的原因。其間既有生命的人性內容的展現,也有生命為捍衛這種人性內容的力量抗爭。丫鬟的自殺、八戒的怠工、燕青的游走等,均是各種生命力自我展現的方式。
2015年版《中國藥典》含片溶化性檢查方法調整的回顧………………………… 尚 悅,洪小栩,劉永利(3·190)
中國宮廷劇之所以以權力爭斗的文化為其主要表現內容,離不開儒家倫理的血緣等級、法家的權力至上一起構成的運轉系統,要求所有的個體生命遵從其最終的大利大義訴求,于是生命的尊嚴、愛情的神圣、性欲的自然、個體的權利常常是被遮蔽的。依附于儒法文化的宮廷劇自然會以生命的扭曲、犧牲、摧殘、受辱為權爭文化做鋪墊,友情、愛情、親情、性愛也隨時會為權力和利益爭斗做犧牲。轟動一時的《甄嬛傳》在此方面有著淋漓盡致的表現:華妃為了自己的愛情和家族延續走上了絕路,而甄嬛則扮演了賜藥酒給心上人果郡王的角色,一死亡一騰達,價值追求卻是一致的。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之所以是兩回事,藝術創造的態度之所以不同于文化現實的態度,是因為藝術創造可以改變對歷史真實的理解,其意義不僅是在虛構一個世界,而且是根據藝術家的獨特理解來建構一個性質和意味上不存在的世界。只有接觸到“性質和意味上從來沒有過”
這個問題,藝術性與創造性才被打通。所以對《甄嬛傳》來說,友情生命和愛情生命沒有與權力和利欲構成相互纏繞的關系,這些生命就成為甄嬛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了,這是這部電視劇藝術上的最大遺憾。而《延禧攻略》的“攻略”之所以有創造的意味,則因為該劇發掘了生命自尊的魅力,某種意義上,與權力和利益展開了對等的互動。
第一,宮廷劇中藝術虛構的生命之愛可以是多元復雜的,既可以削弱男女之愛的中心地位,也會減弱權力和婚姻對生命之愛的支配關系。權力一旦只能呵護男女之愛,便自然會忽略對普通生命的關愛。將愛的關系復雜對等化,權力和功利考量就容易顧此失彼,降格為多元中的一元。《步步驚心》中的若曦不僅處在愛情和權力的關系中,在愛情中她還身陷不同的愛之關系中。一般作品是把友情與愛情相區別對待,也會把親情、愛情和婚姻區別對待,犧牲友情成全愛情、犧牲愛情成全親情、犧牲婚姻成全權力,是我們的現實生活中常見的文化關系。但是當若曦把身邊侍女玉檀的親情看作不低于愛情的感情并為此抗爭的時候,當若曦維護曾經喜歡的八阿哥的時候,當若曦對十三阿哥的信任某種意義上超過對四阿哥的時候,這就是一種區別于男女之愛的“多元并立的情感”了,同樣抵達了忘我的愛之境界。這種復雜,某種程度上已經將若曦愛的豐富性襯托出來了:她要珍視的是所有身邊的人并達到與自己的愛情對等的狀態。同樣,《延禧攻略》里的瓔珞不僅處在自己的戀人和皇上的兩難選擇之中,也同樣承擔捍衛自己親人的生命價值之責任。瓔珞的親人不僅有自己死去的姐姐,還有紫禁城所有可能會死去的弱小生命,這就與《甄嬛傳》中只是為了自己父母生存的掙扎奮斗有了區別。瓔珞具有其他宮廷劇所沒有的憐惜所有的生命之情,與傳統意義上的愛情、友情、親情糾葛在一起,她就不可能去殺害或污辱任何一個人,哪怕這個人是自己的對手。如果說“人”的文化與“仁”的文化的根本區別在于前者尊重人,后者是等級性地對待人,那么若曦和瓔珞當然就屬于在“仁”的文化中生存的“人”,構成了“仁人互動”的藝術張力。
文物解說詞的英譯旨在通過輸送信息,吸引游客并實現文化的輸出。文物名稱過長和語法失誤降低了英譯語言的可讀性,而信息單一和文化內涵的則無法滿足受眾的信息需求和跨文化的交際目的。這要求我們要培養英語思維,提高專業素養。其次,要充分考慮中西方文化差異、語言差異,充分發揮譯者主體性,通過合理摘譯傳遞文化信息。最后,我們應充分考慮到受眾的閱讀習慣,借鑒歐美知名博物館文物解說詞的謀篇布局以實現故宮的外宣,實現跨文化交際的目的。
以此類推,在情感復雜性上理解人物,人物的單面性會被克服,皇帝不會千人一面,而更具有個性。藝術將生活復雜化,不僅愛情可以是復雜的,友情可以是復雜的,婚姻甚至也可以是復雜變化的,當然與之發生關系的權力也可以是復雜的甚至被架空或利用。即生命中的各種情感關系雖然會圍繞權力和利益沖突而展開,但由于其各自的復雜性構成的內在交錯的張力,往往會體現出疏離、消解權力和利益的意味,最后產生審視和互動既有文化觀念的藝術效果。
第二,傳統倫理文化強調個人的愛情、親情和友情在“大義”面前都是可以放棄的,“舍生取義”作為文化之“義”就很難被導演和觀眾重新審視,這是缺乏批判創造性思維的體現。當乾隆對瓔珞說“朕是一國之君不可能有愛情”時,是可以讓我們審視“國君”和“皇后”是否具有呵護生命的一面的。《延禧攻略》在這個問題上以對“義”的改造顯示出編導的獨特思考:只有對生命不可被傷害之尊嚴的優先捍衛,才是屬于現代性地對“義”的獨特理解,也才是唯一可以優先于愛情的“義”。因為只有生命的尊嚴被捍衛,才不會愛得屈辱;只有人格的獨立被尊重,愛情才不是身心的依附;只有生命不被隨意污辱殘害,愛情才不會是生命的乞憐。瓔珞對傅恒有情卻冷酷,傅恒對瓔珞有情卻不追,多數觀眾很難理解,但正是這樣的不理解才凸顯出該劇對愛情的獨特理解:在瓔珞懷疑傅恒的過程中傅恒的愛依然堅定,乃至最后犧牲自己拯救瓔珞的生命,是真愛之顯現。傅恒理解瓔珞的冷酷是以捍衛生命尊嚴為人生第一要義的,瓔珞始終不正面回答自己是否愛乾隆,則隱喻瓔珞對傅恒之愛的理解與守護,這應該是一種有獨特意味的非現實化的心心相印。
第三,從《步步驚心》中的若曦和《延禧攻略》中的瓔珞身上,我們已經能看出捍衛生命尊嚴的不同方法:若曦是用離開宮廷的方式拒絕四阿哥對她身邊侍女的殘害,某種意義上使若曦將生命尊嚴看得比自己的愛情更為重要。雖然這種捍衛生命的方式很難阻止四阿哥摧殘宮廷里的生命,但至少有一些效果。若曦最后希望把宮廷里的人全部忘記,雖然宣告的是她呵護生命努力的失敗,但若曦并沒有把生命的捍衛與自己的愛情看成你死我活的斗爭關系,而是看成親情、友情、愛情都重要的平衡對等關系。比較起來,瓔珞對乾隆無愛卻有歡,只在于瓔珞意識到生命尊嚴的捍衛也可以用權力來呵護,區別于追逐權力之個人利益為目的,這是瓔珞的智慧高于他人的方面。瓔珞對傷害自己和富察皇后的高貴妃、嫻皇后也以牙還牙,這既是生命力之“不順從”之顯示,也是權力毀滅不了生命尊嚴的表現。嫻貴妃作為有權力者對無權力者瓔珞的忌憚,是智慧生命的強大力量對抗權力的結果。關鍵不在生命的個性展示而在對生命魅力的呵護,所以嫻貴妃最后問瓔珞,乾隆為什么喜歡她,瓔珞答:“你喜歡皇上,為什么要說出來呢?”這正是瓔珞對自己生命魅力力量之顯示,也是文化性智慧可以被生命自我捍衛所利用的創造性智慧之體現,所以,也與文化性的“反抗權力”之平庸相區別。
三、路徑二:生命的不同情感與文化構成復雜的張力
經典藝術的敘事寫人往往以生命的復雜意味突破文化清晰的觀念指向,使得文化觀念的現實性強大和藝術體驗的虛擬性強大互有高低,從而構成對等互動的效果。由互動產生的豐富意味在觀眾的內心體驗想象中形成的審美力量,能產生消解文化現實性力量的功效,從而為藝術家對世界的獨特理解提供支撐。而這樣的復雜和豐富,主要是在情感世界中體現出來。
所謂創造性“路徑”
,意味著藝術家基于創造性追求的信仰形成有價值取舍的基本思維方式,從而進行各自不同的批判創造性努力。由于任何文化總是對生命的規范和要求形成理性的、倫理的、宗教的世界,藝術從屬于文化的要求則創造性較弱,突破文化的各種要求形成藝術對文化的審視和批判張力,則創造性較強,這就使得藝術的創造性路徑是圍繞生命與文化的緊張關系而展開的。從中國宮廷劇對此關系展開自己的創造性努力來看,大致形成以下三點可以深入研究的路徑。
當生命對世界的情感體驗與文化形成復雜的互動關系,這種關系就形成了突破既有文化框架的審美態勢。但藝術家這個時候不能選擇自己所認同的文化觀念來理解這樣的關系,而應該基于這樣的關系來建立自己對世界的藝術性理解。由于藝術的非觀念化和文化的觀念化之區別,藝術性理解是趨向于獨特的意味和意緒的,具有難以言說的體驗性。而獨特的藝術性理解是否可能,就看既有文化觀念在把握其意味和意境時是否會顯得牽強或尷尬,其獨特意味、意緒是否突破了中西方文化觀念。
由于中國藝術家們常常會以現實的文化眼光看待、理解、體驗世界并在自己的藝術世界中呈現文化的力量,從而很少站在藝術性的立場穿越文化力量,這是中國多數宮廷劇之所以造成以“斗”為性質的原因。宮廷劇中充斥著利益對婚姻的支配、功名對愛情的支配、道德對人欲的支配,是這種“斗”的文化性原因。違背皇上意志要殺頭,爭風吃醋可能被打入冷宮,就連《如懿傳》中如懿的愛情也是取決于皇上的喜怒,反抗者不是像《甄嬛傳》中的果郡王那樣被藥酒賜死,就是像如懿那樣寡歡孤寂而死,這是“斗”的文化性效果。有沒有突破這個法則的反抗?不是作為宮廷劇出場的電視劇《水滸傳》的一個隱秘立意,也許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忠、孝、義、俠之外還有一個“情”,
才是審視梁山農民起義悲劇的關鍵視角。由于不同的價值取向產生的矛盾張力在作品中是忽隱忽現的,所以在對作品的理解體驗中常常會被讀者所忽略,這就需要文學藝術批評進行深入的闡發和引導:燕青非婚姻化的自由“愛情”,或許才具備對“忠孝節義”藝術性穿越的強大力量,從而突破農民起義的悲劇宿命。
第一,女主人公魏瓔珞攻的“略”之所以不是歷史真實而是藝術創造,是因為歷史上孝儀純皇后魏佳氏的尸體沒有腐爛的謎團,為藝術虛構提供了豐富的想象。劇情中魏瓔珞最后雖然坐到皇貴妃的位置上,其所經歷的各種生死磨難和考驗,明顯區別于《如懿傳》中以害人為業的令貴妃。由于令貴妃害人的“心機”踐踏了他人生命的尊嚴,魏瓔珞的“心智”則用在捍衛他人生命的尊嚴上,故令貴妃竭盡全力通過爭寵獲得權力,而魏瓔珞跑到皇宮里是為了給受污辱致死的姐姐瓔寧復仇,兩者對比明顯,同一種歷史原型在不同的作品中對生命的態度可以看出編導對生命與權力的不同理解。一般說來,“復仇”這個概念很容易被理解為殺人償命,但瓔珞為了讓殘害姐姐的兇手得到懲罰卻不去殘害生命,這就使兇手的母親被“雷劈”成為天意捍衛生命尊嚴的象征。推而論之,劇中的高貴妃為了延續家族榮光的爭斗,嫻皇后為了獲得皇上的愛情的爭斗,與瓔珞為了捍衛生命的尊嚴“對抗”的爭斗不同,這是瓔珞與宮廷里所有女性最根本的區別。瓔珞為宮廷里所有生命的尊嚴討一個公道,從而使“復仇”具有了保衛宮廷里所有生命尊嚴的意義,所以“復仇”在藝術創造中就成為一個中性概念。瓔珞做刺繡宮女時為使同伴不受責罰挺身相護,受皇上誤解時從不辯解,受高貴妃污辱時從不服軟,都是捍衛生命尊嚴的具體體現。多數觀眾會覺得一個小小宮女怎么可能忤逆皇上的意志,這是因為我們對“真實”的理解已經“文化”化了,從而忽略了任何環境都有生命與文化的互動關系。
瓔珞不主動諂媚皇上是對待“男人”的方式,這是瓔珞女性獨立氣場產生的重要原因,也是包括嫻皇后在內的其他嬪妃最后敗給瓔珞的原因,使瓔珞反而具有了“因為不在意皇上的寵愛而捕獲了乾隆的心”的魅力。瓔珞的眼睛被諸多網友評價為“死魚眼”,但生命的尊嚴及性格的倔強正是通過瓔珞這樣的“死魚眼”,才區別于《甄嬛傳》中的甄嬛的楚楚可憐,也區別于《如懿傳》中的令貴妃的喬裝伶俐——“死魚眼”中的“好看”是什么,就成為一個藝術的創造性問題,引發觀念突破文化視角中的群體審美觀念。
余秋雨先生曾經給文化下了一個可謂全世界最簡短的定義:“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剖析余秋雨先生的文化定義,對比“看客文化”,實在為“看客”竟然能夠成為一種“文化”而悲哀。
第一,與愛情內容的多元性相比,愛的對象是由“這個人”來疏離文化性的“什么人”。“這個人”對“什么人”就構成了穿越關系。也就是說真正的愛是對“這個人”的愛而不是對“什么人”的愛,對“這個人”的愛就比對“皇上”“經理”“成功者”的愛更具體更本真。“這個人”是由生命的血肉、性格、魅力、尊嚴構成的,不以身份、地位、權勢、知識等文化、政治、經濟給“人”的定位為轉移,影視藝術只有抓住這樣的視角,才容易實現藝術對文化的創造性突破。這就像《蝸居》中海萍的一句“你愛宋思明什么”,把海藻問住了一樣,如果海藻只能回答宋思明給她很多錢卻說不出“愛他什么”,這個問題就表明她在“愛”的理解問題上的嚴重異化:宋思明到最后也只能用金錢來解決與海藻的所謂情感問題,而海藻的情感迷茫問題也始終無解。《蝸居》的編導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自然使得作品突破不了世俗文化的束縛。從《步步驚心》上來看,若曦與四阿哥的愛是“人”之愛,而與作為“皇上”的四阿哥的愛則是若曦不能接受的。四阿哥為保護若曦的生命,擋住射箭的時候是活生生的“男人”,而八阿哥為了權勢放棄若曦的時候則是“趨利之人”,這就是在愛情上八阿哥輸給四阿哥的原因。但是當作為皇上的四阿哥蒸死玉檀的時候,“四阿哥”作為“這個人”也消失了,八阿哥則醒悟最愛他的人是為他而自焚的妻子,則作為“這個人”覺醒了,這就使劇情產生了奇特的反轉效果。這種反轉,使得若曦敦促八阿哥隨死去的妻子而去,是“愛的成全”;而她遠離宮廷則是在成全自己與四阿哥的愛——她終于只是把皇上當作為她擋箭的四阿哥去思念了。愛與不愛,愛與怎樣的愛,只為那個擋箭的“這個人”而來,也只為那個文化性的“什么人”而去。這就是愛的不確定性,也是愛的確定性。而這種確定性和不確定性,或許不會使《步步驚心》給觀眾以強烈的共鳴,但肯定會給觀眾以“愛的純粹性”的深長思考。
不管時代如何變遷,技術如何更迭,人們對知識的渴求,從來沒有停止過步伐,圖書館仍是用戶獲取信息的殿堂。新一代智慧圖書館重點在于“智慧”二字,一個智慧的空間里,資源被智慧地關聯,服務被智慧地提供。那么,怎樣的服務才算是智慧服務?當我們換位思考時,問題便迎刃而解。
第二,藝術內容如果一定程度上疏離了個人利益的考量,這就必然會突破儒家現實占有性的愛情觀念,為愛情賦予了多元存在形態,給觀眾以“中國式的純粹愛情是怎樣的”
之藝術性思考。這種思考,必然與儒家以婚姻為愛情歸屬的文化產生“對等互動”
的關系。以“男女相愛應該在一起”這一文化觀念為例,《甄嬛傳》中果郡王死了以后甄嬛的愛情就是失敗的,自然也不可能展開甄嬛是否有愛的思念的描繪,故“大團圓”為愛情希望的文化思維定式就滲透在情節設定之中。如懿最后也是以心理上離開乾隆宣布與她的“少年郎”愛情的結束,以男女不能相守作為愛情的結束,這是影視編導沒有突破老百姓忠誠不貳、白頭偕老愛情文化觀念的體現。而《延禧攻略》中的瓔珞與傅恒,雖未能相守,但卻能以“下輩子你能不能守護著我”的問詢,給觀眾以持久的心靈震撼,其原因就在于:劇中歌頌的愛是心靈的陪伴而不是身體的相守,愛是身體聽從心靈的召喚而不是靠身體帶動心靈。愛如果定位在心靈的守護上,情愛戲就不是重要的了。如果能,那是身體的雙雙激越飛翔;如果不能,那是“春江花月夜”的男女相望之美。身體是否在場可以左右身心的舒適,但不能左右以心靈激蕩為標志的愛情忘我——后者正是“愛情穿越身體地在一起”之顯示,
也是這部作品在愛情的方法上有所突破之所在。由于心靈可以尊重、規范和放縱身體,所以身體能否結合并不能說明愛情體驗的有和無、強和弱。如果以心靈陪伴為標志,不僅如懿被打入冷宮依然還愛著作為愛人的令郎而不是權力化的皇上,而且傅恒死了,瓔珞也依然以心靈守護傅恒,而以身體取悅皇上,說明愛的方式常常是身心分離的,也說明真愛是常常伴隨所愛之人不在場之痛苦體驗的。這樣,愛的性質是為對方著想,愛的標志是心靈觸動,愛的方式是深藏思念,愛的結果是相望之美,這已被古今中外的愛情故事所驗證。所謂愛情的悲劇,正好襯托出愛情的永恒和內心的燦爛,何來愛情痛苦?作為藝術形象創造的瓔珞和傅恒,在愛的意義上就是無憾的,這應該就是“純粹愛情”的藝術創造啟示。
四、路徑三:藝術的獨特意味是否突破中西方文化觀念
有意思的是,主人公對這兩起案件的調查和探究,與他作為一個歷史教師的職業之間有著微妙的對應。偵探審訊和歷史探究都需要一種逆向的推理和想像,涉及故事的講述和文本的建構,最終關乎主體對自我的認識、理解和探究,正如歷史教師在其妻子竊嬰的超市所想到的——
比如,《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和《鹿鼎記》中的韋小寶在溢出中國儒釋道文化觀念瓶頸這一點上是相近的:寶玉的“意淫”讓“節欲”“忘欲”“無欲”的儒、佛、道文化觀念均難以概括。寶玉與襲人和碧痕嬉戲的性愛,是不確定的興致即來,既不是男女愛情也不是男女性愛之確定的性關系;而喜歡與丫鬟和秦鐘們在一起開心,也突顯出人的生命之愛的自由性、豐富性,不是“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這種以身體相親行為說明的“戀”,寶玉“美在哪里”由此才成為一個人物藝術創造探索不盡的話題,寶玉也突破了我們可能想到的文化觀念問題。而韋小寶不僅突破了傳統武功高強、棄惡揚善的武俠小說模式,也突破了殺人的俠士文化和情愛專一的儒家文化,被金庸以疏離權力、利益、武功的方法塑造了一個只追求有魅力女性且認真對待的“痞男”,在中國文學史上也是罕見的。仔細想想中國眾多始亂終棄的小說和戲曲,從“杜十娘”“崔鶯鶯”到“杜麗娘”,從“張生”“西門慶”到“章永麟”,
正好是以男性的欲望滿足、女性的欲望依附為文化尺度塑造的各種人物形象,這種不是“輕欲”“無欲”就是“逐欲”“淫欲”的文化逆反同構的人物塑造,與賈寶玉和韋小寶的差別即為藝術穿越文化現實程度之別。
比較起來,宮廷劇中的少數優秀作品在創造程度上雖然無法與文學經典相比,但在人物形象的創造上卻有一定的相通性。宮廷劇既然以權力爭斗為主線,那么創造性的路徑當然就在于突破這樣的主線。但是突破這樣的主線卻不是采取“對抗權力”的文化性思維。由于“依附—對抗”是同一種文化思維的逆反,所以“對抗權力”并不能改變“依附權力”的文化定式,反而是受“權力文化”制約的另一種方式,這已經為中國文化的“分分合合”的歷史循環所證明,也為“節欲背后是縱欲”的人性欲望現實所證明。同樣,道家“淡泊利益”看起來雖然區別于“追逐利益”,但解決不了面對利益應該怎樣“既尊重又超越”的問題,所以沒有突破利益思維的框架——回避利益認同了利益的強大性。藝術創造雖然沒有必要擔當改變現實的文化責任,但卻有必要給改變現實文化予以藝術穿越文化的啟示。正是在這一點上,《紅樓夢》和《延禧攻略》為我們塑造了“利用權力呵護卑微弱小生命”的寶玉和瓔珞形象,并消解了權力和生命的對立思維。
如果說《紅樓夢》利用賈府和豪門之權力產物建構一個獨特的呵護丫鬟生命的紅樓世界的話,那么《延禧攻略》則是利用皇上的愛所產生的權力效應來關愛呵護紫禁城的孩子。與孟子的“民為邦本”是對統治者的勸說不同,瓔珞是不寄希望于統治者的“自爭權力”之實踐。但瓔珞贏得權力的方式是利用自己的個性所產生的女性魅力,這是《延禧攻略》最重要的藝術性的“個體化理解”,也是該劇區別于國內其他宮廷劇對權力與生命關系認知的關鍵點。由于真愛本質上是有尊嚴的生命才能產生的,所以守護真愛也必然伴隨著守護生命的不被摧殘和傷害,這是瓔珞最后成為皇貴妃給觀眾的啟示。瓔珞與嫻皇后的約法三章是劇情發展的核心:要和平相處可以,但紫禁城里的孩子一個都不能被傷害。由于瓔珞呵護的是紫禁城內所有的孩子,而乾隆又呵護著瓔珞,這就使得這十年具有了權力呵護生命的象征意味:和平是呵護弱小生命的和平,而不是無視弱小生命的平靜。權力的不穩定是由呵護生命淡化利益所導致,還是由摧殘生命爭奪利益所導致,由此就成為一個讓人深思的問題。
眾所周知,佛教文化尊重生命,所謂眾生平等、生死輪回,強調的是所有的生命都應該得到善待;而一切生命都是生死無常的緣起循環,佛教讓人們如何正確看待生命的生與死。這種文化理念雖然沒有明顯制約當代的宮廷劇,但編導們同樣需要警惕以此來進行藝術的操作。以解脫為目的的佛教文化之所以難以把握《延禧攻略》的創意,是因為瓔珞的生命觀是“拯救”而不是“解脫”,是“生在當下”而不是“生死無常”,是拯救弱小的被傷害的生命,而不是佛教有情無情的生命。宮女、下人和孩子被“善待”,在這里指“尊重”而不是佛教的“不殺生”;生命的意義是在當下,指宮廷里扭曲的生命何以正常之問題。傅恒所說的“來生你能否守護我”,指的即是此生愛情之扭曲如何通過來生彌補恢復正常,不是指哲學意義上生死無常的超脫。佛教文化同樣是制約現世生命的,故藝術創造同樣要對此持審視改造的態度。饒有意味的是,《步步驚心》最后是以若曦對同時拯救友情、親情、愛情失望而希望自己的骨灰煙消云散的悲觀結尾的,溢出了佛教“吾佛慈悲”“萬事皆空”的生命普適性悲憫,傳達出一種強烈的現世生命關愛而不能的絕望。《步步驚心》之“絕望”區別于佛文化的“悲憫”,正如《延禧攻略》之“希望”區別于佛祖普度眾生之“淡然”,是因為藝術強烈而豐富的情感內容所致,給我們的是走出中國傳統文化去創造中國現代文化的審美憧憬。因而,藝術的創造性意味具有承擔現代文化觀念建設的意義,發揮類似于蔡元培先生所說的“以美育代宗教”的功能。
與此同時,以西方文化觀念注入影視劇中產生的可以觀念概括的“現代意識”,同樣是編導和觀眾在藝術創造問題中需要審視的。這就要求編導的藝術創造具有“改造西方文化觀念”的穿越意識,也要求觀眾能夠發現西方文化觀念難以概括的體驗性內容,從而把影視劇的創造性推向同時審視中西方文化觀念的整體觀上。對于一個受西方文化觀念教育的編導來說,這意味著要以自己生命體驗產生對中國社會的獨特理解,并用這樣的理解來塑造人物,而不是為傳達一個西方現代文化觀念去編織故事。正是在這一點上,《步步驚心》中若曦對待友情、愛情和親情的態度給了我們這樣的啟示:已得到愛情的若曦并沒有導向“愛情至上”,也沒有將愛情與婚姻和權力相捆綁,更沒有因為愛情、權力都在自己這一邊而輕視友情和親情,所以這與西方“個體至上”無關,與儒家婚姻倫理和政治權力也不同,更與“和相愛的人在一起”的世俗文化觀念不可同日而語。若曦為各種感情不能得到同等對待而焦慮,也不能解釋為“人人平等”,因為“人人平等”是權利的平等或人格的平等。如果我們用西方的“人人平等”觀念去解析《步步驚心》,那么你看不到若曦和四阿哥權利的平等,也看不到若曦與八阿哥人格的平等。所以若曦的“情”是一種筆者稱之為“多元對等互動”之復合性纏繞的感情,這種感情似乎已經溢出了中西方文化觀念的瓶頸,忽隱忽現地只與非等級性“先天八卦”
相關聯,但很難形成新的文化觀念。
應該說,這樣的價值甄別是一種批判創造性的思維活動。這樣的活動要求導演將自己對文學內容的核心理解放在是否突破中西方文化觀念的比較中去進行分析,要與自己認同的文化觀念保持審視的距離。由于藝術家對作品內容的理解均受一定的“前理解”制約,這種審視和改造也就成為編導對自己“前理解”的批判創造性實踐。儒家文化的“宗經”思維形成中國作家、藝術家的“依附經典”的文化定式,是不自覺的積淀,而審視經典和改造經典的批判創造性思維在中國文學經典中則是自覺的實踐。所以,只有優秀的導演才可能用自己獨特的生命體驗與所接受的文化觀念保持批判—創造性的關系。李安在《臥虎藏龍》中讓主人公的“情欲”與儒道文化保持糾葛關系,侯孝賢在《刺客聶隱娘》中讓“呵護兒童生命”的聶隱娘與師父的“道心”構成糾葛關系,賈樟柯在《江湖兒女》中讓“江湖情義”與社會世俗文化構成張力,其實都是用生命的獨特體驗對文化觀念的批判—創造性實踐的努力。這種努力激勵著中國影視編導藝術與文化關系思維方式的轉變,促使他們建立起“文化規范藝術”與“藝術穿越文化”對等互動的思維。關鍵是,這樣的鼓勵和轉變對中國觀眾也是一種熏陶,從而具有培養人們“文化規范性和藝術創造性互動”鑒賞思維之意義。
五、結語: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為什么不是創造性命題
歷史題材劇的“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的關系之所以是人們經常討論的問題,是因為理論界關于歷史題材藝術創作的思維方式是一種非創造性思維所致,從而將“真實—虛構”混同于藝術家建構自己的歷史理解之努力。一方面,歷史真實之所以是一種殘缺性的歷史判斷,是因為任何史料只是當時或權威機構或部分個體對當時現實的某種主觀描述和記載,均不能代表各種已發聲音和未發聲音的集合性歷史把握,始皇焚書的經驗已告訴我們遠古歷史的很多種聲音早已煙消云散,而當代史也認為現實感受與文本表達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所有的歷史文本史料均是殘缺的歷史描述。既然如此,歷史真實就需要為不斷發現的史料和永遠不能揭示的人的感受之歷史留下空白,這就是歷史劇可以虛構想象的可補充的真實歷史空間;另一方面,所謂藝術真實之所以要符合史料化的藝術真實,強調的也只能是基本的歷史事件不至于被歪曲,而不是對歷史中的人物思想、情感、性格和心理不能有自己的理解想象。因為所有的史料都不是對人的內在世界的記載,所以藝術虛構的真實可以對歷史人物進行編導自己的創造性激活,但虛構激活的藝術真實即便能讓人身臨其境,也仍然不一定是好的藝術,原因就在于藝術虛構的真實的高度不一定能有哲學式思想的支撐,故藝術真實可以因其生動性而吸引觀眾,但卻可能因缺乏藝術的獨特哲學而難以啟示人、震撼人。
如果“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是個體對世界不同的體驗描述方式,那么由藝術的創造性期待產生的“獨特理解真實”的使命就是一個更高層次的藝術命題。從《甄嬛傳》到《延禧攻略》之藝術創造張力的差異性來看,提出這一命題已經恰逢其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