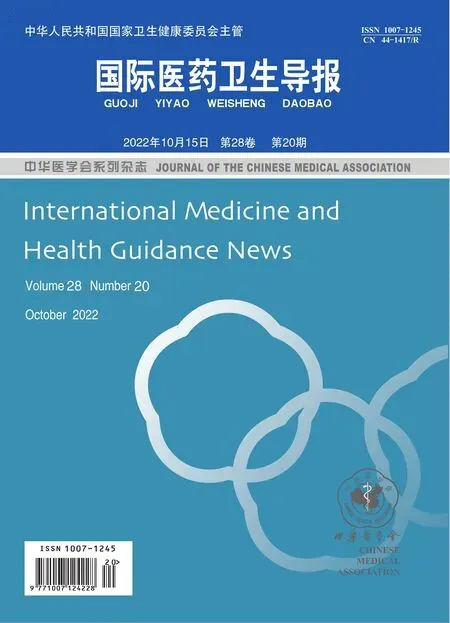尿液膀胱腫瘤標志物的研究進展
楊禮賓 許漢標
1廣東醫科大學第一臨床醫學院,湛江 524023;2惠州市第二婦幼保健院綜合外科,惠州 516000
膀胱癌在世界常見腫瘤中排第9 位,在美國成年男性常見癌癥中排第4 位[1]。約80%的膀胱癌初診時為非肌層浸 潤 性 膀 胱 癌(non-muscular invasive bladder cancer,NMIBC),其余20%為肌層浸潤性膀胱癌(muscular invasive bladder cancer,MIBC)。大多數 NMIBC 將經歷腫瘤復發[2],其中10%~30%將進展為MIBC[3]。因此,腫瘤的早期診斷和復發監測在患者管理中具有重要意義。目前,膀胱癌的診斷主要依靠膀胱鏡和尿細胞學檢查,前者為侵入性檢查,易給患者帶來不適;后者主要的局限性是檢查結果存在主觀性,且對低級別膀胱癌的靈敏度較低[4]。因此,急需探索具有高靈敏度、高特異度、低成本、非侵入性的膀胱癌尿液生物診斷標志物。美國食品和藥物監督管理局(FDA)已經批準包含尿膀胱腫瘤抗原(bladder tumor antigent,BTA)、核基質蛋白22(NMP22)等多種尿液檢測方法用于臨床協助膀胱癌的診斷。然而,出于種種的局限性,在美國泌尿外科協會或歐洲泌尿外科協會臨床指南中,這些檢測方法都沒有在臨床實踐中常規推薦使用。本文旨在綜述尿液生物標志物在膀胱癌中的應用現狀,同時介紹基于DNA、RNA、尿液中的腫瘤微環境成分等新型分子“液體活檢法”的研究進展。
FDA已批準用于臨床的膀胱癌尿液生物標志物
1、BTA STAT/BTA TRAK
BTA 是人補體因子-H 相關蛋白(HCFHrp),它存在于膀胱癌細胞中,可以抑制補體級聯反應,防止細胞溶解。檢測方式包括BTA STAT 和BTA TRAK 兩種方法,BTA STAT是定性檢測,而BTA TRAK 是定量酶聯免疫吸附試驗(ELISA)檢測。雖然都已被FDA 批準用于診斷和監測膀胱癌復發,但僅作為膀胱鏡檢查的輔助手段。一項薈萃分析顯示,BTA STAT 和BTA TRAK 檢測的靈敏度分別為64%[95% 置信區間(CI)58%~69%]和 65%(95%CI54%~75%),特異度分別為 77%(95%CI73%~81%)和 74%(95%CI64%~82%)[5]。然而,BTA 的檢測結果易受血尿、炎癥、結石等因素影響,所以假陽性率較高[6]。
2、NMP22
NMP 是一種細胞內的非染色質結構,負責調節DNA 復制、轉錄和 RNA 加工[7],NMP22 在膀胱癌細胞中呈高表達,當腫瘤細胞發生凋亡后會將其釋放入尿液中,因此可在尿液中檢測到。NMP22 檢測包括定量ELISA 和定性檢測,兩者均可輔助膀胱癌診斷和監測復發。先前的研究表明,定量NMP22 測定對原發性膀胱癌診斷的靈敏度為44%~100%,特異度為60%~95%[8]。2017年,南京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Wang 等[9]對 19 項關于 NMP22 定性檢測的研究進行了單獨薈萃分析,其中包括5 291 例患者測試結果,最后的靈敏度為52%~59%,特異度為87%~89%。像許多其他生物標志物一樣,NMP22 在低級別腫瘤檢測中靈敏度特別低[5]。另外,在合并炎癥、結石、血尿時假陽性結果也很常見。
3、UroVysion
UroVysion 膀胱癌試劑盒是一種多色熒光原位雜交(FISH)分析手段,旨在評估染色體3、7 和17 的非整倍體或9p21 位點的丟失。這項檢測的靈敏度在69%~87%之間,特異度在89%~96%之間[10]。同樣,最近的薈萃分析(共納入11 項研究)顯示其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63%(95%CI50%~75%)和87%(95%CI79%~93%)[11]。另一項研究表明,相同情況下該試劑盒檢測到的NMIBC 幾乎是尿細胞學檢查結果的2 倍,而且對MIBC 的檢出率高達88%,尿細胞學檢查則漏掉了其中32%的MIBC[12]。本試驗特異度高,優于NMP22 和BTA 試驗。該分析不受血尿、泌尿系感染或其他可能導致熒光假陽性情況的影響。此外,大多數證據表明UroVysion 試驗在預測膀胱癌對卡介苗的灌注治療反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13]。
FDA未批準用于臨床的膀胱癌尿液生物標志物
1、DNA相關尿液生物標志物
1.1、DNA 甲基化 腫瘤患者最典型的表觀遺傳現象是DNA 甲基化[14]。在膀胱癌和一些癌前病變患者中發現了DNA 的高甲基化和低甲基化區域[15]。DNA 甲基化狀態可以通過尿液中的游離DNA 片段和腫瘤脫落細胞來評估。與良性病例相比,腫瘤患者的甲基化基因(如APC和細胞周期蛋白D2)含量顯著升高[16]。已在膀胱癌患者中發現包括GSTP1、APC 和 RARb2 在內的特定基因的高甲基化[17]。表1 概括了近些年來主要的DNA 甲基化相關尿液生物標志物及其靈敏度和特異度。雖然這些標志物的特異度令人較為滿意,但檢測這些標志所需的分子遺傳學技術比較費時、費錢、費力。

表1 膀胱癌相關DNA甲基化尿液生物標志物(%)
1.2、微衛星分析 微衛星是人類基因組中長度為1~6個堿基對的重復核酸序列單位,微衛星分析主要針對這些較短、多形性DNA 串聯重復序列。膀胱癌最常見的遺傳變化之一是9 號染色體雜合性丟失[25]。染色體4p、8p、9p、11p和17p 在膀胱癌患者中也經常表現為雜合性丟失。一般來說,這些標志物的靈敏度在72%~97%之間,總體特異度在80%~100%之間[26-27]。微衛星雜合性缺失分析在診斷分級分期較低的膀胱癌方面比單純尿細胞學更敏感(97%比79%),對低級別膀胱癌的靈敏度為95%,對原位癌和其他高級別膀胱癌的靈敏度為100%[28]。
2、RNA相關尿液生物標志物
2.1、微小 RNA(miRNA) miRNA 是一種長為 21~23 個核苷酸的非編碼RNA,它通過與其靶mRNA 的3‘非翻譯區配對來調節基因的表達。它們在體液中可以以自由循環的miRNA 形式存在,也可以與核糖核蛋白復合體結合,或者以外泌體的形式存在于胞外小泡中[29]。腫瘤組織中miRNA 的表達表現出組織特異性,具有很高的穩定性和可檢測性。由于其序列較短,miRNA 比mRNA 鏈更不容易降解,并且可以在室溫下保存長達48 h。因此,miRNA 表達分析被認為是一種潛在的診斷和監測生物標志物。Kutwin等[30]研究成果表明,尿上清液miRNA 靈敏度最高(78.4%),其次是尿沉渣(75.6%)和尿液原液(74.3%);尿液上清液的特異度也是三者中最高的,為79.4%。當然,尿液中miRNA水平也可作為預測NMIBC復發的預后標志物。Kim 等[31]研究發現,在術后隨訪結局為復發的NMIBC 患者中,尿miRNA-214 表達下調,與未復發的患者相比,HR為2.011(95%CI1.027~3.937)。所以,不管是尿液單一miRNA 檢測還是多種miRNA 聯合檢測,未來作為膀胱癌的潛在診斷標志物還是很有研究前景的。
2.2、長鏈非編碼RNA(lncRNA) 隨著對lncRNA 研究的不斷深入,其也逐漸成為膀胱癌診斷的手段之一[32]。得益于高通量二代測序技術(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的出現,目前已經分離鑒定出10 000 多個獨特的lncRNA,并闡明了它們的生物學功能。lncRNA 通過調節參與細胞轉化的信號通路,在膀胱癌腫瘤的發生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33]。張爭等[34]研究了在膀胱癌患者尿液中發現的一種命名為尿路上皮癌癌胚抗原1(UCA1)lncRNA 的潛在應用價值,中國藥科大學藥物科學研究所張本佳等[35]也對此做出了相關報道。結果表明,UCA1診斷膀胱癌的靈敏度和特異度分別為84.4%和92.4%(AUC=0.898)。此外,該研究還強調了UCA1 作為NMIBC 患者預后生物標志物的作用,預測NMIBC 進展為MIBC 的靈敏度為86.4%;特異度為92.3%。同樣,Eissa等[36]的研究表明UCA1對檢測膀胱癌有較高的靈敏度(91.5%)和特異度(96.5%)。結果表明,在NMIBC 患者中,尿UCA1 比尿細胞學檢查更準確。另一項初步研究在90.5%的膀胱癌患者和25.9%的健康對照者的尿沉渣中檢測到lncRNA H19,使其成為膀胱癌診斷的輔助工具[37]。雖然其他lncRNA 的表達也與膀胱癌相關,但大多數研究都是基于組織或細胞;因此,結果需要在尿液中進行驗證,以確認它們作為非侵入性膀胱癌生物標志物的適用性[38-39]。
3、尿液中的腫瘤微環境成分分析
Wong等[40]最近的1份包含32例MIBC 患者的研究報告發現,尿液中的淋巴細胞是很好的膀胱癌生物標志物來源;尿液中的效應器CD8+和CD4+細胞以及調節性T 細胞準確繪制了腫瘤微環境的免疫檢查點情形和T 細胞受體譜系。尿源性淋巴細胞數量的增加,尤其是NMIBC 腫瘤電切術后CD8+細胞上PD-1(PD-1hi)的高表達,與較短的無復發生存期有關。尿液淋巴細胞分析代表了膀胱腫瘤免疫微環境的動態液體活檢,可作為研究MIBC預后價值和免疫治療靶點的潛在手段。
總結與展望
膀胱癌尿液生物標志物檢測領域發展迅速,但目前臨床上還沒有生物標志物可以完全替代膀胱鏡和尿細胞學檢查。最近發現的尿液蛋白質組、基因組、表觀遺傳組、轉錄和代謝組學中的一系列生物標志物,迫切需要通過多中心臨床研究的廣泛數據來進一步進行驗證。缺乏臨床實際測試、驗證性研究有限、不同陽性閾值的確定、膀胱腫瘤異質性,以及不同組學之間的復雜相互作用,這些都是尿液生物標志物開發和驗證中的一系列重要挑戰。在未來,NGS 技術、高級人工智能和新穎臨床試驗模型的應用,可為尿液生物標志物的開發不斷助力。另外,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尿液中游離DNA、DNA 甲基化、miRNA、游離蛋白質/多肽和外泌體來源的核酸可作為尿液生物標志物,有助于鑒別MIBC和NMIBC 或評估治療后的早期復發。最近有相關學者提出,通過分析京都基因與基因組數據庫(Kyoto Encyclopedia of Genes and Genomes,KEGG),可用于發掘與膀胱癌形成有關的生物信號通路,可能有機會發現新的尿液生物標志物。此外,在不久的將來,將人工智能方法應用于尿液生物標志物分析和數據挖掘可能會加速研究的前進步伐。隨著研究的進展,通過更先進的“納米傳感器”檢測尿液中的RNA 和蛋白質也將逐漸成為現實,屆時將改變現有的檢測方法。尿路微生物群的改變(生物失調)也可能與膀胱癌的發生有關。最近有報道稱,通過分析尿液外泌體中提取的DNA 發現,與對照組相比,膀胱癌隊列中存在不動桿菌、厭氧球菌和鞘氨酸桿菌特異度富集的現象。在高危膀胱癌患者中觀察到卟啉桿菌、枯草芽孢桿菌和類桿菌的增加,表明這些菌屬可能是新的潛在生物標志物[41-42]。在未來的臨床實踐中,最有可能的應該是多種檢測手段的聯合應用,特別是基因組相關生物標志物與尿細胞學檢查和新一代膀胱鏡檢查技術的結合使用,將大大提高膀胱癌的診斷準確性和早期發現復發進展。
作者貢獻聲明楊禮賓:醞釀和設計實驗,實施研究,采集、分析/解釋數據,起草文章;許漢標:對文章的知識性內容作批評性審閱,獲取研究經費,行政、技術或材料支持,指導,支持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