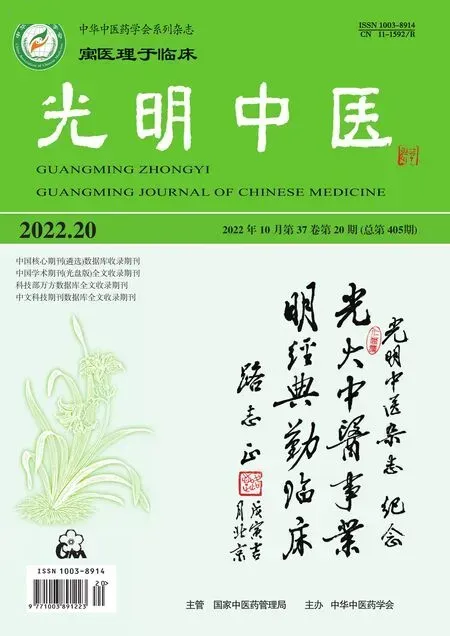補脾益腎方治療潰瘍性結腸炎臨床觀察*
張新春 劉世舉 李 巖
潰瘍性結腸炎(UC)是常見的非特異性的腸道炎癥性疾病,病變范圍廣泛分布于結腸和直腸表面的黏膜層和黏膜下層,很少累及肌層,可延伸到降結腸、橫結腸,臨床表現以黏液膿血便、腹痛、腹瀉等為主[1,2]。目前,臨床上對UC病因病機的研究尚未完全明晰,其中遺傳因素、免疫因素和腸道菌群紊亂是誘發此病的潛在因素。腸道菌群在人體的健康中起到關鍵性作用,一旦腸道菌群紊亂,可能導致機體的免疫系統失衡,最終引起免疫反應損傷和代謝紊亂引起的腸道組織損傷[3]。近年來的研究已表明腸道菌群紊亂是UC發病的始動因素,且在UC的發病、發展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4]。西醫學對UC的治療以美沙拉嗪等藥物為主,但療效欠佳,復發率高。中醫學認為此病早期多由濕熱邪氣內蘊大腸、脾胃運化失司等所致,損傷腸絡而表現為黏液膿血便、腹痛腹脹等癥狀;日久則導致脾虛腸損、泄瀉反復發作,表現為脾腎陽虛證[5]。對于病程日久的脾腎陽虛證多采用補脾益腎、祛濕清熱等藥物治療。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對UC患者在西藥治療基礎上應用自擬補脾益腎方治療取得滿意的療效,調節了腸道菌群平衡,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三附屬醫院2020年1月—2021年1月收診的UC患者80例為研究對象,根據隨機數字表法分成2組,各40例。對照組中:男26例,女14例;年齡26~55歲,平均(40.2±5.5)歲;病程3~10年,平均(7.32±2.11)年。試驗組中:男25例,女15例;年齡23~56歲,平均(40.5±5.7)歲;病程3~12年,平均(7.36±2.13)年。2組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有可比性。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納入標準:①符合UC的診斷標準;②中醫辨證為脾腎陽虛證;③病情嚴重程度為輕度、中度;④年齡≥18歲,且<60歲,性別不限;⑤知情同意,簽署知情協議書。排除標準:①合并結腸癌、腸穿孔等其他腸道疾病的患者;②合并嚴重肝腎功能不全、血液系統疾病、免疫系統疾病等其他疾病;③妊娠期、哺乳期患者;④過敏體質、對本研究藥物過敏的患者;⑤臨床資料不完整者。
1.3 治療方法對照組患者給予西醫療法,選擇美沙拉嗪腸溶片和柳氮磺吡啶治療,口服美沙拉嗪腸溶片2 片/次,3 次/d;口服柳氮磺吡啶1.0 g/次,4 次/d;持續服藥3個月。同時將5 mg地塞米松與1 g柳氮磺吡啶1.0 g與100 ml生理鹽水混合后給予患者保留灌腸,每晚1次,持續2周后停藥。試驗組在上述西醫療法的基礎上加用補脾益腎方治療,組方:山藥、馬齒莧、炙黃芪各30 g,白及20 g,黨參、茯苓、補骨脂、龍眼肉各15 g,陳皮、白術各12 g,砂仁(后下)9 g,肉豆蔻、五味子、干姜各6 g,吳茱萸3 g,炙甘草6 g。可隨癥加減,對于腹脹明顯者加木香和烏藥,對于腰膝酸軟者加菟絲子和杜仲,對于腹瀉者加石榴皮、赤石脂;對于便血者加艾葉和仙鶴草。水煎服,每日1劑,煎汁400 ml分成早晚2次飯后溫服,持續服藥3個月。
1.4 觀察指標①炎癥因子:治療前、治療3個月后分別采集晨起空腹外周靜脈血5 ml,在室溫下以3000 r/min轉速離心15 min分離血清,將血清置于EP管中,置入-80 ℃冰箱中保存待檢,采用ELISA法檢測血清白細胞介素-8(IL-8)、白細胞介素-10(IL-10)和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水平。②腸道菌群:治療前后分別取自然排出的新鮮糞便于厭氧罐中送檢,采用培養基計數法計算菌落,計算大腸桿菌、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的計數。③安全性:主要有惡心、頭暈、頭痛等。
1.5 療效判定標準2組患者均于治療3個月后復查腸鏡,結合臨床癥狀和腸鏡檢查結果判斷治療效果,顯效:大便正常,無其他癥狀,且腸鏡檢查結腸黏膜正常。有效:臨床癥狀明顯緩解,腸鏡檢查顯示黏膜潰瘍面縮小≥50%。無效:未達到上述標準者。總有效率=顯效率+有效率。
1.6 統計學方法收集整理本次研究中相關數據資料,輸入到SPSS 23.0軟件中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計量資料采用均數±標準差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2組患者總有效率對比治療3個月后,試驗組的總有效率97.50%高于對照組的總有效率80.00%,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總有效率比較 (例,%)
2.2 2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比較試驗組治療后的血清IL-8和TNF-α水平均低于對照組,且血清IL-10水平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2組患者炎癥因子水平比較
2.3 2組患者腸道菌群比較試驗組治療3個月后的大腸桿菌計數低于對照組,且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計數均高于對照組,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3。

表3 2組患者腸道菌群比較
2.4 2組患者不良反應發生率比較對照組治療期間出現3例輕度不良反應,其中1例惡心,2例頭暈,發生率7.50%(3/40);試驗組治療期間出現5例輕度不良反應,其中1例惡心,1例頭暈,2例頭痛,1例嘔吐,發生率12.50%(5/40);2組之間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139,P=0.709>0.05)。
3 討論
西醫學認為UC的發病多與黏膜免疫系統、飲食結構改變、腸道內環境破壞等因素有關,在潰瘍發生后釋放大量致炎因子刺激腸道黏膜,進一步破壞腸道黏膜。在治療中西醫學以保護腸道黏膜、抑制炎癥反應、改善腸道菌群平衡等為主,常應用美沙拉嗪等藥物治療,能取得一定療效,但是部分患者用藥后臨床癥狀改善效果不佳,且在停藥后復發率較高。因此,亟需尋找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案提高UC的治療效果。
中醫學中無UC的病名,根據其臨床表現可歸屬到“痢疾”“腹痛”“泄瀉”等范疇,認為此病多為脾腎兩虛、肝脾失調、濕熱阻滯大腸所致,為本虛標實證。本虛為脾腎虧虛,標實為濕熱瘀毒等壅滯于大腸[6,7]。此病纏綿遷延不愈,損傷正氣,致脾胃虛弱,在病情后期表現為脾腎陽虛癥狀,以黏液膿血便、腹脹腹痛、面白肢冷、肛門墜脹等為主要表現,在臨床治療中以補益脾腎為主。本研究中對患者應用自擬的補脾益腎方治療,方中山藥具有益氣養陰、補益脾腎之效;炙黃芪能補氣健脾;黨參具有健脾胃、補中氣之效;補骨脂能溫腎助陽之邪,緩解脾腎陽虛的各種癥狀龍眼肉能健脾養血;白術具有健脾益氣、利水滲濕之效;砂仁能行氣化濕利水,緩解腹脹腹痛等癥狀;肉豆蔻能溫中澀腸之邪,緩解因脾腎陽虛證所致的久瀉久利、脘腹脹痛等癥狀;五味子則能收斂固澀、益氣生津;干姜能溫中燥濕,緩解痢疾瀉下癥狀;吳茱萸能散寒止痛、助陽止瀉;馬齒莧具有清熱利濕、散血消腫之效,對多種痢疾療效肯定;陳皮能理氣燥濕,具有理氣行氣之效;白及能收斂止血生肌;甘草調和諸藥藥性。本方中的黃芪、黨參、補骨脂、白術、茯苓、山藥、龍眼肉等藥具有補益脾腎、補血生血之效,能固后天之本,兼有燥濕利濕、生津助運之效;白術、茯苓、砂仁、馬齒莧、干姜等藥能清熱化濕、燥濕解毒,能清除濕熱之邪;久瀉則多陰津不足,五倍子能益氣生津;肉豆蔻、五倍子等能收斂固澀止瀉。全方諸藥以溫腎健脾為主,并輔以利水滲濕、補氣行氣等藥物,促進患者腹瀉、腹痛等癥狀緩解。現代藥理學研究指出:本方中的黃芪、黨參、茯苓、白術、山藥等藥具有調節免疫功能的作用,龍眼肉、五倍子、干姜、吳茱萸、馬齒莧等藥具有抗炎抗菌之效,對大腸桿菌、痢疾桿菌等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在UC患者治療中應用中藥補脾益腎方治療能有效抑制腸道的炎癥反應,并減少腸道內的大腸桿菌,增加乳酸桿菌、雙歧桿菌等益生菌,調節腸道菌群的動態平衡[8]。
本結果發現,試驗組患者的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且治療后的血清IL-10水平高于對照組,血清IL-8和TNF-α水平均低于對照組(P<0.05),這提示中藥補脾益腎方的應用能提高治療效果,降低腸道的炎癥反應,緩解腸道黏膜的病變程度,提高治療效果。試驗組治療后的大腸桿菌少于對照組,雙歧桿菌和乳酸桿菌多于對照組(P<0.05),補脾益腎方的應用能調節腸道菌群平衡。在安全性方面,2組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且未發生嚴重不良反應,安全性較高。
綜上所述,中藥補脾益腎方在UC治療中應用效果肯定,能調節腸道菌群動態平衡,緩解腸道炎癥反應,安全性高,值得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