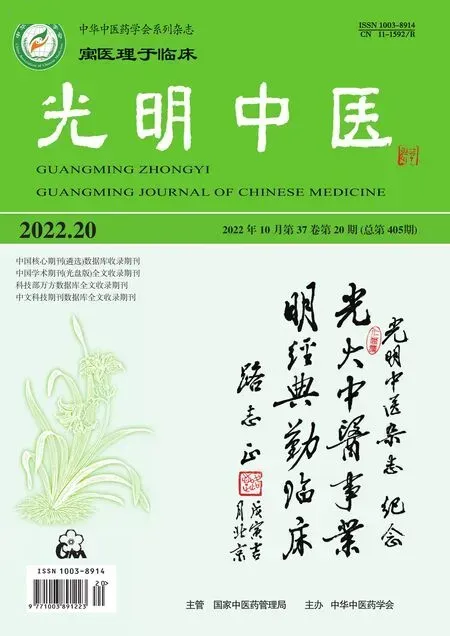補中益氣湯治療膽囊切除術后腹瀉臨床觀察*
孫琪坤 閆萬里 鮑振學 唐秀峰 戶玉鵬 李云紅
膽囊切除術后腹瀉(Post-cholecystectomy Diarrhoea,PCD)是膽囊切除術后以每日排便次數增多、糞質稀溏和排便不適感等消化道癥狀為主要表現的并發癥,亦稱為“膽源性腹瀉”。PCD多發生于術后3~5 d,發生率為15%~25%,可表現為晨間腹瀉、餐后腹瀉或不規則腹瀉,其中19%患者腹瀉癥狀長期持續存在[1],是膽囊切除術后臨床常見的并發癥之一。PCD病情反復,病勢遷延,經久不愈,不僅影響患者消化吸收功能,導致營養物質的流失,而且增加患者精神負擔和心理壓力,對生活質量產生不利影響,引發系列心理、生理問題。目前西醫多采用調整飲食結構、應用止瀉和益生菌類藥物等方法對癥治療,能部分改善患者臨床癥狀,但治療周期長且遠期效果欠理想[2]。在缺乏PCD確切病因病機的情況下,尋找安全有效的治療方案成為目前研究熱點。PCD依癥狀歸屬中醫學“泄瀉”范疇,患者膽腑缺如后引發肝膽氣機失常,失于疏泄,脾虛不運,水濕內停胃腸發而為泄。中醫理論從整體觀念出發辨證施治,在調整脾胃虛弱、運化失暢等消化道功能性疾病方面具有良好的治療效果。本研究針對PCD脾氣虧虛證患者給予補中益氣湯加減口服,觀察對臨床癥狀和胃腸激素水平的影響,有關資料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臨西縣第二人民醫院消化內科PCD患者70例,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各35例。經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患者知情同意自愿參加。2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可比性良好(P>0.05)。見表1。

表1 2組患者一般資料比較 (例,
1.2 納入與排除標準納入標準:①符合PCD的西醫診斷標準[3]。②符合中醫“泄瀉 脾氣虧虛”的診斷標準。主癥:大便時瀉時溏、進食油膩后癥狀加重;次癥:食后腹脹、胸脅脹悶、神疲乏力、納呆;舌脈:舌質淡、苔薄白、脈細弱。需具備主癥全部及次癥2項,參照舌脈即可診斷[4]。③腹瀉時間>4周。④年齡45~79歲。排除標準:①合并潰瘍性結腸炎、胃腸道感染、腸易激綜合癥等消化道疾患者;②合并膽管結石、膽道狹窄、膽系感染等膽道疾患者;③存在嚴重肝腎、心肺功能異常者;④對研究涉及藥物過敏者;⑤妊娠及哺乳期婦女。
1.3 治療方法2組患者均給予調整飲食結構,忌食生冷油膩刺激性食物,適當營養支持,給予雙歧桿菌三聯活菌膠囊(上海信誼藥廠有限公司,國藥準字S10950032),口服,0.63 g,2次/d;給予蒙托石散(博福-益普生天津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000690),口服,3 g,3次/d。觀察組在此基礎上給予補中益氣湯口服,方藥組成:黃芪15 g,黨參15 g,白術10 g,炙甘草15 g,當歸10 g,陳皮6 g,升麻6 g,柴胡6 g。兼腹痛者加白芍6 g;兼氣滯者加木香6 g。每日1劑,自動煎藥機濃煎至約200 ml,分早晚2次各100 ml溫服。2組患者均治療3周后評估療效。
1.4 觀察指標①臨床癥狀指標:記錄治療前后每日排便次數和大便性狀評分,大便性狀評分采用Bristol糞便性狀量表進行,計為1~7分,1分為干球狀便,3分為正常糞便,7分為水樣便[5]。②胃腸激素指標:檢測治療前后胃泌素(GAS)、血管活性腸肽(VIP)和膽囊收縮素(CCK)水平,均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檢測.③臨床療效:參考《中藥新藥臨床研究指導原則(試行)》[6]制定,治愈:排便次數、大便性狀及量正常,伴隨癥狀消失;好轉:排便次數1~3次/d,大便基本成形,或偶有便溏,伴隨癥狀明顯減輕;無效:排便次數無改善,糊狀便或水樣便,存在排便不適感。總有效率=(治愈+好轉)例數/總例數×1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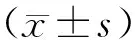
2 結果
2.1 2組患者臨床癥狀指標比較治療3周后,2組患者每日排便次數和糞便性狀評分均較治療前降低(P<0.01),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P<0.01)。見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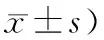
表2 2組患者臨床癥狀指標比較 (例,
2.2 2組患者胃腸激素指標比較治療3周后,2組患者GAS、VIP和CCK等胃腸激素水平均較治療前降低(P<0.01),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P<0.01)。見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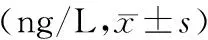
表3 2組患者胃腸激素指標比較
2.3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治療3周后,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高于對照組(P<0.05)。見表4。

表4 2組患者臨床療效比較 (例,%)
3 討論
PCD的發病機制尚未完全明確,主流觀點認為可能與以下因素有關:①膽囊切除術后膽汁無法儲藏和濃縮,不間斷的流入腸道,刺激腸黏膜分泌水分和電解質,促進結腸過快蠕動導致腹瀉;②進食脂肪類食物后,腸道缺乏足夠濃度和數量的膽汁協助消化吸收,脂肪消化不充分產生滲透性腹瀉;③膽囊缺失后引發腸道激素和神經內分泌紊亂,腸道神經功能失調引發腹瀉;④腸道菌群的動態平衡被打破,引起腸道免疫功能異常和黏膜生物學屏障損害,引發腸道功能紊亂導致腹瀉[7]。西醫對PCD的治療多采用對癥治療為主,蒙托石散為吸附性止瀉藥物,口服后在腸道黏膜表面形成保護膜,起到保護腸黏膜、減少水電解質流失的作用。雙歧桿菌三聯活菌膠囊是一種微生態制劑,含有雙歧桿菌、糞腸球菌和嗜酸乳桿菌,可補充腸道益生菌,有助于腸道微生態系統的恢復。止瀉藥物和益生菌的聯合應用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PCD腹瀉癥狀,但未從根本上改變膽囊在解剖上缺失后導致的胃腸功能異常,停藥物復發率高。
中醫理論中PCD依癥狀屬 “泄瀉”范疇,泄瀉是以排便次數異常增多、糞便完谷不化或溏薄,重者瀉出如水樣為主癥的病證。古人認為膽為“中清之腑”,其功能為儲存濃縮和膽汁。PCD患者金刃所傷致膽囊缺如,耗氣動血損傷經絡,肝之余氣無所歸依,不能聚而成精,肝氣郁滯致疏泄功能失常,肝失調達橫逆犯脾,則脾失健運生內濕邪,水濕輸注于腸道混雜而下引發泄瀉。其病位在腸,脾為主病之臟,其病機為脾虛濕盛,水濕犯腸。脾氣虧虛為PCD常見證型,脾位居中焦,主水谷精微和水濕運化,主升清,不宜下陷,喜燥惡濕,脾氣虛失于健運則水谷運化失常,小腸無以受盛化物,大腸無以傳化糟粕,大便溏瀉無常,稍進油膩則癥狀加重。明代醫家李中梓在《醫宗必讀》中提出淡滲、升提、清涼、疏利、甘緩、酸收、燥脾、溫腎、固澀治泄九法,是對泄瀉治療原則的高度總結,在臨床中多有運用。《泄瀉中醫診療專家共識意見(2017)》[4]指出以祛邪扶正為基本治療原則,以運脾化濕為基本治療方法,達到去除病因、緩解及消除癥狀的治療目的。本研究采用補中益氣湯加減口服健脾益氣、化濕止瀉治療PCD,取得良好效果。
補中益氣湯出自元代李東垣所著《脾胃論》,具有補中益氣、升陽舉陷之功效,為治療脾虛氣陷之要方。方中重用黃芪以為君藥,黃芪善入脾胃,可補氣固表、升陽舉陷,為補中益氣要藥;方中以黨參補脾益肺、平調中氣,以白術健脾益氣、燥濕利尿,以炙甘草補益脾氣、緩急定痛,三藥補氣健脾共為臣藥;方中以當歸養血和營、活血止痛,陳皮理氣健脾、燥濕化痰,兩藥補而不滯、行而不傷為佐藥;以升麻升舉陽氣、清熱解毒,柴胡疏肝升陽、和解表里,兩藥助君藥升提下陷之中氣兼具佐使之用;炙甘草調和諸藥,亦為使藥。兼腹痛者加白芍柔肝止痛,兼氣滯者加木香理氣解郁。全方補氣與升提并用,使氣虛得補、氣陷得升,諸藥合用達健脾益氣止瀉之功,從而使PCD患者脾胃調和,水谷精氣生化有源,泄瀉自止,充分體現了治泄九法中疏利、燥脾、淡濕、固澀四法的靈活運用。
消化器官功能除了受到自主神經調節外,胃腸激素在胃腸道動力學的調節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胃腸激素是由胃腸黏膜的化學信使細胞分泌的激素,其水平有效反應胃腸道的功能狀態,對PCD的病情變化具有較好的監測作用。GSA能刺激壁細胞分泌胃酸和主細胞分泌胃蛋白酶原,加快腸道蠕動,刺激胰液、膽汁和腸液分泌,其水平增加能增強胃腸道的運動,引發腹瀉或痙攣性疼痛;VIP具有舒張胃腸道平滑肌、刺激小腸分泌的作用,其水平增高能加速腸道水分和鹽的流失,產生分泌性腹瀉;CCK的功能是引發膽囊和胃腸道平滑肌的興奮和收縮,刺激肝臟、胰腺和小腸等器官的腺體分泌,其水平增高會誘發腸道運動增強,引起腹瀉和腹痛[8]。現代實驗研究表明,中藥可通過干預胃腸激素分泌發揮治療泄瀉的作用[9]。郭蕾等[10]研究分析了補中益氣湯對脾虛大鼠胃腸動力影響的作用機制,認為主要是通過調節胃腸激素水平來實現,其中升麻和柴胡是方劑中除君藥以外起到不可或缺的增效作用的“要藥”。
本研究結果顯示,治療3周后,2組患者每日排便次數和糞便性狀評分均較治療前降低(P<0.01),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P<0.01),觀察組治療總有效率亦高于對照組(P<0.05),說明補中益氣湯在PCD的治療中充分發揮了健脾益氣、化濕止瀉的治療作用。治療3周后,2組患者的GAS、VIP和CCK等胃腸素水平均較治療前降低(P<0.01),且觀察組低于對照組(P<0.01),說明補中益氣湯中含有的皂苷、多糖和生物堿等活性物質調節胃腸功能的作用機制可能是通過調節胃腸激素水平來實現的。受研究條件和時間限制,本研究樣本量偏小,未能對遠期療效進行跟蹤,仍需進一步對補中益氣湯的藥理作用進行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