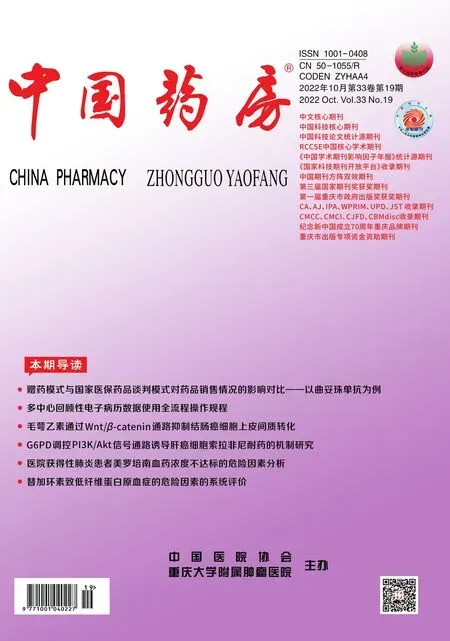基于中成藥說明書探討辨病用藥的可行性Δ
李春曉,王盼盼,凌霄,楊夢,李學林#,楊玉晴,郭靜(1.河南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藥學部/河南省中藥臨床應用、評價與轉化工程研究中心/河南省中藥臨床藥學中醫藥重點實驗室,鄭州 50099;2.河南中醫藥大學呼吸疾病中醫藥防治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鄭州 50006;.南陽張仲景醫院藥學部,河南南陽 700;.河南中醫藥大學藥學院,鄭州 5006)
中成藥是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經過藥效學研究和臨床研究,獲得國家藥品管理部門批準,以中醫處方為依據、中藥飲片為原料,按照規定的生產工藝和質量標準制成的具有一定劑型、質量可控、安全有效的藥品[1]。國產中藥民族藥約有6萬個藥品批準文號,中成藥已從丸、散、膏、丹等傳統劑型,發展到現在的滴丸、片劑、膜劑、膠囊等其40多種劑型。中成藥在疾病預防、治療、康復中發揮著重要作用,是我國醫療衛生體系中具有獨特優勢和特點的一類藥品。調查研究顯示,大部分中成藥需要醫師遵循說明書辨證用藥,而超過70%的中成藥是由綜合醫院的西醫醫師開出的,中成藥處方開具醫師中非中醫背景的醫師約占97%[2―3],這可能增加了用藥風險。隨著現代醫藥學技術的發展,一些國產、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通過研究其辨病用藥機制,在說明書中增加西醫表述,便于西醫按照西醫的疾病名稱、病理狀態或理化檢查結果合理選擇并使用相應的中成藥[4]。本研究對《國家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藥品目錄(2020年)》(以下簡稱國家醫保目錄)收載的國產中成藥及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官網公示的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的“功能”和“主治”項進行了梳理和對比分析,以期為完善中成藥說明書內容及提高辨病用藥可行性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通過藥智網(https://db.yaozh.com/)查詢《國家醫保目錄》收載的國產中成藥說明書;通過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官網(https://www.nmpa.gov.cn/datasearch/searchresult.html)查詢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部分中成藥同一品種可能含有多個劑型,本文僅選擇其中1個劑型進行研究[如九味羌活丸(顆粒),選擇九味羌活丸];部分中成藥同一品種可能有多個生產廠家,本文僅選擇上述網站中第1個廠家的說明書內容進行研究[如九味羌活丸,生產廠家有太極集團浙江東方制藥有限公司、四川大千藥業有限公司,選擇太極集團浙江東方制藥有限公司]。
1.2 方法
將中成藥說明書中的藥品名稱、成分、劑型、功能主治、用法用量、藥品類別等項目錄入Excel軟件中,將說明書中“功能主治”項信息進行拆分,分為“功能”(藥物的治療作用,用中醫術語表述)和“主治”(藥物所使用的病機及證候表現,用中醫證候屬性及癥狀表述,或用中醫的病機或證候屬性加西醫學病名表述,或用西醫病名加癥狀表述)兩部分[5―6],對“功能”和“主治”項的信息分別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中成藥品種統計結果
國產中成藥共涵蓋1 315個品規,從中篩選出1 311個品種。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共涵蓋48個品規,從中篩選出43個品種,按用藥途徑分類,分為外用類中成藥(20種)、口服類中成藥(23種),其中外用類劑型以油劑、搽劑為主,口服類劑型以片劑、膠囊劑和丸劑為主。結果見表1。

表1 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品種統計結果
2.2 中成藥說明書“功能”項表述分類對比結果
1 311份中成藥說明書中有3份缺失“功能”項描述,43份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中有11份缺失“功能”項描述,故對1 308份國產中成藥和32份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中“功能”項表述分類進行對比分析。結果顯示,國產中成藥、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以中醫類術語表述的分別占94.04%、87.50%,如九味羌活丸的功能表述為解表、散寒、除濕;以中西醫結合類術語表述的分別占4.89%、12.50%,如杜仲顆粒說明書“功能”項表述為補肝腎、強筋骨、安胎、降壓,其中補肝腎、強筋骨、安胎屬于中醫類術語,降壓屬于西醫類術語;國產中成藥說明書以西醫類術語表述的占1.07%,如地榆升白片說明書“功能”項表述為升高白細胞,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功能”項中不存在采用西醫類術語的表述分類。結果見表2。

表2 中成藥說明書“功能”項表述分類對比結果
2.3 中成藥說明書“功能”項中的西醫類術語分類對比結果
由表2可知,說明書“功能”項中,分別有78種國產中成藥和4種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包含西醫類術語(包括中西醫結合和西醫2類)。國產中成藥說明書“功能”項中的西醫類術語涉及抗炎(消炎)的占比最高(占37.18%),增加冠狀動脈血流量、改善微循環排名第2位(占15.38%);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功能”項中的西醫類術語涉及抗炎(消炎)的占比最高(占75.00%),其他類占25.00%。結果見表3。

表3 中成藥說明書“功能”項中的西醫類術語分類對比結果
2.4 中成藥說明書“主治”項表述分類對比結果
中成藥說明書“主治”項信息種類豐富,主要包含疾病、證候、癥狀與體征3種要素,將上述3種要素進行組合得到6種主要的表述分類,具體見表4。6種“主治”項表述分類中,國產中成藥說明書以證候-疾病-癥狀與體征表述的占比最高(占48.28%),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以癥狀與體征表述的占比最高(占48.84%),如復方地龍片說明書“主治”項表述為“用于缺血性中風中經絡恢復期氣虛血瘀癥,癥見半身不遂、口舌歪斜、言語蹇澀或不語、偏身麻木、乏力、心悸氣短、流涎、自汗等”。其中“缺血性中風中經絡”為疾病信息,“氣虛血瘀癥”為證候信息,“癥見半身不遂,口舌歪斜……”為癥狀與體征信息。國產中成藥說明書以疾病表述的占比最小(占1.37%),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以疾病表述的占比為16.28%,如蛇傷解毒片說明書“主治”項表述為“用于各種毒蛇咬傷”,其中“毒蛇咬傷”為疾病信息。

表4 中成藥說明書“主治”項表述分類對比結果
對中成藥說明書“主治”項是否包含中醫證候類表述(包括證候-疾病-癥狀與體征、證候-疾病、證候-癥狀與體征3類)進行分類統計,具體見表4。結果顯示,分別有949份(占72.39%)國產中成藥說明書和11份(占25.58%)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中包含中醫證候類表述;分別有362份(占27.61%)國產中成藥說明書和32份(占74.42%)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未包含中醫證候類信息。由此可知,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臨床用藥依據以辨病用藥為主。
2.5 說明書“主治”項疾病的分類對比結果
由表4可知,在1 311份國產中成藥說明書“主治”項表述中,證候-疾病-癥狀與體征、證候-疾病、疾病-癥狀與體征、疾病4類“主治”項表述分類中均包含了疾病信息,共計1 027份(占78.34%);而在43份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主治”項表述中,有19份(占44.19%)包含疾病信息。進一步挖掘分析可知,說明書中的疾病類型可以分為中醫疾病、西醫疾病、中醫與西醫疾病結合3種類型。結果顯示,國產中成藥、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以西醫疾病表述的分別占64.85%、73.68%,如小兒咳喘靈顆粒說明書“主治”項表述為用于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咳嗽,其中“上呼吸道感染”屬于西醫疾病;以中醫疾病表述的分別占19.18%和26.32%,如小敗毒膏說明書“主治”項表述為用于瘡瘍初起、紅腫熱痛,其中“瘡瘍”屬于中醫疾病;以中醫與西醫疾病結合的表述,國產中成藥說明書占15.97%,如龍血通絡膠囊說明書“主治”項表述為用于中風病中經絡(輕中度腦梗死)恢復期血瘀癥,其中“中風病中經絡”屬于中醫疾病,“輕中度腦梗死”屬于西醫疾病,而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此項無分類表述。由此可見,國產、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臨床用藥依據以針對西醫疾病用藥為主。結果見表5。

表5 中成藥說明書“主治”項疾病的分類對比結果
3 討論
中成藥說明書是反映中成藥基本信息的文書,是醫師臨床用藥的核心依據。盡管不同種類中成藥的說明書結構基本一致[7―8],但中成藥說明書不同條目下的內容普遍存在表述分類多樣的問題,這也使得臨床醫師使用中成藥時存在用藥依據不充足、中成藥治療優勢不突出等問題[9―10]。
從本研究結果可知,目前國產中成藥、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功能”項以中醫類術語表述為主,占比分別為94.04%和87.50%。以中醫類術語表述是中成藥具備中醫藥特色的關鍵內容之一,中醫類術語表述主要從中醫藥角度概括中成藥的功能和作用特征,但該表述分類給中醫基礎理論薄弱的西醫醫師帶來了不小的挑戰,可能導致西醫醫師不能全面把握中成藥治療的作用特點,從而發生不合理用藥的情況[11]。國產、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功能”項以中西醫結合類術語表述的分別占4.89%和12.50%,也存在單純采用西醫類術語表述的方式,但西醫類術語在國產中成藥說明書中占比最低,僅為1.07%,而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功能”項中不存在單純采用西醫類術語的表述分類。盡管如此,中西醫結合類和單純西醫類術語表述的出現是中醫藥現代化發展的結果,這有助于臨床醫師尤其是西醫醫師合理選擇使用中成藥。然而,針對以單純西醫類術語表述的中成藥品種,在加強其物質基礎與藥理作用等現代研究的基礎上,也需要重視其中醫藥理論內涵,否則可能導致該類藥物脫離中醫藥理論指導,臨床定位模糊,增加用藥風險[12]。
辨證論治是中醫藥理論體系的核心內容。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看出,目前國產、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中包含中醫證候類的表述分別占72.39%和25.58%,表明臨床上使用的大部分中成藥可充分發揮其辨證用藥的優勢;同時,對未包含中醫證候類表述的說明書進行統計分析,即對說明書中以疾病、癥狀為主要表述的國產、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說明書分析可知,二者占比分別為27.61%和74.42%,可以看出大部分的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在使用時多以辨病為主,且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在臨床上的療效也是有目共睹的,從側面證明了病癥結合用藥已具備堅實基礎,這為國產中成藥加強辨病用藥研究提供了參考。
在現代醫學中,疾病的發病原理和傳統中醫藥理論具有相似之處,二者皆與正氣(內因)和外邪(外因)有關,即“正氣存內,邪不可干”“正邪相爭,百病之由”[13],說明在中醫藥理論指導下的中成藥,也具有辨病用藥的特點。中成藥的辨病用藥分2種情況:一種為辨西醫疾病用藥,另一種為辨中醫疾病用藥。在中醫理論體系薄弱的情況下,辨病用藥更加符合西醫的用藥思路[14]。本研究結果顯示,國產、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主治”項以西醫疾病表述為主,占比分別為64.85%、73.68%。由此可見,中成藥圍繞西醫疾病為主線開展辨病研究已奠定了堅實的辨病用藥基礎;其他已審批上市的未能包含西醫疾病類型的中成藥亟須加強辨病用藥研究,可參考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的研究模式。日本的漢方制劑基于“方證相對”理論對病機進行簡化,在該理論指導下,漢方制劑藥品說明書并未涉及辨病用藥的表述,而多以西醫病名和具體癥狀表述[15―17]。德國通過投料標準提取物,控制藥品質量穩定性,對天然藥物進行質量、毒理學和以疾病為導向的臨床研究,這也為中成藥現代化發展和辨病用藥研究提供了思路[16,18]。以銀杏葉制劑為例,國產銀杏葉制劑說明書中疾病的適用范圍遠小于德國進口藥銀杏葉提取物(商品名“金納多”)。我國首個獲批的中藥創新藥桑枝總生物堿片說明書中明確指出其適應證為“配合飲食控制及運動,用于2型糖尿病”,屬于可辨病使用的中成藥。可見,中成藥在適應國際國情基礎上,通過開展物質基礎和藥理藥效等研究,可逐步形成國際公認的傳統藥物研究標準,這可為加強辨病用藥研究,解釋辨病用藥科學內涵提供有力支撐[16]。
綜上所述,國家醫保目錄中的國產中成藥多數具備辨病使用的依據,所辨疾病主要為西醫疾病;進口及港澳臺地區中成藥多數具備辨病使用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