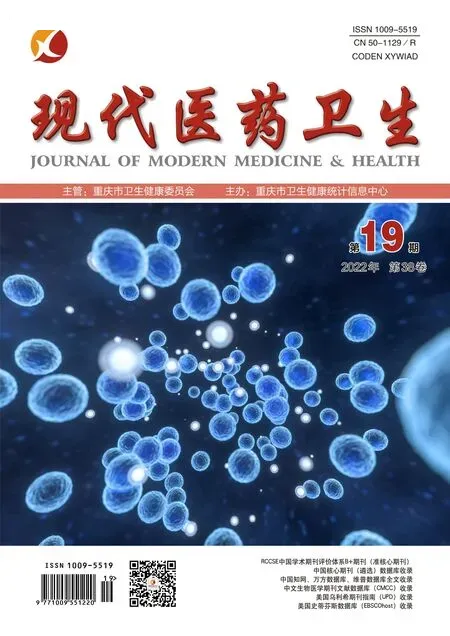腦性癱瘓兒童骨質疏松相關指標調查研究*
董尚勝,陳艷娟,黃小麗
(江門市婦幼保健院,廣東 江門 529000)
腦性癱瘓(CP)是一組持續存在的中樞性運動和姿勢發育障礙、活動受限癥候群,這種癥候群是由于發育中的胎兒或嬰幼兒腦部非進行性損傷所致。CP兒童的運動障礙常伴有感覺、知覺、認知、交流和行為障礙,以及伴有癲癇和繼發性肌肉、骨骼問題等[1]。CP兒童的骨健康問題是該類兒童迫切要面臨的嚴峻議題,3歲后大部分未進行體檢,骨骼問題也很少得到良好的建議。由于一、二級防治的缺失,并多伴有不同程度的肢體功能障礙(尤其下肢負重障礙)、戶外活動或日曬時間減少、營養障礙、服用抗癲癇藥等導致CP患者骨密度(BMD)明顯低于正常兒童[2]。CP患者伴有骨質疏松是影響此類兒童生活質量的高風險因素,基于此,對CP兒童進行系統的骨骼健康管理是重中之重。本研究調查了0~8歲不同類型CP兒童骨質疏松癥指標的分布情況及相關因素,旨在為后繼的抗骨質疏松治療的相關研究進行前期數據準備。
1 資料與方法
1.1資料
1.1.1一般資料 按就診順序選取2020年4月至2022年12月本院兒童康復科收治的0~8歲CP兒童74例,其中男47例,女27例;平均年齡(3.84±2.22)歲;CP分型:痙攣型四肢癱23名,痙攣型雙癱26例,偏癱型6例,共濟失調型12例,不隨意運動型7例;粗大運動功能分級系統(GMFCS)分級:1級10例,2級37例,3級14例,4級5例,5級8例。選取同期在本院兒保科進行健康體檢的0~8歲兒童90例作為對照,其中男50例,女40例;平均年齡(4.25±2.85)歲。2組研究對象性別、年齡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1.1.2診斷標準 CP診斷標準:采用2015年中國CP指南制定的標準[1],指出生前至出生后發育時期非進行性腦損傷所致的綜合征,主要表現為中樞性運動障礙及姿勢異常,常表現為姿勢及肌張力等方面問題,伴骨骼、智力、語言、心理等方面的障礙。
1.1.3納入標準 (1)符合兒童CP診斷標準,CP類型不限;(2)年齡0~8歲;(3)對本研究知情同意,兒童的家屬愿意參與。
1.1.4排除標準 (1)代謝病等引起的骨質疏松;(2)CP伴成骨不全等;(3)伴有嚴重急性病或長期服用抗癲癇藥、糖皮質激素等;(4)近半年有口服及靜脈使用雙膦酸鹽者。
1.2方法
1.2.1資料收集 足夠的營養元素及熱量的攝入、維持正常范圍的體重指數(BMI)及血紅蛋白(Hb)是CP兒童抗骨質疏松的基礎[3]。故收集74例兒童的BMI、Hb等指標,以及與相關因素有關的指標,如CP分型、步行能力分類、GMFCS分級、性別、年齡等。
1.2.2維生素D、血鈣檢測 兒童血清25羥維生素D水平及血鈣是監測骨質疏松的首先實驗室指標,目前認為血清25羥維生素D水平應大于50 nmoL/L,37.5~50.0 nmol/L為維生素D不足,12.5~<37.5 nmol/L為維生素D缺乏,<12.5 nmol/L為維生素D嚴重缺乏。
1.2.3雙能X線吸收儀(DXA)檢測 DXA是兒童評估骨量的首選方法,因其具有良好的可重復性和速度,減少了對電離輻射的暴露,并且可獲得大量參考數據[4]。BMD、骨礦含量(BMC)與兒童骨質疏松明顯相關。DXA測量結果可用T、Z值表示。BMD的T值為將檢查所得到BMD與健康年輕人群BMD相比,以得出高于或低于年輕人的標準差。Z值為將檢查所測得的BMD與健康同年齡同性別人群BMD比較而得出的值[5]。檢測部位為雙側前臂。

2 結 果
2.1CP與健康兒童骨質疏松相關指標比較 不同CP分型兒童BMC、BMD、Hb、血鈣、維生素D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痙攣型四肢癱兒童BMC、BMD、血鈣、維生素D水平最低,偏癱型兒童Hb水平最低;不同GMFCS分級兒童BMC、BMD、Hb、維生素D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血鈣水平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BMC、BMD隨GMFCS級別升高而明顯下降,Hb以GMFCS級別中1級最低,維生素D水平隨GMFCS級別升高而降低,4級最低;CP兒童BMC、BMD、血鈣、維生素D水平與健康兒童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CP與健康兒童骨質疏松相關指標比較

續表1 CP與健康兒童骨質疏松相關指標比較
2.2不同行走功能CP兒童骨質疏松相關指標比較 不同行走功能CP兒童BMD、Hb、維生素D水平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BMD、維生素D水平隨行走能力降低而降低,下肢很少負重的CP兒童BMD、維生素D最低,Hb以扶行的CP兒童最低。見表2。

表2 不同行走功能CP兒童骨質疏松相關指標比較
2.3不同年齡、GMFCS分級CP兒童Z值比較 不同年齡、GMFCS分級CP兒童Z值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隨GMFCS分級升高,CP的低Z值比例明顯增加(1~2級:61.70%;3級:64.28%;4~5級:76.92%)。見表3。

表3 不同年齡CP兒童Z值比較[n(%)]
2.4相關因素分析 BMC與年齡呈正相關,與BMI、行走情況均呈負相關(P<0.05);BMD與年齡、分型均呈正相關,與GMFCS分級呈負相關;Z值與年齡、分級、行走情況均呈負相關,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相關因素分析
3 討 論
3.1臨床意義 CP兒童骨健康問題是此類兒童迫切要面臨的嚴峻議題,國內外對其骨骼發育的生理、病理等進行的單獨研究較少見,對其骨骼的保健及骨骼疾病的治療的研究也面臨著嚴重的缺失[6]。目前,家長對于CP兒童骨骼疾病的一級預防關注不足,其更多關注運動、語言、智力等方面的康復,早期進行兒童保健的次數明顯減少,骨骼問題也很少得到良好的建議。CP患者骨質疏松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嚴重問題,其患病率高,可引起的疼痛、自發性或繼發骨折、血鈣改變等一系列問題,但國內外仍沒有很好的CP患者骨質疏松的指引,導致其難以防治,致殘率高,預后不佳[7-8]。本研究從臨床實際出發,研究CP兒童的骨質疏松相關指標,可以更有效地了解其骨質疏松相關指標的分布,為后期提前預防做好準備。
3.2骨質疏松相關指標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BMC、BMD、維生素D 三方面受CP兒童的嚴重程度影響明顯。痙攣型四肢癱、不隨意運動型,以及GMFCS分級為3~4級的CP兒童均為嚴重類型的CP代表,此類兒童多由于一、二級防治的缺失,并多伴有不同程度的肢體功能障礙(尤其下肢負重障礙)、戶外活動或日曬時間減少、營養障礙、服用抗癲癇藥等,導致其BMD明顯低于健康兒童[2]。由表3可見,低Z值率為61.70%~76.92%,與國外相關骨質疏松指標研究結果相似。有學者在其關于CP患者骨折、骨質疏松及相關影響因素的系統評估文獻中,7篇描述骨折流行病學研究,11篇描述了低BMD的流行病學,14篇描述了相關風險,中重度CP患者骨折的發生率每年接近4%,而股骨低BMD的患病率是77%,低BMD與活動受限、進食困難、繼往骨折、抗癲癇藥物的使用相關,低BMI與較低的BMD的Z評分相關[9]。
3.3CP兒童骨質疏松指標及骨折風險 本研究收集的病歷未發現有骨折現象,但臨床中仍可見到長期不能行走及營養不良的CP兒童隨年齡增加骨折風險明顯增加,但本研究中收集的年齡均以學齡前為主,不排除后期發生骨折的可能性。本研究結果顯示,CP患者BMD、BMC均普遍偏低,導致脆性骨折的風險增加。有研究報道,不能行走的CP兒童及青年的骨折發生率為20%左右,其中重度CP患者每年骨折發生率為7.0%~9.7%,骨折最常見的部位為股骨遠端[3]。CP患者骨質疏松多伴隨一系列障礙,CP兒童骨折發生率較高,骨質疏松是骨折最常見的原因,骨折可造成CP兒童生活質量快速下降;骨關節變形或脫位,如膝外翻、膝內翻、髖關節脫位、脊柱側彎等;骨疼痛明顯,長期的骨疼痛嚴重影響康復及睡眠質量;體格發育差,身高大多數低于同年齡健康兒童。
3.4CP兒童骨質疏松指標的相關因素分析 本研究結果顯示,CP兒童受累部位、嚴重程度、行走能力、營養狀況與CP兒童骨質疏松指標明顯相關,與相關CP骨質疏松危險因素研究結果相似。目前,關于CP患者骨質疏松危險因素的研究較少見,其危險因素多與骨折相關,且主要的危險因素包括低BMD、營養狀態、神經受損程度、GMFCS分級、關節肌肉變形情況、維生素D補充、鈣攝入、抗癲癇藥物使用等方面。PATICHEEP等[10]研究表明,骨折、低BMD與癲癇發作、服用抗癲癇藥密切相關。HENDERSON等[11]使用逐步回歸分析發現,殘疾兒童股骨遠端BMD降低的危險因素按重要性由高至低為神經功能障礙的嚴重程度、進食困難程度、抗癲癇藥使用和營養狀況。HENDERSON等[12]在對CP患者低BMD危險因素的研究中發現,體重Z評分是BMD的Z評分的最佳預測指標,體重Z評分低于平均值-2SD可預測BMD的Z評分也低于平均值-2SD。另外,抗癲癇藥和進食困難進一步降低了預測的BMD。因此,早期做好CP兒童骨質疏松的分類,做好預防。
綜上所述,CP患者骨質疏松是一個容易被忽視的嚴重問題,其患病率高,可引起疼痛、自發性或繼發骨折、血鈣水平改變等一系列問題,但國內外仍沒有很好的CP患者骨質疏松的指引,導致難以防治,致殘率高,預后不佳[13-14]。今后應提高對CP患者的三級防治的意識,提高對一般的預防措施,如肢體訓練、營養、常規鈣元素及維生素D的補充,完善及做好CP兒童骨質疏松的規范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