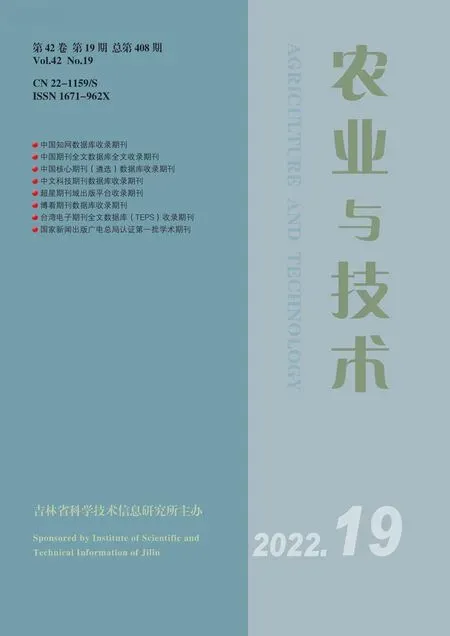騰格里沙漠東北緣飛播造林對植被多樣性的影響
高苗苗蒙仲舉高永張睿姝張麗烏蘭圖雅何英
(1.內蒙古農業大學沙漠治理學院,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18;2.阿拉善左旗林業工作站,內蒙古 阿拉善 750300)
植被是自然環境中最敏感的組成要素,也是最能反映自然條件變化的標志之一[1],營造人工植被是干旱、半干旱區荒漠化防治最為有效的治理手段。飛播造林措施是快速有效實現荒山或沙地植被重建與恢復的重要途徑,因速度快、范圍廣、省勞力、投入少、能深入人煙稀少的偏遠地區等優勢[2],被選為治理內蒙古阿拉善盟境內騰格里沙漠東北緣植被恢復與重建的重要措施。植被群落的變化是反映生態恢復程度的關鍵部分,其物種組成、優勢種變化、物種多樣性不僅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群落的生境變化趨勢[3],更能有助于把握對抗外界干擾的能力[4]。慕宗杰[4]等通過研究渾善達克沙地飛播區不同恢復階段植物群落結構的變化,總結出隨植被恢復時間延長,植被穩定性逐漸增強。李禾[5]等對毛烏素沙地飛播區植被多樣性研究表明,隨飛播年份增加,群落結構逐漸復雜,以飛播植物為優勢種的飛播群落逐漸向毛烏素沙地的頂級群落演替。汪有科[6]等闡述了吳旗飛播區沙打旺草地的群落動態,分析發現沙打旺的快速演替實質是群落內部能量的再分配過程,這種再分配對草地改良、田草輪作十分有利。斯琴畢力格[7]等對鄂爾多斯市3個旗沙地飛播造林區進行分析得出植被恢復的多樣性主要為物種豐富度所推動,而與植被的優勢度和多樣性指數沒有明顯關聯。因此,深入了解沙地植被恢復過程與變化規律,有助于揭示植被演替機制,對沙地植被生態恢復、穩定干旱區生態系統具有重要作用。
綜上所述,多數學者對飛播造林植被恢復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庫布齊、毛烏素、渾善達克等沙地飛播造林區植物群落多樣性以及不同飛播植物、植被群落結構和飛播年限等因子對土壤理化性質的影響,對于騰格里沙漠飛播造林區植被群落結構、生物多樣性特征的研究相對稀缺。鑒于此,本研究主要以騰格里沙漠東北緣飛播造林區植被為研究對象,探究飛播造林區植被恢復過程中灌木與草本的動態變化趨勢,旨在明確該地區飛播后植被恢復變化趨勢,以期為后續開展飛播造林工作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研究區位于內蒙古阿拉善盟左旗境內騰格里沙漠東北緣飛播造林區,地勢東南高,西北低,屬溫帶大陸性干旱荒漠氣候,日照充足,蒸發量大,無霜期較短,溫差較大。年均氣溫8.5℃,年均降雨量80~200mm,年均蒸發量2900~3300mm。飛播造林區土壤類型屬流動風沙土。受氣候、地貌影響,騰格里沙漠東北邊緣主要植物為霸王(Sarcozygium xanthoxylon)、貓頭刺(Oxytropis aciphylla)、白刺(Nitraria tangutorum)等,偶見一年生植物沙蓬(Agriophyllum squarrosum)和珍珠豬毛菜(Salsola passerina)等。
1.2 研究方法
1.2.1 試驗地選取
于2021年7月,通過查閱相關資料,并經過實地勘察,飛播造林區均采用花棒(Hedysarum scoparium)、沙拐棗(Calligonum mongolicum)、籽蒿(Artemisia sphaerocephala)為飛播物種,沙丘高度以及成土母質基本相似,基于此選擇2001年播區(巴潤別立鎮沙勒庫岱嘎查)、2004年播區(豪斯布爾都蘇木浩坦淖爾嘎查)、2008年播區(吉蘭泰鎮哈圖呼都格嘎查)、2018年播區(吉蘭太鎮蘇里圖嘎查)內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樣地,共計4個樣地。樣地基本情況見表1。

表1 飛播造林區樣地基本情況
1.2.2 植被調查
每塊樣地內均設置3條長1000m樣帶,在每條樣帶間隔200m設置一個樣點,每個樣點布設10m×10m灌木樣方,用于調查灌木及半灌木,在灌木樣方內對角線及中心各設置1個1m×1m草本樣方用于調查草本植物。調查內容為各樣方內植被的總蓋度及不同植物種的名稱、自然高度、蓋度、密度等。
1.2.3 數據分析方法
灌木與草本將同一恢復年限植物種群高度、蓋度和密度進行平均,作為相應年份植物種群的高度、蓋度和密度,并對飛播造林區植物群落的高度、蓋度、密度進行分析,以明確飛播后播區植物群落的數量特征變化。
物種多樣性選用Margarlef豐富度指數、Pielou 均勻度指數、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Simpson優勢度指數和重要值等對飛播造林區不同恢復年限的植被群落進行測定分析。計算公式:
重要值=(相對高度+相對蓋度+相對密度)/3
相對高度=(物種高度/樣方內全部物種高度之和)×100
相對蓋度=(物種蓋度/樣方內全部物種蓋度之和)×100
相對密度=(物種蓋度/樣方內全部物種蓋度之和)×100
Margarlef豐富度指數(R):

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H′):

Simpson優勢度指數(D):

Pielou均勻度指數(E):

優勢度指數(C):

式中,S為樣方內物種數目;Pi表示第i種植物的重要值;N為總個體數量;ln為自然對數。
2 結果與分析
2.1 飛播造林區植物群落物種組成及重要值
由表2、表3可知,飛播造林區植被恢復過程中,樣地內植物群落主要由21種植物構成,隸屬9科17屬。其中灌木有4種,即隸屬于3科4屬,占總物種數19.05%;半灌木2種,隸屬于2科2屬,占總物種數9.52%;草本植物有15種,隸屬于6科13屬,占總物種數71.43%。騰格里沙漠東北緣飛播造林區植物主要由天然植物和飛播植物構成,其中飛播植物有3種,分別為花棒(Hedysarum scoparium)、沙拐棗(Calligonum mongolicum)、籽蒿(Artemisia sphaerocephala),這3種植物均呈現抗干旱、耐鹽等特點,是飛播造林樹種選擇的優勢種。

表2 飛播造林區植被生活型組成特征
由表3可知,飛播造林區植被恢復3a,主要以飛播植物為主,草本層僅有沙竹和蘆葦。恢復13a以籽蒿為優勢種,草本層種類逐漸豐富,出現沙蓬、堿蓬(Suaeda glauca)和蒙古蟲實(Corispermum mongolicum)等;恢復17a天然植物與飛播植物都生長趨勢較好,植物種類共有15種,物種種類最豐富,以花棒為優勢物種,天然植物白刺也得到有效的恢復,其重要值為0.36;恢復20a時物種種類有降低趨勢,主要以籽蒿為優勢物種,但蒙古蟲實、珍珠豬毛菜、油蒿(Artemisia desertorum)、沙蓬、針茅(Stipa capillata)、堿蓬等草本層植物其重要值從0分別上升到0.25、0.03、0.04、0.06、0.03、0.16。飛播造林區植被群落類型共3種,見表4,隨植被恢復年限延長,飛播造林區植被群落結構由單一的半灌木群落逐漸變為灌木群落和半灌木加草本群落,草本層植被逐漸豐富。

表3 飛播造林區植被物種重要值

表4 飛播造林區各樣地植被群落類型
2.2 飛播造林區植被恢復群落數量特征變化
由表5可知,飛播造林區各植被層平均高度隨植被恢復年限延長總體表現出增長的趨勢,在植被恢復20a時平均高度最高,灌木層植被平均高度較3a、13a和17a,分別增長100.65%、55.58%、17.50%,草本層平均高度分別增長331.33%、15.68%、107.02%,各植被群落差異顯著(P<0.05)。隨著恢復年限得增加,各植被群落得平均蓋度總體呈上升的變化趨勢,植被恢復20a平均蓋度較3a分別增加99.82%、460.34%,草本層不同恢復年限間差異顯著(P<0.05)。平均密度隨植被恢復年限延長各植物群落呈現波動式上升,各層隨恢復時間的延長均有明顯差異(P<0.05)。

表5 飛播造林區植物群落高度、蓋度和密度的變化
2.3 飛播造林區植物恢復群落物種多樣性變化
通過對飛播造林區不同生活型植被多樣性綜合分析發現,見表6,飛播造林區R、H′、D指數逐年呈上升趨勢,草本層物種種類逐漸增多,飛播造林措施對騰格里沙漠東北緣沙地固定與植被恢復具有顯著成效;飛播造林區植被恢復20a H′與D較3a分別增長89.74%、57.45%,植物各層的多樣性逐漸豐富;飛播造林區C隨著恢復年限延長呈先升高后降低的趨勢,各恢復年限灌木層植被均勻度指數顯著高于草本層;綜上所述,騰格里沙漠東北緣飛播造林區植被恢復狀況穩步增進,草本層在群落中相對占優勢且分布均勻、植被種類繁多。
3 討論
飛播造林是一種大面積治理土地沙漠化與植被快速恢復的沙漠治理方法,在騰格里沙漠東北緣沙地的植被建設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由于飛播后沙地植物成功定居引起群落環境變化,進而對天然植被的生長與繁殖產生一定影響[8]。本研究表明,飛播造林區植被隨時間的延長,物種數明顯升高,但恢復20a時沙地植物的物種數出現下降趨勢。分析其原因,沙地條件不同,氣候多變,不同植物種類自身的生態適應條件有差異,使得恢復20a植物種類相比恢復17a的略低。在沙地不同恢復階段,豆科、蓼科、菊科和禾本科表現出較強的適應能力,流動沙地向固定沙地轉變,沙地植被恢復效果明顯好轉,這與姚國龍[9]對毛烏素沙地不同演替階段沙地植被群落物種多樣性研究結果相似。飛播后,飛播物種耐沙埋、發芽快、生長迅速并且繁殖能力強[10],迅速成為沙地群落的優勢種,因此,沙地植物群落特征也發生一定變化,即在植被恢復的過程中,植物群落的平均高度、平均蓋度和平均密度均有明顯提高,這也進一步驗證飛播造林對天然植被恢復有促進作用。

表6 飛播造林區分層物種多樣性指數
騰格里沙漠東北緣飛播造林區隨植被恢復,一年生草本逐漸占有一定優勢,總物種數達到71.43%,灌木與半灌木次之,分別占總物種數的19.05%和9.52%,表明群落組成結構向多樣化和復雜化發展,沙地逐步穩定。重要值是荒漠植被的綜合體現,通過重要值確定群落類型,能客觀反映植物物種在群落中的相對重要性。本研究結果表明,在飛播造林區植被恢復過程中,群落由單一半灌木類型逐步發展為灌木和半灌木加草本組合類型,說明飛播物種在雨季快速發芽并定居,形成防風屏障,阻止沙丘表面沙粒流動,飛播造林區天然植被得到有效保護,同時為其他植物定居創造穩定的土壤環境,飛播物種與天然植被共生效果較好。張翼飛等[11]對巴丹吉林和庫布齊2大沙漠共計12個點的植被進行調查,結果也顯示以灌木為建群種后都伴有大量一年生沙生先鋒物種植物。因此飛播有助于沙地天然植被的恢復與重建。
物種多樣性是生物多樣性的中心,也是生物多樣性最主要的結構和功能單位[12]。植被群落演替會伴隨著多樣性的變化,有的觀點認為隨植被恢復演替,物種多樣性會逐漸增加[13],還有觀點認為在演替初期到中期物種多樣性會升高,到達峰值后在演替后期則呈現下降趨勢[14]。本研究中,物種多樣性指數隨植被恢復進程先升高后降低。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隨植被的恢復,地表有機物的分解和土壤養分的增加,提高了各物種的競爭能力,導致植被恢復20a時物種多樣性有下降的趨勢,此外,沙漠地區水分限制也是造成物種多樣性指數下降的原因之一。荒漠植被的特征可用物種多樣性指數來體現。司建華等研究阿拉善雅布賴風沙區荒漠植被群落物種多樣性在0.23~1.09[15],騰格里沙漠東南邊緣荒漠植被群落物種多樣性在0.60~1.63[16],新疆阜康綠洲荒漠過渡帶植物群落物種多樣性在0.48~1.57[17],歸納荒漠沙地植被群落物種多樣性普遍偏低,群落整體結構簡單,物種組成稀少,這與荒漠生境條件惡劣且種的分布不均勻有關。本研究區群落H物種多樣3a和17a灌木層>草本層,13a和20a灌木層<草本層,但飛播造林區整體H物種多樣現在0.78~1.48,符合上述沙區研究特點,可見,飛播造林區物種多樣性整體隨植被恢復年限延長而增長,說明飛播造林措施有效促進騰格里沙漠東北邊緣飛播造林區植被恢復。
4 結論
通過對騰格里沙漠東北緣飛播造林區群落數量特征及多樣性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騰格里沙漠東北緣飛播造林區植被恢復處于穩步發展階段。飛播造林區共21種植物,隸屬9科17屬,植物種大多屬于蓼科、菊科、禾本科;灌木層以飛播物種籽蒿或花棒為主,草本層多為旱生或鹽生性植物,如油蒿、蒙古蟲實、珍珠豬毛菜等;在植被恢復過程中,群落由單一灌木類型逐步演變為灌木與半灌木加草本組合類型。
騰格里沙漠東北緣沙地植被群落灌木層的平均高度、密度總體表現為恢復20a比恢復初期3a高出2倍,平均蓋度20a>13a>17a>3a;隨著植被恢復年限的增加,草本層植被各生長指標總體呈上升趨勢,綜上可知,飛播造林有利于改善沙地植被群落環境,植被生長狀況穩定提高。
沙區的生境條件決定群落多樣性指數,降雨是植物生長主要獲取水分的來源。研究區隨著植被恢復年限延長,草本層Shannon-Wiener多樣性指數和Simpson多樣性指數均高于灌木層,總體植被恢復向著穩定和物種多樣的方向發展,環境得到改善的同時也會加速植被演替的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