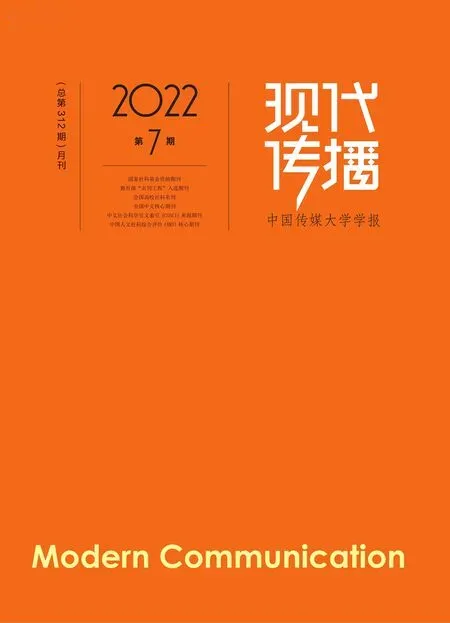物的想象:考古遺存的媒介屬性與主體實踐*
陳華明 孫藝嘉
2021年,習近平總書記在“七一”重要講話中強調要“以史為鑒,開創未來”并由此創建“人類文明新形態”①,歷史悠久、底蘊渾厚的中華文明即將或已經步入世界舞臺中央。我國現代考古學以1921年河南澠池仰韶遺址的發掘為起點,經歷百年發展,在探尋我國古代社會及其文明方面取得了諸多突破。“遺存”是考古學的研究對象,“遺”是指古代人類活動遺留的,“存”即客觀存在、看得見摸得著的實物。②本文的“考古遺存”即指考古學所關注的古代遺留下來的物質性資料,包括實物載體以及載體上的可用信息。考古遺存的研究“延伸了歷史軸線,增強了歷史信度,豐富了歷史內涵,活化了歷史場景”,它對中華文明的內核探索實現了由“中原中心論”到“多元一體論”的認識論轉向。③可見,考古遺存是五千年中華文明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靈魂和精神源泉。“要加強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豐富全社會歷史文化滋養。”④簡言之,“讓遺存活起來”是當下文化建設的重要命題,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目前對于遺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考古學和歷史學領域,重在開發和保護,對其價值利用與傳播推廣的討論尚為缺乏。
而在傳播學的視角下,物質性與文本性交織于對媒介的認知變化中⑤,考古遺存在“物”的具象形態上兼具信息承載與意義彰顯,具有明顯的媒介屬性。媒介考古學以媒介物質性的恢復為研究前提,關注媒介物的非線性歷史敘事和不同社會時代的聯系⑥,而考古遺存正是特定社會歷史情境下集文化內核于一體的物質性產物,面向過去而指向現在和未來,在文化與精神的傳承與撒播中涉及“‘物’與‘物質’的媒介構成、媒介要素、媒介過程和媒介實踐”⑦。本文從存在形態、價值功能和運作邏輯三方面展開論述考古遺存的媒介屬性和主體實踐,以傳播學、考古學和歷史學跨學科研究的視野,對其推廣與應用提供理論與實踐的思考。
一、本源、實體與互動:考古遺存的媒介存在形式
“媒介”是英文“media”的譯詞,源自拉丁文“medium”,大致有三層意涵:一是指“中介機構”或“中間物”,落在物理或哲學觀念上,即一種感官要去體驗或一種思想要去表現,則必須有一個中間物;二是指在技術層面,印刷、廣播、電視、網絡等不同技術形式形成了不同媒介;三則涉及在資本主義權力關系里,例如報紙或影視產業被視為是廣告的媒介。⑧在中國的古漢語中,只有“媒”而無“媒介”一詞,《說文》中解釋“媒”,即“謀也,謀合二姓者也”。“媒”(謀)的位置居間,以“介入”的姿態連接“二姓者”。不論是東方還是西方,對“媒介”本義和譜系的認知都是居中位置及交接轉化。⑨傳播學認為,“凡是能使人與人、人與事物或事物和事物之間發生聯系的物質都是廣義的媒介”⑩。綜上梳理,對“媒介”的認知包含了物質與信息層面、技術構成層面以及和外部互動構成的關系層面。從表征到本質、從具象到抽象,考古遺存作為具有媒介屬性的物,同樣具有這三層存在意涵。
(一)本源:自然性的存在
考古遺存的媒介本源是在歷史發展條件下與生俱來而自然存在的,分為有形的物質性載體和無形的功能性信息。傳統考古學所關注的遺存范疇大體包括遺物和遺跡兩類,但在傳播學視野下,考古遺存的內涵更為廣義,能夠勾連古往今來人類社會聯系的遺存媒介大體可分為三種。一是可移動的遺物,按照不同的原料材質和制作技術可分為石器、玉器、骨器、陶器、銅器、鐵器、金銀器、竹器、木器、玻璃器、紡織品和紙質等,也包括古人采集或種植的植物、狩獵或養殖的動物保存至今的遺骸。二是不可移動的遺跡,包括房屋建筑、墓葬、灰坑、水井、道路、窯、壕溝等。三是記載于實物之上并反映古時人類實踐與社會生活的信息資料,按照信息形式可分為語言文字,例如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和少數民族使用的文字;圖形符號,如圖騰;敘事文本,如神話傳說、歷史典故。按照信息內容可分為精神文化信息,如信仰、思想;行為文化信息,如民俗、舞樂雜技;制度文化信息,如政治、經濟、法律制度。
考古學發掘環境中的“物”來考察其形制、用途、放置的場所、曾經的使用者等,而媒介考古學的重點在于建立“物質檔案”,來研究這些物的發明、載體、機制、設備、空間在時間中的流變,對受眾施與的影響,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到人們身體、感官與認知的構成之中。從考古遺存的媒介本源中可以看到“物質檔案”的諸多知識線索存在于其中。以有形的物質為基礎,例如紙是書、繪、復印、印刷的物質,木、磚、瓦、石等是雕刻的物質,布是刺繡、紋飾的物質等等;無形的信息承載于其上,以文字及其載體的演化為例,從四千多年前刻寫在龜甲和牛、豬等動物骨頭上的甲骨文到兩千多年前鑄刻在青銅器上的金文再到刻在豎石上的碑文……這些文字記錄著我國歷史的發展過程和古代先民的所思所想,由此實現物質實物與抽象的文化知識自然性地共存。
(二)實體:技術性的存在
無論是有形的實物還是無形的信息,都來自于歷史社會上人們的生活實踐,然而隨著生產力和造物技術的不斷演化進步,相似功用的遺存在形制方面出現系統性的變遷,考古遺存的實體是技術性的存在。19世紀80年代,古斯塔夫·奧斯卡·蒙特留斯(Gustaf Oscar Montelius)創造“器物類型學”,通過對挖掘出土的同類器物進行“標型”用以歷史斷代,古斯塔夫·科西納(G.Kossina)提出“考古學文化”的概念來概括這種歷史分期,戈登·柴爾德(Vere Gordon Childe)則直接指出考古學文化是“一批總是反復共生的遺存類型——陶器、工具、裝飾品、葬俗和房屋式樣”。根據主要生產工具的不同,考古學將人類社會的歷史分期劃定為石器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和信息時代六個階段。以生活使用的炊飲器具為例,原始社會多用陶鼎、夏商周流行青銅鼎、漢代出現鐵釜、五代開始燒制青瓷釜……考古遺物在技術制造方面的集中類型普遍呈現出從石器、陶器到各種金屬器的遞進規律。因為加工制作物質實物需要相應的生產條件,工藝技術的精進、溫度濕度的把控、生產材料的探索使得人們所能利用的原始物料愈加廣泛,而后一種器物的發明在使用體驗上普遍要優于前一時期的工具,可見考古遺物的實體隨著技術的進步愈加復雜考究。
同樣,遺跡實體與技術二者的演化關系呈現近似規律。以墓葬為例,隨著儒學禮教和厚葬觀念的興起,古人愈加重視墓葬的修建,伴隨著建筑技術和裝飾技術的不斷進步,我國的墓葬形制在春秋戰國至魏晉六朝經歷了從豎穴土坑墓、土洞墓到磚石室墓的發展過程。從最開始的土坑土洞結構單一,用簡單的挖掘工具即可完成;發展到室墓,出現了“宅地化”特征,地下建造的墓室形態仿造地上的房屋建筑內部設計,這需要更為先進的建筑技術和裝飾技術作支撐。相比于土坑土洞,室墓的建造更加復雜,一些大型室墓在封土之下包含墓道、墓門、甬道、前室、中室、后室、側室、耳室等復雜結構設計,封土之上還有墳丘、塋地、墓垣、圍墻、圍溝等祭祀與保護設施。隨著磚瓦制作技術的成熟,大量帶有畫像雕繪的磚瓦也被設計和應用在墓葬內,使建筑實體更為精美。
考古遺存“物質檔案”中的信息線索隨著技術演化亦愈加豐富多元。譬如雕繪技術和原材料種類的豐富使圖形符號展示的形態發生變化,在原始社會中粗糙的石器只能勾勒出簡單幾何線條的巖畫,到漢代出現了線條更加細膩且相對具象的石刻畫像,在唐代,毛筆、硯、顏料、絲織品的使用成就了精美雕琢、色彩瑰麗的壁畫、帛畫,而至后世紙張使用更為普及,畫像題材和藝術表現形式更成體系。生產力的進步使物質載體不斷演進,依托其展示的畫像實體則伴隨著表現技術的成熟而傳播更加明確的媒介內容;畫面、色彩、符號等信息愈加豐富,體現出古人記錄生活、表達心志、傳遞情感等日趨復雜的精神結構。
(三)互動:關系性的存在
考古遺存依托物質和信息的自然性本源、技術性的實體,在媒介與人、媒介與社會的兩個維度上發生互動,其媒介存在形式的第三層即“人—媒介—社會”關系性的存在。約書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認為媒介技術推動并實現不同形態的“中介式交往”,一種是在微觀上,媒介塑造了個體特定的交往情境和互動形式,另一種是在宏觀上,新媒介與原有媒介矩陣的融合改變了社會互動和社會結構。考古遺存基于其物質性的結構使承載于其上的信息交流融合,以媒介的身份進行“經驗與意義之網”的編織與互動,從而實現分散個體到社會整體的關系性演化。
一方面,考古遺存在某種程度上建構了個體共同生活實踐的傳統。譬如在三峽地區因地勢條件的限制,古人在峭巖陡壁上鑿孔架橋連閣而成一種交通要道,即三峽古棧道。《戰國策·秦》記載“棧道千里,通于蜀漢”,川陜之間的棧道始建于戰國時代,雖在歷史過程中有過損毀,但當地人時有修繕,一直保留了這種通行方式,古棧道的遺跡沿用至今。按照貝爾納·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的表述,人因“原始性的缺陷”故必以技術的彌補而誕生和存在,技術就是人的代具。這種代具并非人體的簡單延伸,也不是人的“手段”或“方法”,它構成了“人類”身體,是人的“目的”,技術之于人是“外移的過程”,是人運用生命以外的方式來尋求生命。古棧道通過技術性的手段延伸了人的生存實踐,并通過代代峽民的沿用得以持續存在,古棧道與人的共生顯示著媒介與人的互動塑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并“限定了所有經驗性的人類社會”。
另一方面,考古遺存塑造了社會的文明和文化體系,形成社會共同體。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曾指出,文化的歷史就是媒介的歷史,文化或文明的過程可以借由不同歷史階段的技術或技術的使用來一窺究竟。從人到社會,通過媒介相勾連的人類經驗實踐指向了社會文本與文化文明的建構。根據哈羅德·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的媒介偏倚理論,考古遺存在時間向度上傳承文明,在空間向度上撒播文化。在時間性方面,文字發明以前,結繩記事的記錄方式難以承受時間的變遷完好延續;至殷商王室,甲骨文被用來卜占記錄、維系神權政治穩定;至后來漢字簡化,文字從皇權貴族普及到尋常百姓,承載文字的物質性載體也逐漸多樣化并在大眾中流行,更多信息得以保留和傳承,成為推動人類文明進程的利器。就空間性來說,考古遺存在不同文化區中發生互動,如漢朝開辟了海上和陸上絲綢之路,將我國紡織品、鐵器、漆器、瓷器等輸出到東南亞、東非和歐洲等地,相應的在我國遺存中也時常可見含有異域風情的舶來文化元素,如珠寶香料、玻璃器皿、佛教等。這促進了不同區域的文化交流并使文化樣貌逐漸趨同,“人類命運共同體”在“地球村”上和諧共生成為可能。
二、物性本體與時空存續:考古遺存的媒介功能呈現
進一步來看,“物性本體”和“時空存續”是考古遺存的核心媒介功能。“物性本體”是指考古遺存作為一種自然產生且具象呈現的物質性載體,在關系互動和文化信息傳播中發出抽象動作,這個發出動作并產生影響的過程即“物性”。正如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物是什么》云:“壺作為一個物而在場。壺作為一個物才是壺。但物如何在場?物物著。物化活動聚集著。”考古遺存作為具有媒介屬性的“物”,同時寓靜和動兩種狀態于其中。物以物性本體的方式在場,同時物性活動因為物的在場,將文化與意義的編碼輸入、聚集在物之上,所以考古遺存的物性本體,承擔了聚集在物之上的在場身份和傳播價值。對于“時空存續”的功能來說,媒介本身具有時空偏倚效能,物性本體的存續在同一個時間切片上的空間范圍內橫向延展,這使考古遺存的媒介功能具有了社會性特征;而其以靜止的空間范圍觀察,在時間的縱向延伸上使其媒介功能具有了歷史性面向。
考古遺存作為媒介嵌入從古至今人類實踐和文化生活之中,并以其悠久歷史和文化輻射力貫通“過去—現在—未來”社會。在某種程度上,考古遺存的媒介功能呈現不僅僅在于勾連人與社會的中介作用,而是作為一個行動主體參與到人與社會更深層次的互動實踐。具體來說,考古遺存的“物性本體”和“時空存續”的媒介功能呈現為:古時社會的基礎設施、現代社會的文化結構和未來社會的映射與延伸。
(一)古時社會的基礎設施
基礎設施反演理論認為基礎設施的基底是實在之物(Substance),同時它是一個關系性概念,顯現在特定的文化脈絡和有組織的實踐中。從古代社會的橫截面看,考古遺存維系著古人生活生產活動,是保障古代社會正常運轉的物質性條件,它具有天然強烈的社會性和可供性,是古時社會的基礎設施。首先,考古遺存以物的姿態為古時社會提供技術基礎。從人們生產生活的常用工具,到或簡單或復雜的聚落民居、墓葬、宗祠、寺廟、交通遺跡,都涵蓋了社會實踐的方方面面,通過技術的運作生動地參與到古代人的生產中并推動社會發展。其次,考古遺存的物性功能使其參與古時社會結構的構建。譬如夏商周的“傳國之寶”九鼎、秦代開始皇帝專用的玉璽、歷代皇室的宮殿、陵墓……這些遺存均是典型的皇權象征,用以區分社會階層,同時也是古代歷任統治者用來維系政權穩定的媒介。
“媒介的潛在特性、能力、約束范圍的關系,能夠在特定背景下配合行動者的感知展開行動。”而考古遺存正是通過古人的感知、選擇和使用與社會環境發生密切關聯,以媒介主體的姿態鑲嵌在社會組織的變遷和社會發展的規律里。如果說考古遺存是先民幾百年乃至于數百萬年一路走來留下的印痕,那么就如羅伯特·凱利(Robert L.Kelly)所說,在這些“腳印”中隱藏著“智慧密碼”,“這些密碼或隱或現,呈現出規律性的排列與組合”。考古遺存為了古代社會的實踐需要被人生產制造,以極大的可用性和實用性嵌入到人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構成了古時社會一般性的基礎設施,塑造了古代社會在不同歷史階段、不同層面上的多種樣貌。
(二)現代社會的文化結構
從古到今,考古遺存歷史性的功能延續使其在現代社會融入并成為社會文化結構的一部分。在現代社會語境下,考古遺存的實用性有所降低,更多地以“文化媒介”的身份存在,將古時社會的文化和精神延續至今并將其深刻地融入當今人們社會生活的血脈。例如對祖先的尊崇禮節、“以孝治國”的儒家傳統和“家國同構”的價值取向等精神內核均與自古以來的喪葬傳統有關,從考古遺存中的墓葬遺址及內部的隨葬品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可以體現。延續至今日,物質性的墓葬形制、制度化的殯葬儀式和精神性的思想觀念依舊存續,“對應于享有共同傳統、共同生活機構以及共同生活方式的一個社群”。考古遺存將中華民族這個群體與其他文化群體區分開來,在塑造這片土地上現代人的行為習慣和生活方式的同時,促使從個體到群體形成統一的認同感與價值觀,進而建構了民族的思維模式和文化傳統。
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將歷史“紀念物”視為記憶媒介、傳承媒介,紀念物把歷史在土地上做出立體的、物質的標記,以此產生帶有集體意義的、延續性的地方。譬如在邏輯語言出現之前,由骨骼、石頭等可以保存持久的材料做成的媒介,以物質象征和抽象符號代替了缺席的過去。考古遺存在時間上傳承文明、實現代際的文化延續,在空間上聯結同時代的人形成具有區域特色的集體。其物質實體的載體和抽象的內容符號在文明傳承與文明傳播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通過組織化、制度化的物性作用和互動過程,過往的歷史及其文化價值才得以在現時的社會中固定并持久存續。
(三)未來社會的映射與延伸
在尚不可知的未來,考古遺存以其物性本體和歷史性的偏向,能夠映射社會并延伸文化價值。約翰·杜翰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指出,“共時性”固然常常發生在橫向空間中,但也可以發生在縱向時間中;歷史并非總是以單線展開,而是以星羅棋布、群星燦爛的方式復現;現在與過去的某個時刻之間總是存在暗合,過去的現象會不時地、選擇性地在當下復活。他將19世紀后期的靈異研究和20世紀30年代的無線電研究相比較,認為二者在媒介元素及媒介動機上存在呼應之處,同時也有區別:19世紀末的人們關心靈媒如何作為生者與亡者交流的中介,而20世紀的人們則關心如何給冰冷的無線電訊號披上溫情的外衣。媒介考古學非線性敘事的歷史觀意味著歷史的傳承“在斷裂和拋棄中形成”,在蛛絲馬跡中探尋歷史社會如何復制與重現,考古遺存作為物質材料的穩定性和持久性保存了自然存在的文化信息,實現社會在時間向度上的延伸。不過這并不意味著考古遺存會讓歷史原樣凍結和不斷堆積,代際間的對話和對過往的重新詮釋都在持續形成新的地方意義和時代文化。就像多琳·馬西(Doreen Massey)所強調的:“地方因不同社會關系的會遇、交織而形成。”這是基于考古遺存作為關系性的存在,與人和環境不斷發生互動而不斷充實新的文化意義,“物性”的作用過程投射在復雜時空的動態演化之中。
無論如何,具有媒介屬性的考古遺存從遙遠的過去路過現在而走向無限的未來,透視了中國社會和文化的發展演變的規律,在構筑未來社會中人們的思維方式、行為活動、社會制度等方面提供不可替代的智慧。
三、物之想象與文化基因:考古遺存的媒介運作邏輯
通過物性本體和時空存續的媒介功能,考古遺存完成了對“過去—現在—未來”社會的塑造,這種力量的賦能源自考古遺存作為媒介的存在形式,使其具有和人同樣的主體性地位,彼此互動依存。媒介化理論指出,媒介作為意義的對象和載體嵌入人們日常實踐,并以“媒介邏輯”介入社會建構。在“人—媒介—社會”的關系中,考古遺存發揮媒介功能的路徑完成從“中介化”向“媒介化”的深入:相比于簡單勾連起人的主體認知和社會的客觀情狀,考古遺存實現由個體到群體的轉化并“浸透”進社會的運作過程。換言之,從媒介存在形式和功能出發,考古遺存體現的主體性既能夠按照自身的運作邏輯組織社會個體與群體的思維模式和“慣習”,又能重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特別是建制化的社會實踐,如政治、文化、宗教、教育等。由此,本文提出考古遺存媒介運作邏輯圖(圖1):考古遺存作為媒介主體和人的多元主體互動以共同建構社會“現實”,其中“物的想象”是考古遺存媒介運作的核心過程,“文化基因”是其媒介運作的重要結果。

圖1 考古遺存媒介運作邏輯圖
“物的想象”指向媒介主體性交互,從更本質的層面解釋媒介運作過程。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三界拓撲學最早關注于人的主體性,為思考媒介功能在人精神層面的作用原理提供借鑒價值。拉康建立了描述和解釋人類心靈組織的模型,即實在界(The Real)、象征界(The Symbolic)和想象界(The Imaginary)。他強調一種“非物質”力量,這種抽象的、理想化的、消極的力量促使個體與環境之間形成了一種內在的、自身的、沒有實體的結構性關系。師承拉康的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i?ek)以“幻象”(Fantasy)為中心重新論述了三界理論。幻象指一種不真實的、形象的但又帶有概念性質的圖式,是人這一主體在現實世界和符號世界存在的意義和方式,是意識形態發揮作用的重要運作機制:在想象界中,幻象基本上是實在界的直接顯現;在象征界,幻象是結構現實和撫平現實對抗的敘事和機制;在實在界,幻象則是存在于人的頭腦中先驗的、帶有欲望的結構性原因的意象,建構起人類的欲望、社會和“現實感”。而意識形態就是一種建構社會“現實”的主體無意識的幻象,處在想象界中,它在主體與大他者的欲望關系之間起著中介作用并實現建構的無限輪回。齊澤克在對電視、電影和賽博空間等媒介形式的分析中認為,大他者是形塑主體的“象征秩序”,而媒介扮演著大他者的角色。象征秩序“以媒介所中介的模糊的力比多力量為基礎來起作用”,并使“單個主體通過對周圍的象征秩序順服主體化而存在”。“媒介體系實現了意識形態效果,在我們的生活中充當文化壁紙,發揮的是去崇高化的作用。”
盡管拉康和齊澤克的思想都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色彩,看似與媒介的物質性取向“背道而馳”,但他們在聯系人如何通過媒介確認自我和社會的存在,進而解答媒介在聯結微觀主體和宏觀社會的實踐過程中所發揮的功能價值方面提供思辨進路。人們對社會的“現實感”體驗通過三界的指示方式相互糾纏而形成,“實在界需要被中介,這些中介過程被象征界和想象界多重建構,在這些建構的表層下實在界持續發酵”。“物的想象”包含了兩個具體過程:一是考古遺存由于來自過去的社會情境,對當下人們的認知來說無疑具有“先驗存在”的屬性,它作為具有媒介屬性的物是社會實在與主體認知之間的中介,通過搭載物質性載體的符號意義形成為大眾所普遍接受的文化象征體系來規訓多元主體的認知和認同;二是人們通過考古遺存所了解到的過去社會可能并非當時的實在與真實,而是通過自身的文化解讀不斷將新的意義附加于其上,再通過新一輪媒介的作用來豐富自己的認知和想象。這樣不斷循環的媒介化實踐,使透過考古遺存而得到的“幻象”或說“意識形態”深深刻進每一個主體的潛意識中,用以確認自身和社會的存在。
“文化基因”(Cultural Gene)類似于齊澤克“幻象”和“意識形態”的概念,在“物的想象”的作用過程中產生并作為主體心靈的中介將人的認知與社會“現實”相關聯。這一概念于20世紀50年代由阿爾弗雷德·克洛依伯(Alfres Kroeber)和克萊德·克拉克洪(Clyde Kluckhohn)提出,梁鶴年將其界定為一種“非生物基因”,是先天遺傳和后天習得的、主動或被動、自覺與不自覺而置入人體內的最小信息單元和最小信息鏈路,主要表現為信念、習慣、價值觀等。它是文化與文明延續的“最高原因”,所以“必須是自在自為的具有‘普遍性的普遍者’”。文化基因有其歷史淵源和傳統底蘊,同時也隨著復制、遺傳、變異、傳播的過程不斷自我調整以適應最新的人群和社會環境,是考古遺存媒介運作的動態性結果。按照段清波的觀點,社會治理觀、宇宙觀、核心文化價值觀共同構成了具有獨特性和差異性的文明,中國已形成以漢字為書寫和交流的語言、以中心四方和陰陽五行為宇宙觀、以禮和規矩為核心文化價值觀的完整體系,其文明蘊含于“中、對立、變通、禮、規矩”之中。相對穩定而又動態變化的文化基因形成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內核、塑造了中華民族內部多元、和諧的思想觀念與行為模式。它隨著媒介時空更替而不斷順應新的歷史、當下和未來,構成一個與時俱進、持續活躍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四、結語
在傳播學視域下,考古遺存是具有媒介屬性的物,并在與人—社會的互動中完成了媒介主體實踐,對這一問題的討論至少有三點啟示。
第一,媒介視角為考古遺存研究提供新進路。以往研究多從遺存本身出發、探尋古代社會情狀,而將考古遺存置于主體關系互動的實踐中,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進行自下而上的考察,挖掘技術和社會的復雜性及其中多元的社會心態,拓展了研究空間。另外,考古遺存涉及的媒介類型與內容豐富多樣,在對考古遺存的意義探賾中,基于物的想象能夠在當下的實踐中將其轉化為內在思維與行為指導的源動力,并為未來的構筑提供新的資源、新的視野和新的可能。
第二,媒介融合的探索能夠“讓遺存活起來”。保羅·萊文森(Paul Levinson)曾把技術演化及作用比喻成“玩具—鏡子—藝術”三個階段:初生的新技術像玩具,對于現實生活影響微弱;逐步發展才能為實用的技術,像鏡子一樣復制現實;到了藝術階段,技術的功能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超越現實,因為它能重組和創造現實。從基礎設施、文化結構到社會延伸,考古遺存在某種程度上是失去實用性的舊媒介,其內在文化性的、藝術性的、創造“現實”的價值需要被新媒介激發來重煥文化傳播的活力。當下數字博物館、數字藏品、虛擬化身等實踐都是對考古遺存媒介融合的嘗試,新舊媒介技術配合的“再媒介化”進程才能使考古遺存超越靜態而真正活化。
第三,考古遺存作為傳播學研究的“盲點”需給予更多關注。章戈浩認為從“萬物皆媒”到“媒生萬物”,實體的物可以成為具有抽象意義的媒介,媒介與實體的物相關聯。對于媒介的分析可從有形的物質形態出發、考察無形的“物性”作用,涉及到多元主體互動的過程與關系。在這種“萬媒皆物”的視角下,考古遺存是根植于本土文化和傳統實踐的內生性媒介,目前尚是一片亟待探索的藍海領域。
注釋:
① 習近平:《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21年第7月2日,第2版。
② 張之恒主編:《中國考古學通論》,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2頁。
③ 王玨:《薪火相傳 詮釋文明》,《人民日報》,2021年10月18日,第16版。
④ 習近平:《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 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求是》,2020年第23期,第4-9頁。
⑤ 丁方舟:《論傳播的物質性:一種媒介理論演化的視角》,《新聞界》,2019年第1期,第71-78頁。
⑥ 施暢:《視舊如新:媒介考古學的興起及其問題意識》,《新聞與傳播研究》,2019年第7期,第33-53、126-127頁。
⑧ [英]雷蒙·威廉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詞匯》,劉建基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版,第299-300頁。
⑩ 邵培仁:《傳播學概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