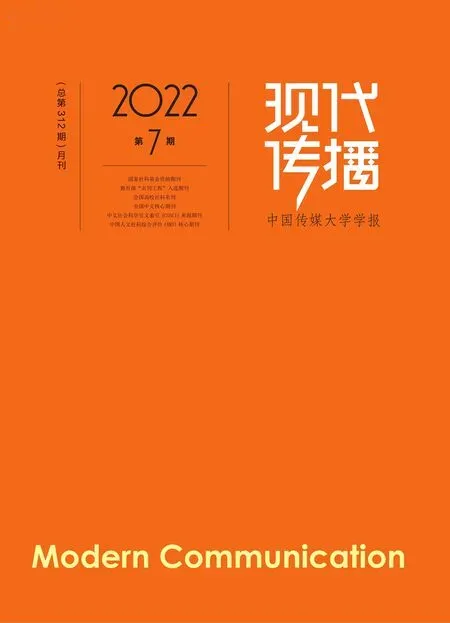啟蒙現代性、共同體意識與視覺景觀想象*
——文化空間視閾下的長城影像敘事與文化傳播
鞏 杰 李 磊
一、問題的提出:影像敘事如何建構和傳播長城精神形象和文化身份
長城關乎民族象征、紀念碑性、傳統符號、人類精神傳承和歷史文化記憶,甚至具有全球性和宇宙化的面向與內涵。關于長城全面具體的研究就顯得極其重要又勢在必行。本文的研究提出以下幾個重要的方向與問題。
一是借助影像媒介和文本,重構原來的地理、歷史和文化空間,如何對長城本體性進行全方位的認知?對長城本體的認知是首要的出發點,也是極其重要的認知觀念。從本體而言,長城空間是方位、地理、歷史、文化和生態的結晶體。從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域外視野來看,“著名的長城終止于中國西部邊疆的北端”①。長城作為邊疆防御的空間建筑和符號象征,建構了中華民族邊疆的地理空間界限和視覺空間標識。因而,我們在談及長城時,就要從地理空間定位出發,充分認識長城作為邊疆地理防御設施的重要屬性和作用,尤其要把長城還原到北方和西部邊疆的歷史地理文化空間中進行考察和審視。
二是長城作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其紀念碑性和歷史文化記憶如何被不斷地塑造和傳承?影像媒介對長城的立體呈現,更加全面逼真地表現中華民族精神和紀念碑性,從而引起現代人對歷史文化的記憶,喚醒民族精神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歷史文化基因。
三是在共建“一帶一路”背景和視閾下,長城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和人類文明的標志性建筑,能夠為人類的生存發展、世界經濟文化交流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因而建設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和作用。這就要更好地建設長城國家文化公園,以此來保存和喚醒民族歷史記憶和重構全人類的文化記憶。同時,長城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地位、作用和價值進一步明確,應該受到全世界更好、更完備的保護。
四是從文化空間視閾來讀解和闡釋長城的影像敘事,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認知意義、審美價值和學術價值。關于長城的傳媒藝術和文化研究,有從先鋒藝術角度和視覺文化角度進行的研究,但是目前缺少從文化空間視閾對長城影像敘事作品的相關研究。我們要重新認識長城的空間意義和功能,對“一帶一路”倡議語境下影視媒介中的長城空間生產和影像敘事進行詳細讀解和闡釋。這也意味著在新的文化語境和新技術條件下,對作為傳媒藝術的影像作品,如何更好地重塑長城的文化符號、影像空間和精神形象,以及對如何更好地傳播與傳承長城的歷史文化遺產,提出了一種可供借鑒的經驗和參照。“長城結果是一種令人著魔的幻象,它現在已經習慣性地深深地嵌入了中國和西方學術和老百姓的想象之中。”②長城影像敘事的時代轉向,也可以看作是長城話語史和長城觀念史,因而為學術研究和人們的文化想象提供了新的可能。
本文重點要研究的是從何時開始,影像敘事中的長城具有了現代啟蒙的精神力量;也要重點探討長城影像敘事作為中華民族精神共同體、文化審美共同體和人類共同體意識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象征和內涵;同時討論長城影像敘事作為一種視覺景觀想象,又如何被納入全球化的消費語境進行體驗和審思。
二、孟姜女傳奇故事影像敘事中“磚石長城”與啟蒙現代性建構
長城作為一種建筑空間是中國西部和北方邊塞的標志,它不僅是一種地理分界,也含括了時間的綿延與空間的交疊。傳統文學藝術中的長城空間積累了邊疆交鋒的歷史意象,是古代詩人在杏花煙雨的江南,對秦漢邊塞的想象構建。影像敘事作品延續了文學藝術,尤其是孟姜女傳奇故事的主題內涵和敘事范式,是“征夫怨邊”與“閨婦思君”兩種敘事視角的有機結合,形成了“容顏離別盡,流恨滿長城”的空間敘事意象和意蘊表達。同樣是傳媒藝術,電影藝術和電視藝術因其媒介生產的時間和本體差異,在影像敘事中也存在著不同點。通過不同的敘事時空呈現出“磚石長城”的空間建構,以及對啟蒙現代性的強烈訴求和真切詢喚。
(一)電影影像敘事中孟姜女傳奇故事及“磚石長城”空間的啟蒙現代性
孟姜女傳奇故事在民間流傳已久。根據顧頡剛先生的研究,孟姜女傳奇故事的敘事走向因隋唐時期長城作為邊疆屏障才開始與“閨婦”和大眾情感進行了關聯和縫合。③著名的理論批評家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說:“傳奇模式提供出一個理想化的世界:在傳奇作品中,男主角英勇,女主角美貌,反面人物是十足的惡棍。”④在孟姜女傳奇故事的理想化世界里,年輕美貌的女主角孟姜女和英俊書生范杞良(范喜良)相愛,范杞良卻被秦始皇征為勞役去修筑工程浩大的萬里長城以防御匈奴。而作為反面角色的秦始皇則是十足的暴君,孟姜女在長城尋夫并堅決反抗,投河自盡,以死抗爭,爭取人生和愛情的自由。長城成了統治者實施“暴政”和維護專制統治的工具,也是人們爭取自由與幸福的阻礙力量,具有了階級剝削和意識形態壓迫的刻板印象。“磚石長城”空間及其意象以反例和反證的方式,體現著現代啟蒙精神和啟蒙現代性訴求。
從媒介考古的角度看,電影是最早書寫孟姜女傳奇故事和呈現長城空間的影像媒介。遵循歷史脈絡就其要者而言,首先拍攝孟姜女傳奇故事的影片當屬邵醉翁導演、胡蝶主演的《孟姜女》(1926)。在袁牧之導演的電影《馬路天使》(1937)中,有金嗓子周璇對長城婉轉纏綿的低吟淺唱:“冬季到來雪茫茫,寒衣做好送情郎。血肉筑成長城長,儂愿做當年小孟姜。”電影插曲《四季歌》伴隨著長城影像的鏡頭閃現,讓故事和長城得到了更好的視聽傳播。由吳村編劇導演、周璇主演的《孟姜女》(1939)則關注到了長城的空間呈現和現實問題。當時有人撰文道:“孟姜女尋夫將上銀幕”,這是抗戰非常時期“國產電影的畸形發展”⑤。“它的中心意識顯然在努力表現‘除奸報國’。”⑥這種改寫與抗戰時期的社會現實和話語語境是密不可分的,對驚醒漢奸、振奮民族精神和國民人格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孟姜女爭取自由和幸福的啟蒙現代性,也體現在周詩祿導演的香港粵語片《萬里長城》(1949),周詩祿編劇、導演的《孟姜女》(1955),屠光啟導演、李麗華主演的《萬里長城》(1957),臺灣地區梁哲夫導演的《孟姜女》(1959),韓國權英純導演的《秦始皇和萬里長城》(1962),香港地區林柯導演的《孟姜女哭倒長城》(1963),臺灣地區姚鳳磐導演的《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1970)等影片中。沙丹導演的黃梅戲戲曲片《孟姜女》(1986)中白雪覆蓋的長城成為人性壓迫的象征,孟姜女哭倒長城象征對愛情和自由的追求,正如片尾的唱詞:“萬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電影藝術通過更加節約化的時間和更為影像化的敘事張力,凸顯“孟姜女哭長城”的敘事邏輯和影像魅力。孟姜女作為一個具有反抗意識的“中國新女性的原型”⑦,呼應著中國近現代以來的婦女解放運動思潮和實踐。長城作為一種被“摧毀”和被“解構”的反證,具有警示、啟迪以及反向的詢喚功能,激發國人對壓迫的抗爭、對人性解放和自由精神的追求,建構和彰顯著“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國家現代性的精神需求、民眾共情和啟蒙現代性的迫切要求。
(二)電視藝術影像敘事中孟姜女與“磚石長城”空間的啟蒙現代性
作為電視藝術的電視劇相比電影而言,有了更大的篇幅和體例,依照連續劇的敘事邏輯和敘事方式,更適合去講述完整的傳奇故事。20世紀90年代以來,電視劇成了呈現孟姜女傳奇故事最好的傳媒藝術和敘事文本。在《長城故事》(1990)、《孟姜女》(1996)、《秦始皇》(2001)等電視劇中,孟姜女傳奇故事和長城空間的呈現得到了較為全面宏大的敘事表達。神話/愛情網劇《九尾狐與仙鶴》(又名《孟姜女》)(2005)等呈現出擬像化的長城景觀和反抗精神,以及對愛情和自由精神的追求。電視劇《秦時明月之萬里長城》(2012)、動畫電視劇《孟姜女》(2012)、越劇電視劇《孟姜女》(2013)等,使得這一題材的傳奇性和虛構性大為增強,更加迎合現代觀眾的審美和消費需求。孟姜女故事和長城空間影像敘事由“征怨”向“閨怨”的轉換,也透露出人們審視長城的角度由政治向道德方向的變化:“從政治角度來看,長城不僅意味著阻隔,亦意味著和平;從道德角度出發,長城則代表著專制、殘暴,最終還代表著政治失敗。”⑧這樣恰切地印證了“孟姜女哭長城”這一原型故事在敘事上的“道德批判意識”和表意上的“啟蒙現代性”的密切結合。
總之,通過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的孟姜女傳奇故事及其影視敘事文本,我們發現長城除了具有軍事防御作用以外,更具有了道德批判與負面價值的話語言說。長城話語被建構為階級壓迫和人性束縛的象征,以及“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阻礙力量。因而,長城是一種磚石構筑的實體,也是一種象征和符號,更加凸顯出人的身體、權力、生存與自由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從空間視閾審視長城影像敘事與文化傳播,雖然存在歷史還原、民間傳說與神話想象等敘事時空的斷裂,但是這些影視作品試圖彌合和修復消失已久的民間記憶和道德譴責與批判。長城空間充滿強烈的反戰思想和人道主義精神,也體現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現代人通過這一傳奇故事,對人性與愛情、覺醒與啟蒙、反抗與自由等共同價值的強烈追求。這充分彰顯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啟蒙現代性訴求,凝聚為寶貴的民族精神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三、“新的長城”話語下長城空間影像敘事的民族精神共同體建構
“孫逸仙率真地開始將長城變成一種民族的進步象征。”⑨在國內首先將長城與民族精神象征關聯在一起的是孫中山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救亡”壓倒“啟蒙”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長城成了被卒然摧毀的軍事防御系統與被重建的民族精神的象征。“更具體地說,把長城定位為一個民族身份的不可動搖的象征,是在日本軍隊1931年侵略中國東北后才被廣泛傳播開的。”⑩長城形象和象征的這種轉變,也見證了以“廢墟”空間存在的長城,具有了著名學者巫鴻所說的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以及如何化腐朽為神奇地變成“英雄式的豐碑”,又如何成為建構民族精神共同體的永恒象征。
(一)“血肉長城”與民族精神共同體建構
長城從人道主義和啟蒙現代性中掙脫出來,成為主張積極抗戰救亡運動和重振民族精神的標志。“長城的形象被重新構造,成為抵抗外族侵略的英雄式的紀念碑,并迅速在抗戰期間的各種大眾媒介和藝術作品中出現,幾乎成為抗戰的象征性標志。”長城紀念碑和英雄豐碑形象的確立在美術(版畫/木刻)、戲劇、攝影、電影等大眾媒介和視覺媒介中迅速涌現,這也揭示出傳媒藝術在建構長城可視的英雄形象、重構人們的歷史記憶、喚醒民眾愛國主義精神方面的強大力量。“這是任何純粹抽象的觀念和意識形態所不能達到的。”
1933年4月梁中銘發表的《只有血和肉做成的萬里長城才能使敵人不能摧毀!》一文,首先提出了“血肉長城”這一觀念。在同一期《時事月報》上,一篇名為《到熱河去》的札記也提到了類似的觀點:“長城本為我國工程浩大之防邊工事,數千年來仍未變其性質與地位。……陸軍軍器之進步,已遠非笨拙之長城所能濟用,今已進至人的長城時代,動的長城時代,非死的磚石的長城時代了。”“人的長城”“動的長城”“非死的磚石的長城”就建構起中華民族精神煥發的“新的長城”不屈不撓的偉岸形象。
有學者指出:“山河破碎的大變局下,存續了兩千多年的長城,應救亡圖存的時勢之需脫胎換骨,成為集體意識空前統一的現代中國的象征。這一象征的固化與傳播同早期國產電影密切相關。”作為一種現代影像媒介藝術,1935年攝制的電影《風云兒女》是現代視聽媒介明確塑造和呈現“新的長城”形象和觀念的發軔之作。其歌曲《義勇軍進行曲》中所歌唱的“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是對這一形象和觀念的視聽形式的有力表達。這首由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的著名歌曲流行開來,1949年后成了新中國的代國歌,后來被正式確定為國歌。電影中呈現的長城拍攝點位于北京八達嶺長城,電影不僅用影像片段指代了萬里長城的莊嚴全貌,還將長城轉喻為中華民族精神共同體的符號象征。其后,1937年“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前,華藝影片公司籌拍的救亡電影《關山萬里》雖然未能拍攝,但由編劇潘孑農作詞、劉雪庵作曲的主題歌《長城謠》卻傳唱開來:“萬里長城萬里長,長城外面是故鄉,四萬萬同胞心一樣,新的長城萬里長!”這就進一步強化了“新的長城”的內外形象與故鄉和中華民族精神共同體建構的內在關聯性。同樣,1938年候曜未能拍攝完成的電影《血肉長城》更加凸顯了這一主題內涵。電影中并沒有出現“磚石長城”,長城成了抵御外辱的象征,人們用身體筑就了一道永不坍塌的“血肉長城”,成為中華民族屹立不倒的民族精神共同體的確切象征。
與之形成同構的是來自國外視野的長城影像敘事與表達。著名紀錄片大師伊文思在紀錄片《四萬萬人民》(1938)中有意識地導演了人們在街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的壯觀場景。這是對長城中華民族精神象征的一次域外視野下的重現和重構。在美國導演雷伊·斯科特(Rey Scott)的紀錄電影《苦干——中國不可戰勝的秘密》(1941)中,林語堂在其導言中說:幾個世紀以前,中國人民在長達萬里的邊境線上修建了雄偉的長城,以此抵抗外敵的入侵。今天,侵略者的鐵蹄雖然跨過了長城,但他們仍然需要面臨一堵新的長城——那就是“中國人民面對外敵時堅強不屈的英雄精神”。同樣,在具有國際視野的美國紀錄片《我們為何而戰:中國戰役》(1944)中,長城也成為抗戰時期不屈不撓的、具有血肉之軀的民族精神共同體的真實象征。
因而,可以明顯地看出,抗戰時期國際視野對“血肉長城”的影像呈現與重構,與國內視角形成了一種共情與同構。電影作品中的長城空間敘事,通過“人的長城”和“血肉長城”的呼喊,旨在喚醒民族的“集體記憶”和建構民族精神共同體。
(二)“鋼鐵長城”與民族精神共同體建構
關于“鋼鐵長城”最早的提法,根據學者吳雪杉的考證,“鐵的長城”這一概念在1933年就出現了。在1937年,“鐵的長城”開始被廣泛傳播。胡繩在其1937年10月出版的《后方民眾的總動員》中寫道:“全國人民在同一的意志下團結起來,組織起來,結成一座鐵的長城,這才是我們的抗敵戰爭的政治基礎。”1938年廖冰兄發表在《抗戰漫畫》上的《筑起我們鋼鐵的長城!》,以視覺藝術的形式見證抗戰,塑造民族精神共同體。這是視覺文化形式對“鋼鐵長城”形象的歷史描摹,而“鋼鐵長城”的影像敘事則出現在新中國成立以后。
抗戰勝利后及新中國建設時期,隨著國家經濟、軍事、科技、文化的發展和民族精神的重構,以“血肉長城”為標識的民族精神開始讓位于實現“四個現代化”為指導的民族精神。隨著軍事力量的崛起和軍工科技的發展,以“鋼鐵長城”為標志的新的民族力量開始被喚醒。電影中的“鋼鐵長城”被賦予了象征和隱喻含義。電影《長城新曲》(1975)賦予了長城新的內涵和意義。“片名《長城新曲》,既寓意人民解放軍‘鋼鐵長城’,又寓意故事發生地:燕山之麓,長城腳下。”在著名導演李俊執導的電影《南海長城》(1976)中,人們反擊和圍剿“海鯊特遣隊”的流寇和特務,在南海上筑起祖國“鋼鐵長城”不可侵犯的威嚴。電影《祖國啊,母親》(1977)中最后的長城影像呈現,凸顯了幅員遼闊的祖國的壯麗河山,以及實現祖國統一和多民族團結的重要意義和價值。電影《吉鴻昌》(1979)片頭的長城影像呈現,是“鋼鐵長城”般民族精神的真切象征。紀錄電影直接以《鋼鐵長城》(1981)為片名,使得這一寓意更加明確和凸顯。此后攝制的《一盤沒有下完的棋》(1982)、《干杯,女兵們》(1985)、《長城大決戰》(1987)、《戰爭子午線》(1990)、《黃河絕戀》(1999)等影片中,巍然屹立的長城彰顯了民族形象的新崛起和“鋼鐵長城”一樣無堅不摧的“民族精神共同體”意識。長城具有了“紀念碑性”和“英雄式豐碑”的特征,是民族希望和未來的象征。
“在很多不同的文化中,象征符號、神話傳說、價值觀念鐫刻在一種自然面貌之上,并服務于現代政府和國家的發展。”因而,作為“自然面貌”和風景空間的長城是中華民族的象征符號和精神圖騰,是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和現代價值集體認同的“文化試金石”。“風景也成為建構‘想象共同體’文化政治的重要媒介。”于是,進入影像媒介視閾下的長城風景和空間也成為一種重要的“風景政治”。因而不難看出,長城開始由本體性的“磚石長城”向指代性的“血肉長城”和“鋼鐵長城”的質性轉變,形成了三位一體的“新的長城”空間敘事形象。影視作品通過舊的“磚石長城”的摧毀和“新的長城”(“人的長城”“血肉長城”和“鋼鐵長城”)的誕生,來激勵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影像敘事通過實拍與意指的結合,以比擬、象征和隱喻為修辭手法,塑造長城空間新的家國情懷、民族精神和民族偉力,充分彰顯了長城的符號化特征及其“英雄式的豐碑”和“紀念碑性”。
四、全球本土化視閾下長城影像敘事的文化審美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
“無論是文明意義上的長城,還是民族意義上的長城,都不能單從中國內部生發出來,而需要一個全球性的視野。只有在全球性的目光下,長城的‘古老’與‘偉大’才能凸顯出來,長城才能夠首先被歐洲,然后才是中國來自東方文明的代表,才能進而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征,與其他世界民族交相輝映。”
進入新時期,紀錄片中的長城書寫重在再現長城的地理、歷史和文化記憶,是對長城全方位、立體性的影像空間呈現,注重長城作為一種地理空間的本體性價值和意義。長城空間紀錄片試圖在彌合風景、記憶與歷史,通過地標符號、國家記憶、身份認同,進一步建構民族文化象征和文化審美共同體、世界眼里的中國文化地標和人類共同體意識。
(一)國內文化視野下長城紀實影像的文化審美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
進入新時期以后,隨著思想解放和文化尋根思潮的興起,中華民族迫切需要在文化精神和文化審美上尋找一個標志性、紀念碑性的民族標志建筑來確立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長城無疑成為這種精神價值的承擔者。除了文字描寫和敘事,長城很快就被納入到影像敘事視野之下。1979年由沈杰等拍攝、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出品的《長城》是我國拍攝的第一部長城紀錄片。影片以航拍的方式呈現出長城的地理風貌和雄姿,試圖探索建構一種文化審美共同體。1981年由殷培龍執導的科教片《萬里長城》以科普的形式介紹了長城的歷史、位置、風貌及傳說,重點展現山海關、八達嶺、嘉峪關長城的結構特點。長城影像引起強烈反響的是1991年劉效禮導演的《望長城》,被譽為“中國紀錄片發展的里程碑”。在拍攝手法上,打破了傳統的電影紀錄片手法,強調實景拍攝、現場收音,又通過探訪者的行動和語言,引導觀眾觀看畫面,具有身臨其境之感。紀錄片以長城為能指符號,喚醒民族的文化歷史記憶,彰顯民族文化的歷史感和自豪感。
進入新世紀以及新時代以來,國內拍攝了多部關于長城的大型紀錄片,開啟了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視閾下長城的新定位和新發現。總長為194集鴻篇巨制的紀錄片《遠方的家:長城內外》(2015)圍繞著長城遺址所發生的故事展開,通過王昌齡的詩句“撩亂邊愁聽不盡,高高秋月照長城”,體現出這部作品的詩意品格和文化審美特質,進而對萬里長城進行了全面探訪和文化審美共同體形象呈現。在《長城:中國的故事》(2015)中,作為農耕與游牧文明的分界線,紀錄片全面記錄了長城的地理、工事、歷史、文化。盡管西方學者說:“長城隔開了神話時代和現實時代。”但是,紀錄片將長城融入到全球本土化視閾中,重新定位長城的地理多樣、歷史久遠和文明交流,告訴世界一個全面、真實的中國萬里長城。正如解說詞所說的:“長城拒絕征服,但從未拒絕交流。”把游牧和農耕文明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拋卻以中原文化和漢文化為中心的傳統理念,從民族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上來重新審視不同文明的碰撞與交融。
從文化空間和文化地理學角度來審視,紀錄片中的長城“已然雜糅了現實性、物質性的‘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s)和想象性、概念化的‘空間再現’(representation of space),而成為一種‘再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并成為“性別、種族、階級等各種權力關系的角力場”。長城已經失去其軍事防御和作為國族邊界的功能,成為遺留下來彌合了人們“集體記憶”的建筑空間、文化遺產、視覺形式和歷史象征。于是,從歷史地理、文化基因和人類文明的角度來全面認識長城空間、歷史記憶和身份認同等問題,紀錄片中的長城敘事自然而然地升格成文化審美共同體和人類文明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空間密碼。
(二)西方文化視野下長城紀實影像中的文化審美共同體和人類共同體意識
盡管西方人早期拍攝了大量的長城攝影和紀錄影像,但長城并未完全納入全球化的文化審視和視覺符號呈現體系。早期域外紀錄片體現出長城的國際化視野和神秘性的探尋,夾雜著西方人的“東方主義”偏見和對古老神秘中國的奇觀化想象。自1987年長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西方人開始重新審視長城及其空間本體。新世紀以來,長城再次進入西方創作者的視野。美國國家地理頻道拍攝的《中國長城》(2008)以域外視野使用了情景再現、電腦CGI特效和航拍等拍攝手法對長城進行了探索和揭秘。此后英國BBC則更熱衷于拍攝中國的長城,產生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紀錄片。BBC紀錄片《美麗中國》(2008)之《風雪塞外》呈現了美麗而氣勢磅礴的長城空間和長城內外人們的生存歷史。《中國長城:塵封的歷史》(2014)再次以英國長城學者威廉·林賽探索長城為線索,根據長城考古的新發現揭秘長城的建造懸念和生存故事。《揭秘長城之魂》(2016)以探訪者的視角和行走,結合科學研究和CGI動畫,揭秘長城的內部構造和軍事秘密。《又見長城》(TheForgottenWall)(2017)以外國人的視野,講述被人們遺忘的箭扣野長城和城墻腳下趙氏一家的故事。《慢速飛翔旅程:中國萬里長城》(ASlowOdyssey:TheGreatWallofChina)(2019)這部史詩般的冒險探索紀錄片,從東海的老龍頭開始到達氣勢恢宏的嘉峪關,見證了長城磚石、墻壁和瞭望塔等標志性的長城空間。
總之,國內外紀錄片中的長城空間呈現,雖然有著不同的文化視野,但卻形成了一種共同的全球本土化視閾,在表達效果上達到了一種共情。國內紀錄片通過全球性反觀和審視本土性,使長城空間的影像敘事從孟姜女民間傳說的啟蒙現代性、抗戰時期激發的民族精神共同體的現實需要中釋放出來,從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的對峙與割裂中超脫出來,成為建構文化審美共同體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象征。西方文化視野下的紀錄片拍攝,試圖在全球性中關照和介入本土性,在某種程度上拋卻刻板的“東方主義”好奇和想象,通過長城來探尋中華文明的神秘性和蘊含的人類文明基因。長城成為人類文化遺產和人類共同體的標志性建筑和核心意象,具有了全人類性的時代特征和未來訴求等復雜多元的文化面向。
五、全球化和消費化語境下長城影像空間敘事的視覺景觀想象
隨著民族文化的重新建構和世界文化的凸顯,長城進入了全球化的文化審美和消費視野,也變成了“東方主義”“反紀念碑性”(anti-monument)、消費化與奇觀化的空間景觀雜糅,甚至具有了超越全球化的宇宙化超人類景觀面向和視覺景觀想象。
(一)動作/恐怖/驚悚片中的長城影像空間敘事的視覺景觀想象
在當代藝術和媒介融合時代,視覺藝術使長城空間敘事變得進一步景觀化和消費化。在以動作、恐怖、驚悚和愛情為主要類型的長城題材電影中,長城的空間內涵在消費化語境下出現了明顯的消解,甚至呈現出從“鴉魔”到“怪獸”的魅惑性的魔怪面孔。
還原歷史的時空語境,中國香港導演王星磊執導的懸疑/恐怖/驚悚片《鴉魔》(1975),是最早呈現出長城的魔怪面孔的影像。古代民間傳說中成千上萬的烏鴉隨機攻擊和殺害居民,村外的長城成了鴉魔的棲息地和庇護所。同樣,在張藝謀導演的電影《長城》(2016)中,電影齊聚了打怪獸、盜火藥、炫愛情等元素的全球性符號。火藥凝聚著中華民族的“智慧和神秘的力量”,西方人對火藥的覬覦與盜取絕不是普羅米修斯的“盜火”之舉,而是深深打上了西方“列強”盜竊原罪的烙印。在長城上展示的東方女性的“身體”與“功夫”,以及與西方白人的愛情體驗和幻想,讓長城在“裝置”“火藥”“怪獸”“身體呈現”“情色展示”等方面,成為由來已久的“東方主義”的視覺景觀想象和刻板印象。電影中的長城不再是一種“紀念碑式”的精神象征,而是一個依靠景觀和特技制作出來的精巧的遍布機關的“裝置”。作為一座“反紀念碑性”的衰朽的軀殼,艱難地抵御著怪獸對人類的兇猛入侵。
同樣,在好萊塢大片《毒液:致命守護者》(2018)中,不明外星物質共生體入侵中國地標建筑——長城,在全球化的消費視野中,長城繼成為“打怪獸”的壁壘之后又成了主體遭受侵害的對象。因而,長城進一步被東方化、想象化、景觀化和消費化。
如果說張藝謀的《長城》是一種“自我異域化”的“東方主義”鏡像,那么好萊塢的《毒液:致命守護者》無疑是西方白人根深蒂固的“東方主義”偏見,對長城以及中國全域“反紀念碑性”的凝視和想象。
(二)愛情/家庭/倫理片中的長城影像空間敘事的視覺景觀想象
在愛情/家庭/倫理類型片中,長城成了類型慣例的景觀象征和情感想象。這些愛與不愛的柔情與承諾,讓長城成了一個情感迷離并具有魅惑性的附屬物。在王正方的電影《北京故事》(1986)中,被拆除的城墻和長城成了電影呈現和表意的主要空間場景,也成了從美國歸來的華人對古舊中國認同的標志性建筑。在馮小剛的電影《非誠勿擾2》(2010)中,大全景俯拍的長城城垛是秦奮斗口中“生米終于要煮成熟飯”的地方,慕田峪長城成了一種消費性十足的關于愛情的視覺景觀想象。電影《追愛》(2011)中的嘉峪關長城,如同電影的英文名字GreatWall,MyLove所表達的那樣,臺灣地區人到大陸看長城,長城與愛和遠去的故鄉關聯在一起,具有一種往事不堪回首的深情凝望和視覺想象。
因而,愛情/家庭/倫理片中的長城影像敘事不再是民族精神和“紀念碑性”的文化符號,而是被有意識地、無情地消解。此類電影是對個人愛情和故鄉情懷,以及“他者”意義上的“景觀”和“風景”的深情凝望和視覺景觀想象。
(三)影像裝置藝術與媒介藝術宣傳中的長城影像空間敘事的視覺景觀想象
影像裝置藝術(video installation art)作為一門以影像、空間、互動、裝置以及觀念的輸出為表現形式的藝術,從錄像藝術到移動影像,從數字藝術、裝置到表演藝術和諸多難以定義的獨特作品,均由技術提供豐富多樣的創作手段。新技術打破了傳統電視、電影的線性敘事模式,以超鏈接的媒體整合及立體拼貼手法,成為多媒體藝術的鏈接方式,通過觀者參與、互動以及對其經驗的開放,為觀者提供了非線性的審美體驗。
1988年被譽為“行為藝術之母”的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在中國創作了行為藝術作品《情人·長城》(TheLovers)。默里·格里格爾導演的紀錄電影《中國的長城:在邊緣的戀人》(1988)就是對這一聲勢浩大的行為藝術的全面記錄,第一次讓長城成為一種具有跨文化視覺消費的愛情景觀想象。2019年9月,影像上海藝術博覽會的“焦點”版塊展出《情人·長城》風格獨特的彩色照片、繪畫以及雙頻錄像,現場錄像首次在中國呈現。《情人·長城》將長城空間、裝置、影像(雙頻錄像)、行為藝術體驗等結合起來,具有很強烈的先鋒藝術特征。1988年10月,溫普林在長城上舉行了以“告別20世紀”為主題的大型行為藝術活動“包扎長城”,成為電視藝術片《大地震》攝制的主要組成部分。青年/行為藝術家在長城上徹夜搖滾、狂歡,還有各種行為藝術表演和表達,像極了美國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Woodstock Rock Festival)。長城被解構為一種行為藝術、影像裝置、視覺想象與身體體驗的先鋒性后現代景觀。
作為媒介藝術宣傳作品,在寧瀛導演的宣傳片《長城腳下的公社》(2002)中,“長城腳下的公社”這一旅游實體景觀酒店,只是對酒店場景的一次影像符號的空間再現,成為電影拍攝的場地和取景地,這就使得長城被解構成一種純粹的消費景觀,其“紀念碑性”的價值和意義被完全消解。同樣,2015年好萊塢大片《星球大戰:原力覺醒》在長城上舉行了主題為“長城之巔 原力覺醒”的商業宣傳和預告片首映活動。長城雖然不是影片拍攝和再現的空間,但“長城作為一個兼具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空間,承載和見證了好萊塢電影作為全球資本主義商品的本土化宣傳”。
這種關于長城的影像裝置藝術和媒介宣傳片,通過參與宣傳、空間重構等方式在不斷消解長城的紀念碑性和精神內涵,具有行為藝術和奇觀化的影像特點,使得長城具有了“第三空間”“東方主義”“反紀念碑性”和視覺景觀想象等異常復雜的文化面向。
總之,在全球化語境下,長城一方面被全球化體系所認知、重構和傳播;另一方面則被消費化、奇觀化的景觀呈現所消解和剝離,具有了“反紀念碑性”的視覺形象和空間面向。長城成了消費視閾下的“景觀的想象”和“想象的景觀”。這種雙向全球化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矛盾性張力,無不反映出長城敘事話語的延異、矛盾和駁雜。此類影像作品/行為藝術中呈現和傳播的長城視覺空間是對民族精神、歷史印記、共同心理、文化記憶和審美共同體的一種有意或無意的消解和解構。
六、結語
將長城納入到全球化的話語重建和文化形象體系中,長城成了中西文化對比、凝視與思考的一種具有差異性的象征物,進而凸顯出中西文化的差異,以及對中華文化在比對凝視與多元化想象中進行身份和屬性認同。這就需要從能指符號和虛幻影像的悄然蛻變中奮力警醒,以影像的再生產來抵抗過度的商業消費化和視覺景觀化、奇觀化的臆想和想象,重新建構長城影像的真實面向,以期獲取更多的民族精神共同體認同和價值認同,為長城國家文化公園建設提供更好的觀念和理論支持;也要努力探尋符號化、圖像化的長城在全球本土化語境下,建構人類共同文明和“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及文化藝術生態理念中新的人類文明傳播與文化傳承價值。
注釋:
① [意]利瑪竇、金尼閣:《利瑪竇中國札記》,何高濟、王遵仲、李申譯,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559頁。
②⑦⑨ [美]阿瑟·沃爾德隆:《長城:從歷史到神話》,石云龍、金鑫榮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286、281頁。
③ 顧頡剛:《孟姜女故事的轉變》,《歌謠周刊》,1924年第69期,第6頁。
④ [加]諾思洛普·弗萊:《原型批評:神話理論》,載葉舒憲編選:《神話——原型批評》,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185頁。
⑤ 未名:《孟姜女尋夫將上銀幕:國產電影的畸形發展》,《至尊》,1936年第6期,第3頁。
⑥ 《電影批評:〈孟姜女〉乙下片》,《電聲周刊》,1939年第10期,第490頁。
⑧ 侯艷:《唐代詩學中的長城意象》,《湖北社會科學》,2012年第9期,第11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