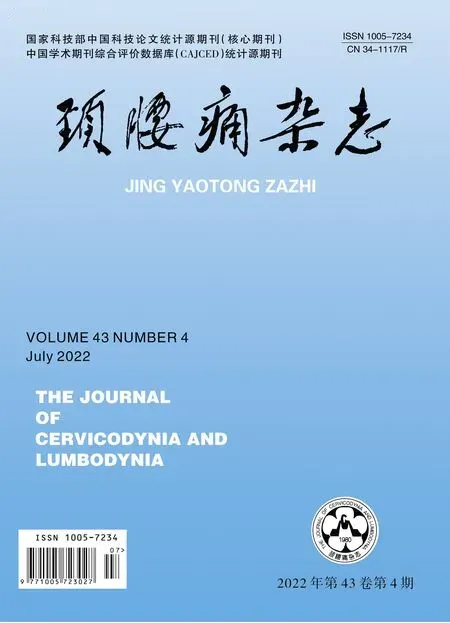腰椎管狹窄癥行后路椎間融合術前、術后鄰近節段退變影像學的研究
馬輝,孫建強,莫濤,孟長峰,高凱旋
(1.洛陽市中醫院骨科;2.洛陽市第三人民醫院骨科,河南洛陽 471000)
腰椎管狹窄癥(lumbar spinal stenosis,LSS)患者多見于中老年人群,隨著年齡的增加,患者術前常見有多個節段存在退變,而真正致病的責任節段多為其中一個。對此類患者制定手術方案,往往面臨嚴峻挑戰:若僅針對責任節段作減壓融合,術前已存在影像學退變的其它節段可能會在術后退變加速、面臨再次手術;若對其他節段提前行預防性減壓,則存在擴大手術指征的嫌疑,且引起節段性穩定性降低、增加了肌肉韌帶復合體的損傷程度,可能會增加術后鄰近節段退變(adjacent segment degeneration,ASD)的風險[1-2]。因此,客觀地評價術前鄰近節段退變對LSS患者行減壓融合手術療效的影響,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既往研究中關于術前鄰近節段退變的評估,大多是基于椎間盤和小關節退變程度來描述和評價[3-4],但在臨床上,鄰近節段退行性疾病(adjacent segment disease,ASDis)的翻修手術更常見于椎管狹窄加重、引起神經壓迫癥狀所致,因此逼著認為,對術后鄰近節段退變的影像學觀察不應忽視“椎管狹窄”這一特征。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的目的有二:(1)通過術前和術后鄰近節段的影像學分析,探討術后鄰近節段的影像學變化特征;(2)探討術前鄰近節段退變情況對LSS患者行減壓融合手術療效和術后鄰近節段退變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2017年3月~2019年3月行后路腰椎減壓固定融合術治療的LSS患者121例,納入標準:①患者有長期慢性下腰痛、間歇性跛行等癥狀,明確診斷為LSS;②病變節段為L4-S1之間,經正規保守治療無效,行后路減壓融合術治療;③術后隨訪時間≥2年;④術前和術后隨訪期間的影像學資料完整。排除標準:①鄰近節段術前存在不穩;②存在軀干冠狀位或矢狀位失衡;③有腰椎感染、腫瘤等疾病;④既往有腰椎融合手術史,或術后失訪、隨訪不足2年,以及影像學資料不全者。
依據患者術前鄰近節段的退變情況分為A、B兩組:A組68例,術前鄰近節段無退變。B組53例,術前鄰近節段存在退變。對兩組患者的性別、年齡、麻醉風險ASA分級、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等資料作比較,僅A組年齡

表1 兩組LSS患者的一般資料對比
1.2 術前和術后鄰近節段退變的判定
依據患者術前相鄰節段MRI表現,擬定以下標準:①椎間盤退變:術前MRI見鄰近節段椎間盤存在輕度突出,或有局限性高信號改變(high-intensity zone,HIZ),壓迫硬膜囊;②椎管狹窄:術前鄰近節段存在中央管或神經根管狹窄。椎管狹窄的分級標準,采用Lee等[5]的方案,分為0、1、2、3級。0級:椎管未見狹窄,馬尾神經前方有腦脊液充盈(圖1a-b);1級:輕度狹窄,且馬尾神經前方無腦脊液充盈,馬尾神經終絲聚集但可辯(圖1c-d);2級:中度狹窄,馬尾神經已積聚成束(圖1e-f);3級:重度狹窄,硬膜囊內幾乎完全閉塞(圖1g-h)。

圖1 Lee等[5]椎管狹窄分級的示意圖
術前無椎間盤突出或HIZ改變,中央椎管形態0級者,判定為無退變,納入A組;反之,存在椎間盤突出、壓迫硬膜囊,或存在HIZ改變,以及椎管狹窄1級以上者,均納入B組。
因本研究所納入病例均為L4-S1節段手術者,故本文統一選擇其上位鄰近節段作為觀察目標。
1.3 手術治療
所有患者全部在全身麻醉下,接受經典的后路腰椎減壓+椎體間植骨融合內固定手術,術中將椎板切除減壓,予以植骨融合、椎弓根釘內固定處理,注意避免上位相鄰節段的關節突和關節囊損傷。患者術后3~5 d可嘗試下床活動,術后3周可開展腰背肌功能鍛煉,3個月內仍應以腰圍保護。
1.4 觀察指標
統計所有患者的手術時間、出血量、住院天數、并發癥情況;術后均獲2年以上隨訪,分別于術前、末次隨訪時進行腰痛、下肢痛的VAS評分、日本骨科學會JOA評分和Oswestry功能障礙指數(Oswestry disability index,ODI)評價,此3項指標屬常用評價工具,為學者們熟知,不予贅述。
1.5 術后ASD的判定
術后獲訪24~31個月,平均隨訪期為27.3個月。末次隨訪時,采用腰椎正側位、屈伸位X線檢查和腰椎MRI檢查,并與患者術前鄰近節段的影像學資料進行比對,以評價鄰近節段ASD的發生情況。X線判定標準:①椎間隙高度丟失>10%;②鄰近節段椎體的滑移>3 mm,或椎體活動>10°;③終板硬化,存在鄰近節段側彎;④原有骨贅增加>3 mm,或有新骨贅形成。MRI判定標準:①鄰近節段椎間盤突出加重、Pfirrmann分級加重,或出現HIZ改變;②鄰近節段的椎管狹窄分級加重。上述所有判定標準中,與術前相比的任一項改變均可視為術后ASD。
此外,基于上述判定標準,將術后ASD的改變特征分為:①椎間盤因素:如Pfirrmann分級加重,或椎間盤突出、HIZ改變等。②椎管狹窄分級變化加重;③鄰近節段出現滑移或側彎等,但除外椎管狹窄。若術后ASD出現的同時,引起患者腰痛或下肢根性癥狀明顯加重,則判定為ASDis。
1.6 數據分析

2 結果
2.1 手術情況和早期并發癥
手術時間、術中失血量和住院時間方面,兩組間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A組術后早期并發癥發生率為11.8%,包括腦脊液漏2例,心衰1例,切口感染1例,一過性下肢無力2例,硬膜外血腫2例;B組發生率為11.3%,包括腦脊液漏3例,切口感染1例,心衰1例,一過性下肢無力1例。兩組并發癥發生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兩組LSS患者的手術情況和早期并發癥分析
2.2 術后ASD發生情況
A組出現術后ASD14例,發生率20.6%;B組33例,發生率62.3%。B組的發生率顯著高于A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從術后ASD發生的影像學變化特征來看,兩組均以椎管狹窄最為常見,分別占比9/14和24/33,見表3。與術前相比,A、B兩組末次隨訪時的Pfirrmann分級未見顯著變化(P>0.05);兩組間相比,術前和末次隨訪時的Pfirrmann分級均有顯著的組間差異性(P<0.05),其中B組的Pfirrmann分級程度更重,見表4。

表3 兩組LSS患者術后ASD發生的影像學變化分析

表4 兩組LSS患者的椎間盤退變Pfirrmann分級比較
2.3 術后療效
2.3.1 總體療效分析
與術前比較,兩組患者術后的VAS評分和ODI指數均顯著降低(P<0.05),JOA評分顯著升高(P<0.05)。A組末次隨訪的JOA評分顯著高于B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5。

表5 兩組LSS患者的療效指標比較
2.3.2 術后ASD患者的療效分析
與術前比較,A組、B組患者末次隨訪時的腰痛、下肢痛VAS評分和JOA評分、ODI指數均獲顯著改善(P<0.05)。各亞組之間的組內比較如下:(1)A組的ASD亞組和無ASD亞組之間,術前、末次隨訪時的各項指標均無統計學差異(P>0.05);(2)B組的ASD亞組在末次隨訪時的腰痛VAS評分和ODI指數均顯著高于無ASD亞組(P<0.05)。見表6。

表6 術后ASD和無ASD患者的療效指標比較
2.4 術后ASD的影響因素分析
將本研究所有的潛在因素,如麻醉ASA分級、患者年齡、性別、BMI、術前鄰近節段存在退變等因素均納入到多因素Logistic回歸模型中進行處理,見表7:術前鄰近節段存在退變(OR=6.571)和BMI(OR=1.623),均是術后出現ASD的獨立風險因素。

表7 LSS患者行后路減壓融合術后出現ASD的影響因素Logistic回歸分析
3 討論
目前,關于腰椎融合術后ASD的原因分析較多,包括患者個體因素(年齡、BMI等),手術因素(融合節段數量、融合方式等),以及脊柱-骨盆矢狀位失衡等[6]。部分研究已證實,術前鄰近節段退變是腰椎融合術后發生ASD的獨立風險因素[7]。但關于術前鄰近節段退變的觀察角度、術前退變對LSS患者術后療效的影響,及其對LSS患者術后ASD發生情況的影響,均少見有系統性文獻分析。本研究逐一探討如下:
3.1 術前鄰近節段退變對LSS患者術后療效的影響
表5-6中可見,A、B組患者末次隨訪時的上述指標均獲顯著改善(P<0.05),但A組JOA評分高于B組(P<0.05);結果說明,術前存在鄰近節段退變對患者行腰椎融合術后的神經功能恢復有一定影響。此外,B組患者中,ASD亞組在末次隨訪時的腰痛VAS評分和ODI指數均高于無ASD亞組(P<0.05);結果說明,術前存在退變的患者,隨著術后ASD的加重,對患者腰痛和腰椎功能障礙的改善效果已產生一些不利影響。筆者分析可能的原因:①當責任節段接受腰椎減壓融合手術后,術前鄰近節段退變相關的輕微癥狀、體征得以顯露,從而對術后恢復產生影響;②術前鄰近節段已產生退變,由于責任節段融合術后喪失了活動功能,導致鄰近節段的生物力學環境發生明顯變化,加速其退變進程,從而使患者術后的腰痛和功能障礙改善效果受到影響。
本研究隨訪時間較短(平均27.3月),雖然術后出現了47例ASD ,但無一例為出現嚴重癥狀的ASDis患者,因此尚不能確定術前鄰近節段退變對LSS患者術后遠期療效的影響。此外,表3中可見,B組術后ASD的發生率顯著高于A組(62.3%vs20.6%,P<0.05);表7中也證實,術前存在鄰近節段退變和BMI均為患者術后發生ASD的獨立風險因素(P<0.05)。結果說明,術前存在退變對患者術后ASD的發生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3.2 術后鄰近節段退變的影像學變化特征
臨床中,腰椎融合術后ASDis面臨翻修手術的主要原因,多為鄰近節段椎管狹窄程度加重、壓迫神經根導致嚴重癥狀[8-9]。因此,單純對鄰近節段椎間盤或小關節的退變程度進行探討,則忽略了其椎管狹窄的情況,也難以從整體上評價術后鄰近節段的退變情況。為此,本研究同時將椎間盤退變和椎管狹窄作為術后鄰近節段退變的主要觀察指標。其中,椎管狹窄的判定依據是參考Nakashima[10]、Yugué[11]和Lee[5]等的研究方案后,決定以Lee等[5]的方法作為標準,該分級標準較為簡便直觀,可信度較高。
表3-4可見,A、B兩組患者術后ASD的影像學改變均以椎管狹窄為主,分別占比9/14和24/33;而椎間盤退變Pfirrmann分級在末次隨訪時并未有明顯加速。這與Cheh等[9]的結論較為一致,他們對188例患者融合術后隨訪5年以上,42.6%(80/188)的患者發生了ASD,30.3%(57/188)的患者則出現ASDis,其中椎管狹窄者占比最高、達82.5%(47/57)。Okuda等[12]也得出類似結論。筆者分析其生物力學原因在于:腰椎融合手術后,鄰近節段的生物力學變化主要表現為應力增加和活動度的代償性增加。活動度的增加,主要源于椎間盤和后方韌帶、小關節退變。但是在術后早期,因椎間盤存在彈性形變的限制,因而其活動度的增加更多地來源于后方關節囊韌帶和黃韌帶的拉伸,以及小關節活動范圍的增加,易引起后方韌帶拉伸褶皺和小關節退變,從而加重椎管狹窄程度。但這一觀點僅為推測,目前尚缺乏三維有限元分析和臨床數據的證實。
總之,術前鄰近節段退變對LSS患者行腰椎減壓融合手術療效和術后ASD均有一定影響;此外,椎管狹窄是術后ASD發生的主要影像學變化,術前對鄰近節段退變的評估中應高度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