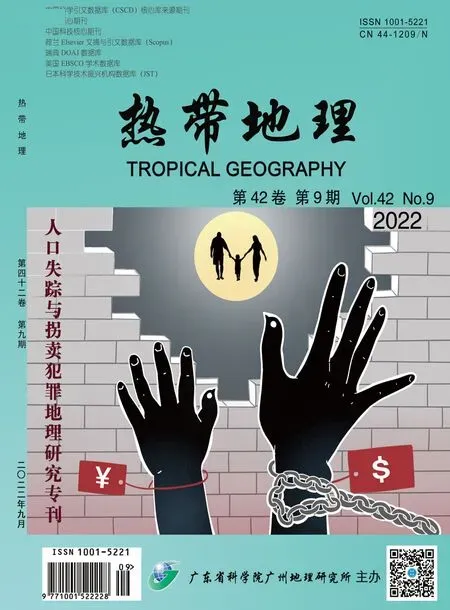新世紀以來中外兒童販運研究熱點與趨勢
——基于CiteSpace的文獻計量分析
周俊俊,李 鋼,洪丹丹,徐 鋒,徐嘉輝,于 悅,陳曦亮
(a. 西北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b. 陜西省地表系統與環境承載力重點實驗室,西安 710127)
人口販運被認為是迄今為止人類發展進程中規模最大、性質最惡劣、影響最深遠、持續時間最長的犯罪活動,已成為繼販賣毒品、走私軍火后位列世界第三的犯罪現象(Logan et al.,2009)。兒童和婦女是人口販運的主要受害者,每年約有120 000名婦女和兒童被販運到西歐(Laczko et al.,2003),這一問題引起了國際社會和網絡媒體的廣泛關注。據聯合國毒品犯罪辦公室報告,全球30%的販運受害者是兒童,被販運的女孩(23%) 多于男孩(7%)(UNHR,2000);2012 年國際勞工組織估計,約有570 萬男孩和女孩處于強迫勞動或奴役狀態(ILO,2012),這不僅是對國際立法制度與人權保障機制的挑戰,更是世界精神文明的衰退。《2018 年全球人口販運報告》指出,女童是全球人口販運的主要被害群體,這一現象與地區間的資源不均衡、性別不平等以及移民政策有關,使女童被用于充當牟利賺錢的工具(UNODC, 2018)。《巴勒莫議定書》將兒童販運定義為,出于性剝削、強迫勞動或服務、奴役、勞役或切除器官的目的,招募、運輸、轉移、窩藏或接收18歲以下兒童的行為(UN,2000)。美國聯邦法律將“嚴重”的兒童販運定義為“性販運”,通過武力欺詐、強迫或利誘使未滿18 歲的人員從事此類行為(Kaufka-Walts et al.,2011)。目前,兒童販運網絡從多樣化的國際組織到小型、靈活的網絡組織甚至是本地網絡屢見不鮮(Paolo,2015),作案團伙與任務分工通常包括業余/低級販運者、中級管理人員和投資者3個等級(Zavrsnik,2012)。由于區域地理環境的差異性與國際環境的復雜性,各國對兒童販運治理的側重點各不相同。其中,美國側重單邊主義的預防策略,通過加強邊界管轄和移民管理阻止兒童販運發生,并建立“安珀警報”系統,助力尋找被拐失蹤兒童(李文軍,2017;Okech et al.,2018);加拿大強調從源頭上降低販運被害人和潛在被害人的脆弱性以抑制兒童販運;歐盟則提出從懲治犯罪者、保護受害者和預防未來犯罪3 個方面打擊兒童販運(董純樸,2014)。
近期中國的“梅姨案”“孫海洋尋子”“劉學州尋親”“豐縣八孩”等事件引發社會熱議和學界關注,眾多事件背后隱藏的拐賣兒童犯罪這一丑惡現象浮出水面。由于國情環境的差異,中國將其稱為拐賣兒童犯罪,經歷了由“合法”到“不合法”的演變過程。在早期,子女通常被視為父母的生育性財產,買賣兒童在法律和道德上都被視為一種可接受的行為(王良順,2014)。199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將拐賣兒童犯罪定義為以出賣為目的,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14周歲以下兒童的行為(有刪減)①http://www.gqb.gov.cn/node2/node3/node5/node9/node109/userobject7ai1382.html。2008 年中國頒布了《中國反對拐賣婦女兒童行動計劃》,2013和2021年陸續2次頒布了《中國反對拐賣人口行動計劃》,這些為有效預防和打擊拐賣兒童犯罪提供了指導方向。2009 年,中國建立了DNA 反拐數據庫,為拐賣受害者科學尋親提供了有效途徑(Yu et al.,2018)。截至2021 年12 月,公安部“團圓行動”已抓獲拐賣犯罪嫌疑人890 名,找回失蹤被拐兒童10 932 名,成功幫助一批失散家庭實現團圓(公安部網站,2021)。當下中國以打擊和預防拐賣為主,側重消除買方市場(蘭立宏,2014)。由于拐賣犯罪通常具有空間距離遠、時間跨度長、總量估算難、追查線索少、找回難度大等特點(李鋼等,2017a),打拐行動只能在特定的時間和地域內起短暫作用,拐賣犯罪屢禁不止(李鋼等,2017b)。
雖然國際公約與各國法律嚴厲打擊兒童販運,然而這種現象依舊屢禁不止,持續影響著國際社會的發展進程。因此,有必要對現階段研究成果進行梳理與總結,比較中外兒童販運研究的差異性,明確兒童販運的研究方向、重點及不足,這對當下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因此,基于Web of Science 和CNKI 數據庫,在文獻梳理的基礎上,運用CiteSpace 軟件對2000 年以來中外兒童販運研究熱點與趨勢進行分析,以期為未來深化相關研究提供參考。
1 數據與方法
1.1 數據采集
國外文獻以“Web of ScienceTM核心合集”為數據源,主題詞為“child trafficking”和“child smuggling”,語種為“English”,文獻類型為“Article”,時間范圍為2000—2020 年,共篩選得到有效文獻215篇。國內以CNKI期刊文獻為數據源,檢索主題為“拐賣、販運、販賣+兒童”,時間跨度為2000—2020 年,檢索得到244 篇有效文獻(核心文獻46篇)(檢索時間為2021-05-08)。為了區別中外文獻研究的差異性,國外文獻梳理表述為兒童販運,國內則為拐賣兒童犯罪。
1.2 研究方法
采用CiteSpace 5.7,導入文獻數據,時間跨度設置為2000—2020 年,單個時間分區選擇1 a,選擇每個時間分區中出現頻次最高的前50個數據,分別調整前、中、后閥值運行軟件,進行發文時間、地區分布、學科分布、關鍵詞共現與高被引文獻等分析。
2 結果分析
2.1 發文時間
根據發文量,利用自然斷裂點分級法將國外研究劃分為2 個階段(圖1)。第1 階段為波動增長階段(2000—2010年),除了2007、2008和2010年以外(分別為9、7、8篇),其他年份發文量均少于5篇,呈相對緩慢的波動增長態勢,這表明兒童販運研究正處于“成長期”。由于信息和數據獲取難度大,兒童販運通常被囊括在人口販運研究中。該類研究主要將婦女兒童歸為1類的混合型(Baldwin et al.,2011)、小樣本定性研究(Raphael et al.,2010),旨在揭示販運受害者的生存困境,并呼吁國際社會關注婦女兒童的健康發展和權益保護。但婦女兒童的合并研究忽視了二者的差異,使得兒童受害者的脆弱性和特殊性被掩蓋。第2階段為快速增長階段(2011—2020年),發文量較上一階段顯著增加,呈持續增長態勢,其中2018 年發文量高達28 篇。兒童受害者被作為獨立個體進行討論,學者們將研究對象擴展到與之相關的其他社會成員上,嘗試從不同視角揭示兒童受害者被解救后的傷害風險、康復治療和發展福祉等深層次的社會問題(Fong et al.,2010;Abu-Ali et al.,2011;Islam,2019)。

圖1 2000—2020年國內外兒童販運研究的發文量Fig.1 The publication number of the child trafficking studies from abroad and China during 2000-2020
依據發文量,將國內研究分為2個階段(見圖1)。2000—2010 年是緩慢發展階段,總發文量80篇,但核心文獻僅有13 篇(占5.33%)。早期學術界大多探究拐賣兒童犯罪的定罪標準(付立慶,2007)、刑法裁定(王吉春,2016)與法律文件的解讀(陳國慶等,2010),注重拐賣犯罪先期預防的功能性作用。2010年以后拐賣兒童犯罪研究處于波動增長階段,發文量顯著增加,年均發文量約為16篇。學者們除了討論拐賣兒童犯罪的法律修訂以外(杜慶貴,2011),也關注兒童解救后的救助保障(李春雷 等,2013) 和收養問題(王葆蒔,2015),并提出通過多方參與和共同協作的方式遏制拐賣犯罪現象。此外,李鋼等(2018)從犯罪地理學視角發現,20 世紀90 年代前后是中國拐賣兒童犯罪的高發期,總量上被拐男童多于女童,拐賣熱點區隨時間推移,由華東向西南以及東南地區演變。
2.2 國家分布
國家分布上(圖2),美國發文量位居首位,高達88 篇,占總發文量的40.93%;其次是英國,占比13.02%;加拿大、南非和中國發文量均在5篇以上;西班牙、意大利、蘇格蘭、荷蘭和墨西哥發文量位居世界前10。可見,兒童販運研究陣地集中在歐美發達國家,這與這些國家早期發生的跨國人口販運問題有關。相比之下,中國的拐賣兒童犯罪研究起步較晚,整體進程相對緩慢,但近年來犯罪地理學的發展為拐賣兒童犯罪研究帶來新機遇。

圖2 2000—2020年國內外兒童販運研究發文量排名前10的國家Fig.2 The top 10 countries of the child trafficking studies from abroad and China during 2000-2020
2.3 學科分布
學科分布上(表1),國外研究集中在社會學領域(Social Work),發文量為37 篇;且與其他學科連接最密切,側重探究兒童販運的國際環境與社會關系。其次是心理學(Psychology),發文量為29篇,主要聚焦兒童受害者遭受的身體虐待、心理創傷與社會回歸等問題。再者,兒科領域(Pediatrics)和家庭研究領域(Family Studies)的發文量分別為27 和25 篇,主要關注醫療機構在兒童販運中的作用,以及兒童受害者的家庭環境與親子關系。犯罪學與刑罰學(Criminology&Penology)的發文量為20篇,主要探究與兒童販運有關的國際公約與法律政策、社會福利與生存環境。

表1 2000—2020年國內外兒童販運研究的學科分布Table 1 The discipline categories of child trafficking from abroad and China during 2000-2020
由表1 可看出,CNKI 文獻中法學領域的發文量最多,占比高達75.82%,大多討論中國拐賣犯罪“設刑重,動刑輕”的現實原因以及過度刑法化問題(趙軍,2016)。其次是犯罪學領域,發文量占比8.61%,聚焦犯罪成因、偵察對策與公安部打拐紀實。再者,社會學和政治學發文量分別占比5.33%和4.92%,主要剖析傳統文化、保障機制、法治宣傳與監護力度等制度性與結構性因素對拐賣兒童犯罪的影響(Chu,2011;趙捷,2012)。此外,以李鋼團隊為主的犯罪地理學研究“異軍突起”,揭示中國拐賣兒童犯罪不僅存在顯著的性別差異與年齡梯度,而且省域拐賣的時空格局、流動路徑與影響因素各不相同(劉玲等,2020)。
2.4 關鍵詞共現與高被引文獻
2.4.1 國外兒童販運的知識圖譜分析 國外兒童販運研究共有225 個關鍵詞節點、782 條連接,密度為0.031(圖3)。詞頻統計發現,兒童販運(child trafficking)和人口販運(human trafficking)的頻次最多,分別為40 和30,中心度分別為0.51 和0.38,網絡關系結構鏈接復雜。其次是商業性剝削(commercial sexual exploitation)、性販運(child sex trafficking)和虐待(abuse),這些關鍵詞的出現頻次均>15,組成了兒童販運的研究熱點。具體來看,兒童販運源于早期的人口販運(Allain,1990),經濟危機、饑餓貧困、戰爭沖突、移民政策或自然災害等因素所引發的人口流動是導致人口販運的主要原因(Sigmon, 2008)。兒童可能在本國、過境國和目的地國與社會進行大量的接觸,但由于兒童的危險辨別能力、自我保護意識和生活處事經驗有限,更容易暴露在危險的環境中而遭遇剝削、欺騙、操縱和販運(Rigby et al.,2015)。兒童受害者大多從貧窮地區或國家流向富裕或相對富裕的地區或國家,流出地的推力因素(如低教育水平、高失業率、性別歧視、貧困等)與流入地“美好生活”的拉力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刺激販運現象的發生(Omorodion,2009),最終形成所謂的“現代奴隸制”——兒童販運(Gozdziak et al.,2006)。商業性剝削和性販運是兒童販運的主要類型,學者們發現長期遭受忽視、虐待和無家可歸的兒童更容易成為性販運受害者,即使被解救后也更易受到心理侵害(Gibbs et al.,2018;Wood,2020)。兒科醫生在識別性販運受害者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他們不僅幫助兒童受害者治療身體創傷,還能引導受害者形成健康、正常的心理狀態(Havlicek et al.,2016;Albright et al.,2020)。

圖3 2000—2020年國外兒童販運研究的關鍵詞共現網絡Fig.3 The co-appearance network of keywords in child trafficking from abroad during 2000-2020
進一步對高被引文獻進行聚類分析得到7個聚類(表2),依據研究內容歸納為以下4個主題模塊。主題模塊1:兒童販運類型,主要包括#0聚類——被販運兒童(trafficked child)和#4聚類——內部販運(internal trafficking)。兒童販運是突出的全球性問題,歐洲和亞洲中部國家有16%販運受害者是兒童,非洲和中東地區則有68%受害者是未成年人(UNODC,2018)。美洲地區的兒童商業性剝削高達51%,中亞和歐洲達到了62%,他們可能來自農村、郊區或城市家庭,包括不同種族/民族、性別和身份的兒童(Cole et al., 2015)。國際勞工組織估計,2016 年全世界約有450 萬兒童是勞工販運受害者(ILO,2017),約47%~49%的勞工販運受害者集中在非洲、中東、南亞和東亞地區。如在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蘭卡,幫傭和乞討是較為常見的勞工販運類型(Hilson,2008;Rafferty,2013),哥倫比亞則以兒童雇傭軍為主(Hurtado et al.,2017)。這些惡劣的剝削形式與各國極端貧困以及童工立法的缺失有關(Ren,2004),其中,男孩比女孩更容易遭受販運傷害,其生存處境和健康狀況較為嚴峻。童婚販運主要集中在南亞地區,其次是西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近東和北非位居第三(Jensen et al.,2013)。受地區婚嫁文化與風俗習慣的影響(Sen,1990),南亞和非洲的女性童婚率普遍較高,分別為48%和42%(Gaffney-Rhys,2011)。人們認為童婚不僅可以改善原生家庭的經濟狀況,還可以解決嫁入地區的勞動危機(Gaffney-Rhys,2011)。因此,在落后貧困和資源匱乏的農村地區,與童婚販運相關的經濟交易更加猖獗(Parsons et al.,2015)。已有研究發現南亞和非洲地區的童婚販賣現象仍高達40%(Nguyen et al.,2015),不平等的性別地位意味著女童在社會角色和責任關系中的選擇和控制更少(Mikhail,2002)。此外,在東南亞地區,與旅游業有關的兒童性販運數量不斷增加,甚至形成了網絡規模龐大、組織結構嚴密的兒童賣淫基地(Rafferty,2007)。

表2 國外兒童販運研究的高被引文獻聚類Table 2 Information table of clusters of highly cited papers in child trafficking from abroad
主題模塊2:兒童商業性販運與性剝削,包括#2聚類——性暴力(sexual violence)和#6聚類——兒童性販運(child sex trafficking)。美國較早關注商業性剝削和性販運帶來的身體創傷、精神障礙和藥物濫用等問題(Le et al.,2018),其中兒童受害者表現出較低的社會支持水平和生活應對能力(Rothman et al.,2020)。Bissias(2016)從接觸性侵犯視角,揭示了性剝削對美國12歲以下兒童造成的持久性傷害,并提出從特定點到網絡解救兒童受害者的建議。在了解兒童創傷和人權保護的基礎上,醫療人員能有效地識別高風險兒童并為其提供健康保障(Greenbaum,2014)。其中,兒科臨床醫生為兒童販運受害者提供了完善的醫療設施和安全的護理環境,通過及時治療和轉診幫助受害者減輕痛苦(Lutz,2018)。針對兒童販運帶來的個體傷害與社會風險,公共政策、醫療教育、健康服務等社會各界工作者需共同合作,幫助兒童康復和重返社會(Millerperrin et al.,2017)。然而,兒童性販運與性剝削受兒童期情感、是否遭受性虐待、是否離家出走、家庭成員是否從事性工作等多種外界因素的影響(Fedina et al.,2019),因而需整合多視角資源識別受害者,將簡單的兒童營救方式轉移到兒童創傷醫療上,以預防疾病傳播,減輕兒童心理和經濟負擔(Ladd et al.,2017;Gordon et al.,2018)。
主題模塊3:兒童販運自殺風險評估,包括#1聚類——自殺行為(suicidal behavior)和#5 聚類——嚴重的身體暴力(severe physical violence)。兒童的成長軌跡主要取決于生存環境及其生活照顧者,貧窮、動蕩和暴力環境中的弱勢兒童極易被忽視,淪為潛在販運受害者(Peck,2020)。兒童在貧困家庭監管不力或被虐待的情況下,更容易遭遇販運(Jobe,2010)。其中居住在國際邊界附近的兒童面臨的跨國販運風險較高,犯罪分子通常會借助發達的人際網絡組織、招募和運輸兒童。兒童販運的整個生命周期與其身體遭受的暴力傷害程度相關,如心理創傷、精神問題和藥物濫用可能導致兒童受害者更具有自殺傾向和反社會行為(Kiss et al.,2015a),而良好的醫療服務是促進兒童受害者心理健康的重要措施(Rafferty,2017)。Kiss等(2015b)發現東南亞61.2%的兒童販運幸存者患有抑郁癥,5.2%的幸存者在1個月內有自殺傾向。一項非政府組織的記錄發現,印度孟買的兒童性販運受害者占總數的一半,貧窮與性別歧視使得女童的性販運風險增加,應采取結構性干預措施改善女童的機會選擇,以減少販運數量(Silverman et al.,2007)。
主題模塊4:兒童保護與販運防控對策,包括#3 聚類——國家轉介機制(national referral mechanism)。兒童販運早期被視為一種孤立的局部現象,社會針對弱勢兒童提供的保護政策和服務體系相對薄弱(Harvey et al.,2015)。兒童販運類型和風險受性別影響,需重視因性別偏差而忽視的販運受害者群體(Mitchell et al.,2017)。Varma(2015)從受害者視角揭示了長期遭受性剝削的兒童可能會經歷抑郁、焦慮、精神分裂和社交孤立等各種創傷綜合癥,造成身體和心理的雙重傷害(Edward et al.,2009),而良好的人際關系和文化融合是兒童幸存者治療心理創傷的有效途徑(Abu-Ali et al.,2011)。Barnert等(2016)基于法律視角指出為了保護販運受害者的最大利益,安全港立法將遭受商業性剝削的受害者視為需要服務的弱勢兒童,而不是罪犯。法醫人員在兒童販運中的作用不容忽視,他們可為兒童受害者提供起訴、康復和賠償保護,幫助其恢復 權 利 和 尊 嚴(Obertová et al., 2018)。Jordan(2018)從醫療健康視角探究了兒童商業性販運的創傷護理情況,讓不同性別、年齡和種族的患者參與制定安全計劃書,并對受害者的創傷敏感性和病情隱私性進行評估。Fong 等(2010)認為兒童受害者的生存環境與福利制度面臨挑戰,福利機構應制定一項符合兒童最大利益的永久性計劃,預防和減少兒童販運的發生。此外,社區參與在預防兒童販運中的作用逐漸顯現(Hynes,2015),孟加拉國從非政府組織視角倡導構建兒童友好型空間,通過改善兒童社區生活環境,降低兒童脆弱性以預防販運風險(Islam,2019)。因此,學者們建議從宏觀社會環境(如經濟危機、自然災害、戰爭疾病、女性歧視、勞工市場與全球性旅游業)與微觀個體風險(如家庭關系、兒童處境、父母疾病)2個層面探究兒童販運的發生機制,并提出針對性的兒童保護對策(Roby,2005)。
2.4.2 中國拐賣兒童犯罪的知識圖譜分析 國內文獻(圖4)共有340個關鍵詞節點、735條連接,密度為0.013,關鍵詞節點和網絡密度較離散。其中,拐賣兒童的出現頻次最高為39,中心度最大為0.35;其次是拐賣兒童犯罪,出現頻次和中心度分別為26和0.29;再者,拐賣婦女兒童、拐賣婦女兒童罪、拐賣兒童罪、拐賣和對策等的出現頻次均>10,這些關鍵詞體現了中國拐賣兒童犯罪的研究熱點。具體來看,已有研究早期著重討論拐賣婦女兒童的罪名構成(楊文龍,2008)、量刑標準與立法完善等(蔡曦蕾,2016),并提出將此種犯罪行為明確規制在法律范圍之內。拐賣作案人通常包括與受害者毫無血緣或情感聯系的陌生人、與受害者有親緣或情感關系的熟人以及受害者的親生父母3類人員(朱兵陽,2019),其中親生親賣案件占近三成(邢紅枚等,2017),然而法律裁定對監護人的量刑較輕(Xin et al.,2021)。收買方通常因合法收養門檻高,在無法生育或生育性別偏好不符的情況下非法購買兒童,兒童收養剛需催生了較大的買方市場(王錫章,2015)。拐賣男童一般為了延續香火,女童則作為“童養媳”(Shen et al.,2013)。為了從源頭遏制拐賣犯罪,2015年中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中提出“買方入刑”的規定,兼顧社會與法制的雙重倫理,對收買方進行法律懲戒(徐穎,2019)。在全國宏觀尺度上,中國拐賣兒童犯罪時間上呈“中段高發、首尾低發”態勢,空間上呈“西部集中拐出,東部分散拐入”的“三片兩線”的“場-流”分布格局,并具有一定的帶動與回流效應(李鋼等,2019);在市域中觀尺度上,省會城市是拐賣兒童犯罪的熱點高發區;在微觀尺度上,鄉村是拐賣兒童犯罪的主要頻發地,包括家附近、街道里巷、集市、車站等人員流動頻繁的開放型地點(薛淑艷等,2020)。區域地理環境、經濟條件、文化傳統等區域性差異以及生育政策、立法執法、收養制度和戶籍制度等制度性規定產生的地區差異梯度力,是拐賣兒童犯罪空間遷移的誘因(李鋼等,2020)。而被拐兒童的生命歷程變遷、所遭受的心理創傷與家鄉網絡成員的社會反應,對尋親成功后的原生家庭融入具有重要影響(薛淑艷等,2021)。

圖4 2000—2020年中國拐賣兒童犯罪的關鍵詞共現網絡Fig.4 The co-appearance network of keywords in child trafficking from China during 2000-2020
3 國內外兒童販運的研究框架比較
國內外兒童販運研究存在較大差異(圖5),國外兒童販運不僅是全球公共衛生問題(Todres,2011),也是重大刑事司法問題(Greenbaum et al.,2018),其主要以剝削為目的,包括直接剝削(控制兒童本身)與間接剝削(控制兒童的近親屬)2種方式(Blazek et al.,2018),涉及非法收養、商業性販運、童工剝削、強迫童婚、兒童雇傭軍和強制器官切除等多種販運類型(DiRienzo et al.,2017)。多數兒童受害者是非法移民,具有受教育水平低和生活孤立等共性(Logan et al.,2009)。國外研究數據來源于家庭服務部門、社會行政部門、醫療衛生部門和社會跟蹤調查等渠道,定性與定量方法應用較多;研究對象從兒童受害者和販運者向家庭監護者、醫療救助者、法律工作者和社會參與者等延伸;研究領域從社會學、心理學和兒科醫學向家庭研究、犯罪學與法學和公共環境與職業健康等擴展,包括販運發生的社會原因與法律政策解析,以及兒童受害者的身體創傷、心理健康、家庭回歸、醫療救助與自殺風險等。

圖5 中外兒童販運研究的主體框架Fig.5 The overall framework of child trafficking studies from abroad and China
中國拐賣兒童犯罪以非法收養為主,包括誘騙養子型、家庭操控型、成人勞工型、復合過渡型等類型,前2 種最為常見(王金玲,2005)。早期研究主要依靠警方統計數據和社會調查數據,缺乏大樣本的定量分析。近年來,裁判文書網(Huang et al.,2019)和“寶貝回家”(王皎貝等,2021)等網絡平臺數據逐漸得到應用,為實證研究提供了多源充足的資料。國內拐賣兒童犯罪多以近距離省內拐賣為主,犯罪人和收買人的共同作案,造成了兒童受害人在流出地、中轉地與流入地之間被動的、無意識的、非正常的遷移現象。國內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學、犯罪學和社會學3 大領域,側重拐賣兒童犯罪的法律政策、打拐行動、社會原因與防控對策等定性分析。目前,犯罪地理學從“人-環境-行為”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角度探討個體的時空行為模式,為理解拐賣兒童犯罪和地理環境的時空交互提供新視角。
總體上,國外兒童販運研究起步較早,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相對成熟,而國內仍處于初始階段。國外兒童販運研究雖取得了重要進展,但對販運來源地、中轉地和目的地的地理環境因素關注不夠,兒童販運的高發場所、地理路徑與遷移網絡被忽視了,難以從完整的“時-空-人”三維視角揭示兒童販運的規律。同時,已有文獻主要探討受害人的個體特征、健康狀況與衛生護理等,尚未考慮周圍環境因素對受害人日常活動的影響。此外,已有研究將犯罪看作孤立的事件,尚未考慮時空環境因素對犯罪人行為決策的影響,且缺乏對犯罪人重復犯罪的系統分析,忽視了犯罪人過去的活動經歷對其“后案節點”的影響。比較而言,國內研究以質性分析為主,缺少長時間序列的跟蹤調查數據,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跨境拐賣路徑與熱點源區。同時,缺乏地理學與其他學科領域的交叉研究,尋親中被拐兒童的記憶空間重構與社會回歸融入尚未得到關注。此外,針對原生家庭的韌性演變與生命周期過程關注較少,未來研究應關注拐賣犯罪人的生命軌跡與社會關系網絡變遷。
近年來,犯罪地理學以社會問題為導向,關注犯罪現象的格局、過程與機理,沿著“揭示問題、服務安全、解決問題”的思路,在公共安全和犯罪防控領域貢獻力量(龍冬平等,2017)。兒童販運作為一種犯罪現象,兼具社會性、時間性、空間性與流動性等多重屬性,涉及犯罪人、受害人或監護人與其他社會人等不同犯罪相關主體,受自然環境、社會經濟、政策制度、文化傳統等諸多要素的復雜交互影響。因此,未來研究如何將時間與空間維度,將兒童販運的相關主體(犯罪人、受害人或監護人與其他社會人)與時空環境(社會環境、建成環境及周圍人流環境)進行綜合貫穿非常重要。如販運中受害人的活動軌跡與居住環境暴露、犯罪人的出行距離與時空行為決策、監護人的群體分異與空間活動交互等均是今后研究的創新突破點,可用于揭示地理環境在兒童販運中的作用。
4 結論與展望
4.1 結論
本文總結與比較分析了2000年以來中外兒童販運的研究熱點與趨勢,主要結論包括:
1)中外兒童販運研究的發文量整體呈波動增長態勢,美國的發文量位居世界首位,國外研究集中在社會學、心理學、兒科醫學、家庭研究與犯罪學等5大領域。國內研究發展進程相對緩慢,早期研究集中在法學、犯罪學與社會學3大領域,近年來地理學領域快速興起。
2)由于區域環境與國情存在差異,國外兒童販運包含在人口販運研究中,更關注以剝削為目的跨國販運,包括直接剝削與間接剝削2種方式,涉及商業性販運、童工販運、人體器官販運、童婚販運等多種販運類型,商業性販運與性剝削是兒童販運的主要研究熱點;國內拐賣兒童犯罪通常與拐賣婦女合并討論,聚焦于以收養為目的的省域拐賣,誘騙養子型和家庭操控型是最常見的2種類型,拐賣兒童犯罪的法律政策與社會原因是熱點關注話題。
3)隨著多學科交叉融合的發展,國外兒童販運的研究主題從兒童受害者的販運類型向兒童被解救后的自殺風險與福祉評估、康復回歸與重返社會、兒童保護與販運防控對策持續拓展;國內拐賣兒童犯罪的研究主題從法律政策與社會原因向時空格局、影響因素、安置回歸與社會融入延伸。未來如何將兒童販運的相關主體(犯罪人、受害人或監護人與其他社會人)與時空環境(社會環境、建成環境及周圍人流環境)進行綜合貫穿,從犯罪地理學視角探究兒童販運的地理環境因素與時空活動軌跡的演變,深入解析“時-空-人”三維視角下兒童販運的發生機制至關重要。
4.2 展望
1)加強對兒童販運的概念界定與法律框架構建。國際兒童販運的概念主要基于《巴勒莫議定書》中對人口販運概念的延伸,以人權維護與司法責任為目標達成共識和制定對策。但兒童販運植根于不同時期的國際發展環境,不同國家的兒童販運類型各異,相關概念界定未達成共識,無法統一解釋兒童販運問題的復雜性與多變性。同時,尚未形成統一的兒童販運法律框架,雖然各國都期望通過刑事法典打擊兒童販運。但由于各國的立法差異,導致兒童販運可在國際間流動,并為其規避法律制裁提供了“避風港”。因此,未來應立足于不同區域的現實語境,加強對兒童販運的概念界定與法律框架構建,促進理論成果向實踐應用轉化。
2)以綜合性思維重新審視兒童販運的國際環境。犯罪地理學秉承地理學的綜合思維,聚焦犯罪活動的發生、分布及其演變規律與機制,為兒童販運研究提供了新視角。在全球化的發展浪潮中,地區新型經濟格局、資源分配與收入差距的形成,導致地方傳統的文化習俗與價值觀念受到沖擊,兒童原有的生存空間和生活方式發生變化,威脅兒童安全的風險因素不斷增加。因此,在全球化與地方化較量過程中,兒童販運的地理格局與路徑網絡也更加復雜,誘發兒童販運的環境因素錯綜復雜,人類必須反思現代文明高速發展背后的“犯罪根源”,探討跨區域和跨文化背景下兒童販運的內在機制與外在影響,這對販運防控具有重要實踐意義。
3)規范區域間人口流動形式,構建國際反販運合作機制。兒童販運不僅是一種嚴重的犯罪現象,更是一種復雜的社會問題,其演化過程具有深刻的時代性與區域性特征。當下,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催生了大量的跨國人口流動現象,同時在巨大經濟利益的驅動下,兒童販運時有發生,特別是口岸、邊防與邊境地區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業的兒童極易淪為販運受害者。因此,如何從個人、組織、社區和政府層面不斷完善政策制度,規范區域間人口流動形式,構建綜合全面的兒童保護機制,防止兒童販運局勢惡化尤為重要。此外,各國還應重視不同區域尺度下公眾參與對反販運行動的反饋效應,突破“區域保護主義”,避免“模式經驗主義”的反販運困境,探索多樣化的兒童販運防治對策與管理模式。
4)反思理論研究與實際成效的局限性。打擊兒童販運是維護國際安全與人權保障的必然選擇,由于受傳統道德和法律漏洞的影響,販運受害者識別受限。并且兒童販運過程涉及大量的時空信息,但由于兒童販運的隱蔽性和分散性,數據獲取和方法應用受限,較難形成統一范式來量化這些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研究結果的推廣性。當下多學科交叉融合與計量分析方法的引入為兒童販運研究提供了新契機,如何從多文化思想碰撞、多學科理論交叉、多方法技術融合解決兒童販運問題至關重要。同時,如何在實踐中充分利用GPS、GIS 和RS 等現代科技手段,追蹤和打擊兒童販運尤為緊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