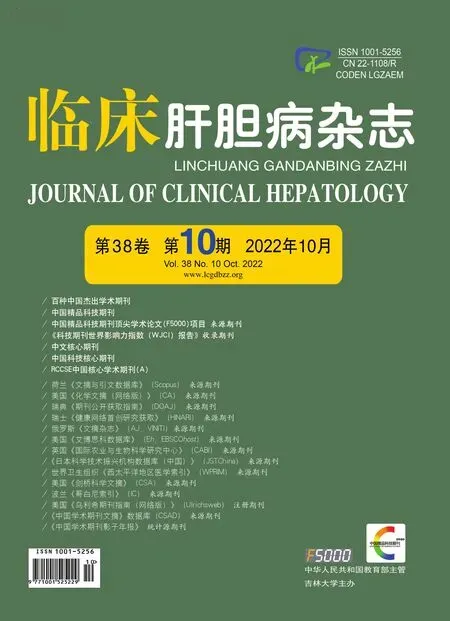糖皮質激素治療重癥藥物性肝損傷的效果分析
嚴 微, 黃會芳
1 山西醫科大學 第一臨床醫學院, 太原 030001; 2 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 消化內科, 太原 030001
藥物性肝損傷(drug-induced liver injury,DILI)是指在使用各類藥物過程中,由藥物本身及/或其代謝產物所導致的肝損傷,是最常見的藥物不良反應之一[1]。據報道,DILI的發病率在逐年升高,相關藥物多達1000余種,由于臨床表現多樣,缺乏特異性生物標志物,使得其診斷率相對較低。大多數DILI患者預后良好,但部分患者可進展為肝衰竭、死亡或需肝移植[2]。糖皮質激素長期以來被認為是治療重癥DILI的潛在方法,然而,國內外對其治療DILI的效果報道不一[3]。本文旨在通過回顧性分析重癥DILI患者的臨床資料,探討重癥DILI患者臨床特征及糖皮質激素治療效果,為DILI診治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收集2019年1月—2021年9月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診治的所有DILI患者的臨床資料。DILI的診斷參照2015年版《藥物性肝損傷診治指南》[4],所有患者的RUCAM評分均>5分,嚴重程度3~4級的患者被認定為重癥DILI。3級(重度肝損傷):血清ALT和/或ALP升高,TBil≥85.5 μmol/L,伴或不伴INR≥1.5;患者需要住院治療,或住院時間延長;4級(急性肝衰竭):血清ALT和/或ALP水平升高,TBil≥171 μmol/L或每日上升≥17.1 μmol/L,INR≥2.0或PTA<40%,可同時出現腹水或肝性腦病;或其他器官功能衰竭。臨床分型:(1)肝細胞損傷型,R≥5且ALT≥3倍正常值上限(ULN);(2)膽汁淤積型,ALP≥2×ULN且R≤2;(3)混合型,ALT≥3×ULN,ALP≥2×ULN,且2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年齡≥18歲的重癥DILI患者。排除標準:(1)其他原因或疾病導致的肝損傷,包括各類肝炎病毒、巨細胞病毒、EB病毒感染,酒精性肝損傷,膽道病變,自身免疫性疾病,遺傳代謝性肝病等;(2)合并有嚴重的全身性疾病,如尿毒癥、嚴重心腦血管、腎和造血系統疾病等。 1.3 研究方法 根據患者是否使用過激素分為對照組和激素組。兩組患者都停用肝損傷藥物,接受靜脈輸注保肝藥物(包括多烯磷脂酰膽堿、谷胱甘肽、復方甘草酸苷等藥物)治療,部分患者進行人工肝支持治療,少數患者因病情需要輸注抗生素和血制品(即人血白蛋白、紅細胞、新鮮冰凍血漿等)。激素組患者因常規治療1~2周后病情未好轉或進一步惡化而加用激素,糖皮質激素的治療方案一般為靜脈滴注甲潑尼龍40~60 mg/d,治療5~7 d。 1.4 療效和終點 療效判定:通過住院期間患者的臨床表現及所監測的生化指標來判斷短期療效。有效[5]:癥狀緩解或消失,血清TBil水平在治療第3天下降>10%或第7天下降>30%,停藥后肝功能無反跳,其中對照組以入院時肝功能為基數,激素組以使用激素前的肝功能水平為基數。無效:未達到以上治療標準或治療過程中病情加重。主要終點:血清TBil<85.5 μmol/L。隨訪時間起始于2019年9月,截止時間2022年11月,隨訪內容包括臨床表現、血常規、肝腎功能、電解質、血糖、血脂、自身免疫指標等相關指標的變化。 2.1 一般資料 共納入88例重癥DILI患者,其中男33例(37.5%),女55例(62.5%);中位年齡49歲;肝細胞損傷型63例(71.59%),膽汁淤積型15例(17.05%),混合型10例(11.36%)。在造成肝損傷的藥物中,以中藥和膳食補充劑(herbal and dietary supplements,HDS)最為常見,共66例(75%),使用解熱鎮痛藥18例(20.45%)、抗微生物藥物15例(17.05%),其他藥物還包括化療藥、激素類藥、降壓藥、降脂藥、降糖藥、精神類藥等,其中23例(26.14%)聯合使用以上多種藥物。患者主要臨床表現包括黃疸(78.41%,69/88)、惡心(37.50%,33/88)、納差(34.09%,30/88)、乏力(25.00%,22/88),其他癥狀為腹部不適、皮膚瘙癢、嘔吐。 27例(30.68%)患者接受了激素治療即激素組,其余61例(69.32%)納入對照組。6.82%(6/88)的患者肝損傷程度達到4級(急性肝衰竭),其中對照組4例,激素組2例。激素組中16例患者因常規保肝治療后肝酶下降但膽紅素(主要為TBil和DBil)持續升高或降低不明顯而加用激素;4例患者因膽紅素穩定下降但轉氨酶波動較大而加用激素;5例患者因轉氨酶、膽紅素、INR等相關指標均改善不明顯而加用激素;2例患者因入院時肝損傷程度已達重度4級而使用激素。88例重癥DILI患者中有31例患者血清學自身免疫指標陽性,女性占70.97%(22/31)。激素組中1例患者抗心磷脂抗體IgG及IgM陽性;對照組共30例患者表現出自身免疫特征,22例抗核抗體陽性,1例抗核糖體P蛋白抗體陽性,5例抗線粒體抗體陽性,10例血清IgG水平升高。22.58%(7/31)的患者存在嗜酸性粒細胞增多,無患者出現發熱和皮疹。以上患者經完善相關指標檢查后均除外自身免疫性疾病,在后續隨訪治療中,僅部分患者復查了免疫指標,其中多數患者在病情改善后免疫指標轉陰。 兩組患者基線特征比較,AST、GGT、TBil及免疫指標陽性占比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1)。 2.2 短期治療不同時間點實驗室指標及其下降率比較 治療3 d時,激素組患者各實驗室指標均較基線時下降;對照組患者ALT、AST水平較基線降低,而ALP、GGT、TBil、INR、TBA水平升高。兩組治療3 d時TBil、INR及TBA下降率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治療7 d時,兩組ALT、GGT、INR和TBA下降率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表2)。治療14 d和21 d時,兩組患者各實驗室指標水平及下降率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 2.3 療效評估 激素組患者在激素治療3 d時TBil、TBA、INR下降尤為明顯,該組治療3 d時有效率達59.26%(16/27),而對照組僅為29.51%(18/61),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55.82,P=0.008)。治療7 d時激素組的累積有效率為81.48%(22/27),對照組仍為29.51%(18/61),兩組比較差異亦有統計學意義(χ2=64.27,P<0.001)。激素組2例急性肝衰竭患者治療均無效;對照組4例急性肝衰竭患者中2例治療有效,并在治療3周后達到終點,2例治療無效,其中1例死亡。激素組16例因常規保肝治療后肝酶下降但膽紅素持續升高或下降不明顯而加用激素的患者中,除1例急性肝衰竭患者治療無效外,余下15例均治療有效。在隨訪過程中,所有治療有效的患者均未出現肝功能反彈。 共41例患者在2周內達到治療終點,激素組在治療3、7、14 d達到治療終點患者的累積有效率分別為11.11%(3/27)、25.93%(7/27)、33.33%(9/27),對照組在治療3、7、14 d的累積有效率分別為4.92%(3/61)、29.51%(18/61)、52.46%(32/61),兩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值均>0.05)。 2.4 使用激素的安全性 激素組共3例患者出現不良反應,1例既往無基礎疾病的患者出現血糖升高,餐后血糖最高達23.4 mmol/L,停用激素并調整飲食后血糖得到控制;對照組和激素組各有2例患者在治療期間出現肺部感染,給予抗生素治療后感染得到控制。 隨著臨床藥物應用的多樣化和復雜化,DILI的發病率逐漸增高。2002年Sgro等[6]基于法國人群的一項研究估計全球DILI年發病率為(13.9±2.4)/10萬;2013年Bj?rnsson等[7]基于冰島人群的研究估計DILI年發病率為19.1/10萬;2019年Shen等[8]收集了我國308家醫療機構2012年—2014年住院確診為DILI的25 927例患者,估計我國DILI年發病率為23.8/10萬,且該研究僅納入住院患者,真實發病率可能更高。盡管大多數患者在停用肝損傷藥物后會自行好轉,但仍有少數患者死亡或接受肝臟移植,因此DILI的診斷和治療對于胃腸病學及肝病學專家而言仍然極具挑戰。 表1 激素組與對照組基線特征比較 表2 短期內不同時間點各實驗室指標及其下降率比較 本研究中,肝損傷藥物以HDS最為常見,這與之前很多研究調查的結果一致。據報道,在亞洲HDS是導致DILI的主要原因,韓國DILI患者肝損傷藥物調查中HDS占比最高,達73%;西方國家中,冰島16%的DILI患者是由HDS所致,而美國人群中HDS導致的肝損傷患者亦由2004年—2005年的7%升高至2013年—2014年的20%[8-9]。由此可見,HDS導致的肝損傷患者數量十分龐大,而具體損傷肝臟的成分鑒別仍有待進一步研究。 本研究中自身免疫指標陽性的患者中女性占70.97%。據研究統計,在各種肝臟疾病中男女發病率確實存在差異,女性易患原發性膽管炎和自身免疫性肝炎,而男性更易患原發性硬化性膽管炎和肝細胞癌[10]。女性易出現自身免疫特性的原因可能與雌激素有關,Mohammad等[11]研究發現,雌激素受體α可以通過促進T淋巴細胞活化和增殖從而促進T淋巴細胞介導的自身免疫性炎癥,特異性剔除雌激素受體α的小鼠對炎癥性腸病的敏感性降低。 與其他類型的肝病類似,DILI患者血清學常常表現為肝酶升高,但目前的數據顯示,ALT、AST水平升高不能反映肝臟受損程度,ALP升高僅代表存在膽汁淤積,GGT升高表明ALP升高為肝臟源性[12],而臨床上明顯的癥狀(腹水、肝性腦病、重度黃疸、多臟器功能衰竭等)、血清中較高的TBil及INR水平才是各類肝病預后不良最重要的指標,TBA亦是有效監測DILI患者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與DILI嚴重程度呈正相關[13]。 大多數DILI患者在停用肝損傷藥物后肝功能可自行緩解,但部分患者因病情持續不緩解或進一步發展常需保肝治療。輕-中度肝細胞損傷型和混合型DILI可試用水飛薊素,炎癥較重者可試用甘草酸制劑,其他常用藥物還包括雙環醇、精氨酸谷氨酸等;熊去氧膽酸或腺苷蛋氨酸可用于膽汁淤積型患者;早期急性肝衰竭患者可在綜合治療的基礎上加用N-乙酰半胱氨酸[1]。而對于糖皮質激素,自其開始被應用于肝病以來一直頗具爭議。一般認為,藥物本身并沒有免疫原性,但當藥物或其代謝產物與宿主蛋白結合后則形成藥物-蛋白加合物(drug-protein adducts,DPA),當DPA抗原表位與宿主人類白細胞抗原表位相匹配時,才被抗原遞呈細胞識別、處理并提交給限制性T淋巴細胞,觸發適應性免疫反應,誘導肝損傷發生[14-16]。基于這種發病機制,糖皮質激素對于特異性DILI的治療理論上應當是有效的。本研究中大約1/3的患者接受激素治療,激素組治療前的TBil水平高于對照組,即激素組初始肝損傷程度較對照組更為嚴重,但在治療3 d和治療7 d時TBil比較無統計學差異,治療累積有效率分別達59.26%和81.48%,顯著高于對照組(29.51%和29.51%),提示短期內使用激素可以加速重癥DILI患者(不包括急性肝衰竭)肝損傷的恢復,并對幾乎所有因常規保肝治療后肝酶穩定下降但膽紅素持續升高或降低不明顯而加用激素的患者治療均有效,證明激素對于降低膽紅素效果顯著,且應用激素治療的患者未出現比常規治療患者更加明顯的副作用。Hu等[17]研究認為激素只對TBil>243 μmol/L的DILI患者才有效,且對于急性肝衰竭患者亦有益。本研究中激素對于急性肝衰竭患者治療無效,因納入研究對象太少而缺乏客觀意義。《藥物性肝損傷基層診療指南(2019年)》[1]中指出,激素適用于超敏或自身免疫征象明顯的患者,本研究顯示,自身免疫特性的1例患者使用激素后治療效果顯著,但Bj?rnsson等[18]對于英夫利昔單抗相關性DILI研究中并沒有發現具有自身免疫特性的患者使用激素治療的效果更好,因此有待收集更多此類患者進一步驗證。Hu等[17]研究發現使用糖皮質激素治療降低了重癥DILI患者的病死率并縮短了恢復時間;而Karkhanis等[19]回顧性研究結果顯示,糖皮質激素與生存率的提高無關。本研究中大多數DILI患者預后良好,僅對照組1例患者死亡。未來需要更多研究探討激素對于重癥DILI患者生存率的影響。 各項研究對于激素治療DILI效果不統一的結果表明DILI的發病機制復雜,并不能簡化為免疫和炎癥反應,個體對糖皮質激素的敏感性差異、不同藥物誘導的肝損傷類型、起病時間長短等對糖皮質激素起效均有影響。董金玲等[20]通過對HBV相關慢加急性肝衰竭患者使用激素發現,激素敏感組患者的肝功能指標改善情況明顯優于激素不敏感者。歐洲肝病學會指出皮質類固醇可用于治療藥物誘導性膽汁淤積性肝病,而緩慢發病的患者較急性發作患者對糖皮質激素或許更敏感[10]。 綜上所述,本研究表明,DILI患者臨床表現缺乏特異性,其中HDS是最常見的肝損傷藥物,女性DILI患者更易表現出自身免疫特征。對于常規治療后膽紅素降低不理想的重癥3級DILI患者短期使用激素可獲益,且無明顯不良反應。但由于本研究為回顧性研究,存在選擇偏倚,激素使用不能嚴格統一劑量與療程,缺乏隨機對照,且樣本數量有限,故未來仍需積累更多數量患者行進一步研究及更長時間的隨訪。 倫理學聲明:本研究方案經由山西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倫理委員會審批,批號:[2022]倫審字(K026)號。 利益沖突聲明:本研究不存在研究者、倫理委員會成員、受試者監護人以及與公開研究成果有關的利益沖突。 作者貢獻聲明:嚴微負責設計課題,收集數據,資料分析,撰寫論文;黃會芳參與擬定寫作思路,指導論文撰寫并修改論文。
2 結果
3 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