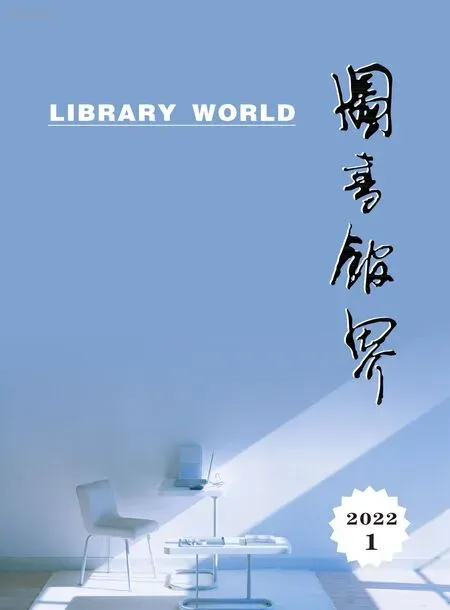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的路徑選擇
——以景寧畬族自治縣為例
何義珠
(麗水學院,浙江 麗水 323000)
2015年,李克強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就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的問題進行部署安排,標志著我國公共服務供給側改革開始啟動。截至目前,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側改革已經在浙江、上海、江蘇等多個省市進行探索和實踐,有了比較成熟的做法和經驗。但是,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供給側改革研究尚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文獻資料并不多見。而互聯網思維被百度創始人李彥宏首次提出后,經過雷軍、周鴻祎、馬云、趙大偉等人通過不同方式的完善提升,在公共文化服務領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供給側改革和互聯網思維對審視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存在政府投入與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的偏離、文化多樣性與文化產品同一性等問題以及指導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與實踐意義。
1 供給失靈: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普遍性問題
根據公共產品理論,社會產品分為公共產品和私人產品,公共產品注重社會效益和公共利益,私人產品追求經濟效益或自身利益。這就極大降低了追求經濟效益的私人產品進入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可能性。民族地區相對落后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特殊的自然環境,獨特的文化資源等讓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表現出一定的差異性和復雜性。而作為一種地區性獨特的公共產品,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普遍存在政府和市場雙重失靈現象。
資金來源單一且供給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失靈。湖北省利川市2014年文化體育與傳媒僅占財政總支出的1.79%,2017年下降至1.34%。周曉麗在對甘肅臨夏縣調查發現,70.8%的調查樣本表示公共文化產品供給中存在的最大問題是資金困難。新疆昌吉州“經費不足是影響少數民族地區公共文化產品供給,制約少數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的突出問題”。全國人大代表、巴彥淖爾市民族歌舞劇院副院長姜蘭指出,邊疆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歷史欠賬較多、資金投入嚴重不足,導致藝術院團下鄉演出和宣傳服務職能不斷弱化,公共文化服務職能未得到充分體現。對貴州省民族地區城鄉公共文化服務的調查發現,貴州傳統的民族文化活動基本處于自發、自籌資金的狀態。
通過梳理政策文件、研究成果和新聞報道發現,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失靈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公益性和滯后性并存導致供給失靈。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落后性與復雜性,很大程度上在公共文化服務提供方面設置了諸多約束條件,進而出現一定程度上的不公平現象。而主要依靠政府這個單一供給主體的現實情況,又必然會引起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失靈的問題。二是機構供給同一性與服務對象需求特殊性引起供給失靈。《文化部“十三五”時期文化發展改革規劃》《“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等政策文件提出的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均等化建設,容易在民族地區形成“一刀切”的供給內容與模式,對民族地區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相關內容的供給不足,顯然無法在特殊性和多元文化需求的少數民族群體中形成“你提供”即“我所需”的供給平衡狀態,政府失靈現象也就不可避免。
2 互聯網思維:民族地區公共文化供給側改革的技術工具
互聯網思維一詞最早的提出者李彥宏認為,互聯網是一種特殊視角的思考,可以解決很多管理上的問題;雷軍對互聯網思維的理解和實踐主要體現在專注、極致、快、口碑、群眾路線等方面;周鴻祎則將互聯網思維總結成用戶至上、體驗為王、免費模式、顛覆式創新等四個關鍵詞;馬云認為互聯網思維就是跨界、大數據、簡潔、整合;趙大偉提出互聯網的九大思維,即用戶思維、簡約思維、極致思維、迭代思維、流量思維、社會化思維、大數據思維、平臺思維、跨界思維。政府官方對互聯網思維從宏觀經濟層面進行解釋,“互聯網思維是一種新的經濟形態,即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將互聯網的創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經濟社會各領域之中,提升實體經濟的創新力和生產力,形成更廣泛的以互聯網為基礎設施和實現工具的經濟發展新形態”。可見,互聯網思維主要體現了連接和體驗等內涵特征,與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有高度的相關性和統一的主張。
2.1 連接: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的效率
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效率并非單純的參考投入資金、場館數量、活動開展等表象,它背后隱藏的是少數民族群眾對傳統文化和習俗的特殊認知和民族心理的表述。假如公共文化服務數量和規模的提升并沒有帶來更好的認可,未形成預期的社會輿論和秩序,那么這種效率也就沒有任何意義。而互聯網思維的“連接”恰好為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提供了合適的效率邏輯。
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第48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1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11億,互聯網普及率達71.6%,其中我國手機網民規模為10.07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比例為99.6%。目前,我國互聯網的高滲透率和普及率應驗了馬化騰于2015年提出的互聯網將成為“連接一切”的新生態的預言,讓連接人與人、人與服務和人與智能硬件的生態圈成為現實。檢視我國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實際,可以發現互聯網技術創造了人與機連接、人與文化連接、設備與服務內容連接的可能和現實,而互聯網思維提供了讓公共文化服務成為有用戶黏性、有體驗感的文化產品的機會和視角。浙江景寧畬族自治縣通過建立與完善政策制度,用互聯網技術將畬族文化資源轉化成各種民族特色節目和群眾文藝活動,形成了人與文化、設施設備與內容、人與設備的連接。
2.2 體驗: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的評價
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是有組織、有資源投入來實現少數民族群眾基本文化權利的社會治理行為,需要平衡“政府需要”和“群眾需要”的共同利益和追求,體現群眾的體驗感和獲得感。公共文化服務領域的互聯網思維,其實是互聯網技術降低了公共文化產品的生產成本與傳遞成本,讓龐大的用戶群體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時空距離影響共享文化與服務的模式,是一種對傳統的服務供給模式和理念的顛覆,其核心內涵是用戶思維、體驗至上。也就是說,互聯網思維可以為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側改革提供一種評價邏輯。
根據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特殊性和復雜性,其評價不僅涉及具體化、關聯化、可衡量化和可實現化等要素,公民參與也是一個重要評價變量。對于公共文化任何一種形式和內容的服務產品而言,不同區域和不同民族的人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價。對本民族沿襲下來的傳統文化和習俗轉化而成的公共文化產品,群眾享用的積極性和參與度會更高,畢竟它們來源于群眾日常生活,貼近實際,展示形式又是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素材,愿意消費的群眾數量都會有一定的增加。事實證明,能讓群眾決定參與的公共文化服務,最能代表群眾的基本文化權利訴求,也符合公益性要求的結果。
3 民族地區公共文化供給側改革的實施路徑
3.1 制度路徑:供給問題的確認
我國民族地區地域廣闊,經濟發展不平衡,東、中、西部差距較大,各地各級政府的財政狀況也有很大差別。雖然國家層面的公共文化服務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規比較完善,但是基于當地實際問題梳理制訂的省、市、縣一級的地方性單行條例,才能實現國家層面的少數民族群眾文化權益可實現、可衡量的現實保障。浙江省“核心+關聯+配套”的政策制度實體化的實踐探索對其他民族地區有借鑒和參考意義。浙江省通過對公共文化服務發展的不均衡現象進行全面梳理,基于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制訂了可衡量、可實現、可評價的《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條例》。《浙江省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條例》通過“成立由政府負責人牽頭的公共文化服務協調機構”強化政府主體責任的落實;實施“公共文化服務預算支出增長幅度應當高于財政經常性支出增長幅度”的“硬性約束”加強經費的保障;以“跨部門、跨行業、跨區域資源的整合”和“重視公共文化服務與科技融合”推進公共文化服務的均等化建設;實施“公共文化設施開放時間應當與公眾工作時間、學習時間適當錯開”和“建立反映公眾文化需求的征詢反饋制度和有公眾、第三方參與的公共文化服務考核評價制度,考核評價結果作為確定補貼或者獎勵的依據”以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效能。浙江景寧畬族自治縣則將公共文化服務標準化和地方立法結合起來制訂地方單行條例:起草出臺“文化新十條”、《浙江省景寧縣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條例(草案)》《關于建立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協調機制的通知》《關于加快構建現代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實施方案》等制度條例,在公共文化服務設施、公共文化產品、公共文化服務效率、社會力量的參與等方面作出了“硬性約束”。
3.2 資源路徑:民族文化多重價值的實現
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具有多重價值,是繁榮少數民族文化的需要,是建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重要工具,是國家認同、民族認同和制度認同的載體。新中國成立以來,黨和政府一直高度關注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文化事業的發展,大力扶持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建設。但是,民族地區與其他地區之間存在的公共文化服務建設不均等、現代化服務水平不高、少數民族文化資源轉化成公共文化產品的能力不足等矛盾已逐漸成為影響民族文化多重價值實現的“絆腳石”。可見,探索公共文化服務的資源路徑是民族地區亟須思考的議題。
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資源類型,包括內部資源和外部資源。外部資源指的是政策和政府支持、公共文化服務的市場化和社會化、公民參與力、資金投入等;內部資源包括公共文化服務團隊的規模和能力水平、發展規劃與愿景、公共文化品牌建設等。對民族地區而言,盤活政策制度、公民參與力等外部資源,加強團隊、公共文化品牌群等內部資源的融合,構建有效的區域輻射與共享的優質資源路徑,是民族地區公共文化服務的新趨向。例如,景寧畬族自治縣通過“項目申報輔導制”“項目上墻”“鳳舞畬山大舞臺”“農民藝術節”打通了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聯系通道。一方面,借助社會公眾的力量充分挖掘畬族文化素材和民間特色活動,增強群眾的信任感和親近感;另一方面,又實現了群眾參與和共文化品牌建設的同向相融,為畬族文化資源的多維度轉化營造了良好的社會環境。景寧各鄉鎮創立的“嘗新節”“湯氏”文化節、“搶豬節”“畬藝節”等特色文化品牌活動,讓畬族文化在景寧區域內形成了一定的影響力,《千年山哈》等文化藝術精品則通過全國少數民族文藝匯演將影響力擴大到了全國范圍。可見,在對民族文化資源和傳統習俗充分挖掘運用的前提下,民族文化的多重價值能在公共文化服務活動中得到實現并在更大范圍內形成潛在的影響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