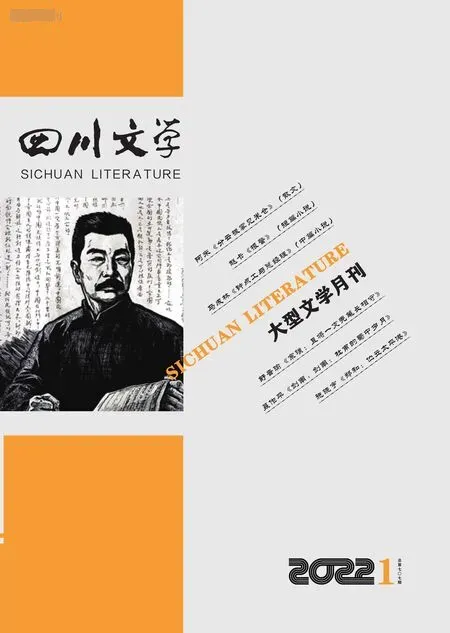綠皮火車(組詩)
□文/阿翔
綠皮火車
它駛過身邊的風景
油菜花和遠處的湖泊促成
一場旅程;它甚至駛過任何一條道路
只要你走過,就不會低于
微妙的震顫;它駛過遠山像春風中
暴露出的幽僻深處,駛過
花枝的影子,駛過蜜蜂的空氣
有一個神秘的回報,駛過外面的世界
在我們的昏昏欲睡中喪失了
對恰當的把握。它駛過春天的螞蟻,
就好像它身上的綠皮恒久得
你也有不愿面對自己的時候;
它駛過迷霧一團的現實,而你感受不到
那些縫隙的存在,仿佛一節一節
等待著我們重新變回去。
當它繼續旅途時,它駛過隧道的黑暗
就像是鉆進奇妙的空間,
流動的時間只是一個幌子,
自深淵,滑動的力量遠遠超出了
我們的想象。它駛過大地的果實
多于印象的果實,駛過只要
涉及分叉口的底線就會觸碰到世界的分歧,
仿佛陡然開始翻倍會把你
套得更牢;它甚至駛過
你很少會意識到曙光比絕對現場
不限于一種新的陌生。
最后一次公路旅行——懷念父親
天暗下來之前我們上路,
踏上最后一次旅程。我重新把我自己
交給你的手上,那柔和的溫度
難以言說,像是輕輕顫動于一個默契
直到暮晚的光線映射在車窗上
沿途繃緊的風景看似很光澤,但光線
觸不到的地方如同我和你之間的
界限至少對命運而言是模糊的,仿佛
過于苛刻,而悲哀有時會用到這樣的模糊。
在高速公路越走越遠意味著終點
越來越近,就像不朽的牽扯——
會有大量的時間不得不一次次緘縮;
作為一種愛的警示,古老的敵意
最終被證明是盲目的;而你在酣睡,
就好像世界的確有過一個盲目。
天將暗下來之前我們繼續上路,你身上
有一個頂峰的高度,足以令影子變得透明,
無邊的寂靜忠于自我的本來面目,
猶如忠于神的孤獨;像是一種暗示,
盡頭意味著即將各奔東西。隔著現場如同
隔著人的一生,呼應過眾多未來,
就好比一條漫長的公路也漸漸
清晰在我們的深淵。天將暗下來之前
我一路護送著你,必須完成的一個儀式
則像是留給我的任務,直到死神
躲進虛無的角落,但不意味著你就缺少
一個化身;我的眼淚浸透了
一份完整的封閉性,這算不算
是久遠的回聲。漫無邊際的全程奔馳
加深了低空中有一束即逝的暮光。
江南來信——致YP
那里,細雨給綿綿無盡的寒冷
加深了一個神秘的積淀;如果不是
因為偶然缺席,你怎么會知道
我像是獨自去過那里,甚至很可能你從未
意識到云霧安靜得像過濾掉
其中可疑的部分。看上去一種美
將絢爛糾正為世界觀,或者說,
顫動的花影是蜜蜂的來信,你會覺得
遠不只于自然的一個疏忽,
更像是一次小小的泄漏;如果你聽得懂
世界的空曠是喜鵲的來信,
那么飛去的身影,則已是枝頭的來信,
完美的自由充當了時間的同謀。
而石頭墜向深淵的影子里,插放的新聞
是過客的來信,以至于你會懷疑
聲音的真實性是不是出了差錯;
或許反過來,沒看見的不算,
但看見之后,春暖江水才是野鴨的來信,
像是和你有過默契。只要我還在,
你怎么會錯過貍花貓加快步伐路過的地方,
蝴蝶是灌木叢最隱蔽的來信,
看上去彼此追逐喚醒了碧綠的烈焰;
除非你站起來,一個漩渦的語言
完全屬于你,深如自我但深不過
人的廢墟之后新芽的來信。
紫藤來信——贈少況
清晨我們散步在湖邊,陽光加快
步伐迅速跟上城墻。那里,它的錦簇
醒目于風中的游蕩,形如夾豆
很難歸類,仿佛沒人聽說過,不同于
現實中的羈絆。一旦綻放,
它傾心于寂靜是一場化身的埋伏,
只有它的直率像是從喜鵲的嘴角逃過一劫,
你很難沒法聯想到喜鵲的挑剔
足以讓天平傾斜,甚至不依賴于
時間的荒謬。在它之前,看上去
很熟悉的東西也很難將命運
作為它的出色的對象,但命運及時會作出
回報的反應。比如,雨后的清晨,
在我們身邊,陽光和紫色的美麗交織
在一起,像一首詩的懸念很少
出現在我們之中。所以,在我們到來之前,
它已卷入我們的交流中心,
成為一首詩的主題,就好像它及時
介入在我們和世界的一種關系。
但你沒法確定,僅憑一己之力,
高貴的熱烈在現場中究竟能持續多久,
即使你建議它應該像反光的波浪
越過大海的影子。或許事情就很好
解釋了。但在它身上,天性充分到隨意
游蕩,雜音仿佛在最隱蔽的地方
還能被全部過濾,這算不算是生命中
最純粹的回聲。
和母親雨夜談話
夜晚的雨聲隔著無邊的寂靜。
在她的談話中,雨下得就好像世界
拿她沒有別的選擇。這里面的黑
是慈悲的,比純粹的時間
仿佛回蕩在愛和死之間。而一件我們曾
隱瞞很久的事,在雨夜不經意間
被她挑明,在我面前平靜像一次攤牌:
你外公外婆都活到了百歲,
這幾年他們已不在了,我過段時間
回去看看,也算是跟他們
作個別。寥寥幾句低調得像是隨意,
雨聲突然大了起來,仿佛掙脫了黑暗,
有一種說不出的輕微;我甚至
不能確定她是不是對我們給予了諒解。
她的神情里有一種隱忍表明
了然于胸,就仿佛這是一個記憶。
比如她,經歷了這么多的悲哀,
依然是外公外婆最愛的小女兒;
20歲時從山東遠嫁安徽,甚至沒有
得到一句祝福;而他們百年后
她沒有奔喪。她的身體有多種疾病,
再也經不起一點刺激;我以為我們曾成功
隱瞞住了母親,但實際上并沒有。
無邊的寂靜顯得雨聲格外清亮,
母親!她從未降低過她對神的祈禱,
一如雨夜此刻從未降低過
深淵深不見底的眼淚。
52赫茲
大海中的深淵只剩下一個角色,
在其他同類的眼里它就像是個啞巴。
你從未意識到它就是你的命運,
它面對的不只是偏僻,
甚于你面對的不只是周圍的環境。
它融洽不進鯨群。它的聲音頻率有52赫茲,
比其他鯨魚高了二十赫茲,
是注定無法碰見同類。
在那么遠的地方,它失去的東西,
也是你注定會失去的東西。
甚至它比你失去的,只會更多。
唱歌時沒有人聽見,肯定要多于沉默時
沒有人理睬。這輩子也就只能
孑然一身在深海中獨自游蕩,
意味著除了幽靈,誰會在乎你是誰。
同樣,它的孤獨更偏向于
也很可能它從來就不曾孤獨。而它履行的,
更像是你在相同的頻率中尋找
另一個自己。但你又沒法否認,要成為
它的對象的可能性幾近于無。
在它沉重的身影中感到柔弱,
抑或在它的52赫茲中繃緊一個懸念;
大海有多浩瀚它比你更清楚,
就如同你比它其實也清楚黑暗的最深處
可以完全不受黑暗的影響。
群山來信——贈森子
甚至與剛下過雨無關,第一瞬間
來自繚繞群山的云霧暴露出
世界的能見度,你會覺得布谷鳥的鳴叫
誤解過花簇的秘密,有時也會低于
蜜蜂的試音;果實集體缺席于自然的口味,
并不妨礙是你判斷好壞的一個理由。
命運的瑕疵中,如果不是抱有偏見,
你的影子怎么會輕盈得疏忽
飽滿的真實含義,即使不擅長辯證法,
至少在風中找出迷宮的后門,
就像在這首詩里謄寫一遍群山的翡翠,
也掩飾不了縫隙的隔音效果。
與距離無關,盡頭就在星星的眼前,
猶如山楂和海棠之間的寂靜之舞,
遠不只于潛伏和附身的關系,更像是
一種減輕的重量,將陌生的自我
收斂在一個虛無中,仿佛玩了一次蛻皮。
甚至與現實無關,除非你恍惚于
滿山都是白云的語境,這種情形下,
誰會需要陪襯喜鵲的下午;所以,
第一瞬間帶來的新能量,就能識破
事實的全部伎倆,跟真的似的,
你身后的野貓低估了你的好奇心。
甚至也與人的最后一點祈求無關,
你從不低估窸窣之間的任何輕微就如同
一場出戲;如果沒記錯的話,
在巨大的孤獨中,你的角色令你自己
常常破綻百出,但又隨時
會得到自愈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