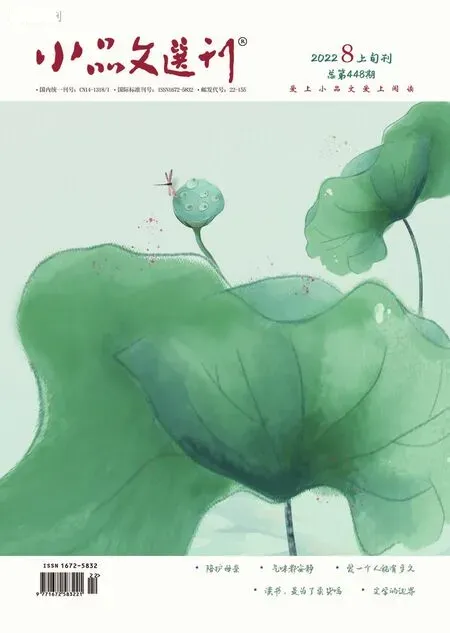生活教我的兩個真理
□葉延濱
生活教我之一,不見為好。
“見見就好”,這種能在心里頭發(fā)酵的念頭,多是情之所至。人不是候鳥,不會返回老路,穿過半個地球來回地折騰。但人心像候鳥,戀舊情。舊情最易萌生者,舊情人,特別是初戀情人。相識相交于青春年華,回憶起來總似春風楊柳拂面。只是總愛忘了分手的原因,更不成想歲月會修改你記憶中的那些故事。
記得我有位老師,一生蹉跎,受了不少折磨。
“平反”后,重新?lián)谓搪殻c初戀女友成婚。那位初戀女友,曾不得不舍離他而與別人成婚。婚姻大概因為勉強,最后回到獨身。于是人們以“有情人終成眷屬”佳話,描繪這場姻緣。
哪知道,歲月厲害,歲月在他們分開的二十年里,徹底地將對方改變成陌生的“怪物”。互不滿意,互相指責,最后很快離婚。老師說:“怪物!怎么變成怪物了?不如不見,滿心歡喜換來一場空。連回憶都丟掉了。”
老師的這番感嘆,我聽后不解。不解其中味,大概都是那些“簡·愛”式的愛情故事,弄得我們失去了判斷力。
讓我體會到不見為好,是一次“同學會”。我出差回到三十多年前讀中學的小城,主人盛情,幫我把高中的同學們招到一起,搞了一場“同學會”。三十多年沒見了,來者都興高采烈。
只是現(xiàn)場發(fā)生沒預料的“事故”。當年的男同學,從少年變成老頭,都還掛像,認得出來。
當年的女同學,從花季少女變成慈祥太婆,一半以上對不上號。面對面喊不出名字,有的尷尬,有的惱怒,我心里一百個后悔:“不如不見,連當年的樣子都模糊了。”是的,老天有安排。
有的好東西,擺在前頭,令人想得到手而前行;有的好東西,只能留在心里,讓人不舍而成為回憶。不見為好,也是生活教給的一門藝術,這里頭的分寸,就是一種珍惜。
生活教我之二,不說為好。
這個念頭是因為最近同行中有幾位相繼逝世。雖是同行,品格和成就相去甚遠。把他們的悼詞放到一起,好像個個都是當代圣人。如果再把友人的追念文章讀一遍,更是難分伯仲。
斯人已逝,其言善也,人之常情。這些溢美之詞,我們很舍不得給活著的人,特別是身邊的人。凡人平民只有在死后,才能享用平日圣賢偉人專享的贊譽,這幾乎成了一種慣例,讓我們習慣這種怪誕的事情。只是我十分熟悉這幾位逝者,讀到他們幾乎相同的悼詞,我才發(fā)現(xiàn)“不說為好”,是個認真的事情。
反觀之,如果他們平時不是那么品行或有欠缺,顏值尚不達標,個個活得真像身后補發(fā)的那紙“鑒定總結”,仔細想想,倒是一件相當讓人害怕的事情。
如孟子所言:“非之無舉也,剌之無剌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從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挑不出毛病,PM2.5和三聚氰胺不傷其樂,上下稱道,內外兼修,想一想也真讓人可疑。
其實我想起他們時,不盡是他們的好,記得清楚的還有他們的毛病。L先生的爭強好勝,H先生的工于心計,L女士的小肚雞腸,都讓他們鮮活成一個人。人無完人,這個道理聽過也說過,但擺到自己身邊的人,卻常常被“期望”成完人。
在無完人的世界上,孔夫子選了兩種人以為可做同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孔老夫子說得真好,有進取心者,只要不是太不要臉者,均可與之為伍。
天天聽人說“圓滿”講“全優(yōu)”的時候,無人提示,只因靜心讀了幾頁好書,想明白了。
其實,正是諸多“欠缺”與“不滿”,讓人生多了許多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