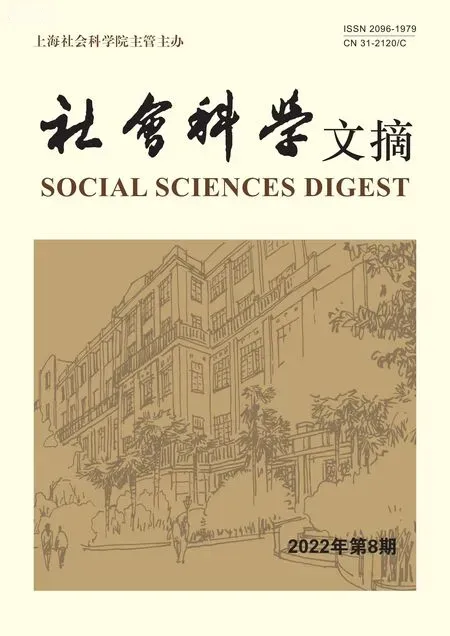從文本理解看釋義學的實踐意義
文/張汝倫
早在20世紀80年代,學界在介紹西方釋義學著作時已經闡明,釋義學有古典釋義學和現代的哲學釋義學之分。在當代世界有壓倒性影響的是哲學釋義學,而不是日漸式微的古典釋義學。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利科這些哲學釋義學奠基者的相關著作陸續被翻譯出版,似乎也表明我國學者主要對哲學釋義學情有獨鐘。然而,有興趣不等于能理解。我國研究者往往是以古典釋義學的模式來理解哲學釋義學的話語,而對哲學釋義學的革命性體察不深。具體表現為,基本上還是把釋義學的理解與闡釋視為一個主體對客體的認知活動,關心與討論的問題往往集中在如何克服理解的主觀性和任意性,達到解釋的客觀性,等等;沒有理解被人稱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現代釋義學真正的革命性意義;沒有理解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和利科等人一再強調的——對于釋義學來說,理解與解釋一方面是人與他人及事物建立聯系的事件,另一方面是人基本的存在方式,它涉及的是與他人、世界和歷史的一種基本的實踐樣式。嚴格說,釋義學活動是實踐活動,而不是認知活動或理論活動。本文以利科的文本理論以及伽達默爾的相關思想為例,來說明釋義學存在論意義上的實踐性質。
一
利科是繼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之后的、當代西方哲學釋義學又一個重要代表人物,他對于哲學釋義學理論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而文本理論是其解釋理論的核心。利科的文本概念是海德格爾的生存論哲學與結構語言學思想相結合的產物,主要歸結為如下五個命題:語言總是實現為話語;而話語又實現為一個有結構的作品;在話語和話語作品中,言與寫是關聯在一起的;話語作品投射了一個世界;話語作品是自我理解的中介。
話語是說出和寫下的語言,是語言的實現,就此而言,它是一個“事件”,它是在時間中實現和出現的。但是,話語作為文本,必然是有意義的。通過進入閱讀者的理解過程,它超越了自己的時間性,而成為意義。我們閱讀一個文本,首先追求的是其意義,而不是它的時間性或事件性。然而,文本與直接言說不一樣,由于通過書寫被固定了下來,它面對無數后來的讀者;另一方面,它的意義也必然會超出最初作者意象的視域。這意味著后來的讀者理解它時,可以去除當初的語境,同時又通過他們的理解和闡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將此文本重新置于一個語境中。這樣,歷史間距不再是影響我們理解文本意義的障礙,也不再是只有消極地與文本保持距離以保證客觀性的方法論意義;它對于文本具有建設性意義。
西方文學批評和《圣經》批評從19世紀中期以來,主要關注作品的內容,關注這些作品產生的社會歷史條件,或者它們指向的共同體。解釋一個文本本質上就是認為它表達了某些社會—文化需要,回應了某些時空中的困惑。這種歷史主義的思路,直到今天還是我們解釋歷史文獻和作品的基本思路。但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西方哲學產生了一個重要的成果,此成果可稱為“意義的發現”。它肇端于弗雷格哲學和胡塞爾的《邏輯研究》。這兩位現代西方哲學的奠基者發現:意義不是人頭腦中的觀念;它不是某種內心的內容;而是可以為不同時期的不同個人一再認定為是同一個對象的理念性對象。
與此同時,在心理主義和社會學至上思潮過度泛濫后,西方文學批評領域也出現了相似的變化。人們同樣把文本視為某種無時間性的對象,書寫就意味懸置歷史過程,從話語進入到觀念的領域,這個領域可以被后代無數可能的讀者無限擴大。意義的客觀化成了作者與讀者之間必要的中介,在意義這個平臺上,作者可以是讀者的同時代人。
這意味著通過對文本的解讀和闡釋,解讀者進入了文本的世界,這個世界不是只屬于作者,而是讀者與作者共有的世界。與一般的言說不同,文本的意義不是指向某個特殊事物,而是揭示了一個世界。當我們說《紅樓夢》的世界或《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世界時,就部分說明了這一點。話語的所指是正在說的事情,是可以用直接指稱的方式來確定的。但用文字書寫成的文本,卻無法用直接指稱的方式來確定它的所指。隨著書寫,事物已經開始發生了變化,不再有作為對話者的作者與讀者共有的處境,指稱行為的具體條件也不再存在。
換言之,文本的指稱不再是直接指稱,不再是像日常話語的指稱那樣的一級指稱;直接指稱的取消為二級指稱的解放創造了條件。而文本的指稱之所以是二級指稱,不僅是因為它的意義不是精神性的意向,更是因為文本使得實在在其中變了形。伽達默爾在《真理與方法》中討論其游戲理論時,提出了一個重要的“變形”概念。“變形”是事物一下子整個變成了另一個東西,這樣,另一個東西作為變了形的東西,就是該物真正的存在,相對于它來說,該物以前的存在是無意義的。
如果文本解釋也可以視為一種游戲或藝術的話,那么這種游戲也是創造物的變形。這里變形的是“實在”本身。當我們在解讀文本時,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再存在,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封閉于自身的世界”,即文本的世界。換言之,日常世界變形為文本的世界,這是一個可能性的世界。所以它的指稱是二級指稱,二級指稱達到的不是可操控的事物層面的世界,而是胡塞爾講的“生活世界”或海德格爾的“在世的存在”。“闡釋就是闡明面對文本展開的那種類型的在世存在。”而這些二級指稱為我們打開了一個世界,打開了我們在世存在的種種新的維度。
二
文本提出可能性的世界,而讀者則通過自己的理解占用這個世界。因此,讀者與文本的關系實際上是與文本世界的關系。這種關系不是近代認識論設想的主客體的關系,而是存在論意義上的從屬關系,讀者屬于這個首先通過他的闡釋揭示出來的可能性世界。理解文本不是理解作者的原意,而是理解客觀化的意義。正是客觀化的意義消除了作者與讀者的時間間距,通過對意義的“挪用”,讀者與作者成為同時代的人。
“挪用”是利科從德語中借來的一個詞,是指當前的讀者通過闡釋實現文本的意義。對文本的解釋不是讀者與作者之間主體間的相互理解的關系,而是通過理解達到對文本所揭示的自己的可能世界的把握。這種把握不是知識論理論意義上的認識,而是生存論實踐意義上的“挪用”。這種“挪用”,不是具體應用某個理論,而是將文本世界作為自己規劃的世界。通過“挪用”,讀者與文本的時間間距被克服了。哲學著作,尤其是哲學經典,之所以有無限闡釋的可能性,就因為它提出了這樣一種新的可能性世界。
然而,要“挪用”這個世界,解讀者也必須首先失去自己。理解和闡釋不是把我們有限的理解能力加于文本,而是將自己暴露在文本之前,從它那里接受一個擴大了的自我。對文本世界的領悟使我們進入了那個可能的世界,大大擴展了我們的視域。文本的世界不是藏在文本背后的一個主觀意向,而是文本展開、發現、揭示的東西。理解完全不是建構一個主體已經掌握了的東西,而是主體被文本的問題所建構。也就是說,通過對文本的解讀,我們理解的不是一個異己的意向,而是我們自己存在的新的可能性,從而使自我得到了豐富。具體言之,“挪用”文本的世界就意味著擴大了自己的世界。被“挪用”的世界不再是異己的世界,而是我們自己的世界。
由此,解讀文本不是一個主體(讀者)單向作用于客體(文本)的主觀操作,文本不是讀者知識論的對象,解讀文本也不是像地質學家分析其礦石那樣的一種客觀知識論行為,而是人最切己的存在方式,通過文本解讀,讀者擴大了他的存在可能性。
三
如果文本解讀不是主體單向作用于客體的主觀操作,那么,它也就不應該是實用主義的應用研究。實用主義的解讀有兩種基本模式。一種是以自然科學的理論應用為榜樣,把文本視為提供了某種或某些理論,這種或這些理論可以立即加以應用。還有一種是把文本視為行動的指南,解讀文本的目的是為了解決當下的問題,甚至是為了“制度設計”的方案。除了這兩種主要模式外,還有更為鄙俗的以經典文本來曲證己意的做法。無論是哪一種實用主義的解讀模式,都是一種主體主義的思維方式和解讀方式,解讀者不想通過對文本的解讀擴大自己的存在境域,而只想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文本的意義,從而剝奪了文本的揭示力量。文本不再揭示一個可能的世界,而只是讀者達到其外在目的的工具。文本不再是唯一的,而是可以被無數其他文本替代的。實用主義的解讀模式對文本實際是一種“謀殺”,同時也失去了文本解釋的意義。
當然,這也絕不意味著文本解釋是一種通常意義的純粹的理論活動。現代哲學釋義學的奠基者海德格爾和伽達默爾都強調理解與解釋不是主觀的知性活動,而是人基本的生存論的實踐模式。伽達默爾更是在《真理與方法》中特意把“應用”規定為與理解和解釋一樣的釋義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個要素。
“應用”這個概念非常容易引起誤解。人們往往會望文生義,從尋常字面意義上去理解此一概念:釋義學的“應用”難道不是把所理解的文本用于現實生活?這難道不正好印證了釋義學的實踐哲學性質嗎?這難道不正是作為實踐哲學的釋義學所要求的嗎?
這樣的理解是對伽達默爾的“應用”概念的莫大誤解。在文本理解過程中,理解者總是不同的,有著自己的特殊性。根據自己的處境來重新理解文本,這是伽達默爾“應用”概念的一個基本規定。但這不是說,在理解和解釋文本時,讀者完全根據自己的需要來理解和解釋文本,伽達默爾當然不可能主張這種極端主觀主義和實用主義的釋義學。對于他來說,讀者與文本的關系是一種普遍與特殊的關系。文本流傳萬代,始終是同一個文本。
釋義學的應用與實用主義的應用不同之處在于:它并不是應用者主觀性的證明;相反,它是對其主觀性的限制。應用要求理解者與解釋者通過對文本意義的理解和闡釋進入文本的意義世界,同時也因此豐富這個世界本身。應用其實就是一種溝通,我與你的溝通、古與今的溝通、可能與現實的溝通。“絕不會有這樣的讀者,當他面對文本時,只是簡單地讀那個文本。應用發生在一切閱讀中,因此,誰讀文本,本身就已身處所獲得的意義中。他屬于他理解的文本。”史學家如果想要理解歷史傳統的話,他就要把他自己生活的時代與這個傳統打通。應用不是將異己的東西納入自己的世界,而是打通自己的世界與一個可能的世界,使自己融入那個世界。
伽達默爾始終堅持文本的不可超越性,堅持要在切合文本的意義范圍內理解文本,并因此對19世紀的歷史主義史學家們對待歷史文本的態度提出了批評。歷史主義的史學家將自己置身于文本之外,把文本視為他們可以從外部加以客觀審視的對象。這至今仍是許多史學家對待文本的基本態度。
盡管史學家對待文本采取的是像法官審問證人的態度,但畢竟還得理解證據的意義。就此而言,史學家也不能拒絕釋義學的普遍性要求。也就是說,只要事關文本,史學家終究得面臨文本理解和解釋的問題。不過,哲學釋義學不是將文本的理解與解釋視為單純的理智活動,而是一個通過我們的生存實踐完成的活動。文本的意義對我們有實踐要求,它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將它完成。伽達默爾以理解命令為例來說明這個觀點。
命令可以被視為一個文本,所謂理解命令,就是知道它要我們干什么。我們可以通過重復命令來表示我們已然理解了該命令,但是,“其真實意義只是由‘根據其意義’具體執行來規定的”。拒絕命令與執行命令都是對命令意義的確定,都是命令的意義在某人身上的實現。理解命令包括的不僅僅是簡單地在理智上理解命令的意義,而是涉及接受命令者對具體情況的研判和他的責任。命令的意義包括所有這些實踐要素,沒有這些實踐要素,命令的意義是不完整的。所以伽達默爾說:“命令的接受者必須創造性地理解意義。”顯然,這種對意義的理解不是理論理性,而是實踐理性的。它不是一種純粹的認識,而是一種實踐的行為。命令的意義是通過執行或拒絕執行命令得到理解和完成的。
問題是,我們能否把如《中庸》這樣的傳世文本也理解為命令?初看起來,那樣理解是荒謬的,經典文本并沒有命令什么,它們只是要我們理解它們的意義。但如果我們不是把它們的意義理解為不依賴讀者的理解與解釋而恒久固定了的,而是通過讀者的理解與解釋不斷得到完成,并揭示了一個可能的在世存在模式的話,那么文本就在雙重意義上是命令。首先,它命令它的讀者創造性地理解它,因為它沒有固定不變的意義。其次,更重要的是,讀者必須通過自己的在世存在,即從自己的歷史性出發(這是每一個文本解讀者的釋義學處境)來理解和解釋。這種理解和解釋也就是打開自己存在的新的可能性。文本的意義成為我們新的存在境域、新的存在世界,我們在此新的境域,向著新的可能世界存在。只有這樣,我們才真正理解了文本的意義。理解和解釋首先是存在而非主觀認知,文本的意義不是認知的對象,而是我們存在之趨向。
只有當我們不再像古典釋義學那樣狹義地把釋義學理解成正確解讀文本的方法,只有我們突破這樣的習慣性思維,而真正理解釋義學向我們揭示了存在的一種基本樣式,釋義學才能真正在我國哲學研究與其他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中產生革命性的影響,得到廣泛的應用,成為統一哲學與其他人文學科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