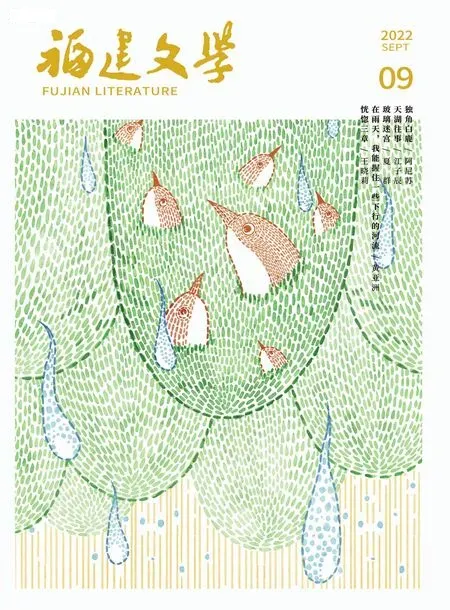《閩韻鄉風》的地理文學書寫
蘇少偉
地理環境、地理空間,是作家們審美視野、文學視界的基礎性的生成背景;而地理文化、地理現象則更為深刻,對作家的深層意識結構的影響更顯著,它是一種多元素的綜合作用,包括傳統文化形成的人文環境的種種因素(歷史、風俗、方言等)。由此可言,“地理”,顯性地構成了作家們的創作因子。具體到八閩大地,它蘊含著豐富的地理信息、地理文化,包括傳統與現代的地理環境,相似又存異的地理空間,豐富而又精致的地理文化,這些引起了很多作家的注意。近些年來,在關注八閩大地的閩籍作家中,林彬是較為出色的一位。他的散文集《閩韻鄉風》對閩地的“地理性”進行了綜合濃縮,以文學性的話語將閩地的典型風格呈現出來,建構了閩地的地理文化特征。
地理文學書寫的一個要點是文本中的語言、材料,需要從生活、歷史中去發掘。鮮活的生活圖景、活潑的歷史感受,構成了作家個人體驗中的兩個活躍因素。這就是說,對很多地理文學書寫來講,站在當代生活角度省思,從歷史厚重感中挖掘地理信息,是一種較為常見的敘事方法。《閩韻鄉風》也有這方面的特點,它的敘述內容、呈現方式反映了一種強烈的當代體驗感和深厚的歷史情懷。這兩種因素的獲得,首要是借重于豐富的歷史文獻,并以此為敘述的基點,來鋪陳對閩地的觀察、書寫。
事實上,閩省歷經千百年歲月,積累了厚實的典章文獻。輿地、民俗、工藝、飲食、建筑……不一而足。要對這些“國故”做出整理、進行呈現,首先靠的是遍覽相關材料。這在《閩韻鄉風》中具有鮮明的體現,它的內容涵蓋了閩地的名山武夷山、戴云山、太姥山、冠豸山等,名江閩江、晉江、九龍江等,文化事業如方言、詩歌、繪畫、工藝、刻書、菜肴,等等。在對這些敘事對象的呈現中,作家援引了豐富的歷史素材進行加工。以“漫說泉州之‘多’”這一章節為剖析對象,我們見到了一種多角度、豐富的呈現:
泉州古建筑中最有地方特色的是泉州民居建筑,尤其是貴族、官僚、富豪、士大夫階層中的文人和畫家,他們的宅第規模可觀,形式講究,其造型、格局、技藝、用材等都蘊含著某個特定時代的文化氣質。其中,有三開間或五開間紅磚白石雙坡曲燕尾脊的漢式古大厝,有“手巾寮”的縱向住宅,有騎樓式的商住合一的建筑,還有與山村環境十分協調的“吊腳樓”(木樓),就地取材,十分簡樸,卻獨具風格。還有一種是外圍護有高大堅固防御墻體,適應大家族集居特殊形式的土樓建筑。中西合璧的住宅稱“洋樓、番仔樓”。千百年來,民風民俗的傳承衍化,使泉州民居建筑自成一派天然風韻。
短短的文字,對泉州的民居建筑進行了一番有聲有色的介紹,注重歷史傳承、歷史之變的同時,也抓住了它的特點,顯示了泉州民居的獨一價值。其實,在論述泉州的“多”時,《閩韻鄉風》還聚焦了它的“小八景”、“十八景”、南音、百戲、木雕、彩塑等,涉及社會、歷史生活中的多個方面,顯示出異常的豐富性。余者,如福州的“脈”、廈門的“開”、漳州的“精神”,漫說“八姓入閩”、方言、詩歌、繪畫、工藝、刻書、菜肴等,均帶有這種敘事傾向。通概而言,《閩韻鄉風》的全部文本內容都明顯具備這一種寫作特色。也基于此,我們說《閩韻鄉風》的內容多且實、繁且精,材料基礎扎實。在多方面的敘事中,我們也感受到了作家對多樣態生活的接受和開放性視界的呈現。
從豐富的歷史文獻里,《閩韻鄉風》還生發出一個非常顯性的特點:識見,即不黏著于材料本身,而從歷史材料中生出自己的見解,從而使材料邏輯化。說到這種識見,《閩韻鄉風》一書經常以一個字來捕獲各地的獨特性,把住了一鄉一地最核心的精神內涵。譬如福州是“脈”,廈門是“開”,嵩口是“境”,雙溪是“慧”……這種歷史識見,是本書地理文學書寫的一個重要價值。
看一看《閩韻鄉風》是如何有識見性地凝練、挖掘出鼓浪嶼的獨特之處。在“漫說鼓浪嶼之‘聚’”時,文本道出鼓浪嶼的生成乃是“聚”的力量結果:
“聚落”文化的獨特呈現——“更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礎上為鼓浪嶼貢獻了新穎獨特的‘聚落’文化元素,最終促成了鼓浪嶼歷史國際社區的面貌,這方面集中體現在從華僑洋樓宅院的演進變化,最終產生獨特的廈門裝飾風格建筑。”
“聚合”文化的獨到呈現——“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說鼓浪嶼在整體上是以‘聚落’文化的形態展示在世人面前,那么鼓浪嶼在微觀上則以‘聚合’文化的形態供世人欣賞。”
“聚薈”文化的獨辟呈現——“從某種意義上講,鼓浪嶼可以說是一個百花匯聚的園林,是中西合璧式園林‘聚薈’文化的呈現。”
“聚聲”文化的獨一呈現——“為此,鼓浪嶼天然的‘聚聲’環境和后天形成的獨有的音樂文化底蘊,成就了鼓浪嶼‘琴島’‘音樂之島’的雅稱。”
“聚心”文化的獨樹呈現——“這種魅力、氣質是在鼓浪嶼特有的人文生態環境中形成的,也只有這種獨樹一幟的人文生態環境才能鑄就別有風韻的鼓浪嶼文化。”
這些從歷史材料中凝練出的理性認識,豐富了我們的認知。所以,我們說《閩韻鄉風》的歷史感、生活性是十分明白的。文學畢竟是語言的藝術,地理文學書寫也非常注重語言的獨具匠心的運用,語言部件、語言表達是地理文學書寫的“外殼”。“審美對象化”這個理論研究式的表述,從一定程度上說,也包含著地理文學語言的獨特運用。
語言,靈動地決定了作家的地理創作特色、文學含義、藝術高度。具體到《閩韻鄉風》,它將個人的語言習慣、文化氣質,與閩地豐富的材料進行有效融合。可以說,論到“語言”,觸及的就是《閩韻鄉風》的鮮明的文本特點。有三種語言風格深刻地體現在這本書中:精練、整飭、細密。
論“精練”,一段時間以來的閩地地理文學書寫,似乎均不及《閩韻鄉風》。這個文本,全篇都重在以精練的詞匯(有時候甚至是一個字)來抓住一地的地理個性、一地的文化精髓。就以“漫說武夷山”這個篇章為例,武夷山是有代表性的,因為武夷山之美、武夷山之韻,閩地的人大多眼見耳聞,但能對之進行概括、提煉,而又提煉到何種程度,大概也是作家們的一個寫作挑戰。在這方面,《閩韻鄉風》詳細地提煉出武夷山的幾個“然”。它先講出武夷山的地形、地勢、關口等“自然”,此為介紹自然地理風光:
東坡舒緩,有層級地形發育;西坡陡峻,斷崖顯著。在武夷山脈中有許多與山脈走向相直交或斜交的埡口,古稱“關”“隘”“口”,是重要的交通通道和軍事要沖,如浦城與江山之間的楓嶺關、武夷山市與鉛山之間的分水關、光澤與資溪之間的鐵牛關、建寧與廣昌之間的甘家隘、長汀與瑞金之間的古城口和武平與尋烏之間的樹巖隘等。
武夷山這種“簡單”的地理景觀背后,是一種深刻的“地理精神”。因此,《閩韻鄉風》繼續發揮出武夷山的另外幾個“然”:傲然、沛然、天然、悠然、肅然。“傲然”這一點,主要講出武夷山“傲”的緣由:無諸、朱熹,以及吟詠武夷的歷代文人,為武夷山增加了文化底蘊的“傲氣”——“歷代文人騷客偏愛武夷山的情致總是躍然于筆端,流傳于山水之間,不僅給武夷山留下了一份份彌足珍貴的瑰麗篇章,而且使武夷山匯集的眾多之美更加‘傲然’于世。”
“漫說武夷山”的最后點出了武夷山的“肅然”,詳細介紹了武夷是儒釋道的“三教名山”,以此增添“肅然”的氣氛,足見武夷山的歷史文化之厚重。至此,我們看到的“自然、傲然、沛然、天然、悠然、肅然”,都是以簡潔精練的詞匯對一個地方(武夷山)做整體上的價值提煉,并恰當地抓住了其社會、歷史、生活寄寓在地理上的精髓。
在《閩韻鄉風》中,這種寫作風格很強烈,很容易再現。如,莆田的“化”是“興化而名”“教化而厚”“神化而安”“文化而潤”“造化而達”;嵩口之“境”是一種豐富的“場境”“語境”“化境”……這些都是精練的詞匯表達,都有簡潔明了的特點。然而,再細細品味,我們還可以看出作者對一種語言習慣的偏好,即擅長運用整飭的語匯結構來進行表述。
其實,這種語言風格并不是突然出現,作者的上一本作品《脈動鄉土福州》中就已顯露出他對這種語言結構的熟練運用。在這本書中,作者以“水脈”閩江為贊嘆對象時,特別強調了它“之于福州是‘源遠流長’的”“之于福州是‘生生不息’的”“之于福州是‘母愛綿綿’的”“之于福州是‘廣澤福祉’的”“之于福州是‘文化使命’的”;“文脈”這一章中說三坊七巷“神”之所在時,指出它具有“神明的文脈”“神奇的文化”“神妙的文物”“神韻的文教”“神采的文豪”“神往的文雅”“神品的文墨”……
《閩韻鄉風》是對這種語言風格的繼續深化。我們可認為,這種整飭的話語結構是一種有意為之且充滿審美個性的文學行為。在遣詞造句之間,整齊的句式之用,構造出浩蕩的文氣,也體現出多重的文字張力、情感張力。
在精練、整飭的語言風格之下,《閩韻鄉風》沒有使人形成一種抽象甚至縹緲的閱讀觀感,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文本還有一個特別的語言建構手段——“細密”,即反復吟詠、多重論述,造成一種綿密、優美的表達效果。仍以“漫說武夷山”中的“悠然”這一點為例:
人坐筏上,全方位地沉浸在碧水丹山之中,無噪音、無污染,抬頭可見山景,俯首可觀水色,側耳能聽溪聲,伸手能觸清波,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剛柔相濟,悄然間就會生出“悠然見南山”的憧憬與夢幻。坐筏觀山,極目皆圖畫,丹山、碧水、綠樹、藍天、白云相映成趣,呈現出武夷山大自然五彩繽紛的色彩美。沿途看到奇峰相疊、嵌空而立,那高低相錯的山巒,如旌旗招展,那氣勢磅礴的巖峰,如萬馬奔騰,展示了大自然中極富韻味的參差美……
短短文字中,就有細致的景觀鋪陳、細膩的心理感受、細微的景物辨別,更寫出了山、水、石各自的特點。其文學審美趣味,極素雅、極自然,整體上看來又展露出強烈的文學藝術色彩:凝練、傳神,時而雄渾,時而又沖淡。所以,我們閱讀后,能得到一種細膩的審美感受。
通篇而言,《閩韻鄉風》以獨特的語言系統,精細地呈現了閩地的百態生活,挖掘了閩地的千年歷史和豐厚的文化,形塑了閩地的地方個性,讓我們品味到了閩地的鄉土之美好、歷史之厚重和文化之絢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