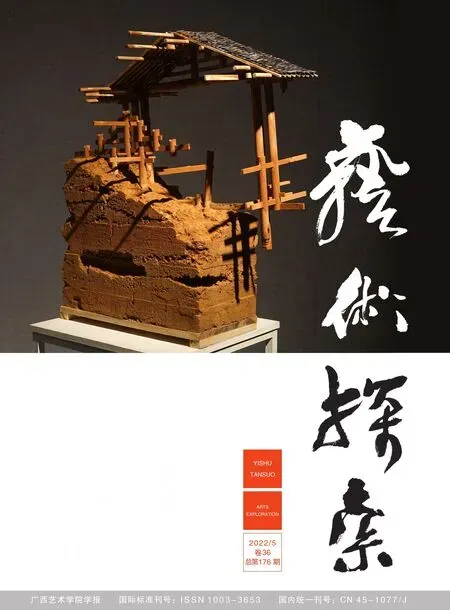元代繪畫風格與畫家身份、心態研究
李晨輝
(廣西藝術學院 學報編輯部,廣西 南寧 530022)
唐宋以來,身份逐漸成為論者評判繪畫高下的參照。其意義在于,繪畫逐漸掙脫政教,它所呈現的趣味、風格甚至手法都更緊密地同畫家的經歷、人格、修養等私人話語相聯系,以畫抒懷的繪畫功能也逐漸使繪畫成為像詩歌一樣的文人藝術。朱景玄《唐朝名畫錄》中便在神、妙、能三品之外另設逸品,著錄并贊美游于規矩之外的王墨、李靈省和張志和:“三人非畫之本法,故目之為逸品,蓋前古未之有也”。北宋后期,供奉宮廷的職業畫家已經建立了完善的法度,新的風格必須從對院體繪畫體系的突破中才能得以實現,故此時對畫家身份的強調更多表現為對“畫工”或“眾工”的批判。蘇軾提出“士人畫”的概念,以區別于“畫工”。郭若虛《圖畫見聞志》繼承了這一觀點,并進一步將“士人”身份細化為“軒冕才賢”和“巖穴上士”:“竊觀自古奇跡,多是軒冕才賢,巖穴上士。依仁游藝,探賾鉤深,高雅之情,一寄于畫。……凡畫,必周氣韻,方號世珍。不爾,雖竭巧思,止同眾工之事,雖曰畫而非畫”。南宋鄧椿《畫繼》直以畫家身份作為編目的依據,其中便包含以蘇軾、李公麟、米芾等為代表的“軒冕才賢”,以林生、李甲、江參等為代表的“巖穴上士”,另設《圣藝》篇錄趙佶,《侯王貴戚》篇錄趙令穰、趙伯駒、王詵等,《縉紳韋布》篇錄劉明復、鄢陵王主簿、揚補之等,以及《道人衲子》《世胄婦女》等篇。北宋后期至南宋、金朝的文人事繪,并非像魏晉南北朝的畫家那樣規范技巧,增飾華美流麗的作風,而是進行了新的水墨實驗,將水墨作為新的造型基礎。對“形似”或技巧的輕視,實為對抗成熟的院體風格和繁復的手法。宋金文人通過實驗簡淡、天真的形式(“墨戲”),初步將繪畫同詩歌和書法聯系起來。而三者的深度融合,則是有元一代的文人畫家完成的。
元朝國祚不足百年,對峙的朝廷和割據的勢力重新熔鑄于以大都為政治核心的大一統政權中來,文人畫家的構成似乎也比他時更為復雜。他們之中既有由金入元的遺民,也有由宋入元的遺民,既有歸于林泉的真正隱士,也有渴慕林泉卻不得歸去的官員。不同的經歷、身份和心態,影響著他們對傳統和手法的選擇,以及對不同風格的實踐。本文試圖從身份和心態的角度,歸納元代繪畫風格如何從宋金藝術的土壤中生成,又如何矯正甚至批判宋金藝術。所論多為文人畫家,也涉及一些宮廷畫家。鑒于元初畫家對元代繪畫風格的奠基作用,本文的研究對象以元初畫壇為主。
一、宋金遺民:托物言志和以書入畫
(一)金朝遺民的宋金傳統
金初的宋朝遺民沒有元代遺民那么復雜的構成。入金的兩宋文士在民族認同方面,“即使接受金政權,也是帶著抗拒的矛盾心理去接受。有的無所作為,詩酒唱酬,排解郁悶,這是一種無聲的抗拒;積極作為者也表現出另一種形式的抗拒,如宇文虛,他努力地變革女真社會,極力地把中原王朝的典章制度植入女真社會,這是以變革的方式、從內部抗拒女真社會”。而南宋和金朝的文士入元之后,對新王朝的態度則呈現出較大的區別,兩個群體的內部也存在一些微妙的差異。“與南宋遺民相比,北方金遺民們的心態相對要平和一些,對金王室、金王朝的感情也比南宋遺民對南宋王室的感情要淡得多。……當天下逐漸安定后,他們也就漸漸適應了這種安定,并且還似乎慶幸于這種安定……有的作品中還充分流露出對于新王朝的贊頌之意和天下一統的自豪感。”不同的心態,加之北方和南方不盡相同的文化傳統,影響了兩個遺民群體對繪畫題材、手法、趣味和功能的選擇。
例如金朝遺民何澄,入元之后,“是以畫獲貴得福的,一個對漢文化了解不多的朝廷,能對一個畫人如此恩寵有加,何澄自是感恩不盡,所以退休后還以九十歲高齡再度獻藝。說何澄希望大元帝國國祚永葆是不錯的”。他的《歸莊圖》描繪了陶淵明歸園田居的主題,作品以勾染為能事,勾線剛勁,而較少圓潤的彈性,尤重輪廓線的粗重勾勒,染法卻是簡率,常以飽滿的淡墨作大塊面的渲染,有溟濛浩渺的效果。樹的畫法有拖枝的痕跡,也有一些北宋畫法,樹葉的勾點頗為放逸粗獷,人物造型則多南宋意味。其用筆強調一定的變化,但仍過于粗放。此作融匯了文人偏愛的高雅主題、民間的樸實畫風和宮廷的趣味,筆法更多承襲南宋院體,也參照了一些北宋山水樹石之法,當然也有時風的痕跡。多種傳統的交匯,顯示了宮廷畫家豐富的技巧,對明代宮廷人物畫的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與何澄類似,劉貫道也是由金入元的遺民,曾供奉于宮廷。《圖繪寶鑒》記載他:“工畫道釋人物,鳥獸花竹,一一師古,集諸家之長,故尤高出時輩。亦擅山水,宗郭熙,佳處逼真。”他的《消夏圖》也塑造了一名文士的形象。重屏和人物的姿態,讓人聯想到周文矩、王齊瀚、孫位的作品,甚至更遙遠的《北齊校書圖》。他的線條卻與上述作品大異其趣,他運筆較快,甚至忽作凌厲的轉折,筆勢起伏跌宕,釘頭鼠尾的用筆尤顯得尖利。這種筆法既不同于吳道子,又不同于李公麟,而是南宋李唐、馬遠等院體的遺風。
郝經則呈現出金朝遺民畫家的另一種風格選擇。郝經屬文人官員,有著建功立業的進取心,他對元朝不僅沒有對抗,還期望能在新王朝實現政治和文學藝術上的理想。如其詩《老馬》云:“百戰歸來力不任,消磨神駿老骎骎。垂頭自惜千金骨,伏櫪仍存萬里心。歲月淹延官路杳,風塵荏苒塞垣深。短歌聲斷銀壺缺,常記當年烈士吟。”文論《文弊解》云:“方今道喪時弊,正氣湮塞,生民墜溺,志士振起之秋也。”可見郝經并未受到當時所謂“華夷之辯”的過多束縛,在文學藝術方面也有堅守正統以矯正時弊的愿望和氣魄。他進入了元朝上層官僚體系,并對宮廷繪畫產生了一定的影響。華彬認為,郝經的作品屬于金宋文人畫體系,其“書法繪畫氣韻高古,俊逸遒勁,全無嫵媚之姿,被推為‘當代名筆’,可惜已無真跡流傳”。我們推測,他應繼承了北宋和金代的文人畫傳統。
由以上幾位元初畫家的創作可知,元初的宮廷繪畫實際上融匯了南宋院體畫風、宋金的文人畫風及在文士中流行的高雅主題。之后,元代宮廷繪畫又逐漸受到統治者好尚、元代文人畫風和宗教主題的影響,至王振鵬,形成了典型的宮廷風格,畫面的躁動之氣逐漸消減。
(二)南宋遺民的文人畫
與金朝遺民相比,南宋遺民表現出對新王朝更為強烈的抗拒,以及更加復雜的風格選擇。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追憶了南渡前后的文人畫家。鄭思肖效法揚補之,用北宋后期以來的四君子題材寄托遺民的亡國之痛,以繪畫的形象表達激烈的遺民情緒。筆無空發,皆為言志。這實際上是對文人畫內涵的充實和發展。托物言志的繪畫功能,在他的筆下,要比前代更加明朗,并借由遺民群體,形成更廣泛的影響。
自蘇軾等提出“士人畫”理論,文人便努力搭建繪畫和詩歌之間的橋梁。宋代便有所謂“無聲詩”的說法:“畫是無聲詩,此說至宋代最勝,甚且有徑以無聲詩為畫之別號者。如蘇軾《韓幹馬》詩云‘韓幹丹青不語詩’,黃庭堅《次韻子瞻題〈憩寂圖〉》詩云‘李侯有句不肯吐,淡墨寫出無聲詩’,又《題〈陽關圖〉》詩云‘畫出無聲更斷腸’……未易僂指而數。”蘇軾以王維的詩畫作例,提出“詩中有畫”和“畫中有詩”的主張。然而這時關于繪畫與詩歌的聯系,更多是從二者相似或相通的境界而言,還未從繪畫本體的角度,落實在可操作的技術手法之上。其時的作品具備了文人畫的風范,基礎的造型手段卻仍化自院體花卉,且尤喜營造詩歌一般的優雅境界,如文同的竹子清影搖曳,揚補之的梅花暗香浮動,趙孟堅的水仙花葉婆娑。兩宋之際至南宋,誕生了一批擅畫四君子題材的文人畫家,但在南宋一代,他們的創作都未成為主流。新的風格要靠元代畫家尤其是南宋遺民畫家來完成。鄭思肖、龔開等一批遺民,滿腹的牢騷和難以排遣的抑郁“一寄于畫”。鄭思肖畫蘭不畫土,隱喻家國之思,龔開用瘦骨嶙峋的駿馬,感嘆志士懷才不遇。龔開的《中山出游圖》同樣有所寄托,盡管較為曲折隱晦:“表面上以鐘馗及其妹出游為題材,在自題詩中則用安史之亂故事,隱含了世事變遷,有志難伸的意思,他說:‘道逢驛舍須少憩,古屋無人供酒食,赤幘烏衫固可烹,美人清血終難得,不如歸隱中山釀,一醉三年萬緣息,卻愁有物覷高明,八姨豪買他人宅,侍□君醒為掃除,馬嵬金馱去無跡。’然后又似《駿骨圖》一樣,故意對戲筆‘墨鬼’此類題材發一番議論,謂:‘鐘馗事絕少,仆前后為詩,未免重用,今即他事成篇,聊出新意焉。’以掩飾原意。”南宋遺民畫家賦予繪畫言志的功能,元季倪瓚正是在此基礎上融合隱逸文化,將遺民之“志”轉化為高士之“逸”,提出了“逸氣說”。至此,繪畫像詩歌一樣具有了言志和抒懷的功能,成為像詩歌一樣的文人藝術。
繪畫功能的轉變只是文人化的一個方面,元初,遺民畫家還改造了舊有的繪畫形式,使之符合文人的書寫習慣。其中最有成效的探索當屬趙孟頫的“書畫本來同”。關于繪畫和書法的關系,前人已有論述涉及“用筆”“筆法”“書畫用筆同法”,趙孟頫所做的,不是簡單類比書與畫的形態,而是將書法筆意轉化為畫法,落實到創作的本體,并形成范式。在趙孟頫的倡導和影響之下,大量不同身份的畫家參與到這場筆法和造型關系的實驗之中,促成元代畫壇梅蘭竹菊和墨花墨禽蔚為壯觀的創作局面,北宋后期以來的文人畫才真正突破院體繩墨,成為主流的創作方式,并逐漸形成大異于院體的手法和風貌。值得提出的是,元初李衎的竹子仍然較多承續了南宋院體勾填及全景式的傳統,他似乎并未像趙孟頫那樣去嘗試書法的筆意,而是注重竹子在不同時節、不同環境之下的自然情狀,具有寫真的趣味。
元代的遺民畫家一方面因襲宋金的院體傳統,一方面加強繪畫和詩歌、書法的聯系,使繪畫不僅具有詩歌的境界,也具有了詩歌的功能,成為同詩歌一樣的高雅藝術形式,同時,書法筆意的引入和向畫法的轉換,為文人畫的表達找到了更豐富的表現形式。正因此,筆意、筆法才逐漸成為具有表現性的造型手段,并成為元代繪畫風格形成的重要依據。
二、仕隱之間:矯正時弊和托古改制
南方的宋遺民多有歸隱之想,當然也有趙孟頫、任仁發等投仕新朝的文人畫家。關于趙孟頫改節仕元后的心態,陳傳席在《中國山水畫史》中有較詳細的闡述:“趙孟頫本人既希望發揮自己的才干,又不希望出仕元朝,最后半推半就做了元朝的官”,“他的一生可用‘矛盾、痛苦、悔恨、委屈’八字來概括……痛苦極了”。陳傳席認為,趙孟頫批判南宋和推崇古意,與他改仕新朝的經歷密切相關:“趙孟頫以一個宋室王孫的身份‘被遇五朝’,表現了他在政治上極端謹慎態度。……金及南宋均為元所滅。批判南宋(趙稱為‘近世’)是一種‘保險’的態度,宣揚南宋就有可能惹麻煩”。但實際上,如前所述,金朝遺民不乏入大都侍奉宮廷的文人畫家和職業畫家,他們的作品并未回避金朝和南宋的傳統,何澄還受到了元朝統治者的褒獎,甚至被獎授官職。趙孟頫雖極力保持與南宋繪畫尤其是院體的距離,其詩歌卻無法割裂與南宋的聯系,甚至其古意說也有可能脫胎于南宋以來的文學理論:“就繪畫思想而言,古意論是自南宋晚期以來,由文論中的古意論,滲透到畫論中的一股思潮。這種思潮在南宋表現得還不是非常明顯。至元初始因趙孟頫等人強調繪畫‘古意’為人注意”。同時,他在詩文集中也并不規避仕元之后的心路歷程。而據陶然等對趙孟頫文學的研究,趙孟頫應征入仕,“既非強迫,則可見其用世之志;既非首選,則進京后所受恩遇,足以對他產生較大的心理影響,進一步激發其參政意識”,“現存記載中,未見趙孟頫有任何拒絕程鉅夫此次征聘或猶豫遷延的記錄。因此趙孟頫出仕主要與其自身的用世追求有關”。陶然等認為,趙孟頫在詩文中述及仕元,有“捉來官府”“誤落塵網”“詔舉遺民”和“擢自布衣”四種“敘述方式或解釋模式”。而這四種方式“與當時特定的現實處境、心理感受均有密切聯系。……當他境遇不順利時,自然就傾向于從被迫或自悔的角度來解釋自己的出仕,而當他功成名就之后,就可以相對比較得意地說自己是‘擢自布衣’了”,這也是“趙孟頫在追憶中的一種自我美化和強化。……其潛在意圖是以符合傳統觀念的做法自飾,并且不斷地加以強化,以期避免自我心靈的痛苦拷問,獲取心理平衡,力求徹底消解心理矛盾”。
因此,趙孟頫拋棄南宋傳統,轉向五代、遠溯晉唐的“復古說”,與其仕元并無太必然的聯系。趙孟頫矛盾心態的披露,于其詩中似乎更為鮮明。他在《次韻舜舉四慕詩》中說:“去之千載下,淵明亦其人。歸來北窗里,勢屈道自伸。仕止固有時,四子乃不泯。”仕隱的沖突就像一道藩籬,趙孟頫無法沖破,他只能徘徊于仕進以濟世和隱退而遁世之間,既不能像任仁發那樣積極地奔走于政務,又不能像錢選那樣瀟灑地隱跡于山林,既要浮沉于宦海,又渴望悠游于林泉。
類似的心態還表現在元初另一位畫家高克恭的身上。高克恭仕途順暢,身居顯要,頗有政績,但也常常表達隱逸之思。高克恭不存在趙孟頫那種因仕元而致的心理沖突,對隱逸的渴慕顯得平和而從容,既不強烈,也不矯飾,如其《贈英上人》詩云:“為愛吟詩懶坐禪,五湖歸買釣魚船。他時若覓云蹤跡,不是梅邊即水邊”。
兩人均選擇了董源的傳統。趙孟頫將董源風格作為復興的依據,目的便是要通過更古老的繪畫傳統,構建適合文人書法筆意表達的繪畫形式,其深層驅動力應和金朝遺民郝經所期望的一樣,即矯正時弊——南宋以來“創造力低下、追求新奇,而實際上是名利之爭所致的風氣”。
趙孟頫首先擷取了董源平遠的山水空間,而拋棄北宋以來的繁山復水,更不用南宋形式主義的一山半水,他甚至解構了董源山體的茂密幽深,把主山布于更“遠”的位置,并以極盡簡淡的形式,將畫面向兩側延伸。煙波悠遠,畫意無限。
其次,趙孟頫將董源以線條為基礎的皴法發展為新的形式。趙孟頫的披麻皴不同于董源,他大大削弱了染法,把由書法用筆轉換而來的線條提升至造型最重要、最根本的位置,枯淡而蒼潤的線條蜿蜒開來,相互交織映襯,既構成山體,也具有了獨立的審美趣味——畫面所呈現的風格,很大程度上受到線條質感的影響。由此,趙孟頫構建了一種新的風格,它與董源有關,卻又完全不是董源的。趙孟頫用線條皴矯正南宋塊面感強烈且常露鋒芒的斧劈皴,同時也對北宋以勾染為基石的山水畫提出挑戰。書法轉換為畫法,激活了線條在造型方面的無限可能,引發了之后一系列關于皴法的探索。其后的元四家,有悠長華麗的披麻皴,也有穩健華滋的披麻皴,有簡括的折帶皴,也有繁密的牛毛皴,這些無不是趙孟頫解放線條的產物。
再次,趙孟頫選擇董源,實與高克恭一樣,借平靜淡遠的江南山水,構建理想的隱逸之境。其《題董元(源)溪岸圖》詩云:“石林何蒼蒼,油云出其下。山高蔽白日,陰晦復多雨。窈窕溪谷中,邅回入洲溆。冥冥猿狖居,漠漠鳧雁聚。幽居彼誰子,孰與玩芳草?因之一長謠,商聲振林莽。”或許對趙孟頫來說,以詩歌披露心跡,到底不如“畫象布色”“臥以游之”能獲得更多的心理慰藉。其后的整個元代,很大程度上,主流山水畫創作的主題選擇都與隱逸文化結合了起來,如朱德潤《松溪釣艇圖》、唐棣的《霜浦歸漁圖》、盛懋的《秋江待渡圖》、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吳鎮的《漁父圖》、倪瓚的《漁莊秋霽圖》、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圖》等。正如韋賓所說:“在元中后期……復古思想則轉向與隱逸文化合流。”
同是南宋遺民也同仕元的任仁發則與趙孟頫有很大差異。這位出身寒微的官員在新的王朝主要奔波于地方,疏浚河道,興修水利,有《浙西水利議答錄》。他的繪畫也有復古的傾向,其《二馬圖》圓潤流暢的線條和精勻細膩的設色,具有唐宋時的風范。他以二馬肥瘠隱喻士的廉濫,使得他的藝術帶上了文人畫的趣味。有趣的是,像北方金朝遺民畫家一樣,他并沒有拋棄南宋之法,如其花鳥畫《秋水鳧鷺圖》,手法和趣味均沿襲南宋院體,尤其是前景大石,運用了南宋常見的斧劈皴。任仁發的作品,實際上反映了在文人話語日益增強的情勢下院體繪畫所做出的改變。
而真正實現宋代院體花鳥畫向元畫轉變的是錢選。錢選在入元之后就做了隱士,“但他又不像鄭思肖那樣具有強烈的反元情緒與行為,而是潛心研究繪畫藝術,以至終老”。“錢選的思想幾乎沉浸在淡泊寧靜之中,但南宋之‘興廢’事偶爾也叩擊他的心房,他的《梨花圖》卷題詩傾述了他的思宋之情”,畫面題詩云:“寂寞闌干淚滿枝, 洗妝猶帶舊風姿。閉門夜雨空愁思,不似金波欲暗時”。
錢選并未完全拋棄院體傳統,其花鳥畫化出于兩宋院體,具有院體所擅長的折枝形式和較微觀的視角,以及勾描設色的基本程式,觀察精細入微,作風精工細致。“錢選的繪畫,仍然沿襲了‘近世’也即‘宋季’畫院‘畫史’的精微作風,顯得‘精巧’有余”而‘遒勁’不足。盡管錢選本人的身份是文人,也盡管他的畫風與一般的‘畫史恒事’有所不同,而是在精微之中多少摻入了一些士氣,但對于文人畫的要求來說,無疑還是不能滿足的。因此,不僅遭到了趙孟頫的委婉批評,即在明代董其昌的《畫禪室隨筆》中,對之也不無微詞。”但錢選并非僅僅“在精微之中多少摻入了一些士氣”而已,他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重要的時代意義,他的花鳥畫脫胎于院體,更是對院體的反叛。兩宋院體尤其是南宋院體花鳥畫具有較為強烈的生活化氣息,色彩或沉穩樸實,或鮮艷明亮,民間的世俗趣味和宮廷的裝飾趣味相融合。從五代綿延至南宋的“寫生”觀念,強調的是物象細致入微的真實感。跟宋人不同,錢選的作品并不基于真實,而是在形式構造中刪繁就簡,尋找簡括的表達,從結構、圖式、趣味等方面都對院體進行了總結、整合及改造。他采用更簡單的形式和程式,營造了更符合文人的典雅、清麗、含蓄的趣味。如《桃枝松鼠圖》卷,畫中兩枝桃枝在畫面下端偏左的位置分別向右上和左上舒展,右向的桃枝沿對角線作S狀盤旋,松鼠的身體和尾巴分別跟兩枝桃枝的方向保持同步,并在畫面上半部,與桃枝共同圍成臥倒的C形。桃葉桃實則沿構圖線作正反偃仰和穿插交搭,顯得虛實有致。畫面布局可謂氣息悠長,同時又呈內斂之勢。
跟花鳥畫相類,其山水畫也呈現出形式概括的特點。或受到趙孟頫復古說的影響,他回歸了古老的青綠傳統,一些樹木的造型甚至與傳為李思訓的《江帆樓閣圖》有著一定的聯系。如《幽居圖》卷,畫青山幾座浮于清波之上,煙嵐隱于遠山之前,有江舟閑云和茅屋小橋。他采用了新穎的用筆方式,而非李思訓青綠一派,盡管多方折造型,卻不露鋒芒,線條挺括整齊,頗含溫潤,收筆處則細勁飄逸。錢選沒有采用趙孟頫等所倡導的線條皴,他對山石的塑造有著醒目的結構感,形式簡括,設色沉著。
對錢選來說,線條呈現出更強的抒情性質,而非像兩宋院體那樣與造型緊密相連,這與趙孟頫是一致的。在兩宋院體中,線條作為形象質感呈現的手段,帶有不同的趣味,形成了不同的筆法,但所有線條都與形象相關,造型選擇線條。在錢選的花鳥畫中,造型隨筆而行,線條引領造型。有時為了筆意的表達,他甚至舍棄了一些宋代花鳥畫中常出現的細碎的小筆觸(造型的細節)以及較厚的設色。這在他的《牡丹圖》卷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因此,錢選并不是簡單地將文人情趣注入兩宋院體花鳥畫之中,同趙孟頫相似,他致力于一種新的造型理念和手法,這恰恰是對院體的背離,當然也是對時弊的矯正。在他之后的墨花墨禽,如王淵、邊魯、盛昌年等畫家的作品,以墨代色,或工或放,都是探尋院體風格轉化的嘗試,這有趙孟頫的倡導之功,當然也有錢選的垂范之勞。
結語
從兩宋至元代是中國繪畫風格轉捩的重要時期,文人群體掌控了繪畫話語權,決定了繪畫發展的方向。尤其是在元初畫壇,宋金遺民,官員和隱士,不同身份的文人借畫言志,托古改制,從功能、形式和手法等各個方面矯正南宋以來的“時弊”,實現了宋畫向文人畫的轉變,繪畫從此成為文人群體抒懷寄情的重要形式,就像詩歌一樣。同時,元初畫家對隱逸的踐行和向往,奠定了元代繪畫主題的基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