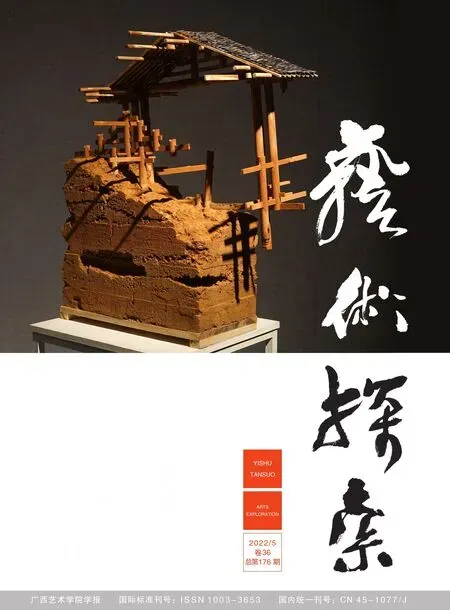蓮子破生門:從克孜爾到敦煌的摩尼珠辨義
張 強
(四川美術學院 當代視覺藝術研究院,重慶 401331)
一、摩尼珠的含義及視覺史的經驗衍化
關于“摩尼”這個概念,佛經里面多有描述。《佛學大辭典·如意摩尼》條云:
摩尼者,梵語Mani,珠寶之總名,即如意珠也。《探玄記·二》曰:“摩尼是珠寶通名,簡通取別故云如意摩尼。”
摩尼珠其實就是通常所謂“如意珠”:
Mani又作末尼,譯曰珠、寶、離垢、如意珠,珠之總名,《玄應音義·一》曰:“摩尼,珠之總名也。”同二十三曰:“末尼,亦云摩尼。此云寶珠,謂珠之總名也。”《慧苑音義·上》曰:“摩尼,正云末尼。末謂末羅,此云垢也,尼謂離也,謂此寶光凈不為垢穢所染也。”又云:“末尼此曰增長,謂有此寶處,必增其威德,舊翻為如意、隨意等,逐義譯也。”《仁王經·良賁疏·下·三》曰:“梵云摩尼,此翻為寶,順舊譯也。新云末尼,具足當云震跺摩尼。此云思惟寶,會意翻云如意寶珠,隨意所求皆滿足故。”《圓覺大鈔·一·下》曰:“摩尼,此云如意。”《涅槃經·九》曰:“摩尼珠,投之濁水,水即為清。”
首先,摩尼本身是音譯,曾經叫作“末尼”,是寶珠的總名稱;其次,末是垢,尼是離,末尼(摩尼)即離垢,清凈不染;再次,摩尼可增加威德;第四,因為是思維寶,所以它能夠滿足各種欲求;第五,它具有凈化功能,投放于濁水能使其變清澈。
摩尼珠又被稱為“如意珠”,其意義也得到拓展:
從寶珠出種種所求如意,故名如意,出自龍王或摩竭魚之腦中,或佛舍利所變成,《智度論·十》曰:“如意珠,生自佛舍利,若法度盡時,諸舍利皆變為如意珠,譬如過千歲水化為頗梨珠。”同三十五曰:“如菩薩先為國王太子,見閻浮提人貧窮,欲求如意珠。至龍王宮……龍即與珠,是如意珠能雨一由旬。”同五十九曰:“有人言,此寶珠從龍王腦中出。人得此珠毒不能害,入火不能燒,有如是等功德。有人言,是帝釋所執金剛,用與阿修戰時碎落閻浮提。有人言,諸過去久遠佛舍利,法既滅盡,舍利變成此珠,以益眾生。有人言,眾生福德因緣故,自然有此珠。譬如罪因緣故,地獄中自然有治罪之器。此寶名如意,無有定色,清徹輕妙,四天下物皆悉照見。是寶常能出一切寶物,衣服飲食隨意所欲,盡能與之。”《雜寶藏經·六》曰:“佛言,此珠摩竭大魚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剛堅也。”《觀佛三昧經·一》曰:“金翅鳥肉心為如意珠。”《往生論·注·下》曰:“諸佛入涅槃時,以方便力留碎身舍利,以福眾生。眾生福盡,此舍利變為摩尼如意寶珠。此珠多在大海中,大龍王以為首飾。若轉輪圣王出世,以慈悲方便能得此珠,于閻浮提作大饒益。”
從這段文獻可以看出,如意寶珠的來源有六:一為龍王腦中;二為摩竭魚腦中;三為佛舍利所變;四為金翅鳥的肉心;五為帝釋所執金剛在戰爭中碎裂;六為“德因緣”。
其中,關于佛舍利的來源有五種情況,一是“法既盡滅”,舍利變為如意珠;二是過千歲水化為如意珠;三是因為可以滿足祈求者的心愿而化為如意珠;四是作為龍王首飾;五是轉輪圣王出世,以慈悲獲得。關于龍王腦中的來源,一是如意珠可以由龍王自取,有下雨功能;二是得此珠者被下毒也不受侵害;三是持此珠可以辟火。關于摩竭魚腦中的來源,此珠有金剛之堅。關于德因緣的來源,一是沒有具體的色彩;二是輕妙如羽,清澈似冰;三是可以顯見天下之物;四是能變化出來一切寶物;五是一切生活用度的需求和愿望,都可以通過此珠得到滿足。
《增一阿含經》卷第三十三:“世尊告曰:‘于是,比丘!轉輪圣王出現世時,是時珠寶從東方來,而有八角,四面有火光,長一尺六寸。”這是對珠寶形狀的描述——一個柱形水晶體,可以反射光芒。日本學者上原和辨析了摩尼珠在佛教造像中被誤讀的情況:
把克孜爾石窟和云岡石窟相聯系在一起的,表現著絲綢之路內陸風土特色的還有水晶形摩尼(梵語mani)。摩尼在漢譯佛經中解釋為如意,即滿足人們心愿的不可思議的寶石之意。通常稱為摩尼寶珠。而最初摩尼寶珠在漢人的印象中是像貝殼中的珍珠那樣的珠子形。是海產的寶物,所以在臨近大海的南朝進入了梁代,還出現了奉持摩尼寶珠的觀音菩薩像。
可是在龜茲國,克孜爾石窟第 38窟的穹廬天井右側所見的摩尼卻不是珠子形,而是作為寶石,表現為長方六角形的水晶形狀。在云岡石窟,同樣的水晶形摩尼在第17 窟南壁拱門上部的供養臺上,由奏樂的飛天奉持,同窟的天井也是有飛天圍繞的摩尼。在敦煌莫高窟,北魏第431 窟天井、西魏第249 窟頂東面、西魏第285 窟頂東面與南面,也都有水晶形摩尼寶珠。可是這種從西域傳來的可以說是“胡風”的水晶形摩尼,迄今為止的學者都沒有加以區別而通稱為“摩尼寶珠”。值得注意的是水晶形摩尼在龍門石窟賓陽中洞的脅侍菩薩頭部(東京國立博物館藏)、蓮花洞脅侍菩薩頭部都可以看到。
然而,摩尼珠被闡釋為“圓形的寶珠”,并不僅僅是“寶石圓珠”的緣故,還因為它同一個花卉體系連接在一起,這就是蓮花的視覺敘述系統。它同時保留著六角形式,并被賦予另外的意義。
在克孜爾石窟壁畫中,摩尼珠的表現是獨立的。(圖1)

圖1 水生動物裝飾,克孜爾石窟第38窟主室券頂東側壁下皮、西側壁
“38窟主室菱形格壁畫與天宮伎樂壁畫間,繪一橫列水中動物,其中有摩尼寶珠、魚、蛇、鴨、蛤、異獸等,含義不詳。”很顯然,將摩尼珠與水生動物畫在一起,便是要通過視覺形象,講述其源于大海,即龍王與摩羯魚的腦中。
“48窟后室券頂繪散花、執蓋供養飛天。壁上滿繪摩尼寶珠、眾星、花束、彩帛等物。似是表現釋迦死后人天供養的盛大場面。”(圖2)

圖2 伎樂飛天局部,克孜爾石窟第48窟后室券頂
正面描繪摩尼珠,并且顯示與人的關系的有第101窟的貢獻摩尼寶:“坐佛右側為一身作世俗打扮的男子,作供養狀,此似為婆羅門施珠。有一婆羅門,善別如意珠,他將此珠供奉于佛。佛稱:善來比丘。于是婆羅門須發自落,法衣著身,即得羅漢果(參見《雜寶藏經》卷七)。”(圖3)

圖3 菱形格因緣畫局部,克孜爾石窟第101窟主室券頂南側壁
貢獻者雙手上舉至頭部,摩尼珠整體為球形,上面被分割成為方塊狀,有黑、白、藍、綠四色。摩尼珠上部圓形弧線上升出五縷光焰。由于原本渲染的色彩如今已經被氧化為黑色,與人物的面部,手臂成為一樣的色彩,我們也無法揣度其原始色彩了。
通過文獻和克孜爾石窟壁畫圖像,我們以線描的形式,將摩尼珠的形態提取出來,來觀察其造型變化和這種變化的視覺邏輯。(圖4)

圖4 摩尼珠形態線描圖
在圖4中,我們列出了十種形態的摩尼珠:1.圓球混沌狀態;2.圓球,顯露傾斜的橫痕;3.圓球,顯露豎痕;4.長方形立柱;5.兩頭尖的長方形;6.兩頭尖的橫長方體,有紋樣;7.兩頭尖的豎立柱形,或斜立的長方柱體,四面皆有紋樣;8.兩頭尖的橫長方體,有紋樣,與6不同的是,左邊出現樹葉般的三角薄片;9.兩頭尖的橫長方體,有紋樣,與8不同的是,上邊出現呈山字形組合的三片樹葉般三角薄片,下邊出現單片三角薄片;10.堵塞了“透明性”的倒梯形,四面各有一片羽毛般的三角薄片,共計四片。
以上圖像變化依據了“化變”原則。所謂“化變”,是在沒有任何外力影響的情況下所發生的自我演繹性變化。所謂“自我演繹”,指的是在演繹結果之中還有上次衍化的痕跡。
在圖5中,衍化的形態已經呈現出來,并逐漸顯現出不同的方向,而與后世同類主題圖像發生邏輯關聯。1.圓形的核心開始出現,它類似花苞,有承托,有張揚的雙翼。2.中間為橢圓形,里面有兩扇圓形門,周圍張開四個三角形。3.主體為獨立的花葉形,里面有一個稍小的花葉形,橫向有三個格,左側綴著兩層半圓形。4.主體呈一個豎立的兩頭尖長方梭形,左邊是三片橫向的三角形從梭形上生長出來,右邊附一圓弧,左側是三層半圓形。5.主體是一個飛翔的鳥形,雙翅為長三角形,底部有一個三角形,上部有一個半圓形的鈕狀物。6.形式開始朝向復雜發展,左邊的是一個扁圓形,扁圓形左側有三顆圓粒,里面有兩顆圓粒;右邊是兩片上下展開的翅狀形式。7.形式變得更為復雜而趨于組合型,共有三個部分組成:上部是一對羽翅,羽翅中間有圓粒,圓粒外邊有托;中間部分是由鱗狀豎紋與橫向三角紋組成的半圓形;下部是六個豎立的三角形。

圖5 摩尼珠衍化線描圖
視覺形式的梳理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關涉相關的化生、化變的研究。
克孜爾石窟是中國開鑿最早、地理位置最西的大型石窟群,大約開鑿于3世紀,在8—9世紀逐漸停建。圖6、圖7是云岡石窟的兩個圖像,均作于470—494 年這20余年間,與克孜爾石窟第38窟相比,晚了將近半個世紀。
此時最為重要的觀念變化,在于摩尼珠圖像被重新設置了。位置的變動帶來一系列圖像邏輯的改變。在克孜爾石窟的畫面之中漂浮、游弋的摩尼珠,到了云岡石窟則居于正位。但是作為一個神圣的視覺符碼,摩尼珠的形式演變別有意味。
摩尼珠的雙尖梭形結構,來自對透明石頭的觀察。在透視效果下,長方柱形的平面表達,是一種正常狀態,但將透明部分的透視線遮擋,便自然呈現出雙尖梭形的結構,也就是日本學者誤讀的“六棱體寶石”。到了云岡石窟第9窟的拱形內門券之上,這個長方柱形寶石,已經成為柱形透視圖的輪廓線形式。
“此頂部前后用復合忍冬紋、波狀忍冬紋裝飾,左右以蓮瓣紋飾帶相隔,形成了一個近梯形的外框,反映出前室小、后室大的洞窟結構。中央蓮缽里升起一團熊熊燃燒的火焰,焰心乃一摩尼寶珠,火苗朝向后室。寶珠呈六角形,蓮缽上刻單瓣蓮紋,兩飛天單手共托,另兩飛天雙手觸摸火焰。”(圖6)

圖6 云岡石窟第9窟拱門內門券浮雕局部
另一個圖像,來自云岡石窟第7窟的石窟穹頂之上。圖中,兩個飛天共同托舉一個單瓣型結構的形象。(圖7)“藻井中心內凹,較寬敞。雕8身飛天團團圍繞中心團蓮自由飛翔。南側兩身共舉摩尼寶珠。”

圖7 飛天(局部),云岡石窟第7窟后室窟頂中部南側
同樣在大同,沙嶺7號墓室壁畫(圖8)則有著明確紀年,即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我們從圖中可以看到:“甬道頂部繪有伏羲女媧,兩人頭戴花冠,雙手袖于胸前,下半身龍身長尾交纏在一起,兩人頭部中間有一圍繞火焰紋的摩尼寶珠……有一龍尾上卷的長龍,龍頭刻畫清晰。”在這個圖像中,中間的摩尼珠形態是一個純粹的立方體石頭的“透視略圖”,其“忽略”的是高透明下的線條結構。

圖8 沙嶺7號墓室壁畫,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年)
回到云岡石窟的兩個圖像,圖9為位于第9窟顯著位置的摩尼珠。此時,長方柱式的寶石形態已經完全變為圓梭形了,以往透明狀態下的透視線也已被完全改為兩個弧形。不過,有關摩尼珠的化變,仍在光焰之中演繹。光焰中出現了9粒小的棗核型摩尼珠,下方曖昧的“花葉”,也有了仰承蓮的雛形。圖10的摩尼珠中,光焰背光開始向蓮花的單瓣形態發展。不過,里面圖形上下尖細的特征,愈加明晰了。

圖9 云岡石窟第9窟摩尼珠線描圖

圖10 云岡石窟第7窟摩尼珠線描圖
敦煌莫高窟的摩尼珠又是什么樣的表現形態呢?
莫高窟第272、275窟被認為是北涼據敦煌時期的作品(圖11、圖12),制作于420—442年,早于云岡石窟一期和平年間(460—465年)。
如果說曇曜將北涼風格帶到大同,那么北涼占據敦煌,自然也為莫高窟帶來了北涼的樣式。在此層面上,二者的源發地是一致的。
這個時期,莫高窟的摩尼珠顯示出另外一種形態。第272窟是一期的早期石窟,在該窟的圖像中,天王所持舍利塔與摩尼珠結合在了一起。在手托的小塔之上,安置了摩尼珠橢圓形框口和兩個橢圓形活門,呈現出摩尼珠來源于佛舍利碎片的含義。摩尼珠與出入口構成一種必然的聯系,這在后文相關分析中尤為重要。(圖11)

圖11 莫高窟第272窟甬道北壁壁畫局部
同時期的第275窟,則把摩尼珠與蓮花瓣進行了置換。這是視覺符碼發生歷史性轉變的標志,摩尼珠在視覺史中完成了真實的嬗變。
圖12是《說法圖》及其局部。主尊在蓮臺上說法,蓮臺周圍以仰承蓮為飾,其中一瓣蓮花張開,出現了一個單瓣蓮花形狀的洞口,邊際金光粲然,里面幽深不可窺探(圖12中、下)。這幅圖從另一個角度,開辟了意義的通道,創造了象征空間。

圖12 《 說法圖》及其局部,莫高窟第275窟
之所以說是視覺史層面的標志性圖像,是因為摩尼珠自此開啟了新的視覺旅程——它不再只是寶珠層面上的神奇之物,而成為一個空間的載體,且與蓮花這個龐大的視覺形態連接在一起。
與蓮花的進一步結合,還體現在莫高窟北魏第263窟主尊背后的蓮花之上。主尊頂部的蓮花結構,變成了五瓣仰承蓮,上托一個豎立的蓮蓬(替代寶珠),光焰紋則保留了原本摩尼珠的模式痕跡。(圖13)窟龕外部飄蕩、游弋的蓮花,則為下一步的衍化,提供了邏輯基礎。

圖13 莫高窟北魏第263窟中的五瓣仰承蓮
二、 蓮子破生門的形成與視覺經驗遞變
在進入蓮花構筑的視覺史系統之時,我們必須要注意一個基本形式,即所有圍繞蓮花左右展開的紋樣(通常被解讀為忍冬紋)。其實,莫高窟已開始將這些相似的形式歸入蓮葉系統。我們現在看到的莫高窟第285窟的蓮花(圖14),便是呈現這種變化非常關鍵的樣本。以中心蓮花右側蓮葉為例,上面一片舒展而上揚,頂部上舉,底部有四處卷曲;下面一片向右下伸展,如刀匕外刺,底邊左側向內卷曲,背面則有回勾。我們將這種花葉的視覺構成方式,稱為“漸次打開的側面抽象蓮葉”。

圖14 莫高窟第285窟供養人像,西魏
至此,方柱型摩尼珠作為獨立形態開始在實際意義上退出視覺史,而化變為兩種新的樣式:一是活門形態。由于立體的方柱形態逐漸退場,原本的方柱形開始被誤讀為門框,而成為半圓形,左右兩側的柱身形態則被作為兩個橢圓形的活門(圖15右);二是圓形的蓮花寶珠端坐于橫截面的蓮蓬(隱藏在花心之中的三角形)之上,具有了空間創造的意義。(圖15左)
北魏—西魏的莫高窟圖像制作家,并沒有明確的透視理念,也沒有透明效果圖的概念,因此對神圣物圖像的塑造,盡可能地忠實于原本的畫譜。而制作者理解能力各異,也就導致了在誤讀基礎上的不斷的形式改變。
不過,摩尼珠與蓮花圖像的結合,被制作者消解到另外一種空間形態之中,加之時間性因素的介入,蓮花的形式得到更大的想象空間去生長和發展,從而衍化出更多的視覺形態。
“蓮花中摩尼寶呈四棱晶體狀,光芒四射,表現光芒的線紋已脫落,只存留光的橢圓形輪廓,兩側各有一荷葉形天蓮花。摩尼寶向上又伸出一枝蓮花,表現出豐富的想象。花葉如在水中蕩漾,婀娜多姿,生機盎然。紋樣勾線流暢,簡潔明快。”第431窟前坡這兩幅獨立又有邏輯關聯的圖像,可以說是莫高窟中最為明確地將摩尼珠與蓮花相結合的完整形式。
右邊的圖像分為三個部分:下部是分別向左右伸展的抽象蓮葉,其中左側為一脈四波的翻騰蓮葉,最下一波向內卷曲,中間兩波呈舒展狀,最上一波作張揚下折。葉片正反揚抑,姿態多變。中部為有五枚花瓣的垂瓣蓮簇擁著一個由半圓形坡面和倒立柱面構成的蓮蓬,蓮蓬上面是單瓣蓮花的形式。核心位置是一個曖昧的形式,它要么是一個立柱,要么是一個橢圓形的門框,里面是兩扇橢圓形活門。不過,在此立柱意識仍然存在,它表現為兩邊色彩的不同,但橢圓形活門的感覺也已出現。在蓮蓬的兩側,對稱性地分布著兩片張揚的具象的側面蓮葉,部分邊線呈鋸齒狀,蓮葉中心有一個隆起的花苞,與蓮蓬上的單瓣蓮花形成對比關系。上部,一條細線從中間的單瓣蓮尖上引出一個倒圓錐體的蓮蓬,由五瓣垂蓮簇擁著,垂蓮花瓣呈左右對稱。側面蓮葉零落狀的變形,顯示出花葉的偃仰變化。(圖15右)
左邊的圖像,則由兩大部分構成。下部是S型向上伸展的蓮花主莖,此時畫面的對稱性被徹底打破,階梯形的遞進感、收縮性的放射感、卷曲性的張揚感,這些對比性因素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畫面的張力。同時,蓮葉的變形也更加放縱。不過,這一切似乎都是為了渲染蓮花及其上面的花葉形態。上部是一個仰承蓮苞,其左右是兩枚張開的花瓣,蓮苞上方如鳥口,吐出左右兩片向下回勾卷曲的花葉,花葉上方是后來在佛教圖像里出現更多的五葉花形態。(圖15左)

圖15 蓮花摩尼寶紋,莫高窟第431窟前坡,北魏-西魏
這兩個圖像,其上下關聯邏輯是清楚的,其生長性是非常明晰的。左邊圖像的花苞衍化出摩尼寶,從中分離出左右伸展的側面具象蓮葉,上方的五葉花之中再度化變為蓮蓬(花心之中的三角形)。所以,與蓮花相融的摩尼寶,再度增強了化變的可能性,化變的邏輯基礎便是植物的生長本身。
圖16向我們展現了摩尼寶另一種化變空間。水滴形的單瓣蓮花結構發生了變化,原本的光焰變得曖昧起來,似乎是花苞中生長的花須。花苞似乎是被切開的剖面,展現出兩扇橢圓形的小門,此時摩尼寶的方柱體透視圖形式被徹底遺忘,保留在制作者記憶深處的是如何為這兩扇神秘的“小門”,尋找一個可以打開的“空間”。而這是立牌的形式(云岡模式)所無法承擔的。或許花的深處,是一個別有洞天的世界。因此,在這組圖像中,花苞可以用橢圓形的蓮蓬平臺來承接,蓮蓬下是抽象變形的蓮葉。蓮葉的波浪狀邊沿與蓮葉的葉脈,展現出雖聯結卻已有分離的趨勢。圖像通過色彩的差異,來表達這種將要分離的意識。

圖16 莫高窟第431窟前坡圖像局部,北魏-西魏
帶橢圓形活門的形式,安置在蓮蓬之中,提示著蓮蓬、蓮籽與蓮蕊的邏輯關系。這個居中的花苞繼續向上升騰,頂起了一朵五瓣蓮花——底部是兩片伸展的蓮瓣,上面是三片仰承的大蓮瓣。這樣倒置的視覺表述,其實也沒有什么不妥,但這些花苞畢竟不能成為一個孤立的存在。于是,在另外的情景之中,這些花苞被放置在側面的具象蓮葉之中,共計三對六片。
畫面的上半部分,不斷揭示著蓮花世界里更為豐富的衍生關系。中間的蓮莖彎曲升騰,居中是一個九瓣垂蓮簇擁的柱形蓮蓬,上面站立一只羽彩斑斕的鳥雀,左右兩側分別是盛開的五瓣仰承蓮和欲開的蓮苞,呈對稱狀。自下而上有兩對夸張的具象側面蓮葉,蓮葉中間邊線呈鋸齒狀,里面則是鼓起的毛茸茸的花苞,這為進一步打開兩扇橢圓形活門做了準備。
三、場境構成中的蓮子破生門:莫高窟諸窟的摩尼珠與門戶
關于莫高窟第249窟的窟頂東披(圖17),《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一書這樣表述:

圖17 莫高窟第249窟窟頂東披圖像局部,西魏
東壁坍毀,窟頂東披下部亦已殘損。東披寬4.63米,上部中間畫二力士承托摩尼寶珠,飛天左右護持,朱雀和孔雀相對飛翔。力士以下胡人與烏獲現百戲。胡人倒立,高鼻大眼;烏獲獸頭、人身、鳥爪;所演系西域傳來的百戲。胡人北側是作龜蛇相交的玄武,為四神之一,即我國古代傳說中守護北方的神。烏獲南側是我國古代神話中的天獸“開明”。這樣的形象,窟頂東南北三披均有,北披的十三首,南披的十一首,圖中東披的九首。《山海經》: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與壁畫形象相符。開明前有一猿猴,蹲踞樹上,作眺望狀,十分生動。
以上描述與解釋大致沒有什么錯誤,然而忽略了一個更為重要也最為關鍵的地方,便是“上部中間畫二力士承托摩尼寶珠”。既然是大放光明的摩尼寶珠,為什么其下面卻是九瓣垂蓮呢?為什么寶珠的四個方位不是光焰紋,而是抽象的側面蓮葉紋呢?最重要的是,為什么在這個類似橢圓形的物體中間,卻是一個上下圭形的紋樣呢?在這個雙圭形的空間里,居然有兩扇橢圓形的活門,這又當如何解釋呢?
其實,這是一個蓮瓶空間,是一個“化生之門”。如果圖11中力士右手塔上兩扇半開的門是“化生入門” ,那么這里顯然是“化生出門”。在這個“門”之下,是各種具有典禮色彩的畫面,充滿了慶賀的意味。中間類似橢圓形的形式中,是一個模擬摩尼珠方立柱變形的上截面,我們稱這個形式為“變形的摩尼寶”。這是制作者對透明方立柱透視圖的集體遺忘,這種形式也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與本窟窟頂東披的畫面建構邏輯一樣,南披畫面也是如此(圖18)。原本似乎是分離的蓮爐與花盤,在此似合為一體。中心的梭圓形蓮瓶,立在了蓮蓬的圓弧形面上,橢圓的蓮蓬下方則是九瓣垂蓮。蓮瓶的兩側是飛舞的花枝紋樣,左右的外側邊沿是兩扇側面展開的蓮葉。蓮葉的周邊又綻放出六片細碎的小蓮瓣,右側蓮瓣下方是一個向右旋轉的蓮花圖形。

圖18 莫高窟第249窟窟頂南披圖像局部,西魏
托舉者、力士在此皆已不見,只有兩支蓮莖立于地面之上。與同窟西披相比較,最大的變化是多出了旋轉的花枝。畫面左方呈三角形分布著四個旋轉的蓮花(兩個向左旋轉,個向右)及抽象蓮葉組成的“旋轉化生門”,畫面右方呈斜線分布著三個旋轉的蓮花(兩個向左旋轉,一個向右)及抽象蓮葉組成的“旋轉化生門”。與左邊化生門不同的是,右邊第二個旋轉蓮花紋樣的左右,是兩個已經成形的“單瓣背光型蓮珠”及簇擁的蓮花花枝。蓮瓶上出現了彎曲的光焰云紋,表示化生之門即將打開。中心的梭圓形蓮瓶顯出了兩個上下對稱的圭形空間,蓮瓶里面有兩個半圓形活門,這便是所謂的“化生出門”。
圖19描繪了一個混沌的世界。畫面中心還是飛天簇擁的蓮花花束。花束上面是一朵白色的蓮花,蓮花下面向右上伸展出側面蓮葉,與左下的側面蓮葉形成呼應。這個花束由蓮莖貫穿而生。花束左右飛天的身下各有一個向右旋轉的蓮花“旋轉化生門”。在這個畫面的左下部分,呈品字形分布著三個向右旋轉的蓮花“旋轉化生門”。而畫面右邊的“旋轉化生門”上方又是一個蓮花花蕊為頭、花瓣為身的L形“天人化生空間”。

圖19 莫高窟第285窟窟頂北披圖像局部,西魏
其實,蓮子破生門一方面代表了“天宮”的象征空間,另一方面也將蓮爐、蓮瓶、蓮花苞等相似的器物圖形,統攝在一個相關的視覺系統之中,建構起不同層次的意義。
從摩尼寶的形態衍化可以看出,其制作者沒有以透明物體來表達透視圖的相應知識與經驗,無法正確描繪出摩尼寶柱形透明透視圖,所以自然地將其描繪成雙圭形。在這種誤讀的前提下,他們又將其巧妙地嫁接到蓮花系統之中,從而建構其一個更為特別的空間通道,成為化生者破門而出的門徑——蓮子破生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