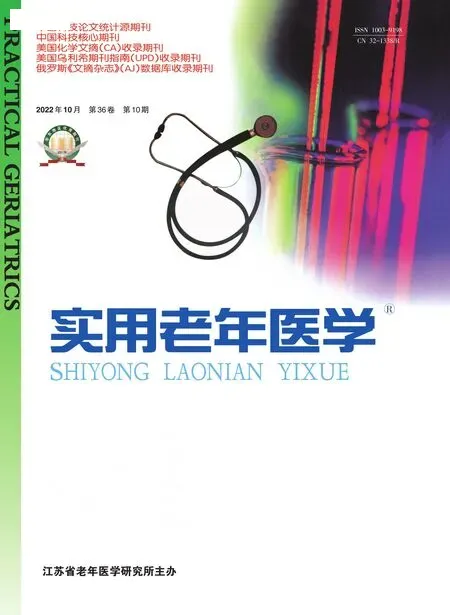頸動脈斑塊和ABI協同預測老年人群遠期新發心腦血管不良事件臨床價值探討
馮衛濤 李垚 李薇
目前認為動脈粥樣硬化是心血管疾病發生的主要預測指標,其中頸動脈斑塊與急性心肌梗死(AMI)及腦梗死發生關系均密切[1];而多項報道提示,低踝臂指數(ABI)亦是導致心血管疾病發生的潛在危險因素,低ABI的男性和女性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風險分別增加20%、35%[2-3]。盡管既往研究顯示,頸動脈斑塊形成和低ABI均可增加心血管不良事件發生風險,但對于兩者同時存在是否可協同增加心血管疾病發生風險尚無明確定論[4]。基于以上證據,本次研究納入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于我院參加職工體檢并完善頸動脈超聲及ABI檢查的老年人共821例,探討頸動脈斑塊和ABI協同預測老年人遠期新發心腦血管不良事件的臨床價值,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納入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在我院參加職工體檢并完善頸動脈超聲及ABI檢查的老年人共821例,其中男515例,女306例,年齡60~83歲,平均(67.21±5.87)歲。入選對象根據有無頸動脈斑塊及ABI水平分組,其中A組未合并頸動脈斑塊且ABI>0.9,B組合并頸動脈斑塊且ABI>0.9,C組合并頸動脈斑塊且ABI≤0.9。排除既往有心腦血管病史、隨訪過程中拒絕接受相關檢查、死亡或離職等失訪者。研究設計符合《世界醫學大會赫爾辛基宣言》要求。
1.2 方法 查閱電子體檢病歷系統收集研究對象性別、年齡、身高、體質量、合并疾病情況、實驗室檢查指標、頸動脈超聲檢查指標及ABI等資料。吸煙指近12個月每天吸煙≥1支;飲酒指近12個月每天攝入白酒100 mL以上[5]。實驗室檢查均由我院檢驗科完成,空腹8 h后于清晨7:00~9:00抽取靜脈血4~5 mL,離心后取上清液待檢,檢測儀器采用羅氏Cobas C2500型全自動生化分析儀。頸動脈超聲檢查由中級及以上職稱超聲科醫師完成,檢測儀器采用飛利浦HD-15型彩色多普勒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設置為5~12 MHz,保持仰臥及頭略后傾位,掃描頸總動脈、分叉處、頸內及頸外動脈,記錄內膜中層厚度(IMT)及斑塊形成情況。斑塊形成判定標準:局部隆起突出動脈管腔>0.5 mm,或局部隆起高度達頸動脈IMT值50%以上,或IMT>1.5 mm[6]。ABI計算方法:檢測雙側脛后或足背動脈收縮壓高值/肱動脈收縮壓高值,并取其中較低一側ABI,ABI≤0.9判定為異常[6]。
1.3 隨訪情況 采用電話或門診復查方式完成隨訪,記錄隨訪過程中新發AMI和腦梗死發生情況;隨訪截止時間為2021年6月;前24個月每3個月隨訪1次,之后每6個月隨訪1次。
1.4 統計學處理 選擇SPSS 18.0軟件分析數據;正態性評估采用Kolmogorov-Smirnov檢驗,符合正態分布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3組間比較采用單因素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頻數、百分比(n,%)表示,比較采用χ2檢驗;多因素分析采用Cox比例風險模型;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各組臨床特征資料比較 3組年齡、性別、吸煙比例、飲酒比例、SBP、FPG、LDL-C及接受調脂藥物治療比例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各組臨床特征資料比較(±s)

表1 各組臨床特征資料比較(±s)
項目A組(n=263)B組(n=534)C組(n=24)年齡(歲)66.34±12.7068.94±10.4677.90±13.45*男性(n,%)134(50.94)362(67.79)19(79.17)*吸煙(n,%)52(9.74)168(31.46)8(33.33)*飲酒(n,%)52(9.74)138(25.84)6(25.00)*FPG(mmol/L)5.74±1.076.05±1.116.14±1.23*SBP(mmHg)134.45±12.23139.39±14.20147.05±17.14*DBP(mmHg)83.87±12.2483.29±11.3380.02±9.30BMI24.20±2.7524.94±2.5224.83±2.21TC(mmol/L)5.24±1.165.67±1.205.49±1.05LDL-C(mmol/L)2.88±0.622.91±0.663.12±0.80*HDL-C(mmol/L)1.61±0.351.66±0.321.68±0.42合并高血壓(n,%)137(52.09)337(63.11)18(75.00)*合并T2DM(n,%)30(11.41)96(17.98)7(29.17)*降壓藥物治療(n,%)84(31.94)245(45.88)16(66.67)*調脂藥物治療(n,%)20(7.60)70(13.11)2(8.33)*注:3組間比較,*P<0.05
2.2 各組隨訪新發心腦血管事件發生情況比較 中位隨訪時間為60(44~76)個月,共出現缺血性心腦血管事件38例,其中腦梗死26例,AMI 12例;3組缺血性心腦血管事件和AMI發生率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3組腦梗死發生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2。

表2 各組隨訪新發心腦血管事件發生情況比較(n,%)
2.3 頸動脈斑塊及ABI水平預測遠期缺血性心腦血管事件發生風險價值 Cox比例風險模型單因素分析結果顯示,B組和C組遠期缺血性心腦血管事件、AMI及腦梗死發生風險均顯著高于A組(P<0.05),見表3。單因素Cox比例風險模型結果還顯示,性別(HR=6.43, 95%CI:3.65~9.36,P<0.05)、年齡(HR=5.86, 95%CI:2.99~11.47,P<0.05)、血壓(HR=4.77, 95%CI:1.67~8.35,P<0.05)、BMI(HR=5.49, 95%CI:2.99~9.56,P<0.05)與缺血性心腦血管事件發生風險相關,未發現FPG(HR=3.36, 95%CI:0.74~8.77,P>0.05)、TC(HR=1.23, 95%CI:0.35~3.46,P>0.05)、吸煙(HR=2.45, 95%CI:0.44~3.11,P>0.05)、飲酒(HR=4.33, 95%CI:0.69~6.41,P>0.05)及藥物服用情況(HR=2.74, 95%CI:0.41~5.34,P>0.05)與缺血性心腦血管事件發生風險相關。多因素Cox比例風險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在校正性別、年齡、血壓、FPG、BMI、TC、吸煙飲酒情況及藥物服用情況后,B組和C組遠期缺血性心腦血管事件發生風險均顯著高于A組,見表4。

表3 單因素Cox比例風險模型結果

表4 校正了混雜因素后的Cox比例風險模型
3 討論
以往報道顯示,合并頸動脈斑塊和ABI≤0.9均預示存在動脈粥樣硬化性病變發生風險[7],但本研究納入的老年人中2種指標異常檢出率存在差異,其中合并頸動脈斑塊且ABI≤0.9占比僅為3%(24例),而合并頸動脈斑塊且ABI>0.9占比為65%(534例),這一數據進一步提示解剖或以ABI指標為代表的血流動力學因素在動脈粥樣硬化性病變發生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本研究Cox比例風險模型分析結果顯示,在校正性別、年齡、血壓、FPG、BMI、TC、吸煙飲酒情況及藥物服用情況下,B組和C組老年人遠期缺血性心腦血管事件發生風險均顯著高于A組(P<0.05),C組和B組發生缺血性心腦血管事件風險分別是A組的8.51、4.76倍。有報道顯示,IMT增厚聯合ABI≤0.9預測心腦血管疾病發生風險效能優于兩者單一應用[8-9]。
一項Meta分析研究顯示,ABI≤0.9人群遠期AMI發生風險約為ABI>0.9人群的2.5~3.0倍;而合并頸動脈斑塊人群則為未合并人群的1.5~2.0倍[10]。盡管本次研究未發現合并頸動脈斑塊但ABI> 0.9組老年人群AMI發生風險增加,但合并頸動脈斑塊且ABI≤0.9老年人群AMI發生風險增加達37.42倍,說明此類老年人是遠期AMI發生高危人群,應給予更為積極有效的早期干預以改善臨床預后。已有研究顯示,他汀類藥物治療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延緩甚至逆轉亞臨床血管病變[11],故理論上合并頸動脈斑塊且ABI≤0.9者可通過服用他汀類藥物控制血脂水平,同時結合飲食運動干預最大限度預防動脈粥樣硬化發生,降低AMI發生風險[12]。
本次研究結果證實,僅合并頸動脈斑塊但ABI>0.9者遠期腦梗死發生風險增加4.33倍,但未發現其較合并頸動脈斑塊且ABI≤0.9者腦梗死風險升高,表明低ABI水平可能并非老年人群遠期腦梗死發生風險獨立預測指標,而對于合并頸動脈斑塊且ABI≤0.9者風險未增加具體原因及機制仍有待進一步分析。以往針對不同人群中ABI與腦梗死發生風險間關系報道結果也存在明顯差異[13-14]。一項回顧性隊列研究顯示,ABI下降并非腦梗死發生的獨立危險因素[15];但另有研究顯示,ABI≤0.9人群較ABI>0.9人群腦梗死發生風險增加1.7倍。考慮到本次研究中合并頸動脈斑塊且ABI≤0.9人群的樣本量及發生腦梗死事件均較少,故研究結果仍有待后續研究進一步確證。
本次研究證實,合并頸動脈斑塊和ABI≤0.9可協同增加老年人遠期缺血性心腦血管不良事件發生風險,可能機制如下[16-17]:(1)此類人群存在更多動脈粥樣硬化危險因素,或在相同危險因素作用下暴露時長更長,呈現出多血管床病變;(2)個體間存在遺傳易感性,使得相當部分病人在相同危險因素暴露下出現更為嚴重的動脈粥樣硬化,且范圍更為廣泛。
本次研究存在一定不足:(1)納入人群既往均為無心腦血管病史者;(2)ABI≤0.9檢出率較低,可能影響研究結果;(3)研究對象均為行職工體檢老年人,結果外推性受限。
綜上所述,老年人群如存在頸動脈斑塊且ABI水平≤0.9則遠期更易出現新發心腦血管不良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