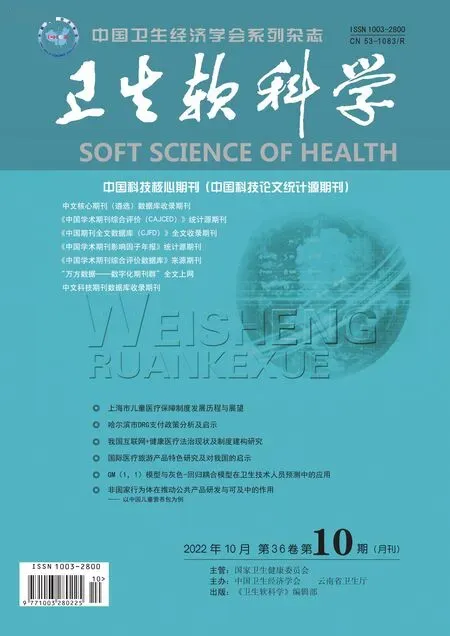集采常態(tài)化背景下重構(gòu)我國仿制藥新格局
——基于印度的5點(diǎn)啟示
崔秀娟,李明陽,梅之清,唐文熙,2
(1.中國藥科大學(xué)國際醫(yī)藥商學(xué)院,江蘇 南京 211198;2.中國藥科大學(xué)藥物經(jīng)濟(jì)學(xué)評價研究中心,江蘇 南京 211198)
印度作為中國鄰國,1991年開始對外改革,過去30年中經(jīng)濟(jì)發(fā)展速度位于世界第2,于 2019年成為全球第5大經(jīng)濟(jì)體,2020年人口數(shù)量為13.8億。由上述數(shù)據(jù)看出,印度在地理位置、經(jīng)濟(jì)發(fā)展以及人口方面都與我國較為相似,但印度醫(yī)藥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卻比我國走得更遠(yuǎn)。印度藥品目前產(chǎn)量約占全球規(guī)模的10%,市場銷售額約占全球1.5%,位列全球前15名,體量全球排名第3。此外,印度也是除美國之外獲得美國FDA獲批藥品最多的國家,印度出口的仿制藥占全球仿制藥出口量的五分之一,有著“世界藥房”之稱。印度藥品以其物美價廉和專利強(qiáng)制許可的巨大優(yōu)勢扎根國際醫(yī)藥市場,是同為發(fā)展中國家的中國在國際市場上較為強(qiáng)勁的競爭對手。
目前我國制藥企業(yè)以生產(chǎn)仿制藥為主,仿制藥也在藥品供應(yīng)市場中占據(jù)主流。據(jù)統(tǒng)計,2020年在國內(nèi)藥品市場上,仿制藥占比高達(dá)63%,而且仿制藥的市場占比還在不斷增長。2011年之前我國創(chuàng)新研發(fā)力量相對較弱,許多企業(yè)無法達(dá)到研發(fā)的高要求,國內(nèi)又面臨“無藥可用”的難題,因此相較于創(chuàng)新藥,仿制藥更為符合當(dāng)時國情。但中國仿制藥市場經(jīng)過過去10年的快速發(fā)展,也產(chǎn)生了仿制藥質(zhì)量療效與原研藥差距較大、企業(yè)多小散亂差、藥價虛高等問題。為此,2018年我國開始實(shí)施國家藥品集中帶量采購政策,重構(gòu)仿制藥格局,一定程度上解決了以上問題,但也產(chǎn)生了如仿制藥供應(yīng)不足等新問題和新風(fēng)險。因此,本文通過分析當(dāng)下我國仿制藥領(lǐng)域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印度在國際市場上獨(dú)有的競爭優(yōu)勢,為提高我國藥品國際競爭力提供參考。
1 目前我國仿制藥存在的問題
1.1 仿制藥的質(zhì)量和臨床療效堪憂
實(shí)施國家集中帶量采購的初衷之一是以市場份額砍掉仿制藥企業(yè)虛高的藥品價格。但是,集中帶量采購的仿制藥質(zhì)量難以保證,中標(biāo)企業(yè)在低價中標(biāo)后為謀得更高的利潤,通常采取各種手段壓縮成本。談在祥等人研究認(rèn)為集采政策下,存在醫(yī)藥企業(yè)減少藥品的有效成分的現(xiàn)象,以降低藥品質(zhì)量來控制成本。即使有仿制藥一致性評價保證藥品基本質(zhì)量,但仿制藥質(zhì)量與印度相比仍存在差距。同時集采低價中標(biāo)的機(jī)制會導(dǎo)致高品質(zhì)仿制藥落選,造成“劣幣驅(qū)逐良幣”的現(xiàn)象。
1.2 仿制藥的穩(wěn)定供應(yīng)難以保障
2021年8月20日,華北制藥因產(chǎn)能不足和原料藥漲價,導(dǎo)致三批集采中標(biāo)藥布洛芬緩釋膠囊違約斷供,受到主管部門的嚴(yán)厲懲戒,這引起醫(yī)藥衛(wèi)生界的廣泛討論。藥企信用評價體系和失信名單的懲戒是否真正解決了當(dāng)下的仿制藥供應(yīng)難題有待探究。雖然企業(yè)在參與投標(biāo)報價時,均進(jìn)行了嚴(yán)密的成本測算,但在靜態(tài)固定的中標(biāo)價格下,成本是動態(tài)變化的。居高不下的原料、環(huán)保、注冊以及申報成本、巨大的藥品價格降幅,加上疫情的沖擊,諸多不確定因素都可能使得企業(yè)測算的“最低價”失效,導(dǎo)致藥企違約斷供。而國家藥品集中帶量采購中的市場份額是供應(yīng)公立醫(yī)院臨床使用常用仿制藥的80%,中標(biāo)藥企斷供將直接大規(guī)模影響地區(qū)臨床常用仿制藥的供應(yīng)穩(wěn)定性。
1.3 原材料的質(zhì)量風(fēng)險和價格上升
原材料的成本和質(zhì)量直接影響仿制藥的質(zhì)量和供應(yīng)。一致性評價以及集采一定程度上是市場對藥品、醫(yī)藥企業(yè)、原材料供應(yīng)商進(jìn)行篩選的工具,在對藥企進(jìn)行擇優(yōu)挑選的同時,相當(dāng)于間接授權(quán)醫(yī)藥企業(yè)篩選原材料供應(yīng)商。另外,原材料的成本上升是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我國如今在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上的價格比較優(yōu)勢削弱,目前仿制藥的價格比較優(yōu)勢已經(jīng)轉(zhuǎn)移到東南亞地區(qū),但這也是我國仿制藥創(chuàng)新藥發(fā)展格局轉(zhuǎn)型和重構(gòu)的機(jī)遇。
1.4 仿制藥國內(nèi)競爭格局低迷
我國仿制藥發(fā)展格局包含2個方面,一是仿制藥自身發(fā)展格局,二是仿制藥與原研藥的競爭格局。就仿制藥自身而言,中國仿制藥市場大而不強(qiáng),企業(yè)“多小散亂差”的局面依然存在,藥品的質(zhì)量參差不齊。從原研藥與仿制藥的競爭格局來看,我國仿制藥市場發(fā)展并不景氣,仿制藥市場規(guī)模低于整個醫(yī)藥行業(yè)。歐美等發(fā)達(dá)國家和地區(qū)的仿制藥增速是創(chuàng)新藥的2倍多。而2020年起受新冠疫情影響,中國藥品市場出現(xiàn)罕見下滑,仿制藥整體市場規(guī)模同比下降16.7%,而全行業(yè)同比增長7%。隨著疫情的控制和經(jīng)濟(jì)的恢復(fù),2021年仿制藥市場規(guī)模或?qū)⒒厣赃h(yuǎn)低于整個醫(yī)藥行業(yè)。
1.5 我國仿制藥國際化水平不足
醫(yī)藥企業(yè)國際化發(fā)展的第一步就是需要通過國際上公認(rèn)的專業(yè)機(jī)構(gòu)的認(rèn)證,經(jīng)過認(rèn)證的企業(yè)和產(chǎn)品才能增加信譽(yù)度和影響力,才有資格將產(chǎn)品銷往海外。印度企業(yè)無論是原料藥出口時期還是仿制藥發(fā)展時期都積極進(jìn)行國際認(rèn)證。原料藥的認(rèn)證主要通過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簽署的DMF文件和歐洲藥品質(zhì)量管理局(EDQM)頒發(fā)的COS證書,2008年印度在美國FDA獲得的DMF占總量的32%,位居世界第一,而同期中國的DMF認(rèn)證僅為印度的1/3。印度在本土醫(yī)藥企業(yè)建立優(yōu)勢的基礎(chǔ)上,通過在美國積極申請藥品主文件和新藥申請,在美國、歐洲等規(guī)范市場進(jìn)行頻繁的并購活動,確立起全球范圍的競爭優(yōu)勢,同時結(jié)合原料藥出口時期的生產(chǎn)和國際認(rèn)證經(jīng)驗(yàn),打開了國際上的制劑生產(chǎn)業(yè)務(wù)。以進(jìn)入美國市場的簡化新藥申請(ANDAs)為例,我國審批通過的申請數(shù)量遠(yuǎn)不如印度,產(chǎn)品和企業(yè)的國際認(rèn)證工作也未能迅速展開,導(dǎo)致中國仿制藥在國際競爭中和印度仿制藥相差甚遠(yuǎn)。
2 印度醫(yī)藥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經(jīng)驗(yàn)
2.1 印度仿制藥的鼓勵措施
2.1.1 國家仿制藥體系布局
印度自20世紀(jì)70年代開始就有意識地培育和扶持本土制藥業(yè),在政府的謀劃和支持下印度仿制藥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通過頒布《專利法》、外匯管制法案和一系列藥品價格管控法律法規(guī)等為本土制藥企業(yè)早早利用國際醫(yī)藥技術(shù)、開發(fā)仿制藥提供了政策保障;其次是簽署了《與貿(mào)易有關(guān)的知識產(chǎn)權(quán)協(xié)定》(TRIPS協(xié)議),加入WTO為印度仿制藥迅速發(fā)展提供了機(jī)遇;最后在恢復(fù)醫(yī)藥產(chǎn)品專利保護(hù)后,改變發(fā)展策略頒布《生物類似藥指南》,加大研發(fā)投入,促進(jìn)生物類似藥領(lǐng)域仿制藥的發(fā)展。
2.1.2 政府創(chuàng)新政策引領(lǐng)
印度醫(yī)藥創(chuàng)新是以仿制藥作為發(fā)展起源的創(chuàng)新。政府通過授予食品和藥品工藝專利,而不授予產(chǎn)品專利的方法來鼓勵印度醫(yī)藥企業(yè)對專利藥品進(jìn)行仿制。此外印度政府還推出“專利強(qiáng)制許可制度”,規(guī)定在一些特定條件下可對藥品專利行使強(qiáng)制許可權(quán)。
2.2 印度藥物的價格控制
印度政府對藥品的價格進(jìn)行嚴(yán)格控制。1963年后通過各種法令宣布一系列價格控制制度,這些法令在控制藥品價格的程度和性質(zhì)各不相同。1966年的《Drugs(Price Control)Order》沒有降低藥品價格,但規(guī)定若提高藥品價格需通過政府批準(zhǔn)。1970年的《Drugs(Price Control)Order》中政府首次設(shè)定原料藥價格上限,但之后逐漸放寬對原料藥價格的限制,轉(zhuǎn)為市場機(jī)制定價。在2012年之后,印度國家化學(xué)及肥料部(Ministry of Chemicals and Fertilizers)對印度國家基本藥品目錄(National List of Essential Medicines,NLEM)內(nèi)的藥品價格進(jìn)行統(tǒng)一管理。印度國家藥品價格管理政策部門(National Pharmaceutical Pricing Policy)制定并頒布各藥品的價格上限以及零售價(Drug Price Control Orders)。NLEM由政府統(tǒng)籌決定及更新。從2013開始,不在NLEM目錄內(nèi)的藥品,可以由生產(chǎn)企業(yè)自主定價,因此自2013年藥品價格控制令出臺以來,許多藥品的價格大幅下降。
2.3 印度藥物的供應(yīng)保障
印度政府為了保證基本藥物價格出臺了相應(yīng)的政策,在較低的藥品價格前提下保障藥品的穩(wěn)定供應(yīng)就顯得尤為重要。因此為了防止醫(yī)藥企業(yè)在當(dāng)前的價格機(jī)制下停止生產(chǎn)藥物,政府規(guī)定醫(yī)藥企業(yè)在沒有政府允許的情況下不能停止生產(chǎn)基本藥物。如果要停產(chǎn),必須至少提前6個月通知政府。此外政府有權(quán)利要求醫(yī)藥公司繼續(xù)生產(chǎn)一定數(shù)量的基本藥物,以確保基本藥物的供應(yīng)。
3 集采常態(tài)化背景下我國仿制藥產(chǎn)業(yè)發(fā)展建議
3.1 加強(qiáng)政府謀劃和支持,保證仿制藥監(jiān)管與發(fā)展
印度較早開始對仿制藥產(chǎn)業(yè)的布局,再加上產(chǎn)業(yè)鏈位置設(shè)定、較低的生產(chǎn)成本,使其實(shí)現(xiàn)在2012 年底 WHO 預(yù)認(rèn)證藥物清單中的231 種(74%)仿制藥中有200種(87%)在印度制造。其開發(fā)、測試、制造和營銷仿制藥的成本通常是西方國家成本的20%-40%。再加上較低的勞動力投入、較少的環(huán)境法規(guī)和較低的市場準(zhǔn)入壁壘等導(dǎo)致印度在世界仿制藥市場發(fā)揮重要作用。與印度相比,我國則因過早地采用了與發(fā)達(dá)國家類似標(biāo)準(zhǔn)的專利保護(hù)制度,某種意義上錯失發(fā)展本國醫(yī)藥企業(yè)和仿制藥的良機(jī)。目前雖已有相應(yīng)政策出臺提高仿制藥質(zhì)量,但仍需政府部門加強(qiáng)頂層設(shè)計,做好戰(zhàn)略引導(dǎo),發(fā)揮統(tǒng)籌協(xié)調(diào)的作用。
3.2 加大仿制藥研發(fā)投入,促進(jìn)仿創(chuàng)結(jié)合發(fā)展
制藥業(yè)多年位居印度私營部門研發(fā)投入行業(yè)排名第1,大部分研發(fā)投入被用于仿制藥、原料藥和疫苗的研發(fā),其次才是新藥和藥物輸送系統(tǒng)的研發(fā)。印度制藥業(yè)走向世界開始于仿制藥生產(chǎn),近年來印度的公共衛(wèi)生支出穩(wěn)定增長,政府還計劃設(shè)立基金,為本土制藥業(yè)提供資金支持。數(shù)據(jù)顯示,2017年以來在全球藥企研發(fā)投入整體下降的大環(huán)境下,印度藥企仍保持了較為穩(wěn)定的研發(fā)投入比例。相較之下,我國目前政策向創(chuàng)新藥傾斜,加上科創(chuàng)板的實(shí)施,醫(yī)藥健康領(lǐng)域融資中對仿制藥的投資占比較低。現(xiàn)實(shí)和政策本意有些偏差,本意是給予傳統(tǒng)頭部仿制藥企業(yè)穩(wěn)定的現(xiàn)金流,鼓勵往高風(fēng)險、高回報的創(chuàng)新藥轉(zhuǎn)型。但實(shí)際上,能夠轉(zhuǎn)型做創(chuàng)新藥的仿制藥企業(yè)屈指可數(shù)。轉(zhuǎn)型做研發(fā)是藥企發(fā)展的途徑之一,但仿制藥發(fā)展也是重中之重。加大仿制藥研發(fā)投入,是培育大型仿制藥企業(yè)的前提。
3.3 完善價格管控制度,保障藥品持續(xù)供應(yīng)
國家藥品實(shí)行集中帶量采購政策,通過一致性評價的仿制藥企業(yè)進(jìn)行招投標(biāo)競價,以期用較低的價格獲得公立醫(yī)院常用仿制藥80%的市場份額。雖然政府和企業(yè)均進(jìn)行了嚴(yán)密的成本計算,以求通過最低價采購質(zhì)量優(yōu)異的仿制藥。但是原材料的價格是動態(tài)變化的,這極易對企業(yè)后續(xù)供應(yīng)情況造成影響,這也是目前集采政策尚需完善之處。在價格控制政策上,我國長期以來受藥品差別定價政策和政策的不連續(xù)性影響,醫(yī)藥企業(yè)開發(fā)高質(zhì)量仿制藥的積極性仍然不高。相比于我國在20世紀(jì)90年代就逐步放開價格控制,印度通過三階段逐步實(shí)現(xiàn)從嚴(yán)控藥品價格,到適度開放價格范圍,再到最后以市場為基礎(chǔ)的價格形成機(jī)制的管理轉(zhuǎn)變,其政策連續(xù)性要優(yōu)于我國。在企業(yè)利益的基礎(chǔ)上,降低藥價才能滿足患者需求和促進(jìn)醫(yī)藥企業(yè)良性發(fā)展。
3.4 客觀看待創(chuàng)新藥與仿制藥發(fā)展“有機(jī)組合”格局
首先,正視仿制藥保基本的“基本盤”地位。創(chuàng)新藥決定了人民健康水平的想象空間,但仿制藥真正決定了人民健康的基礎(chǔ),是提高藥品可及性和提升全民幸福感的重要途徑。根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WHO)的統(tǒng)計顯示,醫(yī)生開具的處方中仿制藥占85.5%,卻只消耗12%的醫(yī)藥費(fèi)用支出。我國除了高等級治療需求的疾病,大多數(shù)疾病使用的藥品仍是仿制藥。因此需要重新定位仿制藥格局,要求仿制藥既能滿足基本用藥需求,達(dá)到同等質(zhì)量或療效標(biāo)準(zhǔn),又以更低廉的價格服務(wù)于非高等級治療需求的疾病領(lǐng)域。其次由于醫(yī)保基金的有限性,創(chuàng)新藥給醫(yī)保基金帶來不小的沖擊,也使得擴(kuò)大仿制藥發(fā)展更符合我國國情。但創(chuàng)新藥的發(fā)展代表著人們對健康的更高追求,也意味著國家的藥品研發(fā)實(shí)力,需要與仿制藥發(fā)展“有機(jī)結(jié)合”。
3.5 抓住國際藥品市場契機(jī),把握仿制藥市場發(fā)展
由于新冠疫情下我國優(yōu)先恢復(fù)生產(chǎn),且印度制藥在國際市場上頻頻出現(xiàn)質(zhì)量問題,目前是我國仿制藥拓展海外市場的有利契機(jī)。以往,印度制藥因其價格低廉且質(zhì)量穩(wěn)定頗受國際市場歡迎,但是近年來印度的監(jiān)管體系逐年惡化,藥品質(zhì)量問題廣受國際社會關(guān)注。自從2008年印度第一大制藥企業(yè)蘭博西實(shí)驗(yàn)室被美國FDA發(fā)出禁令,印度藥品質(zhì)量管控迎來了巨大的挑戰(zhàn),在2016年進(jìn)入美國市場時須接受FDA的監(jiān)督審查項(xiàng)目高達(dá)840項(xiàng)。質(zhì)量問題多次出現(xiàn)是由于印度中央對醫(yī)藥監(jiān)管空白,各州勢力強(qiáng)勢,中央無從管控,并且一直沒有落實(shí)公共采購政策,大量劣質(zhì)藥流入市場。有研究表明,從印度出口到非洲的藥品質(zhì)量比運(yùn)往其他地方的藥品質(zhì)量差,同時根據(jù)世界衛(wèi)生組織數(shù)據(jù)顯示,印度國內(nèi)的醫(yī)藥市場上20%的在售藥品和35%的出口藥品不符合現(xiàn)有標(biāo)準(zhǔn)。因此,在這一時期我國仿制藥發(fā)展應(yīng)當(dāng)重視仿制藥質(zhì)量通過一致性評價、積極對接國際標(biāo)準(zhǔn)、拓展海外市場:一方面不斷提升本土制藥企業(yè)的研發(fā)技術(shù)水平,加快申請美國、歐盟和世衛(wèi)組織等相關(guān)監(jiān)管機(jī)構(gòu)的認(rèn)證;另一方面加強(qiáng)監(jiān)管,促進(jìn)仿制藥企業(yè)整合升級,抓住集中帶量采購的機(jī)會,升級成具有大規(guī)模生產(chǎn)配送等能力的企業(yè),把握國內(nèi)外市場。
目前,在國家集中帶量采購政策環(huán)境下,國內(nèi)仿制藥企業(yè)格局被重構(gòu),我國仿制藥市場迎來新的發(fā)展機(jī)遇,應(yīng)正確定位我國仿制藥貿(mào)易的競爭性與互補(bǔ)性。在該契機(jī)下,政府應(yīng)保證仿制藥質(zhì)量達(dá)標(biāo)、供應(yīng)穩(wěn)定、價格合理,幫助藥企在滿足國內(nèi)市場需求的同時,積極對接國際標(biāo)準(zhǔn),占據(jù)國際市場。
- 衛(wèi)生軟科學(xué)的其它文章
- 商業(yè)健康險與基本醫(yī)療險的耦合協(xié)調(diào)時空特征分析
- 非國家行為體在推動公共產(chǎn)品研發(fā)與可及中的作用
——以中國兒童營養(yǎng)包為例 - 湖南省疾病預(yù)防控制機(jī)構(gòu)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現(xiàn)狀分析
- 城鎮(zhèn)職工心力衰竭患者衛(wèi)生服務(wù)利用和直接醫(yī)療費(fèi)用現(xiàn)狀分析
- 多主體協(xié)同下城市社區(qū)醫(yī)養(yǎng)結(jié)合服務(wù)困境與對策研究
——基于南京市秦淮區(qū)的調(diào)查 - 基本公共衛(wèi)生服務(wù)項(xiàng)目社區(qū)診斷報告編制規(guī)范指標(biāo)體系的構(gòu)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