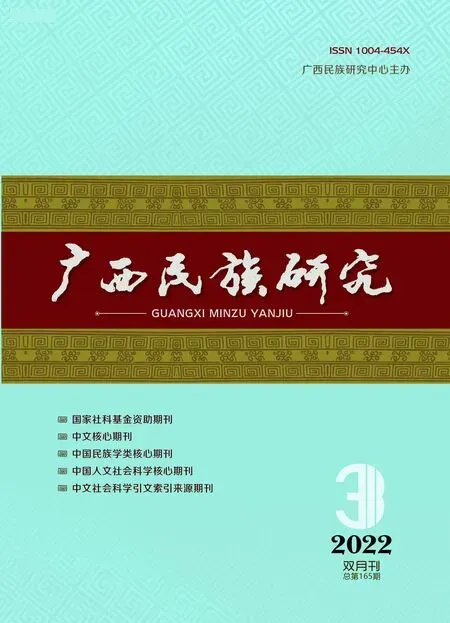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視角下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
黃孝東 張繼焦
2021年8月12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guó)務(wù)院辦公廳印發(fā)了《關(guān)于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工作的意見(jiàn)》(以下簡(jiǎn)稱(chēng)《意見(jiàn)》),《意見(jiàn)》開(kāi)宗明義對(du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簡(jiǎn)稱(chēng)“非遺”)進(jìn)行了準(zhǔn)確的時(shí)代定位:“非遺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華文明綿延傳承的生動(dòng)見(jiàn)證,是連結(jié)民族情感、維系國(guó)家統(tǒng)一的重要基礎(chǔ)”。可見(jiàn),非遺保護(hù)已成為我國(guó)民族工作的重要構(gòu)成部分,相較于以往將非遺保護(hù)視為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認(rèn)知和適當(dāng)利用,《意見(jiàn)》中對(duì)中華文化、民族情感、國(guó)家統(tǒng)一的強(qiáng)調(diào)凸顯了我國(guó)主流意識(shí)形態(tài)在非遺保護(hù)工作中的主導(dǎo)地位,并將其上升到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與建設(shè)社會(huì)主義文化強(qiáng)國(guó)的高度。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是新時(shí)代我國(guó)非遺保護(hù)工作的積極探索與實(shí)踐,該理念以文化整體觀為指導(dǎo)框架,認(rèn)為非遺深深植根于社會(huì)文化傳統(tǒng)的積淀中,與族群的生存環(huán)境、歷史發(fā)展脈絡(luò)、經(jīng)濟(jì)生活方式、社會(huì)關(guān)系等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將非遺納入動(dòng)態(tài)時(shí)空?qǐng)鲇颍瑥?qiáng)調(diào)非遺本體、相關(guān)環(huán)境與人之間的和諧共生關(guān)系,這種關(guān)系建立在非遺形成與發(fā)展過(guò)程中不同族群多元生產(chǎn)生活方式相互碰撞、相互包容、相互欣賞的基礎(chǔ)上,是一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關(guān)系。
多元文化共生是構(gòu)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基礎(chǔ)。從文化認(rèn)同的角度來(lái)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是要從思想意識(shí)形態(tài)上認(rèn)知中華民族是一個(gè)“多元一體”的共同體,目的是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每個(gè)成員的內(nèi)心深處培育和構(gòu)建強(qiáng)烈的共同體意識(shí),在“形”“氣”“神”等多個(gè)層面強(qiáng)化中華民族大家庭全體成員的認(rèn)同力和內(nèi)聚力。在中國(guó)民族工作話(huà)語(yǔ)中,“大家庭”是一個(gè)充滿(mǎn)感情色彩的詞語(yǔ),用來(lái)形容中華各民族之間相互依存的親情共同體,這種親情共同體的形成需要建立在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中華文化認(rèn)同基礎(chǔ)之上。因此,有必要樹(shù)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號(hào)和中華民族形象,這與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理念高度一致。目前,學(xué)界對(duì)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單向維度探討較多,對(duì)二者之間關(guān)聯(lián)性的探討還較為鮮見(jiàn)。基于此,筆者嘗試將二者置于同一框架下進(jìn)行探討和分析,首先,對(duì)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的內(nèi)涵進(jìn)行梳理,在此基礎(chǔ)上,分析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關(guān)系,進(jìn)而分析中國(guó)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過(guò)程中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深層機(jī)理及路徑。
一、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的內(nèi)涵
如果說(shuō)“整體性保護(hù)”側(cè)重的是非遺的內(nèi)容,那么“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則著眼于非遺的空間性或場(chǎng)域性,即非遺得以孕育和發(fā)展的整體文化與自然環(huán)境,目的是在非遺保護(hù)過(guò)程中維護(hù)文化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在保護(hù)文化生態(tài)空間完整性的基礎(chǔ)之上實(shí)現(xiàn)非遺保護(hù)、非遺活態(tài)傳承和地方社會(huì)發(fā)展的全面協(xié)調(diào)。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理念源于我國(guó)近年來(lái)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的探索與實(shí)踐,這一術(shù)語(yǔ)首次出現(xiàn)在201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簡(jiǎn)稱(chēng)《非遺法》)中,《非遺法》第二十六條規(guī)定,對(duì)非遺代表性項(xiàng)目集中、特色突出、形式和內(nèi)容完整的地區(qū),進(jìn)行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這一規(guī)定不僅為非遺的全面保護(hù)提供了法律依據(jù),也為建構(gòu)具有中國(guó)特色的非遺保護(hù)體系奠定了基礎(chǔ)。以《非遺法》精神為指引,2021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印發(fā)的《“十四五”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規(guī)劃》為新時(shí)期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工作指明了具體方向,要求結(jié)合空間文化具體而獨(dú)特的社區(qū)、村鎮(zhèn)、街道等,有序推進(jìn)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的新探索與新實(shí)踐,涵蓋“非遺在社區(qū)”、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中國(guó)傳統(tǒng)村落非遺保護(hù)、非遺特色村鎮(zhèn)與街區(qū)建設(shè)等四個(gè)方面。《意見(jiàn)》中也進(jìn)一步指出,完善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體系,保護(hù)非遺和孕育其產(chǎn)生發(fā)展的文化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突出地域性和民族性。
概言之,“區(qū)域性”對(duì)非遺整體性保護(hù)的范圍進(jìn)行了限定,使非遺保護(hù)更加具象化和可操作化。換句話(huà)說(shuō),“整體性”是多年來(lái)世界范圍內(nèi)逐步形成的非遺保護(hù)工作的基礎(chǔ)理念與基本共識(shí),是世界各國(guó)公認(rèn)的遺產(chǎn)保護(hù)方式和原則,“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則是對(duì)具體保護(hù)內(nèi)容和范圍的描述,這個(gè)理念更有中國(guó)特色,更符合中國(guó)國(guó)情,是我國(guó)非遺保護(hù)工作的一項(xiàng)重要實(shí)踐成果和重大創(chuàng)新。
二、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關(guān)系試辯
我國(guó)是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guó)家,各民族長(zhǎng)期交往交流、相互碰撞、彼此融合,積累了大量傳統(tǒng)音樂(lè)、傳統(tǒng)技藝、傳統(tǒng)舞蹈等非遺,這些非遺大多處于交融復(fù)合的共享狀態(tài),是中華民族共有和共享的文化符號(hào),是鞏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重要情感保障,在培育中華民族的族源意識(shí)、價(jià)值觀、歷史觀以及民族審美情趣上,有著重要的精神聚合意義。因此,在討論如何通過(guò)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之前,有必要先對(duì)二者的關(guān)系進(jìn)行梳理和辨析。
(一)二者都將“整體觀”作為基本出發(fā)點(diǎn)
我國(guó)對(duì)非遺整體性保護(hù)理念的解讀大致分為兩個(gè)層面。一是文化事象的整體性,即保護(hù)非遺的所有內(nèi)容和形式,而不是某個(gè)部分或某個(gè)環(huán)節(jié)。例如京劇藝術(shù)的保護(hù)既包括“詩(shī)”(唱詞、念白)、“樂(lè)”(音樂(lè)伴奏)、“舞”(演員的表演技藝),又包括工具、道具、舞美、服裝和化妝等,這些內(nèi)容不能被孤立地看待;二是文化整體觀層面,即對(duì)孕育非遺及其傳承人的環(huán)境進(jìn)行整體保護(hù),既要保護(hù)非遺自身及其有形外觀,更要注意它們所依賴(lài)和應(yīng)對(duì)的結(jié)構(gòu)環(huán)境。可見(jiàn),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是對(duì)上述兩個(gè)層面的整合。“區(qū)域性”打破了行政區(qū)劃對(duì)非遺保護(hù)的限制,使多元化非遺保護(hù)主體在更大的文化圈內(nèi)充分融合。“整體保護(hù)”則是將人、物、生活有機(jī)結(jié)合在一起,凸顯了非遺保護(hù)和發(fā)展的活態(tài)性與共享性。
文化的主體是民族,民族也是文化的統(tǒng)一體,文化和民族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guān)系。中華民族共同意識(shí)源于中國(guó)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精神傳統(tǒng),傳統(tǒng)文化與精神傳統(tǒng)以特定民族為載體,通過(guò)群體成員強(qiáng)烈的心理認(rèn)同感加以強(qiáng)化和凸顯。中國(guó)有56 個(gè)民族,各族之間雖然有差異,但56 個(gè)民族都有一個(gè)共同的族名——中華民族,“中華民族是一個(gè)不可分割的整體,這個(gè)整體又由許多不能分離的民族組成……你變成我,我變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非遺作為中華民族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與精神財(cái)富的象征,背后凝結(jié)著各族人民在長(zhǎng)期生產(chǎn)生活實(shí)踐中沉淀在內(nèi)心深處的情感認(rèn)同、價(jià)值觀念和社會(huì)歷史記憶,這種穩(wěn)定性以特定民族內(nèi)部或多民族長(zhǎng)期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文化“和合觀”為基礎(chǔ)。非遺就像一個(gè)不斷滾動(dòng)的雪球,一面滾動(dòng)一面粘連上新的附加物,雪球的核心是各民族在相互尊重、相互欣賞、相互借鑒的基礎(chǔ)上,以?xún)r(jià)值選擇、情感鏈接而形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在特定區(qū)域中多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混雜、聯(lián)結(jié),發(fā)展出既有差別而又完整統(tǒng)一的文化形態(tài),最終實(shí)現(xiàn)“主我”與“客我”、“自我”與“他者”的融合,這既是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的基本原則,又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在文化認(rèn)同層面的具體體現(xiàn)。
(二)二者都以人民為中心
《“十四五”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規(guī)劃》中明確提出非遺保護(hù)要堅(jiān)持以人民為中心,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主體地位和創(chuàng)造性表達(dá)權(quán)利,推動(dòng)非遺融入人民群眾的生產(chǎn)生活,讓人民參與保護(hù)傳承,非遺保護(hù)的成果為人民共享,從而不斷增強(qiáng)人民群眾的認(rèn)同感、參與感、獲得感,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人是非遺的核心”“保護(hù)非遺的前提是保護(hù)人”、非遺保護(hù)要“見(jiàn)人見(jiàn)物見(jiàn)生活”,這些觀點(diǎn)早已在學(xué)界達(dá)成了共識(shí),學(xué)者們關(guān)注的重心也由非遺構(gòu)成要素及其表現(xiàn)形式轉(zhuǎn)向了非遺的發(fā)展過(guò)程和人本身。與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不同,以人民為核心的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首先強(qiáng)調(diào)保護(hù)非遺的生命力抑或說(shuō)存活能力,這依賴(lài)于非遺傳承人發(fā)揮主觀能動(dòng)性主動(dòng)保護(hù)和傳承非遺,在此基礎(chǔ)上培育和激發(fā)該區(qū)域內(nèi)人們的整體文化自覺(jué);其次,以人民為核心的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意味著人和文化的關(guān)系是平等的、相互包容的“我與你”的關(guān)系,而非彼此物化、相互利用的“我與它”的關(guān)系;第三,以人民為核心的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應(yīng)與該區(qū)域的公共文化建設(shè)相結(jié)合,將非遺與社區(qū)、族群的日常生活融為一體,實(shí)現(xiàn)非遺活態(tài)利用的共享性。
(三)二者相互嵌入,互為動(dòng)力條件
首先,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是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的基本內(nèi)驅(qū)力。情感認(rèn)同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在各族社會(huì)心理層面的表現(xiàn),情感認(rèn)同產(chǎn)生內(nèi)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動(dòng)力,促進(jìn)各族人民形成對(duì)中華民族大家庭的認(rèn)同,形成自覺(jué)踐行和主動(dòng)擔(dān)當(dāng)?shù)闹黧w意識(shí)。非遺是共同體成員的情感表達(dá)方式和成員關(guān)系的外在表現(xiàn)形式,只有在情感上產(chǎn)生共鳴、文化價(jià)值上形成認(rèn)同并被共同體內(nèi)的成員所接受,才能稱(chēng)之為民族文化遺產(chǎn)。可見(jiàn),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與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的出發(fā)點(diǎn)和落腳點(diǎn)高度一致。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使各民族成員在內(nèi)心深處自覺(jué)地意識(shí)到,自己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者和繼承者,有責(zé)任和義務(wù)主動(dòng)地保護(hù)和傳承非遺,對(duì)非遺進(jìn)行創(chuàng)新性利用的所得也必將惠及共同體中的每一位成員,進(jìn)而激發(fā)和培育各民族成員的文化自信,使其在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過(guò)程中同頻共振、共同發(fā)力。
其次,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是培育和增強(qiáng)新時(shí)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有力途徑。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以文化整體觀為基本發(fā)展框架,以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為現(xiàn)實(shí)依托,強(qiáng)調(diào)不同類(lèi)型和層次的非遺項(xiàng)目、非遺與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非遺與民族、非遺與自然文化的關(guān)聯(lián)性,對(duì)多元文化形態(tài)開(kāi)展綜合性保護(hù)。在實(shí)踐層面,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包括對(duì)社區(qū)生態(tài)環(huán)境的保護(hù)、對(duì)區(qū)域內(nèi)居民生活環(huán)境的改善、對(duì)非遺項(xiàng)目的生存空間(例如古戲臺(tái)、古祠堂等)進(jìn)行良性修復(fù)等。此外,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在公共生活領(lǐng)域也發(fā)揮著巨大的功能,例如濰水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將非遺融入公共文化服務(wù)體系,以國(guó)際風(fēng)箏節(jié)為平臺(tái),圍繞代表性非遺項(xiàng)目,打造集文化展示與傳承、經(jīng)貿(mào)、旅游為一體的特色文化發(fā)展區(qū),實(shí)現(xiàn)了非遺與地方經(jīng)濟(jì)的互嵌式發(fā)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形成需要一個(gè)“物化”過(guò)程,即通過(guò)將其傳遞的精神思想、價(jià)值觀念凝聚在一定的客觀物體或物質(zhì)環(huán)境上,給廣大人民群眾一個(gè)具體實(shí)際、形象直觀的接受情景,而這需要通過(guò)滿(mǎn)足個(gè)體需求得以實(shí)現(xiàn)。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直接或間接地將無(wú)形的文化轉(zhuǎn)變?yōu)橛行蔚呢?cái)富,滿(mǎn)足了人們的物質(zhì)需求、社會(huì)需求和精神需求,形成了以文化為紐帶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yùn)共同體,為共同體內(nèi)的成員共筑精神家園注入永續(xù)力量。
三、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的地方實(shí)踐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
近年來(lái),我國(guó)各級(jí)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試驗(yàn)區(qū)建設(shè)的實(shí)踐意義與理論價(jià)值日益彰顯,具體表現(xiàn)為保護(hù)主體多元化、保護(hù)內(nèi)容層級(jí)化和全面化、保護(hù)方式活態(tài)化。從各級(jí)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的規(guī)劃方案和建設(shè)實(shí)踐來(lái)看,區(qū)域內(nèi)各族人民在非遺整體性保護(hù)過(guò)程中的參與感、認(rèn)同感和獲得感得到了顯著提升,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得到了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
(一)保護(hù)主體多元化——強(qiáng)化區(qū)域內(nèi)成員的參與感,形成行動(dòng)共同體
《非遺法》第七條和第九條規(guī)定,我國(guó)非遺保護(hù)的原則是政府主導(dǎo),鼓勵(lì)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參與。從我國(guó)非遺保護(hù)工作發(fā)展歷程來(lái)看,在啟動(dòng)初期,政府主導(dǎo)發(fā)揮更大的作用,而在保護(hù)工作走上常軌后,非遺社區(qū)、傳承人群的主動(dòng)性更受重視。在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過(guò)程中,我國(guó)逐漸形成了政府引導(dǎo)+民眾參與+組織協(xié)助的非遺多元保護(hù)主體模式,打破了非遺碎片化管理方式,形成了跨區(qū)域、多層級(jí)、多部門(mén)的聯(lián)動(dòng)機(jī)制,促成了更大范圍內(nèi)以非遺為核心的多種資源調(diào)度,激發(fā)和增強(qiáng)了社會(huì)組織和當(dāng)?shù)孛癖娮杂X(jué)參與非遺保護(hù)的意識(shí)。
首先,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需要政府部門(mén)發(fā)揮統(tǒng)籌和協(xié)調(diào)作用。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的設(shè)置雖然以文化要素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圈作為重要?jiǎng)澐謽?biāo)準(zhǔn),但同時(shí)也是一個(gè)覆蓋面積廣大、輻射人口眾多、發(fā)展程度不平衡的復(fù)雜文化生態(tài)系統(tǒng)。《國(guó)家級(jí)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管理辦法》指出,依托相關(guān)行政區(qū)域設(shè)立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區(qū)域范圍為縣、地市或若干縣域。例如,閩南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涵蓋福建省漳州、泉州、廈門(mén)三市12個(gè)區(qū)、4個(gè)縣級(jí)市、13個(gè)縣,徽州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則橫跨安徽省和江西省的三個(gè)市。在同一個(gè)文化圈內(nèi),行政區(qū)域的疊合、文化遺產(chǎn)的龐雜、生態(tài)與文化系統(tǒng)的平衡都需要政府自上而下地進(jìn)行整體規(guī)劃、資源調(diào)度和統(tǒng)籌推進(jìn)。例如,海洋漁文化(象山)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建設(shè)中,象山縣加強(qiáng)頂層設(shè)計(jì),形成了“政府主導(dǎo)、部門(mén)為主、鄉(xiāng)鎮(zhèn)聯(lián)動(dòng)、人大督查”的強(qiáng)大合力。熱貢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成立黃南熱貢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管理委員會(huì),負(fù)責(zé)文化區(qū)建設(shè)規(guī)劃的制定和實(shí)施,對(duì)區(qū)域內(nèi)的非遺進(jìn)行挖掘、鑒定、申報(bào)、審核、保護(hù)與傳承,對(duì)非遺項(xiàng)目及其保護(hù)資金進(jìn)行統(tǒng)一管理,并開(kāi)展相關(guān)建設(shè)項(xiàng)目招商引資等工作。政府部門(mén)利用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內(nèi)的文化資源開(kāi)展公共建設(shè),為區(qū)域內(nèi)的非遺傳承人、非遺傳習(xí)者、消費(fèi)和體驗(yàn)非遺的普通居民參與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共享建設(shè)成果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其次,民間組織在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中發(fā)揮著主體性和帶動(dòng)性作用。《文化部關(guān)于加強(qiáng)國(guó)家級(jí)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的指導(dǎo)意見(jiàn)》明確指出,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要堅(jiān)持人民文化主體地位原則。非遺主要產(chǎn)生于民間,民間組織在非遺的創(chuàng)新性轉(zhuǎn)化、專(zhuān)業(yè)技術(shù)指導(dǎo)、社會(huì)監(jiān)督保障等方面具有先天優(yōu)勢(shì),是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過(guò)程中溝通政府與個(gè)體之間的橋梁。更重要的是,支持和鼓勵(lì)民間組織參與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能夠使區(qū)域內(nèi)的民眾意識(shí)到,非遺是“民俗”而非“官俗”,非遺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guān),從而將非遺保護(hù)視為一種責(zé)任和義務(wù),自覺(jué)主動(dòng)地參與非遺的保護(hù)、傳承和發(fā)展。2007 年以來(lái),我國(guó)先后設(shè)立的21 個(gè)國(guó)家級(jí)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大多成立了非遺保護(hù)自組織,例如濰水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的工藝美術(shù)協(xié)會(huì)、核雕協(xié)會(huì),熱貢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的藏戲研究中心、黃南州熱貢文化協(xié)會(huì)。成立這些民間組織的原動(dòng)力除了政府的大力引導(dǎo)之外,還凸顯出地方民眾的內(nèi)生性力量,從表面上看,這種內(nèi)生性動(dòng)力是由文化市場(chǎng)化所催生,但其深層邏輯則是根植于內(nèi)心的文化認(rèn)同。
加強(qiáng)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基礎(chǔ)支撐,促進(jìn)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動(dòng)力機(jī)制則由政府/國(guó)家主導(dǎo)的“傘式社會(huì)”力量和民間主導(dǎo)的“蜂窩式社會(huì)”力量共同構(gòu)成。非遺區(qū)域性整體保護(hù)的多主體性,其意義和價(jià)值并非保護(hù)非遺本身,而是將自上而下的“傘式社會(huì)”力量和自下而上的“蜂窩式社會(huì)”力量充分融合,實(shí)現(xiàn)區(qū)域內(nèi)更多個(gè)體(群體)的交流互動(dòng)。在此作用下,非遺不再局限于特定群體,而是作為大眾認(rèn)同的公共文化演進(jìn)和重塑,這種認(rèn)同傾向于群體的文化自覺(jué)和集體歸屬感。政府引導(dǎo)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的同時(shí),也是向該區(qū)域的人們傳輸我國(guó)主流價(jià)值觀和精神思想的過(guò)程,在此過(guò)程中,個(gè)人、企業(yè)或其他社會(huì)組織積極參與非遺保護(hù)和開(kāi)發(fā)利用,在平等交流與資源互嵌中作為文化創(chuàng)造者的主體身份和地位得以強(qiáng)化,經(jīng)濟(jì)收入的增加和文化的享受,使共同體中的每個(gè)成員在無(wú)形之中提升了群體內(nèi)聚力。
(二)保護(hù)內(nèi)容層級(jí)化、全面化——增強(qiáng)區(qū)域內(nèi)成員的認(rèn)同感,形成命運(yùn)共同體
有別于經(jīng)濟(jì)區(qū),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是指在特定的自然和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區(qū)域中有形的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和無(wú)形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等相依相存,并與人們依存的自然和文化生態(tài)環(huán)境密切相關(guān)和諧相處。麻國(guó)慶認(rèn)為,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的核心內(nèi)容,是以非遺為核心,著眼于維護(hù)、修復(fù)和滋養(yǎng)一個(gè)區(qū)域的文化生態(tài),有計(jì)劃的、動(dòng)態(tài)的整體保護(hù),其關(guān)鍵在于如何實(shí)現(xiàn)非遺保護(hù)與地方社會(huì)協(xié)調(diào)發(fā)展。具體來(lái)說(shuō),要把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納入國(guó)民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發(fā)展規(guī)劃以及城鄉(xiāng)發(fā)展規(guī)劃中,根據(jù)具體文化區(qū)域的實(shí)際,實(shí)現(xiàn)非遺保護(hù)與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保護(hù)相結(jié)合,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和自然生態(tài)保護(hù)相結(jié)合。
羌族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位于“5·12”汶川地震的重災(zāi)區(qū),地震不僅對(duì)該地區(qū)的自然環(huán)境造成了巨大破壞,也對(duì)羌族非遺資源及其保護(hù)成果造成了嚴(yán)重破壞。據(jù)統(tǒng)計(jì),地震造成了各級(jí)非遺代表性傳承人12 人死亡、97 人受傷,眾多非遺傳承人家園被毀,大量羌族文化的重要存續(xù)空間——羌族村寨或被夷為平地或嚴(yán)重受損。2008 年10 月,文化部批準(zhǔn)設(shè)立羌族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實(shí)驗(yàn)區(qū)建設(shè)被納入國(guó)家汶川地震災(zāi)后重建總體規(guī)劃中。根據(jù)區(qū)域內(nèi)不同文化生態(tài)特征、震后不同受損程度、民族分布以及不同非遺類(lèi)別,試驗(yàn)區(qū)將搶救和保護(hù)羌族文化與震后家園重建有機(jī)結(jié)合,設(shè)立了核心區(qū)域和一般區(qū)域,對(duì)區(qū)域內(nèi)的非遺由搶救性保護(hù)過(guò)渡到整體性保護(hù),在充分尊重羌族民眾的意愿和選擇的基礎(chǔ)上,對(duì)震后基本為原址重建的村寨(例如阿壩州理縣蒲溪鄉(xiāng)休溪村),盡可能按原貌恢復(fù)和制造非遺用具及非遺文化空間。對(duì)完全異地重建的村寨建設(shè)新的非遺傳承空間。
家園是人們生活的依托,家園的重建除了居住空間,還應(yīng)包括文化空間與精神空間。如果說(shuō)羌族居住空間在政府的大力幫助下能夠在短時(shí)間內(nèi)得以重建,那么文化空間和精神空間的建設(shè)則相當(dāng)漫長(zhǎng),并較多地依賴(lài)非遺。羌族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實(shí)驗(yàn)區(qū)的設(shè)立和建設(shè),實(shí)現(xiàn)了以人為中心的非遺保護(hù)、物質(zhì)文化傳統(tǒng)保護(hù)和自然環(huán)境保護(hù)的和諧統(tǒng)一,充分發(fā)揮了非遺的文化治理功能,強(qiáng)化和重塑了更大范圍內(nèi)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成員的家園情結(jié)、家國(guó)情懷和命運(yùn)共同體意識(shí),為人們?cè)诿鎸?duì)災(zāi)難時(shí)重建家園樹(shù)立了信心。更重要的是,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增強(qiáng)了人民的文化自覺(jué)意識(shí),增進(jìn)了民族團(tuán)結(jié)、民族自信和民族凝聚力,為共同建設(shè)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奠定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
(三)保護(hù)方式活態(tài)化——提升區(qū)域成員的獲得感,形成利益共同體
馬克思曾說(shuō):“要使各民族真正團(tuán)結(jié)起來(lái),他們就必須有共同的利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的形成需要以一定物質(zhì)基礎(chǔ)作為支撐,物質(zhì)需求的滿(mǎn)足是精神建設(shè)的基礎(chǔ),只有建立起共同的利益基礎(chǔ),才能將人們凝聚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體,進(jìn)而形成命運(yùn)共同體和文化共同體,構(gòu)建起真正的共有精神家園。以非遺保護(hù)為核心的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在一定程度上實(shí)現(xiàn)了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在此過(guò)程中,非遺得到了活態(tài)保護(hù)與傳承,區(qū)域內(nèi)各民族成員實(shí)現(xiàn)了利益共享,人民的外在獲得感(參與文化生態(tài)保護(hù)區(qū)建設(shè)帶來(lái)的直接經(jīng)濟(jì)利益)與內(nèi)在獲得感(非遺作為公共資源和群體文化符號(hào))得以提升,這是我國(guó)鞏固和發(fā)展平等、團(tuán)結(jié)、互助和諧社會(huì)主義民族關(guān)系的必然要求,是我國(guó)作為《保護(hù)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公約》締約國(guó)的履約實(shí)踐,在講好中國(guó)故事的同時(shí),也為世界各國(guó)非遺保護(hù)提供了中國(gu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