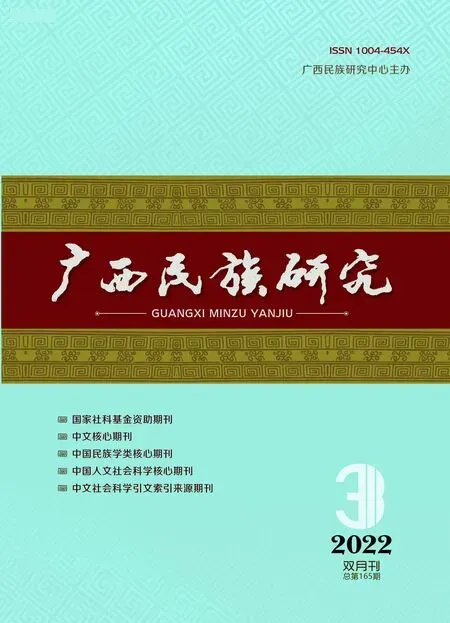明代云南治邊實踐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黃 超 安學斌
晚明李贄在所著的《焚書》中,對明朝治理云南200 余年的歷史,做了以下評價:“夫滇南迤西,流土并建,文教敷洽,二百余年矣。蓋上采前王封建之盛制,下不失后王郡縣之良規者也。夫前有封建,其德厚矣,而制未周;后有郡縣,其制美矣,而德未厚。惟是我朝,上下古今,俯仰六王,囊括并包,倫制兼盡,功德盛隆,誠自生民以來之圣之所未有也。”李贄的評價雖有溢美之處,但仍肯定了明朝在治理云南過程中,建立制度、推行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幾十年之后,清初戴名世在其所著的《南山集》中,對明朝治理云南的歷史,也做出了“承平且三百年,其富麗擬於中原矣”的評價。然而,根據晚明陳全之所著《蓬窗日錄》、清初鄭大郁所著《經國雄略》等文獻記載,明初的云南卻是“崇岡嶻嵲,激澗縈紆,城郭人民,夷居十七,時恬則蜂屯蟻聚,有事則獸駭禽奔,蓋人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本中國梁州裔境。臨于徼外,為諸蠻雜處,人自為險,勢難統一者也”。從“臨于徼外”“勢難統一”到“生民以來之圣之所未有也”“富麗擬於中原矣”。李、戴、陳、鄭4 位學者的論述,雖有時間、空間的描述差別,但通過比對,研究者依舊可以看到明朝治理下云南發生的歷史巨變。
云南古稱梁州,按“五服”劃分屬于“要服”。“滇南僻處萬里,古稱要服”,雖然遠在中央王朝核心統治區外,但地理位置卻極為重要。根據清初顧炎武所著《天下郡國利病書》的描述,云南的地理位置是“綢繆防御不可不周者,以滇、黔與楚、蜀輔車唇齒之勢也。說者謂云南山川形勢,東以曲靖為關,以霑益為蔽;南以元江為關,以車里為蔽;西以永昌為關,以麓川為蔽;北以鶴慶為關,以麗江為蔽。又云南要害之處有三:東南八百、老撾、交阯諸蠻,以元江、臨江為鎖鑰;西南緬甸諸蠻,以騰越、永昌、順寧為咽喉;西北吐蕃,以麗江、永寧、北勝為阨塞。識此三要可以籌云南矣”。正因為云南的地理位置極為重要,自秦開五尺道后,云南與內地交往聯系逐漸增多,到了明朝時期,明朝統治者在承繼前代“因其政不易其俗,順其性不拂其能”治邊實踐的基礎上,結合所處時代特點,采取了一系列的新政,加快推動云南與內地的一體化進程。陳碧芬就此指出,在云南歷史地位的動態發展變遷過程中,明代是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轉折時期。這一時期,是云南成為“腹地”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而隨著云南與內地一體化進程加快,各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也大大加深,翻閱與之有關的《云南圖經志書》《滇志》《萬歷云南通志》等方志典籍,到處可見,諸如“府治之近,多舊漢人,乃元時移徙者,與僰人雜處,而服食器用及婚姻喪葬、燕會饋餉之俗,大抵同風”,“士知向學,科第相仍。男事耕藝,女務織紡”,“昔惟緬字,今漸習書史。民風地宜,日改而月化”等。
費孝通曾在其文集中談到,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由此可見,不管是在“自在”階段,還是“自覺”階段,中華民族都是以“實體”的面貌出現,且隨著時間的發展,其自身的包容度、凝聚度均呈不斷強化狀態,最終形成了由中華各民族所共同組成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及孕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相較于“自覺”民族實體近代的百年淬煉,“自在”民族實體可言古代的千年浸潤,且“自覺”以“自在”為基礎,如果沒有“自在”的基礎,“自覺”必不能成型,而“自在”的形成,說到底,離不開歷代中央王朝對邊疆的治理。以云南為例,云南作為中國西南邊疆的重要省份之一,自古以來就是多民族的主要聚居區,元代以降,在元明清三代“大一統”王朝的努力推動下,云南在清代被正式劃為內地十八行省之一。從“內”到“外”的轉變,是云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加深,更是云南各民族對中央王朝邊疆治理中“國家認同”的肯定,而云南各民族則在“交往交流交融中逐漸建立起彼此間的緊密關系,發展出不同程度的共同特征”,進而為奠定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孕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做出了“云南貢獻”。結合陳碧芬所說的明代“承上啟下”的重要轉折期,有必要就有明一代的云南治邊實踐做一個系統性的探究,從而窺探其在“奠定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孕育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中的歷史作用。
一、洪武入滇與明朝在云南統治的確立
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鑒于云南“孤處遐荒,猶未臣服”的分裂狀況,派遣翰林侍制王祎出使云南,意在勸服元梁王把匝剌瓦爾投誠歸降。王祎到了云南后,幾經勸說,梁王出現了“意動”的傾向。然而,偏巧此時盤踞大漠的元廷派使者脫脫到云南向梁王“征糧餉”,知曉了明廷使者王祎出使云南的消息。在元使脫脫的脅迫下,梁王被迫處死了王祎。王祎死后,明太祖仍沒有放棄“以和招撫”的策略,又于洪武八年(1375),派遣湖廣參政吳云陪同梁王降使鐵知院等人再次出使云南,結果在行至至云南沙糖口時,鐵知院叛變,在說服吳云投降未果的情況下,遂將吳云殺害。
兩次出使的失利,促使明太祖堅定了“以戰統一”的決心。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派遣以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為左、右副將軍,率領30萬大軍征討云南。臨行前,明太祖向諸將做出了如下戰略部署:“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出一軍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乃云南之襟喉,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令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援永寧之師,大軍直搗云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云南既克,分兵趨大理。先聲既振,勢將瓦解,其余部落,可遣人招諭,不必皆煩兵也。”傅友德等明軍將領在行至湖廣地區時,采取明太祖的進軍策略,一方面命令胡海洋等明軍將領率兵由永寧直趨烏撒,另一方面則親率主力并會同沐英等將領率兵趨貴州、攻普安、普定,兵鋒直指云南“襟喉”曲靖。梁王把匝剌瓦爾聞明軍將至,先是派遣司徒平章達里麻率精兵十萬,抵抗傅友德大軍,然而在白石江戰役中達里麻大軍遭到重創,《國史紀聞》記載為“英縱鐵騎衛其中堅,敵披靡,遂大敗,死者不可勝計,橫尸十余里。生擒達里麻,俘其眾萬余”。白石江戰役后,傅友德大軍一舉攻克曲靖,梁王聞訊,被迫率領其家人退守滇池島。最后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梁王“焚其龍衣,驅妻子俱赴滇池死”。
梁王兵敗身死,傅友德等明軍將領對大理段氏等地方割據勢力又進行了一系列的征戰。在此期間,大理段氏末代總管段明曾致信傅友德,要求“請依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篆,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試圖繼續保持相對獨立的半割據狀態,但遭到了傅友德“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的嚴詞拒絕。大理段氏覆滅后,車里、平緬等地的土司迫于大勢所趨,相繼歸降傅友德等明軍將領。洪武十五年(1382)二月,傅友德等明軍將領最終實現了“云南悉平”的戰略目標。由此,開啟了明朝對云南200余年的統治歷程。
二、“華夷無間”“一視同仁”理念指導下的明代云南治邊實踐
統一戰爭結束后,如何治理“西南極境,蠻僚錯雜,種類繁多,且疆域遼邈,山川盤結,林箐深茂,物產繁饒”的云南,就成為明太祖及其繼承者所必須思考的重要問題,而作為明朝開國帝王的明太祖,其治理態度、治理觀念如何,必然會影響到其歷代繼承者的治理態度、治理觀念。翻閱《明實錄》,明太祖的兩段言論頗為重要,一則為“朕既為天下主,華夷無間,姓氏雖異,撫字如一”,另一則為“圣人之治天下,四海之內,皆為赤子,所以廣一視同仁之心。朕君主華夷,撫御之道,遠邇無間”。“華夷無間”“一視同仁”,從中可以看出明太祖敢于打破傳統“華夷之辨”觀念的束縛,而確立其一種民族關系相對平等的理念。正是在這樣一種理念的指導下,明太祖及其繼承者們,采取了一系列舉措予以推動明代云南的治邊實踐。
(一)承繼創新:明代云南治邊實踐中的制度設計
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明太祖發布諭旨,就云南平定后的制度設計做出清晰的擘畫:“今云南既克,必置都司于云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必置都司于云南”“必置布政司”,“都司”即都指揮使司,“布政司”即布政使司,上述兩個機構均為明代所設立的地方行政機構,分別掌管軍政及民政。明太祖此舉意在將云南的行政體系納入中央王朝的整體行政體系中,從而便于中央直接管理。于是,在洪武十五年(1382)閏二月,“詔置云南布政使司、都司及各州縣”,洪武三十年(1397)正月,“始置云南按察司”。至此,以“三司”機構設立為標志,云南地方行政事務被納入到中央王朝管轄范圍中,從而使中央集權得以加強,在確保中央政令得以暢通的同時,確保了云南與中央的步調一致、全面發展。
此外,考慮到云南“大寓西南,百夷叢集”的歷史現狀,為了避免出現社會動蕩,明太祖及繼承者們,一方面“留西平侯沐英鎮守云南”,開啟沐氏家族世代鎮守云南的序幕;另一方面“踵元舊事,悉加建設”,不僅承繼了元代設立“參用其土人”的土司制度,“就土官而統馭之,分宣慰使、宣撫使、安撫使、正副長官司、土府、土州以治之”,還在元代設立的土司制度基礎上,對土司的品秩、俸祿、朝貢、征調等方面,進行了嚴格規定,從而實現“額以賦役,聽我驅調”的目標。
“三司”的設立、沐氏家族世鎮體制的形成及對土司制度的改造,體現了明朝在治理云南過程中的承繼創新精神,而這種精神則在制度層面加強了中央政府對云南管轄的法理依據,適應了云南民族眾多、社會生產較為落后的現狀,對推動云南與內地一體化發展提供了制度保障。
(二)善擇良吏:明代云南治邊實踐中的官吏任用
“朝廷設官,凡以為民也。而郡縣之官,于民最親。邊方之民,去朝廷最遠,官于民有最親也,則不可不擇其人以任其官。”這是明代正德年間時任云南巡撫何孟春關于“邊疆擇吏”的論述,通過何孟春的論述,不難看出選擇“良吏”對于邊疆穩定的重要性,而以“抗疏極諫”著稱的何孟春,在擔任云南巡撫期間,除了平定以阿勿、阿寺為首的十八寨叛亂外,還積極加強鞏固云南邊防力量,如“奏設永昌府,增五長官司、五守御所”等。
何孟春仕宦云南僅僅是明朝在云南200 余年治邊實踐中的一個典型代表人物。事實上,縱觀有明一代的云南官吏任用,“謹修內治,廉察邊吏,毋令貪吏需索,結怨起釁”幾乎成了一條必須遵守的原則。此外,為了更好督察官吏,明成祖還創設了巡按云南監察御史,“御史巡按,則代天子狩,轄所按藩服大臣、若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大事奏裁,小事立斷”,以此督促云南各級官員勤勉任職。雖然中央政府在云南官吏任用上也錯誤使用了諸如程宗等人,但從總體趨勢看,有明一代中央政府在云南官吏的任用上依舊是“良吏”為主。除前述的何孟春外,明初的張紞、明中的王恕、明末的陳用賓,都是明朝云南有名的治邊良吏。
張紞在洪武年間擔任云南左布政使期間,“凡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經費程度,皆為裁定,夷民悅服”,后張紞被擢拔為吏部尚書,云南民眾對張紞離任倍感惋惜,以致出現“如失父母”之感;王恕,在成化年間,擔任云南巡撫期間,不僅同時任云南鎮守太監錢能的不法行徑做了堅決斗爭,促使錢能“虐焰少挫”,還積極利用手中權柄為民眾做了許多好事,如上奏朝廷減輕民眾負擔,減少“貢品”索取,積極加強武備,防止安南進犯等,此外,王恕在擔任云南巡撫期間,自身也保持著廉潔的品行,“王端毅公恕來巡撫云南,不挈僮仆,唯行灶一,竹食羅一,服無紗羅,日給唯豬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水皆取主家給狀,再無所供”,后王恕被錢能“廣以金寶饋當路”的方式所排擠,被迫改任南京,聽聞此訊,云南民眾對王恕改任痛心疾首,以致編出了“王恕再來天有眼,錢能不去無樹無皮”的民謠;陳用賓,在萬歷年間,擔任云南巡撫期間,不僅上疏力陳礦稅之弊,直言“其裨國用也甚微,其誤國用也甚大”的弊端,還積極設立“八關二堡”,以防備緬甸的入侵,后因“武定失印”事件,逮訊下獄死,云南民眾對此多“憐之”,以致發出了“議者竟以失印為罪案。非夫!”的慨嘆。
張紞、王恕、陳用賓等為代表的云南“良吏”,在施展自身政治抱負的同時,也贏得了云南民眾的普遍認可,從而拉近了云南民眾與中央王朝的距離,確保了國家治理體系的向下延伸。
(三)大興文教:明代云南治邊實踐中的文化浸潤
開展文教,實現“以夏變夷”的目標,早在先秦時期就已逐漸形成。孟子對此闡述為:“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此后的歷朝歷代,除了少數王朝刻意強化“華夷之辨”“華夷對立”的觀念外,大多數王朝都會在自身所轄的領地內,實現“以夏變夷”的政策,即不遺余力的向邊疆民族聚居區傳播儒家文化,由此實現各族民眾在思想上的“大一統”。
早在洪武初年,明太祖便提出了“武功以定天下,文教以化遠人”的“文武并用”戰略思想。隨著統一事業的不斷加快,云南等地相繼納入中央政府統治的版圖。針對“云南一省夷居十之六七,百蠻雜處,土酋割據”的現實情況,為了明太祖發表了如下詔令:“邊夷土官,皆世襲其職,鮮知禮義。治之則激,縱之則玩。不預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邊夷土官,皆設儒學。選其子孫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之知君臣父子之義,而無悖禮爭斗之事,亦安邊之道也。”在此詔令的影響下,明朝開始了200余年向云南等地系統傳播儒家文化的歷程。
傳播儒家文化,學校是衡量其興旺程度的重要指標。因為在中國古代社會,學校不僅是傳授儒家學說的地方,還是科舉考試的必由之路。所謂“科舉必由學校”,無疑也是凸顯學校的重要地位。有明一代,是云南學校快速發展時期,據石碩等學者的統計,明代云南書院共72所,儒學共72所。盡管從分布上看,這些學校大多集中在滇中、滇東的云南、大理、臨安等地區,分布有差異,但學校的建立,還是使儒家文化在云南各地普遍傳播開來,以大理地區為例,自從源泉書院、明志書院、金華書院等學校建立起來,“頓使四境之內,藹然生弦誦之風矣”,“南向以來,登科第者日漸以盛,作興有徵矣”,“建立學校以化導之,故百余年,氣習丕變,風俗淳美,父子兄弟各盡其道,士農工賈各精其業,衣冠文物彬彬然”。“氣習丕變”“登科第者日漸以盛”的背后,是儒家文化廣泛傳播的結果,更是云南各族民眾“心向”中央的直接體現,而在此影響下,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儒家綱常體系逐漸成為云南地區各族民眾的行為準則,中華文化的向心力進一步增強。
(四)移民興邊:明代云南治邊實踐中的人口遷移
云南初定伊始,“遠隔絕徼,山川阻修”的地理環境,加之“夷居十七”的人口分布,促使“屯田”政策的興起。洪武十九年(1386),黔國公沐英向明太祖上奏道:“滇南地廣,宜置屯田,令軍士開耕以備邊儲”。沐英的“屯田”政策,著眼于“以備邊儲”的長遠計劃。明太祖對此十分認可,當即下詔:“屯田之政,可以紓民力足兵食,邊防之計莫善于此”。在“屯田”政策的影響下,明代開始了大規模由“內地”向“滇南”的移民潮。
李中清在《中國西南邊疆的社會經濟:1250—1850》一書中指出,十六世紀漢族人口已增長到西南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而據《明會典》記載,洪武二十六年(1393),云南共有戶數五萬九千五百七十六戶,人口二十五萬九千二百七十口,萬歷六年,云南共有戶數一十三萬五千五百六十戶,人口一百四十七萬六千六百九十二口。云南的戶數、人口從洪武末年一直到萬歷初年,分別增長了約2.28 倍和5.7 倍。人口的增長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繁衍,但更重要的來源在于內地漢族移民。大量的漢族移民,或從征入伍、或舉家遷移、亦或流徙發配,從內地的不同省份相繼前往云南安家落戶,他們的到來,改變了云南不少地區民族結構單一的格局,形成了民族雜居的局面,如云南府,自內地漢人到來之后,云南府出現了“云南土著之民不獨僰人而已,有曰白羅羅、曰達達、曰色目,及四方之為商賈、軍旅移徙曰漢人者雜處焉”的情況。此外,隨著內地漢族移民的到來,內地的農業生產技術、手工技術乃至民俗也隨之傳入,這些技術和民俗,一方面,改善了云南少數民族的物質生活,促進糧食生產和手工業技術進步,以致出現“今諸衛錯布于州縣,千屯倫列于原野。收入富饒,既定以紓齊民之供億”、“器用陶、瓦、銅、鐵,尤善采漆畫金。其工匠皆廣人,與中國侔。漆器貯鮮肉數日,不作臭;銅器貯水,竟日不冷。江海舳艫,與中國同”的現象;另一方面,在長時間的相處過程中,漢族的民俗逐漸為少數民族所接受,“婚姻論門第,力耕致富”,“衣冠禮義,悉效中土”,這無疑是“以漢化夷”的最好例證。與此同時,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多,刺激了消費需求,云南地區的商業也有一定發展。雖然與內地相比,云南地區一直以“貝”為貨幣,直到天啟五年(1625)才實現了“舊俗用貝,議者以滇產銅,用錢興利甚便,至是始易之”的“廢貝行錢”變革,但人口增多及需求旺盛,還是刺激了大量商賈“不脛而走四方”。在商賈的活動下,大理、麗江、“三宣六慰”等地出現了“城中居廬亦甚盛,而北門外則阛阓皆聚焉”,“今麗江其地也,江滸沙泥金麩雜之,貧民淘而煅焉,日僅分文,售蜀賈轉諸四方”,“閩、廣、江、蜀居貨游藝者數萬,而三宣、六慰、被攜者亦數萬”的繁榮景象。
人是文化的“載體”,文化也是人的“反映”。明代云南大規模的移民,最初的意義是為了“屯政”所需,但卻在客觀上促進了云南少數民族與內地漢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促使兩方在交往交流交融過程中,增進了彼此的了解,做到了民心相通。
三、明朝云南治邊實踐成效
然而歷史的前進,并非是以某一帝王的意志或某一事件的發生為轉移,立足“馬克思主義大歷史觀”的立場,將“回顧往昔、立足現在、開創未來三者作為一個統一整體”理念為治史思路,重新審視明朝云南治邊實踐的歷史進程,可以發現,明朝為后世留下了如下歷史遺產。
(一)云南與內地一體化進程加快
云南因其處于“要服”的地理位置,加之“多夷少漢”的歷史現狀,元代以前,一直未能有效被中央政府所管轄。元代以降,云南逐漸被納入中央政府的管控范圍,“賦役之,比之內地”。延至明代,除“三宣六慰”等少數地區保持著一定程度的“羈縻治理”外,云南大多數地區均已納入中央政府的管轄范圍,且消除了諸如大理段氏這樣長期割據一方的世家大族勢力,確保了地方安定。此外,明朝還采取了一系列從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著眼的舉措,從而營造了云南少數民族與內地漢族一起開發云南、建設云南的氛圍,在這種氛圍推動下,不僅內地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手工技術為云南廣大少數民族群眾所掌握,進而轉化為物質財富,而且內地的儒家文化、節日風俗也為云南廣大少數民族群眾所認可,進而成為精神依托。明人高岱對此稱贊到:“自古及今,未有郡縣其地,二百年寧謚底定無反側如今日之盛者。蓋由我圣祖神謨圣略,而諸將規畫甚詳,經略甚當,故能變荒裔之民為文明之俗”。
經過明代的系統治理,到了明末,雖然云南“江外”的少部分地區,依舊保持著其民族的風格特性,如“三宣官目,蓄發加冠;六宣土官舍把,亦惟禿頭,戴六舍五彩尖頭夷帽”。但從全局上看,云南的大部分地區已逐漸納入華夏文化體系,不僅實現了“書同文、車同軌、法同律”的外在管轄一致,還實現了“內圣外王”的文化心理一致,由此,云南與內地一體化的進程達到了新的高度。
(二)云南各族民眾“國家認同”增強
根據方立江的解釋,國家認同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對自己歸屬哪個國家的認知以及對這個國家構成要素,比如政治、文化、民族等要素的評價和情感。回歸到明代的歷史語境,由于中國古代“家天下”的政治體制,帝王既是國家最高統治者,又是民眾最高精神領袖,所以對“帝王”盡忠,也就是對“國家”盡忠。因此,明代的“國家認同”是指對以帝王為核心的明代中央政府的認同。雖然這種做法不啻將君王神圣化、神秘化,但對于培養民眾思想深處的“大一統”觀念,維系中國社會長期穩定、確保民眾生活安居樂業確實有著巨大作用。
在明朝大力倡導下,特別是“文化浸潤”的影響下,云南各族民眾的“國家認同”大大加深。縱觀有明一代的云南政治人物,不僅出了如以“愛樂賢士大夫”聞名的內閣首輔楊一清、以“樸忠”聞名的兵部尚書傅宗龍等封疆大吏,也出現了如蒙化左氏土司左近嵩、石屏州土司龍在田這樣“心向中央”的地方土司:前者在參與平定奉赦、猛廷瑞叛亂的同時,積極在所轄區域內大興文教,“勸勉族人左重、左宸、左壂勤學應試節中鄉科”,獲得“睦族崇文”“愛士興文”的匾額;后者則參與了平定普名聲、吾必奎叛亂,并參與了明朝對中原農民軍的軍事行動,在取得“凡五載,捷二十有八”功績的同時,更發出了“臣愿整萬眾,力掃秦、楚、豫、皖諸寇,不滅不止。望速給行糧,沿途接濟。臣誓捐軀報國,言而不效,甘伏斧鑕”的誓言。
以楊一清、傅宗龍、左近嵩、龍在田為代表的云南籍政治人物的背后,是云南各族民眾對明朝“國家認同”的增強,正因為有這樣的“認同”,云南各族民眾在中央政府遭受內憂外患之余,才能挺身而出,為之效力。
(三)云南實現了由“徼外”到“腹里”的地位轉變
如前所述,云南作為“要服”之地,雖然地理位置遠離中央政權,但卻極為險要,且與中央政權的安危息息相關。林超民曾就“云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論述到:據有云南,就一定能一統天下;失去云南,就一定失去統一。縱觀明代以前的云南與中央政權關系,雖然總體趨勢是處于不斷加強的狀態,但也必須指出“云南”仍保持著相當大的獨立性,并建立起了一系列政權如唐朝的南詔政權、宋朝的大理政權等。這些政權的存在,不僅造成了數次“云南”與“中央政權”的武裝沖突,更重要的是導致了“云南”長期處于落后、邊緣的狀態。
明代以后,由于明太祖“定天下于一”的目標,加之在“華夷無間”“一視同仁”理念指導下,明太祖及其后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治滇舉措,促使云南“彬彬文獻,與中州埒”。在此影響下,云南“徼外屬性”弱化,“腹地屬性”增強,逐漸成為明代西南地區的重要屏障,這種情況,甚至延續到了明朝滅亡后,由于云南獨特的地理位置,它不僅成為永歷小朝廷行在,還成為“南明”抗清的物資供應、兵員輸出的重要基地,“據崎嶇一隅之地,以當興朝百戰之師”,前后支援近20年。而這一切的產生,恰恰說明了云南地位的歷史性巨變。
結語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為依托,并對其發展歷程、衍變由來做“能動反映”,它“以涵括56個民族生命存在圈的形式強調了多元一體的存續狀態,能動于共同體穩定的社會歷史聯系和共同文化心理,表現為中華各族命運與共、文化共享、心理共通、責任共擔的自知與自覺”。由此可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最大價值在于肯定了中國歷史上“多元一體”的民族格局,并在此基礎上建構了一套為中國境內的民族所信奉、認同的價值觀念。
習近平同志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首次提出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其后習近平同志又在2019 年的全國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2021 年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分別強調,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把民族團結進步事業作為基礎性事業抓緊抓好。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就是要引導各族人民牢固樹立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共同體理念。由此可見,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對于黨和國家民族工作的非凡意義。
一部中華史從某種程度上說,也是一部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正是因為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斷加深、加強,中國的疆域才得以不斷開拓、擴大,中華各族民族才得以形成“中華民族共同體”,并在形成過程中,逐步孕育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同理,中國歷史上的中央王朝所進行的治邊實踐活動,其出發點雖是為“一家一姓謀”,但其結果卻是充當了“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孕育的“歷史的不自覺的工具”,而學人要做的就是,從中提煉出歷史經驗,以為現實所參照。結合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在有明一代的云南治邊實踐中,中央政府從建制、擇吏、文教、移民四個主要方面進行著手,對西南邊陲要地——云南從各個方面加強了治理,推動了云南各族民眾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度聯系,實現了其所倡導的“天下一統,華夷一家”的執政目標。雖在執政后期,因帝制王朝自身的統治缺陷,造成了云南地區的動蕩,但其歷史功績不容抹殺,其遺留下的治邊歷史遺產則無疑為當今中國社會所倡導的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提供了歷史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