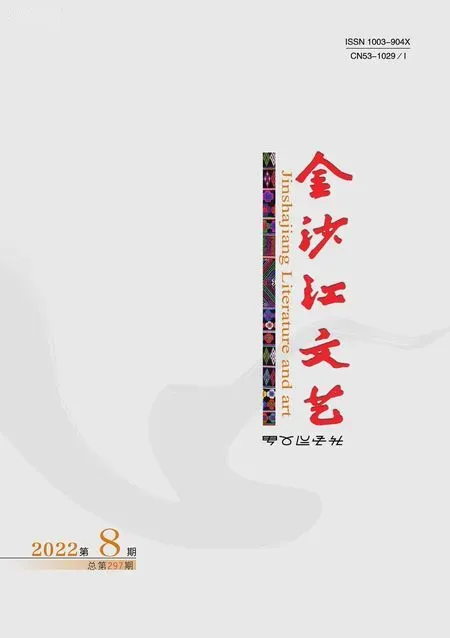曲 中 人
◎楊曉燕
病房里刺鼻的消毒水味,伴隨著從門縫里吹進來一股陰冷的風,無端的惶恐侵蝕著病房里的人們。
此時,我似乎能感受到父親漸行漸遠的生命,他陷在病床上的身體越來越單薄,那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冰冷儀器,就如一雙雙無形的手,一點點剝奪了父親臉上往日的神采,慢慢的,漸漸的,將父親的生命一點點抽走……
“爹,我們回去吧!這里風大。”傍晚時分,我在醫院里找了老半天,才發現他坐在花園的石凳上。
父親一動不動,期待的眼神看著遠處的天邊即將消逝的最后一縷霞光,手機里播放著令人傷感的二胡樂曲,婉轉悠揚中,清冷憂傷的旋律縈繞在父親周圍,幽怨至情的琴聲把父親搖搖欲墜的身影放大了數倍,忽然有種莫名的疼痛感撕咬著我的內心。
父親大概是在病房里呆得太久了,今天好不容易把纏在身上的那些管子拔掉,趁著上衛生間的機會偷偷溜出來花園里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順便聽一聽久違的二胡聲。
曾是軍人的父親,一直以來都是以國防身體自稱,如今卻突然病倒了,這近一米八的個頭,八十多公斤的體重,不到半年的時間就瘦得不成樣,似乎稍不注意就要被風吹走。
這以后,父親一天天,變得脆弱與倉惶,我們擔心他一閉眼就再也看不到這個美麗的世界。
恍惚中,我看到了父親年輕時那個高大的背影,那時候,父親很健壯,似乎有使不完的勁。但是就是這樣的一個身板,勞動力令人堪憂,沒有能力給我們娘兒幾個過上衣食無憂的日子也就罷了,卻不能幫助母親減輕更多的農活重活,我們姊妹幾個都對他多少有幾分成見,在一次和父親爭吵過后,我將近三個月都沒有喊過他一聲“爹”。父親似乎對此不太在意,依然樂呵呵地寵著我,什么事情都順著我意,而我對他終究冷著一張臉。
那一年我考上師范,父親甚是開心,刻意要送我,他將我的全部行李背在背上,腳步異常輕快,陪我走了十幾里的山路去趕車,我空手跟在他身后,還得一路小跑才能跟上。
濕式誘捕器投放高度20、40、60 cm處理誘捕茶尺蠖成蟲總量分別為321、158和148頭,平均每臺為 80.25、39.50 和 37.00 頭,可見高度 20 cm 處理誘捕量最多,并與其他2個處理均達到顯著差異,高度40和60 cm處理誘捕效果相當,因此,濕式誘捕器在茶園的最優投放高度為20 cm。
到了學校門口的時候,父親拉了拉已經弄皺了的勞動布服,拍打了幾下灰塵,臉上帶著憨厚討好的神情:“我就不進去了,你看我這身衣服,怕你同學見了給你丟人。你打飯菜時多打點,莫省……”我此時還是冷著臉,不接父親的話。父親轉而弓著腰客氣地和門衛說:“同志,我娃的行李放這兒,她一會來取……”然后在衣服上擦了擦手,從貼身衣袋里掏出一小疊用橡皮筋扎著的紙幣遞給我。
等我報到完畢到大門口拿行李的時候,父親已經走遠了,看著父親一身勞動布服的身影消失在車來車往的街道上,我終于哽咽出了一聲“爹……”任淚水洶涌而出。
等父親做了手術,身體稍微好轉了一些,醫生建議回家休養一段時間。為方便就醫,父親帶著他的二胡住進了我城里的家。每天晚上我下班回家,都會看到父親拿著他的二胡,戴著一頂鴨舌帽,也不開燈,坐在落地窗前,看著樓下人來人往的湖邊景色,拉著二胡。路燈清冷的微光灑在父親瘦削的臉上,此時的他顯得更加憔悴了。只見他長吁了一口氣,一手抱著琴筒,一手拉著弦,節奏不快不慢,時而如竹林流珠,時而如山澗水鳴,時而如燕子掠過水面……雙眉隨著節奏時而舒展,時而緊鎖。父親的身體隨著音樂的節奏而起伏著,完全沉浸其中。雖是夜晚,我似乎能夠感受到了琴聲里的陽光已經流淌進了父親的內心。那雙枯枝般的手嫻熟地在琴弦上滑動,仿佛此刻他才是人生最自由自在的時刻。
我打開燈,父親才發現我回家,于是把二胡收起來。打開電視,電視里正播放著電視連續劇,鏡頭里,一個小孩尿床,他母親正在斥責他,此情此景不由得讓我想起姑姑給我講的一個關于父親小時候的故事,故而問道:“爹,聽我姑姑說你小時候尿床,早上被我奶奶打了你的屁股,然后又罰你挑豬糞,有這回事吧?”父親張了張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其實那時,你小叔和我換了床鋪的位置。”
“那你白白挨了揍。”
“嘿嘿,你小叔他從小成績好,身子骨單薄,所以……”。父親依舊那副憨厚的口氣,此時的父親,一改病痛加身的不適,叨念著小時候和姑姑叔叔們的那些陳年往事,聽得出來,他對親人以及這個美好世界的種種不舍和依戀。
記憶中,父親是一個很講究的人,他年輕的時候喜歡穿干凈的衣服,喜歡拉二胡,喜歡用錄音機播放流行歌曲,喜歡趕時髦,一心向往著城市的生活,卻獨獨對干勞動不是那么用心。因此,在村里人和親戚朋友眼中,父親是一個不務實的人。
此時,祖母巴望著父親能回老家干農活,彌補勞動力不足的遺憾,而父親沒有如她所愿。祖母對父親愈加失望,家里的大小事情都不愿意放手給父親。
父親偶爾回家,跟著母親下地,但他干農活不太內行,經常被母親數落。家里蓋新房的時候,沒有耕牛的我家就靠人力下水去踩泥、和泥,但是父親不愿意下水,他只是在泥潭邊上接過母親遞上來的泥,用土墼模子制作著一個個土墼。如此種種,父親便遭了村里人的挖苦和家里人的責怪。
夏日的夜晚,山頂上的蒼穹閃爍著星星,黝黑的群山剪影把孤獨投擲到孩子們的心上。此時,我們家的院子里,就多起來了許多聽二胡的娃娃,他們拽著父親:“二叔,拉一段《白蛇傳》呀!”“二大爹,拉一個《小郎參軍要走了》”此時的父親,坐在家門前的石階上,嘴里叼著一根自制的煙卷,左手持著二胡,右手握著琴弓,琴筒放在膝蓋上,于是那些充滿鄉土氣息的調子和著孩子們的笑聲充滿整個小院子,這琴聲和笑聲吸引了眾多村里的男女老少,于是我家就成了簡陋的鄉村音樂吧。
父親是一個不善于表達感情的人,我那時候不懂音樂,卻能夠聽出父親二胡聲里的憂傷與快樂。母親有時候下地干活回來,看到父親還沒有做飯,屋子一片狼藉,母親就會和父親生氣,父親趕緊丟下二胡,匆匆忙忙幫著母親燒火做飯。
后來因為弟弟生病需要去省城手術,而手術費湊不夠,父親就把自己一件心愛的羊毛大衣變賣了,湊錢給弟弟看病。可是在祖母看來,這是沒有志氣的行為,還沒有窮到賣家當的地步,父親竟然如此不靠譜。受到數落的父親,拿出二胡,坐在門口,閉著眼,任琴筒里凄婉哀傷的調子恣意流淌,我湊近他,看到有淚痕滑過腮邊,我叫了他一聲,他急忙收住琴聲,拉著我進屋了。
“拉,拉,拉!你一天到晚只曉得拉二胡,拉二胡能填飽肚子?”祖母又開始叨叨。在外漂泊了多年,弟弟生病住院,住院費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父親已經和戰友們、工友們借了些錢,但那只不過杯水車薪。回到家里,父親依舊喜歡拉二胡,似乎只有沉浸在二胡聲中,父親所有的不如意才可以得以釋放。
為了照顧家里人,父親在城里繼續待下去的愿望落空了,辭掉了建筑工人的工作,回老家跟祖父學中醫,祖母說:“你這種腦子么怕是算了,莫要把老楊家的名氣給整沒了……”父親沒有接祖母的話茬,一個勁地悶頭和祖父學習,夜深人靜的時候,我們常常在睡夢中聽父親背那些中醫里的湯頭歌訣。后來,父親不甘心就此罷休,又想辦法自費去衛校脫產進修了幾年。機會往往是給有恒心毅力的人,父親終于學有所得,考取了鄉村醫生的資格證,回家接替了祖父赤腳醫生的崗位,開始正兒八經的養家糊口過日子。
幾年后,經過父母不辭辛勞的四處求醫問藥,弟弟的病醫治好了,盡管債臺高筑,但是父親的心情似乎輕松了不少。祖父母年歲漸高,父親協助母親挑起了撫育下一代,贍養兩個老人的重擔。對于這些,父親毫無怨言,只要有二胡聲相伴,似乎他的世界里都是光芒。
父親終究沒能逃過病魔的手,他走的那天,我回到家的時候,他靜靜地躺在床上,床頭依然掛著那把陪伴了他一輩子的二胡。
后來母親告訴我,父親因為在部隊腳受過傷,小腿韌帶拉傷過,再加上有關節炎,經常隱隱作痛,天陰下雨腳就會浮腫,干重活就疼痛,要是下水就會更加嚴重了,但是他為了不讓家人擔心,自己默默忍受著,也不做過多的解釋。此時,我才徹底理解了父親,覺得父親這輩子不容易,被誤解,被冷落,被嘲笑……可他沒有為自己辯解,依然善待生活,善待身邊的每一個人。
此時,再抬眼看看墻上掛著的二胡,它似乎吸收了父親生活中的霜和雪,吐出來的是光與暖。
這把承載著父親憂傷與歡樂的二胡依舊靜靜地掛在父親睡過的榻前,上面落滿了灰塵,它孤獨寂寞地躺在那里,無聲無息。它將父親人生歲月里的憂傷和喜悅,深深地烙在了骨子里。父親的琴筒里流出的曲調,是他生命的光芒……
不知何時,鄰居家播放的二胡聲打斷了我的思緒,再聽,已是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