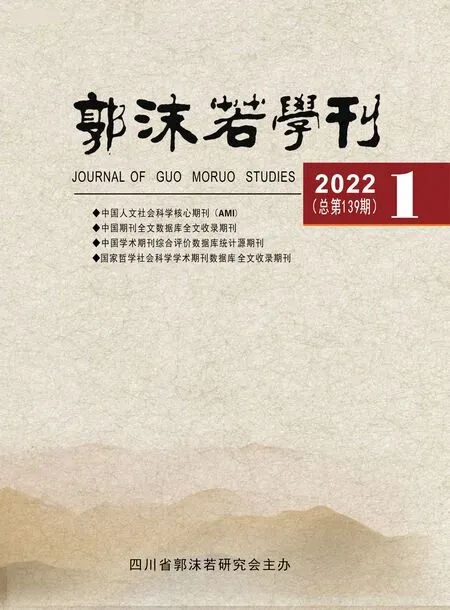論黃現璠對奴隸社會肯定論的批判與先秦社會形態理論重構*
周書燦
(蘇州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蘇州 215123)
一、《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兼論世界古代奴及其社會形態》一書的著述背景、中心觀點、框架結構、論點體系
《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兼論世界古代奴及其社會形態》(以下引用是書文字隨文標出頁碼,不再一一詳細作注)為黃現璠先生遺作。該書的中心論點即“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1981 年12月,黃氏在該書《自序》中說:
余早就認為,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漢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少數民族歷史也沒有奴隸社會,這在拙著《廣西壯族簡史》(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 年6 月)及之后相繼發表的拙文《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廣西日報》1962 年4 月2 日)和《土司制度在桂西》[《壯瑤族史科學討論會論文集(壯)》,第一集,1962 年7 月]中皆有論述。(《自序》P1)
在該書《緒論》中,黃氏又說:
余于新中國成立之前長期堅持中國古史“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只是因為思考尚未成熟,研究尚未透徹,一直無意草率撰文公表,參與社會史大論戰。1949 年12 月,余任廣西大學中文系主任,兼講《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一段時間,通過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深入研究,余開始對郭沫若先生一貫主張的中國歷史存在“奴隸社會發展階段說”產生懷疑,自己原來的認識和觀點逐步動搖。(《緒論》P2)
綜上可知,1949 年前后,黃氏對中國先秦社會形態,尤其是中國歷史上有沒有奴隸社會問題,歷經長期深入思考,有一個從有到無的180 度大轉彎的變化過程。黃氏強調,促成其在中國歷史上有無奴隸社會這一問題的認識發生重大轉變的動因在于“精研馬列”(《緒論》P2),但從甘文杰執筆撰寫的《黃現璠傳略》可知,黃氏一生,“工于史學、民族學、民俗學、語言學、壯學,博通中英日壯侗瑤語”(《黃現璠傳略》,P7)及前揭《自序》中“皆有論述”的篇章可知,促成黃氏對中國歷史上有無奴隸社會這一重大問題的認識發生深刻變化,可能還是緣于其對民族史尤其壯學的深入研究,而受到若干啟發。
茲列舉以下數證,略加申論。早在1957 年,黃氏在《廣西僮族簡史》一書中即較早通過對壯族古代社會組織的考察和研究后指出:
此后,在《儂智高起兵反宋是正義的戰爭》一文,黃氏對學術界有些學者認為“隋唐以來,桂西壯族地區是奴隸社會”的觀點進行反駁:
黃現璠史學研究涉及的領域頗為廣泛,可謂縱貫古今,畢其一生,對當代學術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對壯學的開拓性研究和積極倡導“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說。自20 世紀50 年代中期開始,黃氏對中國歷史分期與社會形態諸問題曾進行過長期深入的思考,黃氏言及,《我國民族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之探討》一文連刊于《廣西師范學院學報》1979 年第2、3 期和《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兼論世界古代奴及其社會形態》完稿之前,黃氏已陸續完成“起草于1955 年10 月3 日的一稿《我國古史分期應該重新估定》、修改于1974 年5 月8日的二稿《我國歷史分期必須重新估定》、修改于1976 年3 月2 日的三稿《我國古代歷史沒有經歷過奴隸社會》、修改于1977 年12 月6 日的四稿《中國古代史沒有奴隸社會初探》和修改于1978年11 月30 日的五稿《我國古史分期應該重新估定——古代沒有奴隸社會》”(《緒論》P2)。綜上可知,黃氏“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說,總體上是在20 世紀50 年代以后中國古史分期大討論的背景下,通過長期深入學習馬列經典著作,并從對桂西壯族歷史發展的道路和社會形態的探討中獲得啟發,逐步建立起來的。
《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兼論世界古代奴及其社會形態》共分為四編:
第一編《漢文“奴”》,分設六章,分別從語言學角度對漢文“奴”、“隸”、“奴隸”、“眾”、“民”等的語義進行考察。
第二編《外文“奴”》,分設四章,分別考察了蘇美爾、古巴比倫、古印度、古希臘文獻中“奴”的等級身份。
第三編《奴役制》,分設兩章,重點討論奴隸的定義、來源及家庭奴隸制等相關問題。
第四編《先秦社會形態》,分設四章,重構新的先秦社會形態理論,對先秦社會發展階段重新進行劃分。
全書圍繞著“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這一中心論點,層層展開,在對“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這一中心論點進行論證的同時,黃氏亦重新構建起獨到的先秦社會形態理論,并由此建立起互為關聯、勾連貫通的論點體系:
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中國古代史的發展衍變軌跡應該是“堯舜時代的族國→夏禹時代的氏國→殷商時代的城國→周代的王國→秦代的帝國”這樣一個演進過程,與此相應的社會形態為“原始社會→上貢社會→領主封建制社會(雛形)→領主封建社會(典型)→地主封建社會”(P583)。
二、黃氏對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奴隸社會肯定論的反駁與批判
自20 世紀30 年代起,長期堅持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理論指導下研究古史分期與先秦社會形態的郭沫若,在漫長的學術生涯中,雖然有關中國古史分期的論點不斷發生變化,但其始終堅持奴隸社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并肯定中國古代經歷過類似古希臘、羅馬的奴隸社會的觀點。為積極申論“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這一中心論點,黃現璠從文字語義、邏輯推理以及對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理論公式化、教條化、生搬硬套等方面,對以郭沫若為代表的有關中國奴隸社會肯定論進行了激烈的反駁和嚴厲的批判。茲仍擇其要者,舉證如下:
當戰俘或俘虜被俘后被反縛其雙手直接用為人牲,他們未經過“被奴役”的過程,何來“奴”之“身份或稱謂”?即便這些被反縛其雙手的俘虜未被立即當作“人殉人祭”或“人牲”而關押時繼續被反縛其雙手,同樣非奴也。因為淪為奴者(奴婢或奴隸),是要被奴役的,所謂“受奴役”,意味著就沒有自由只被使喚的人供主人隨便使喚和處置,而供人隨便使喚意味著就要干苦力,干苦力者不可能被反縛其雙手(P12)。
在郭先生認識的奴隸社會中,沒有自由人,沒有農民,一切民眾皆是奴隸。按照這種“郭式想象造史法”及其思維邏輯推論,我國數千年來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廣袤農耕地上世世代代從事耕種的農夫或農民,全都可以被視為“奴隸”,又何止于先秦三代焉。(P60)
黃氏以下對郭氏的批判,言辭頗為激烈。許多帶有諷刺挖苦口吻的廢話,大大超出了正常學術批評的范疇:
郭先生的政治意識太強,對奴隸先入為主之見根深蒂固。為了滿足自己構建先秦奴隸社會的主觀愿望,他不惜從“太陽下耕作的農民”中挖掘“奴隸的痕跡”,先將在“太陽下耕作的農民”形容為“農民在日下從事苦役”。苦役往往與奴隸相提并論,如此一來,“奴隸的痕跡”呼之欲出,繼而補充點郭式文學筆墨和其他牽強附會的史據,再蓋上一頂自以為正統的“歷史唯物主義”大帽,農民便等同于奴隸了。這種三段式邏輯在以郭沫若先生為代表的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的學者中普遍可見。事實上,郭先生已經正確地認識到“殷末周初稱從事耕種的農夫為‘眾’或‘眾人’”,但他為了滿足“五種社會形態說”,非要從農夫中去尋找“奴隸的痕跡”,無異于無中生有削足適履多此一舉(P64—65)。
此外,黃氏還批評“郭氏杜撰的所謂眾人或庶人一類耕種奴隸的來源為夷人俘虜,純屬虛構。至于所謂‘夷人奴隸兵’的‘前途倒戈’,更是荒謬絕倫”(P417)。
郭先生對金文“民”字之解,則具有郭氏三段式邏輯的特征,即所謂“民之為言萌也,萌之為言盲也”,民盲每通訓,則盲其一目為言奴隸也(前提),金文“民”字“均作一左目形而有刃物以刺之”而盲其左目(前提),故金文“民”字為奴隸之總稱(結論)。問題在于:郭氏三段式邏輯推理總是前提存在問題,結論自然難以成立或存在錯誤(P67)。
黃氏指斥郭氏“疑民人之制實始于周人”是“誤識”(P69),批評郭氏“對詞語、術語和概念的區別,向來是粗枝大葉或混為一談,可謂思慮過淺”(P69)。黃氏批評郭氏議論荒唐:
郭沫若先生向來是對古文詞語、術語和概念不加具體區別的,自然對詞義的演變不屑一顧,由此便會錯誤地以漢代文獻之《賈子·大政下篇》說“民之為言萌也,萌之為言盲也”來解釋周初之金文“民”字義,從而得出“今觀民之古文,民、盲殆是一事然也。然其字均作左目,而以之為奴隸之總稱”這樣十分荒唐的推論(P70)。
黃氏不厭其煩地批評郭氏:
實不知郭先生依據為何又以何據從金文“民”字形義中想象而看出了奴征?假如郭先生解金文民之說成立,商王盤庚豈不是在“恭承瞎奴之命”,周康王治下的萬民豈不都成了萬名瞎奴,全國周民一片瞎奴,這與史料記載的事實相距甚遠。以史為據,郭先生解“民”為“盲眼奴隸”之說,從史料記載上難覓蛛絲馬跡,實可謂無中生有、荒誕不經,可以休矣(P73)。
與此同時,黃氏批評郭氏將奴隸概念模糊化傾向:
在郭沫若先生看來,西周的農業生產者皆為奴隸。他認為古文獻上記載的連同土地封賜的“臣”、“鬲”或“人鬲”皆是奴隸,而庶人則是下等的奴隸;至于《詩》、《書》中的農人、農夫、和周初分封的“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懷姓九宗”、“殷頑民”等,在郭沫若先生看來都是為周族統治者生產的奴隸和種族奴隸。這類將“戰俘奴隸”與“受剝削的當地居民生產者”視為一體;將“奴隸”、“農奴”、“耕奴”、“農民”等概念混為一談,實為概念不分,混淆史實(P199)。
黃氏還批評郭氏在先秦奴隸社會產生這一問題上的單純化和教條化傾向和“郭沫若式”反復無常的主觀論證(P225),并一一舉證如下:1.郭沫若先生將奴隸制等同于奴隸社會,這已是眾所周知的事實,此為一誤(P220)。2.郭沫若先生將被奴役者一律視為奴隸,并認為由此造成社會發生質變,從而由原始公社制轉變為奴隸制,此為二誤(P220)。3.(郭沫若先生)是按照斯大林同志“規定”的條條框框認識奴隸制度的,這就難免有教條主義傾向,實為三誤(P221)。4.(郭沫若)所謂中國的“五種社會生產方式”和“五種社會形態”說,是對馬克思學說的曲解,當為四誤(P223)。5.以郭沫若先生為代表的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的一大批學者,大多數都以階級斗爭理論為綱,將中國乃至世界古代社會存在的所謂奴隸社會簡單地劃分為“奴隸主與奴隸”兩大對抗階級,實為五誤(P224)。6.郭沫若先生將夏、殷、周三代的生產力方式斷定為奴隸制度,只是在用自己主觀設定的“五種社會形態”套用于歷史,當為六誤(P225)。
此外,黃氏還批評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主張奴隸社會存在論的學者混淆恩格斯所區分的“古典古代的勞動奴隸制”和“東方的家庭奴隸制”,“將科學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生搬硬套于中國古代社會”(P230)。
綜上可知,黃氏對郭氏“眾”、“眾人”奴隸身份說的批判,的確暴露出郭氏奴隸社會肯定論中若干嚴重的缺陷和不足,這對于推動學術界對相關問題作更進一步周密的思考和研究,顯然是有一定的啟發意義的。
不惟如此,黃氏對以郭沫若為代表的奴隸社會肯定論的反駁與批判過程中,在證據和方法運用方面,也存在一系列突出的問題。如黃氏大量使用默證,茲以其第一編《漢文“奴”》為例,黃氏結合語言學材料,屢屢論及,“奴”字的本義為罪人,殷代是否有罪人為奴者,未見于甲骨卜辭文例(P13);甲骨卜辭中可能無“奴”字,……甚至懷疑殷人是否有“奴”或“奴婢”的意識或觀念(P14—15);“奴”在《說文》中所釋的本義是指古之罪人,而非奴隸(P15);隸人、徒隸、隸仆、流隸、賤隸、隸役、隸臣妾等稱謂大多始于秦代之后(P36);中國先秦社會沒有“奴婢”“奴仆”“奴隸”等連稱(P47)等。事實上,無論以上論述能否成立,都很難為其“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中心論點提供證據支持。從論證方法上,這顯系極不健全科學的默證法。黃氏的推論,很容易被駁倒,同樣,我們可以反問,甲骨文中沒有“民”,是否也意味著商代沒有“民”的存在?甲骨卜辭中沒有記載的人物和事件多得去了,我們能說只要未見卜辭記載,就意味這些人物在商代就不存在?這些事件在商代就沒發生?
在對郭沫若奴隸社會肯定論的激烈反駁與嚴厲批判和先秦社會形態理論重構過程中,黃氏對改革開放前中國學術界在馬克思主義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主導下的古史分期與社會形態研究成果,幾乎采取了全盤否定的態度,戴帽子、打棍子、上綱上線、以偏補偏,以左糾左的論述,貫穿于全書。如黃氏批評郭氏:
他將古文字學識用于研究古代史時,習慣于教條主義,并配以豐富的文學想象力,對古代史來一個張冠李戴的重塑。由此自然難免漏洞百出,許多觀點或結論呈現出淺思淺慮強詞奪理的特點,完全經不起推敲。……郭氏于史料上找不到直接有力的證據用以自圓其說時,便習慣于拿出得心應手的“奴隸轉換套用概論法”,拋棄嚴格科學的概念和定義,拋棄歷史科學法則,甚至置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法于不顧,從不對奴隸作具體論證,似乎認為僅憑自己的學術地位和聲望只要概說幾句:殷周時代的“民、庶、眾、鬲、臣、黎、工、農”都是“奴隸”,然后登高一呼,響應者便會蜂擁而至。果真不出所料,中國文人的“身重言重”傳統陋習以及以往的“階級斗爭”需要伴隨著“郭沫若效應”,開始急速惡性膨脹,以至于三十多年來眾多參與者制造的奴隸“層累說”呼之欲出,并滲透到中國當代學術界的各個角落。(P507)
此外,黃氏論著中,諸如“揭開以郭沫若先生為代表的主張中國存在奴隸社會的學者們一些杜撰和虛構史事的面紗”(P415)、“郭沫若先生的‘殷周奴隸社會’偽說”(P508)、“以郭氏、范氏為代表的‘奴隸層累宣教說’的荒誕不經”(P386)、“我國主張奴隸社會存在論的學者們習以為常又津津樂道的讕言”(P500)、“揭示出當代教條主義學奴虛構古史的面目”(P427)及“郭氏空想論證法”、“范氏幻想羅列法”(P384)、郭氏“文學虛構臆斷法”(P417)、“郭沫若史學的奴仆”(P519)、“胡言亂語的曲解”(P504)、“沒有任何具體論證的信口開河”(P505)、“欺世盜名”(P320)、“添油加醋,大放厥詞”(P418)等情緒宣泄類的抱怨和反右、文革時期目空一切、唯我獨尊、盛氣凌人乃至人身攻擊的表述,比比皆是。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對郭沫若奴隸社會肯定論反駁與批判的學術品質,也大大降低了論著的學術質量和價值。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對以上問題,僅僅點到為止,不作全面展開和進一步的深入論述。
三、對黃氏重構先秦社會形態理論的幾點思考
綜上可知,黃氏論著的中心論點即“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而欲論定“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說成立,黃氏所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即要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五種社會形態理論主導下的各種古史分期學說。從《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兼論世界古代奴及其社會形態》一書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由于該問題固有的復雜性,黃氏四面出擊,無的放矢,不惟批判郭沫若,可以說見奴即批。綜觀黃氏論著,則不難發現,黃氏把中國奴隸社會肯定論的學者,如范文瀾、呂振羽、侯外廬、周谷城、日知、尚鉞、金景芳、孫作云、王玉哲、于省吾、束世澂、趙光賢、童書業、岑仲勉、王承祒等幾乎全部批判了一遍。然而在對中國奴隸社會肯定論的批判過程中,黃氏很難抓住問題的關鍵,論證雜亂無序,不僅達不到各個擊破的目的,反而使得其對先秦社會形態理論的重構陷入破立兩難的困境。茲僅就黃氏所重構之先秦社會形態理論,作一番深入思考,略陳以下管見。
1.“族國”、“氏國”等概念術語的使用是否妥當?
2.“上貢社會”是否可以構成先秦社會發展中的一個階段?
較之于其他持“中國歷史無奴隸社會”說的學者,黃氏對先秦社會形態的理論建構最獨特之處,即認為原始社會和封建社會之間的夏代,是一個“上貢社會”。黃氏論及:
雖然夏代部落公社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具有二重性,但支配生產資料的階級是貴族統治階級,他們不僅決定著直接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而且決定著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概而言之就是上貢關系,具體的表現形式為部落公社黎民與部落公社貴族的從下貢上的經濟關系。這種上貢的生產關系在生產發展的不同階段,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具體表現形式。上貢制的產生以私有制和父權制的形成為基礎,從奉公制演變而來,它幾乎貫穿著夏代社會生產領域的各個層面,因而余認為,夏代社會是一個上貢社會,即上貢制社會。(P319)
綜觀黃氏論著,不難發現,黃氏判定夏代為“上貢社會”的主要文獻依據即《尚書·禹貢》中“任土作貢”和《周禮·天官·冢宰》中“九貢”的記載,與此同時,黃氏又一再強調,“殊不知《尚書·禹貢》所記貢賦之法而對夏禹時代的附會描述”(P310);“《周禮》中所記九貢、九賦并非完全是周代之事,甚至許多學者認為《周禮》是偽書,因而《周禮》所言不可全信”(P312)。既然《禹貢》、《周禮》所記“任土作貢”、“九貢”和夏代乃至西周時期均無關系,不知黃氏為何在“夏代之貢”一節不厭其煩地對《禹貢》、《周禮》“任土作貢”、“九貢”大做文章!此外,頗為費解的,黃氏一方面說,上貢制的生產關系“幾乎貫穿著夏代社會生產領域的各個層面”,同時又說:“夏禹時代的貢尚處于初級形態,為‘貢無定期,物無定品,品無定數’之貢,這與夏代正處于國家初級形態的部落聯盟制國家相適應。到商代,貢仍處于初級形態,只是到了周代,貢似乎始有了一定的定期,即歲貢。至于貢之定品、定數,還要到春秋戰國時代。”(P312)這里暫且不說,貫穿于黃氏全書中的“周代”是否包括春秋戰國時期,既然夏代乃至商代,“貢”均處于初級階段,換言之,夏商時期,“貢”尚未成為具有普遍和典型意義的制度,那么,為何夏代被單獨稱為“上貢社會”?根據黃氏的前后論述,則似乎西周、春秋戰國時,更應稱之為“上貢社會”!既然如此,“上貢社會”是否可以構成先秦時期社會形態發展的一個階段,自然就頗為值得懷疑!
3.“封建”一詞的濫用及領主制、地主制“封建社會”階段劃分的邏輯疑難。
黃氏力主“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但其并不否認中國歷史有封建社會。在黃氏重塑的古史體系中,雖然有領主封建社會和地主封建社會的區分,但卻屢屢將周代的分封制和西語中的“封建”互為混淆。諸如黃氏屢屢論及:“殷之所謂封,實際上不過是所封子姓或異姓同族諸侯名義歸服于殷而已,并非殷用武力滅之而行封建也。故余將其稱為領主封建社會雛形,有何不宜乎”(P379)。“商代雖有封建之制,然而土地既非商城國所有,又非商王一人所有,而是商王和方國、各諸侯國之王分別所有,商王所謂分封,僅為分封稱號以及承認各諸侯國之王自有的土地而已,此謂‘有封無建’也。而對各諸侯各國君王而言,他們擁有土地以及對土地上生活的平民百姓擁有征兵、征役等絕對統治權,此為初期領主封建制的特征之一,亦為與后世的地主只擁有土地所有權而無征兵、征役等權力的地主封建制的本質區別所在”(P451)。與此同時,黃氏又批評主張西周封建論的童書業、岑仲勉“過于強調古之‘封建’含義而忽視了其生產關系”(P451)。黃氏所強調的“封建”究竟是什么,似乎其自己也說不明白。
在黃氏論著中,黃氏一方面強調說,“商代并存的氏族公社、部落公社和地域公社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具有二重性,但支配生產資料的階級是王公貴族或封建領主統治階級,他們不僅決定著直接生產過程中人與人的關系,而且決定著分配關系、交換關系和消費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概而言之就是領主式的土地關系”(P450-451),“在商代生產關系中占主導地位的便是封建領主制”(P451),既然領主制的生產關系在商代已經占“主導”地位,卻不知黃氏為何又將商代社會稱為“領主封建制社會(雛形)”?這種文字表述上的自相矛盾,讓人屢屢感到困惑不解。還有,黃氏將周代社會視為封建領主制的典型時期,黃氏著作第四章第五節標題即為《周代無井田制》,按照人們通常理解的周代,自然應包括西周和春秋、戰國長達八百余年的歷史,而黃著《領主封建社會(典型)》一章,則寫至西周末年宣王時期,突然收筆。春秋、戰國的東周時期究竟應歸入黃氏所劃定的“領主封建社會(典型)”階段還是“地主封建社會”階段,只能令人猜謎式地進行推測了。
黃氏長期被視為改革開放以后“無奴說”的開創者和“無奴學派”的領袖,黃氏《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兼論世界古代奴及其社會形態》一書曾被部分學者稱之為“無奴說”的集大成之作。黃氏對于中國先秦社會形態的理論重構,是有著篳路藍縷的開拓之功的。然由于時代的局限,無論其對以郭沫若為代表的中國奴隸社會肯定論的反駁與批判,還是對“中國歷史沒有奴隸社會”的申論,以及對先秦社會形態理論的重構,都存在諸多嚴重的缺陷和突出的問題。本文無意全盤否定黃現璠先生的學術貢獻,對黃氏學術研究中若干缺陷與問題的全面揭露,則在于喚起學術界,在新的學術背景下,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引領下,批判繼承學術界已有研究成果,積極探尋這一對于學術界早已興趣銳減但卻永遠不會過時的重大理論問題探討獲得新的突破的嶄新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