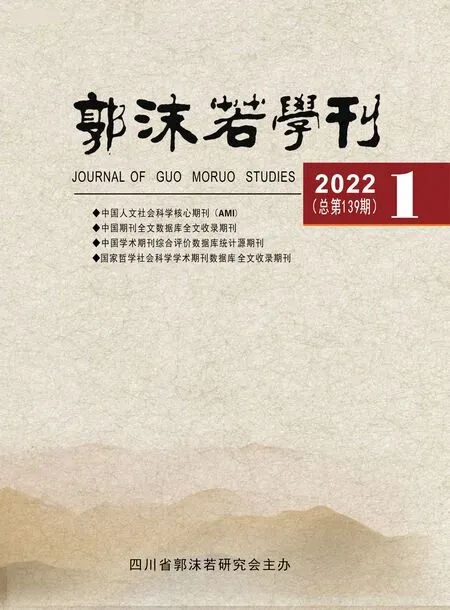從郭沫若的誤解說到鄧析對古代法制建設的特殊貢獻
楊勝寬
(樂山師范學院 文學與新聞學院,四川 樂山 614000)
歷史上那個曾經在春秋后期的鄭國政壇因屢次與子產為難而一時聲名大噪的鄧析,在郭沫若對先秦諸子學術的全面研究中并未受到起碼關注,盡管自西漢劉向、劉歆以來的歷代公私書志多將其列在名家之首,而清代《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者又將其歸入法家四子之一,但這些信息并未受到郭沫若的重視,無論在其所著的《十批判書》《青銅時代》中,還是在涉及古代社會發展演變的相關專論中,都未曾正面提及,更不用說對其開展深入研究了,這是一個頗為令人疑惑的現象。今天追溯其所以抱此態度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與多方面的因素相關。首先是直接跟20 世紀前半葉盛行的疑古思潮有關,因為那個時代的學者基本偏向于認定《鄧析子》一書乃后人偽托,并不能反映鄧析本人的學術思想。其次可能跟郭沫若對一些歷史材料的誤讀有關,或許在他的眼里,鄧析只是一個以淫辭怪說與政治改革家子產故意為難的詭辯者,而郭沫若對這類人的評價是極為負面的。在他看來,他們的學說不僅無用,而且會阻礙歷史的發展與進步。
但如果認真分析鄧析其人及其學術建設,他不僅不應該受到忽視,而且其所作所為,在其所處的發生著巨變的歷史時代,作出了不容低估的法制建設積極貢獻。
一、郭沫若把鄧析與鄧陵視為一人的理由站不住腳
在郭沫若于1945 年1 月完成的《名辯思潮的批判》一文中,歷舉分屬諸子各派的八位所謂“辯者”進行評析,在其論述荀子的名辯思想時,順帶提及鄧析。
郭沫若以為,荀子是戰國時代積極參加學術爭辯的儒家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孟子),主張“君子必辯”。郭沫若引述荀子《非相》對“圣人之辨”與“小人之辨”具有本質差別的論述之后,進而作出分析評判,認為在荀子心目中,達到“圣人之辨”境界的,可以孔子為代表;而其他諸子百家,都被歸入“小人之辨”一類。他指出:
為了證明荀子對名家的“破口大罵”,郭沫若援引了《荀子》一書的《不茍》《非十二子》《儒效》三篇文章中的具體論述,作為支撐其論點的證據。《荀子·不茍》有云:“山淵平,天地比,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也,而惠施、鄧析能之。”郭沫若在引述了這段文字之后,加括號作了如下解釋:
鄧析頗疑是墨家別派鄧陵之誤,陵或作林,后人不察,誤改為鄧析。鄧析雖辯,但與戰國時辯者實異其統類。
郭沫若提出這一“頗疑”觀點的核心依據主要有兩個,一是鄧析乃后人誤改為鄧陵;二是“陵”字在有些文獻里通“林”,所以鄧林又被誤認為了鄧析。雖然他只用了“頗疑”這樣的或然之辭,未作斷言,但其認定鄧析乃是傳習墨經的“別墨”之一,則非常清楚。然而,郭沫若的這一新奇見解,卻是沒有確切文獻內證的不合理猜測,所舉的理由根本站不住腳。
首先,郭沫若自注所舉的“陵”“林”可以通用的證據缺乏說服力。其所列舉的這些證據,最多只能證明“陵”“林”兩字在不同文獻里確實有相互通用的情況,但根本不能證明鄧析與鄧陵就是同一個人。不知道郭沫若秉持怎樣的論證邏輯,他用那么大力氣去查找“陵”“林”相通互用的文獻證明材料,但似乎他根本沒有發現,“陵”“林”互通與“析”字沒有任何邏輯上的聯系,除非他能夠證明鄧析在不同歷史文獻里又叫“鄧林”。但據筆者目前掌握的材料,關于春秋后期與子產執政為難的鄭國人鄧析,沒有又名“鄧林”的任何歷史記載。所以他只能說系后人不察而誤改,但又無法指明這“后人”是誰,故這只能算作沒有可信根據的隨意猜想。
二、《鄧析子》及其學派歸屬
今天要了解鄧析的思想學說,除了先秦諸子文獻所記載的事跡及論列的學術觀念之外,《鄧析子》一書也是值得重視的重要文獻資料。
《四庫全書總目》的編撰者認為從《鄧析子》的內容看,有與申韓刑名之學相近者,也有與黃老之學相近者,但要論鄧析的學術宗旨,與法家更為相似。表明鄧析的學術思想并不為“九流十家”的某一家所拘限。郭沫若通過對先秦諸子百家學術思想的研究分析,已經充分注意到,在戰國時代齊威王、宣王時期,稷下學宮成為天下學者的匯聚之地,各家思想在這里交流碰撞,互相訾議,互相吸納,成為歷史上百家爭鳴的一道學術風景,諸子在齊國固有的道家思想文化土壤里,孕育出后來的主要學術流派,儒家、名家、法家、陰陽家,乃至墨家,都有從道家思想中吸取滋養的印記。郭沫若指出:
三、鄧析對古代的法制建設及其歷史貢獻
我們不知道郭沫若當時如果把關于《管子》一書的法家思想的論著寫出來,他會怎樣評價管子及其后學的法治思想與實踐成效,但起碼其所謂法家的產生追溯到子產的觀點,就存在可以商榷的余地。恐怕重視并推行法治的政治觀念,其源頭應該追溯到早于子產一百多年的管仲那里,才更加符合古代歷史發展實際。
有了這樣的認識,再來評判鄧析為難子產鑄刑鼎,及其在法治理論建樹方面的貢獻,才能找到更加適合的歷史坐標。
歷來將鄧析歸為名家,都以為其擅長察辯,兩可之說、無窮之辯、淫詞怪說等等,把歷史上的鄧析描繪成一個沒有是非觀念,靠詭辯之術來為難當權者,造成社會觀念與秩序混亂的“麻煩制造者”。但從《鄧析子》一書的理論傾向看,并非如此。他在《無厚篇》里說:
這話與道家的論調頗為相似,也屬于老子所講的“君人南面之術”范疇。而鄧析對于長期以來同異無別、是非不定、黑白不分、清濁不辨的局面是憂慮和反感的,其意更不在于闡明“兩可”的合理性,而是要消弭“可”與“不可”、“此可”與“彼可”的差別,對人君而言,能夠把這套權術用好,就可以專制于上,讓臣民震懾,不敢用其私智。所表現的應該是道法思想。
《轉辭篇》云:
“民一于君,事斷于法”,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言,是鄧析法治思想的核心觀念。要真正做到遇事用法,而無所行其私智,這才是法治國家。在這樣的國度里,人君可以擁有獨尊專權的地位,但同樣不能徇私枉法。所以,在鄧析的思想觀念中,臣下與君上,在“無私”的要求上是一樣的,沒有例外。這是早期法家賞罰分明、公正無私法治觀念的反映。這種觀念,在戰國時代的法家政治家推行變法時,得到大力倡導,且不斷強化其理論的現實意義和實踐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