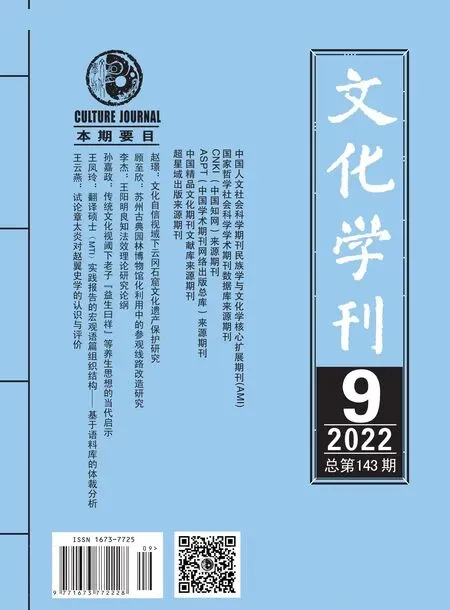淺析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完善
曲 朦 周美辰
200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以下簡稱《婚姻法》)第40條正式確立了家務貢獻補償制度,承認了家務勞動的社會經濟價值,否定了工作高于家庭、生產高于再生產的傳統觀念。但此時該制度適用以夫妻分別財產制為前提條件,嚴重背離我國“婚后共財”的社會背景,導致在司法運行中呈現“低功效、適用難”的特點,違背立法初衷,進而引發學術界對該制度的存廢之爭。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以下簡稱《民法典》)的頒布,該詰問得到了立法上的反饋。我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第1088條規定:“夫妻一方因撫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負擔較多義務的,離婚時有權向另一方請求補償,另一方應當給予補償。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決。”該規定一方面對舊有制度進行保留與改良,肯定了制度本身存在的價值;另一方面取消了分別財產制作為適用前提,為該制度的適用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一、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正當性
(一)經濟價值
家務勞動是國民經濟鏈條中重要的一環。貢獻方對家庭的付出,使得其配偶有更多的時間、精力去進行工作、生產和經營,從而間接地增加了家庭財產,而每個家庭財產的增加又促進了社會財產積累,最終為國民經濟做出了貢獻。因此,對于社會來說,家務勞動即使沒有進入生產環節直接產生經濟價值,但是對于整個社會關系的勞動來說,其是社會生產、消費等經濟圈中的重要一個環節[1]。
(二)社會價值
國是家的基礎,家是國的根基。對家務貢獻方提供離婚救濟,具有深厚的社會價值,不容忽視。其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
1.有助于提高我國結婚率和生育率
目前,我國大多數家庭都是雙職工家庭。女性在工作的同時也需要養老育幼,而男性只需要處理好工作本身。這就導致女性承受了來自社會和家庭的雙重壓力,而男性卻享受著舒適的家庭環境,毫無后顧之憂地提升自己。若是這種愛與奉獻不能得到法律的保障,那么我國愿意步入婚姻殿堂的女性人數就會縮減,相應的生育率也會降低,不利于我國人口結構合理發展。
2.有利于增強家庭凝聚力
當家務貢獻方沒有經濟來源時,其配偶因手握經濟大權產生了更高的家庭地位,甚至還可能出現經濟控制這種家庭暴力,造成夫妻雙方均不愿意犧牲自己去成就家庭的整體利益。在這種“不團結”狀態下,矛盾和摩擦就會接踵而至,最終導致家庭破裂。所以對家務貢獻方予以離婚救濟,不僅可以促成婚姻關系穩定長久,也有助于提高家務貢獻方在家庭中的地位,實現兩性平等。
3.有益于間接維護社會秩序
當夫妻感情確已破裂,離婚經濟補償有助于撫慰家務貢獻方的心理創傷,從而減少對社會的沖擊。大部分離婚案件最后的爭議都圍繞在財產分割上,對家務貢獻方給予一定的補償,可以撫慰離婚帶來的悲痛,從而間接維護了社會的穩定,減少了對社會秩序的沖擊與妨害。
(三)理論依據
作為理性的個體,夫妻雙方在決定家庭內部的角色分工時會考慮雙方不同的比較優勢以實現家庭福利函數的最大化。女性自帶生育價值,對養老育幼更加熟稔,男性自帶生產價值,對社會勞作更為在行,這也是“男主外,女主內”的分工模式一直延續至今的根本原因。除此之外,結婚意味著一個幸福家庭的結合,更意味著一份責任與道義的承擔,還意味著魚水相依的守候。因為有信任,有憧憬,有期待,才會驅使他們為家庭奉獻。承擔較多家務勞動或者做出犧牲的一方基于對婚姻的信任,有理由形成內心確信:自己可以享受到對方既得利益或者期待利益。此時,收獲方憑借貢獻方的專用性資產而獲益,提升了自身的經濟價值。一旦婚姻關系破滅,貢獻方不能享受到收獲方因人力資本提升產生的收益,夫妻之間的權利義務在離婚時失衡、付出和回報未成正比,不公平的現象形成。秉承矯正正義和分配正義的原則,有理由且有必要建立一個家務貢獻補償制度來進行平衡。
二、現有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缺失
(一)權利適用條件嚴苛
現有家務貢獻補償制度以“撫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負擔較多義務”為前提的適用條件需要修補。首先,以貢獻方付出“義務”為獲得補償的前提不夠周密。生育子女、照料對方親屬、自我犧牲、自我奉獻等很多情況都不屬于夫妻間的義務,若是將適用前提局限在義務下,對貢獻方是畸重的,不能全面評價其所做貢獻。如全職太太、全職煮夫為配偶放棄自己事業投身家庭而成就對方事業,又或如夫妻一方為滿足對方學習、進修的愿望而家務勞動和掙錢養家兩手抓,這均不能評價為夫妻之間的義務。其次,“較多”這樣的立法表述會對夫妻關系產生不良影響。“較多”的表述過于寬泛,不能確切傳遞救濟的理念,反而誤導當事人糾纏誰做家務做的更“多”上。[2]165家務貢獻補償制度本身就是為了離婚救濟,其設定本身若是具有破壞夫妻感情的隱患,便與立法初衷背向而馳,反而得不償失。最后,權利阻礙要件欠缺。家務貢獻補償的前提在于夫與妻權益的失衡,而非夫妻之間誰做的家務更多。換言之,若有填補因素可以齊平夫妻間權益,家務貢獻方便不能享有補償權。
(二)補償具體標準闕如
我國現有家務貢獻補償采用“具體辦法由雙方協議;協議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決。”的補償標準,但是在實踐中當事人往往無法達成合意,此時補償標準的量化便由法官自由裁量。囿于沒有具體的操作指南,法院都會采取較為保守的做法,對補償的具體數額進行“打折”,導致家務貢獻補償普遍偏低,救濟力度差。為此,法律應當將家事勞動進行量化,明確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計算方法,提供個案衡量的參考因素,增強制度的可操作性。
(三)給付相應規則不詳
1.給付方式不明
家務貢獻補償的最后一個環節便是非貢獻方支付貢獻方經濟補償金,該問題看似只是權利實現早晚的問題,并不值得討論,但追本溯源后可以發現不同的給付方式與補償能否實現以及補償數額的多寡休戚相關。從動態視角看待,共同財產形成包括三個階段:對人力資本的投入、人力資本的獲得、通過人力資本的變現積累共同財產。如果在第二階段離婚,有分割共同財產之權,卻無財產可供分割,此時一次性補償明顯有失公允。但采用分期補償的方式又存在變數大、風險高、執行難的隱憂,那么具體給付方式的設計,便應當從非貢獻方離婚時給付能力、分期支付下如何確保執行兩個維度加以斟酌。
2.給付形式僵化
我國司法實踐對待家務貢獻補償始終存在刻板印象,除了將補償對象限定在具體家務勞動以外,連補償形式也局限在金錢給付,這樣僵化的處理模式只會愈發地使家務貢獻補償制度虛化。相較而言,域外在此方面的規定更為活絡,除了金錢給付以外,還包括實物補償、提供擔保、設立居住權,用益物權的方式保障離婚時的家務貢獻方,家務貢獻方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選擇補償的形式。善學者假人之長以補其短,應充分借鑒域外法在此方面的處理方式,擺脫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懸置與低效。
三、現有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完善
(一)修補權利行使條件
1.修正行使條件
《民法典》第1088條將家務貢獻表述為,撫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協助另一方工作等負擔較多義務并不嚴謹。因為家務勞動不僅有勞動的強度和質量為表征,而且有親情和精神的投入[3],“義務”并不足以涵蓋全部的家務勞動。經過剖視可以發現,不論是家務勞作抑或是因家庭利益而自我犧牲,其背后蘊藏的均是對家庭的付出。所以將“義務”替換成“為家庭的付出”則更相合。只要夫或妻對家庭的付出與回報未成正比,導致離婚時夫妻利益嚴重失衡,貢獻方便享有家務貢獻補償請求權。
2.補充阻卻條件
婚姻締結,姻親關系建立。當夫妻雙方均是職工時,他們的父母或基于疼惜子女又或為“老有所依”的目的,通常會加入其家庭,成為家務勞作的主體。這種家庭模式下,只要非貢獻方父母幫助自己子女履行替代責任,使夫妻間利益處于平衡狀態,承擔更多家務勞作的夫妻一方不享有補償權。畢竟,繁重的家務勞作會對非貢獻方父母身心造成巨大消耗,這種消耗會在其變老的過程中日益顯露。一旦夫妻婚姻破裂,該消耗只由非貢獻方一人承擔,顯然不公平。
(二)合理酌量補償標準
1.避免依家政人員薪資計算
家務貢獻補償按照家政人員薪資進行計算,似乎最直接、簡便、具體。但是這種方式卻不符合人們對婚姻的預期。婚姻共享、同甘共苦、風雨與共的家庭倫理,是婚姻關系的本質,將補償按照家政人員薪資計算是對貢獻方愛與奉獻的貶損,是對付出者人格的侮辱,有悖于婚姻關系的社會屬性。
2.過錯不是減少補償的理由
家務貢獻補償制度不具有懲罰的功能,本質是調整夫妻間的利益,與過錯無關。家務貢獻補償制度的基本訴求是財產的公平分配,其中并不包括過錯行為的否定性評價。即言之,請求權人為家庭做出的犧牲或者貢獻已成既定事實,不能因過錯而被抹殺或者降低。
3.增加機會成本的量化基準

4.個案衡量的參考因素
法律規范在被適用時,法律關系主體是具體的、個別的[4]。所以,對家務勞作進行補償除了關注共相的家庭模式,也不應忽視個別的家庭關系。首先,婚姻存續期與補償的數額須成正比。婚姻存續期越長,補償數額應越高,尤其是對于全職的家務貢獻方。有西方學者研究顯示,一個人脫離社會長達8年以上,便無法回歸主流社會。此刻即使夫妻雙方平分了財產,可能依舊不足以彌補貢獻方的損害。所以婚姻存續時間較長,可以酌量多分一些補償。其次,結合家庭財產關系來確定補償數額。共有財產的家庭與全部分別財產的家庭、部分分別財產的家庭使用同一的家務補償標準,無疑割裂了家庭財產與家務勞動之間的關聯[2]167。共有財產的家庭離婚時已經平分財產,其中已經囊括了一部份經濟補償,所以與全部分別所有、部分分別所有的家庭相比補償標準需要降低。再者,受益配偶的無形獲利也不應忽視。工作的晉升、學歷的提高均屬于無形利益,但提升對方人力資本的花銷卻可以評估,評估后的數額可以包含在補償計算之中。最后,勞動強度越大,證明貢獻方遭受的損害越大,尤其是精神損害。法官可根據撫養老人和子女數量、家庭就職人數等因素來判斷強度等級,考量補償數額。需要說明的是,上述參考因素只是總的影響補償數額,而不是逐一累加計算補償總額。
(三)靈活確定給付方案
1.給付能力鎖定給付方式
夫妻無法對給付方式達成合意,法院可以根據非貢獻方的給付能力加以判定。在非貢獻方個人財產充裕的情況下,一次性給付當然是不二之選。這種方式不僅可以迅速齊平夫妻雙方權利義務,而且更高效、快捷、安全。但如果義務方責任財產稀少,人力資源還未變現,一次性給付的優勢喪失,分期給付則較為相宜。為克服分期付款的弊端,法院可視情況要求義務人提供擔保、為家務貢獻方提供具有強制執行效力的債權文書,或將分期付款協議通過計算機代碼轉化為智能合約,上傳司法區塊鏈上以確保貢獻方權利的實現。
2.給付形式契合基本需求
病人之病,憂人之憂,給付形式承擔著扶危濟困的機能,家務貢獻補償不能拘于金錢給付。法院應根據義務方的具體情況,主動詢問貢獻方的具體需求,為其進行最佳安排或者讓其自由選擇。在義務方無力現金支付時,可以采取實物分割的形式進行給付,當事人如果對實物價值存在爭議,可以進行市場評估后分割。對于離婚后居無定所的貢獻方,應在義務方的房屋上為其設定一定期限的居住權對其進行補償。值得注意的是,以股票或者有價證券進行補償,法官應主動告知這類資產價值波動大,是否保值,能否達到救濟效果并不明確。隨之由貢獻方選擇直接補償還是將股票或有價證券折價、拍賣,變賣后獲得金錢補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