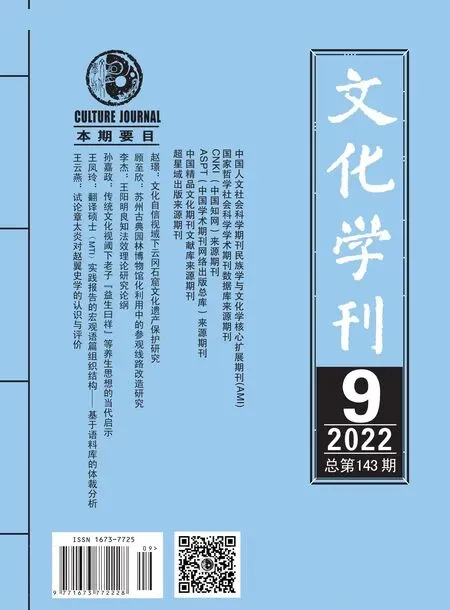翻譯碩士(MTI)實踐報告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
——基于語料庫的體裁分析
王鳳玲
一、 引言
“學位論文寫作是檢驗和考查研究生是否具有必備的知識結構、問題分析能力和研究水平的一個重要環節”[1]33。翻譯碩士(MTI)學位論文是證明翻譯碩士研究生實際翻譯水平的重要標準,是對該專業教學質量評估的重要依據,也是衡量其教學效果的重要指標[2]。實踐報告作為翻譯碩士學位論文的主要類型之一, 不僅是學生對翻譯學習和實踐的總結,也是翻譯領域知識與技能交流傳播的重要載體。特別是由于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強調培養學生的翻譯實踐能力,因此,實踐報告成為MTI研究生的主要學位論文形式[3]。然而,由于MTI專業設立至今僅十余載,論文寫作模式仍處于摸索階段。加之實踐報告作為一種新興的報告體裁有別于以往的學術學位論文,因此,學生乃至導師在實踐報告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仍存在問題和疑惑[4]。表現在學生往往已經進行了大量的口/筆譯實踐,獲得了一定的口/筆譯實踐能力和經驗,但面對將口/筆譯實踐寫成實踐報告作為學位論文時仍感力不從心,無從下手。同樣,翻譯碩士導師們也因為先前的語言學或文學研究背景,有意無意地忽略了MTI實踐報告和學術學位論文的體裁區別,仍將后者的宏觀框架結構用于指導翻譯實踐報告的寫作。雖然已有學者提出了MTI實踐報告寫作的指導性模版[5],但MTI實踐報告作為一種新興的報告體裁在實際的寫作中是否遵循了此模板?是否形成了自身典型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回答這些問題還需要借助實證研究。鑒于國外在體裁研究(genre analysis)上已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和近些年來針對新興報告體裁的實證研究在國際體裁研究領域中初現鰲頭[6-7]。國內也有不少學者對各領域新興體裁進行了研究[8-10],但目前還未有運用體裁分析理論對MTI實踐報告這一新興體裁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的實證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科學系統地采集具有代表性的MTI實踐報告自建語料庫,基于體裁分析理論和方法,分析歸納出該體裁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并進而比較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在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的異同。希望本研究能夠引起體裁研究學者們對這一體裁的關注,借此擴展體裁分析研究領域。也希望本研究能夠為MTI實踐報告寫作在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提供有價值的借鑒,服務于MTI學位論文寫作與教學,最終助推翻譯碩士專業的進一步發展。
二、理論背景
體裁在應用語言學中被廣泛地用來描述具有特定交際功能和典型結構模式的文本類型。Swales把體裁定義為話語團體成員能共享交際意圖的一組交際事件[11]。基于Swales的研究,Bhatia認為體裁是運用話語團體規約中的語言和話語資源完成特定交際意圖的成功例證,因此,交際意圖是體裁的核心因素[12]。“交際目的決定了體裁的存在,形成了語篇的‘圖式結構’(schematic structure), 即宏觀結構”[13]。基于Swales對體裁的定義,理解掌握一種體裁的關鍵在于從具有相似交際意圖的語言特征、語法形式、句子和內容中厘清其基于共同交際意圖的圖式結構,也就是總結歸納出在特定語境下的文本作者們如何運用其他成員熟悉的話語團體規約組織特定的語言資源來實現其體裁的交際意圖。為實現這一目標,體裁分析被廣泛運用于探究體裁,特別是一種新興體裁在特定的語境下為實現其交際意圖如何形成體裁自身典型的圖式結構,即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因此,體裁分析是一種自上而下(Top-down)分析語篇文本的研究范式,重在關注語篇的宏觀建構。用Bhatia的話來說,體裁分析運用語言學的分析方法回答了“為什么特定的體裁文本被寫為它自身的結構范式”[12]。體裁分析的總體目標是探究為什么一些特定的語言特征(如宏觀語篇組織結構)被某種體裁的作者們采用來實現其交際意圖。也就是說,體裁分析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從特定體裁的文本結構一致性元素中勾勒出其宏觀語篇結構和微觀語言特征。
在本研究中,MTI實踐報告(包括口/筆譯)指的是翻譯碩士研究生基于自身的口/筆譯實踐經歷,運用所學翻譯理論知識、語言技巧、技術策略和管理能力報告如何處理口/筆譯實踐過程中遇到的典型困難和代表性問題[14]。該體裁是中國翻譯碩士專業學位培養領域為實現口/筆譯教育目標而形成的具有特定交際意圖的文本類型。縱觀以往的研究,雖然不少學者就MTI實踐報告的寫作模式進行了多方的探索[15-18],然而對MTI實踐報告宏觀語篇組織結構的實證研究卻有所不足。因此,鑒于MTI實踐報告作為一種新興的報告體裁在其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給該體裁使用者造成的困難。本研究試圖采用基于語料庫的體裁分析方法致力于回答以下兩個研究問題:
(1)MTI實踐報告(包括口/筆譯)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特征是什么?
(2)口譯實踐報告和筆譯實踐報告在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有何異同?
三、研究設計
(一)自建語料庫
語料庫的設計是進行基于語料庫研究的重要前提,代表性(representativeness)是設計語料庫的核心[19]。為保證語料庫的代表性,即語料庫能較好地反映當下MTI實踐報告寫作的實際情況,本研究從我國不同省份獲批MTI專業的不同類型的院校中采集實踐報告樣本。考慮到從各省院校采集紙質的MTI實踐報告樣本的不可行性,本研究主要借助中國知網碩士論文全文數據庫進行語料收集。
本研究的語料庫建立經過了系統的多階段采樣,包括(1)確定語料庫大小:鑒于體裁分析研究具有強勞力(labor-intensive)性質和基于對以往關于報告性體裁和學位論文體裁研究的語料庫大小的參考,該語料庫決定采用60篇實踐報告,包括30篇口譯實踐報告和30篇筆譯實踐報告。(2)確定研究主體(population):基于翻譯碩士教學指導委員會頒布的院校名單,截至語料庫建立時獲批MTI專業的院校共159所。(3)分類采樣:將159所院校按外語類院校(FLI)、985院校(985PI)、211院校(211PI)及普通院校(CI)進行歸類,目的是為了保障樣本能代表不同類型院校的MTI實踐報告寫作狀況。(4)比例抽樣:如圖1所示,根據四類院校在159所院校中的數量比率,即外語院校10所(占6%)、985院校32所(占20%)、211院校49所(占31%)和普通院校68所(占43%)。因此,從四類院校分別采樣30篇口譯實踐報告和30篇筆譯實踐報告的數量比率依次為外語院校2篇(6%)、985院校6篇(20%)、211院校9篇(31%)及普通院校13篇(43%)。(5)隨機抽樣:根據以上比例從四類院校上傳到中國知網的優秀碩士論文數據庫中隨機抽樣對應數量的英語口/筆譯實踐報告。

圖1 語料庫的比例抽樣示意圖
通過以上科學系統的抽樣方法,最終從全國16個省份30個獲批MTI專業的高等院校共采集60篇MTI實踐報告,包括30篇口譯實踐報告和30篇筆譯實踐報告。具體信息如表1所示:

表1 自建MTI實踐報告語料庫信息
(二)數據分析方法
基于體裁分析以語篇交際意圖為核心的原則,識別和歸納出MTI實踐報告中具有相同交際功能和語義主旨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是本研究數據分析的基本方法。數據分析包含以下步驟:(1)依據每篇樣本的自然章節,將30篇口譯實踐報告和30篇筆譯實踐報告按章節分割為獨立的語篇,并記錄下每一個語篇的章節名稱。(2)根據章節名稱,將30篇口譯實踐報告和30篇筆譯實踐報告中具有明顯相同交際意圖的語篇章節分別歸納入同一個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在這個過程中,對一些以不同標題命名但具有相同交際意圖的章節仍需歸入同一個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3)對于不能從章節名稱清晰判斷其交際意圖的章節,研究者認真研讀章節內容以確定其交際意圖并據此歸納入對應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在這個過程中,對于具有兩個以上交際意圖的語篇,根據體裁分析的原則按主要交際意圖進行劃分。(4)根據以上步驟,完成30篇口譯實踐報告和30篇筆譯實踐報告所有章節的劃分并歸入對應的次級語料庫。
(三)信效度保障
為降低分析過程的主觀性和保障研究的信效度,研究者邀請了兩名MTI研究生對30篇口譯實踐報告和30篇筆譯實踐報告的語篇組織結構分割結果做雙重檢測(double-check)。具體來說,每一名學生嚴格按照上述步驟分別負責30篇口譯實踐報告或30篇筆譯實踐報告的章節語篇歸納結果進行二次審校。然后,研究者本人對于雙重檢測反饋出的不一致的章節語篇進行重新審讀和歸納。對爭議較大的語篇結構單元,研究者與兩名研究生協商討論后決定。最后,根據歸納入同一個宏觀組織結構單元的章節名稱及其頻次,將頻次最高的章節名稱用于標注該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這樣做是為了保障該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名稱具有最大的代表性。
四、結果與討論
(一) MTI實踐報告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特征
研究結果表明,MTI實踐報告(包括口/筆譯)共包含8個可能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采用該單元使用頻次最高的章節名稱依序標注為Abstract(摘要)、Introduction(引言)、Task Description(任務描述)、Literature Review(文獻綜述)、Theoretical Background(理論背景)、Process Description(過程描述)、Case Analysis (案例分析)和 Conclusion(結論)。可以看出MTI實踐報告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不同于實證研究型學位論文的I-M-R-D(Introduction-Method-Results-Discussion)結構。這一發現和Swales提出的一種體裁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形成并服務于該體裁的交際意圖的觀點一致。下面分別就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的主要交際意圖,使用的章節標題及其頻次進行分析和討論。
MTI實踐報告摘要(Abstract)的主要交際意圖是為口/筆譯實踐報告提供簡短、精練、準確的總結。和研究型學位論文摘要的交際功能一樣,目的是引領讀者對即將閱讀的內容進行總覽[20]。研究分析發現,語料庫中60篇實踐報告都包含摘要,且每一篇樣本都采用Abstract來作為這一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的標題。從這一點可以看出MTI實踐報告在摘要的標題上嚴格遵循傳統的學位論文規范。
MTI實踐報告引言(Introduction)的主要交際意圖是介紹口/筆譯實踐報告中任務的基本背景信息,包括選擇任務的原因、任務的核心要素及實踐任務的意義和價值。這一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具有相似于研究型論文引言的交際功能,即為理解論文中的研究活動過程和研究結果提供基本的背景信息。研究結果表明,除3篇筆譯實踐報告使用了Translation Project 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ion Project和 Task Description為標題外,所采樣的口/筆譯實踐報告在該語篇結構單元的標題上都較為統一地使用了Introduction為標題。
任務描述(Task Description)單元具有詳盡描述實踐任務核心要素的交際意圖,即交代實踐任務的目標、性質和質量等因素。這一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既不存在于具有I-M-R-D宏觀結構的實證研究型論文體裁中,也不存在于專業性體裁如信件[21-22]和課題申報書[23-24],更不存在于報告體裁,如試驗報告和商業案例報告中,因此可以說任務描述(Task Description)是MTI實踐報告體裁中獨有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從研究結果可以得出,語料庫的60篇樣本中,分別有14 篇口譯實踐報告和10篇筆譯實踐報告統一采用了Task Description 來命名這一章節。但是,由于實踐任務的多樣化,語料庫中也有樣本使用了具有自身實踐任務特點的章節標題,如Description of the Simulating Interpretation Task。
文獻綜述(Literature Review)是對某一專業領域的問題或研究搜集大量相關資料,通過提煉、分析、整理當前問題的最新進展、不同學術見解而做出綜合性介紹和闡述的一種文體。一般來說,實證研究型學位論文中都會包含這一章節。但在本研究中,MTI實踐報告是對已經完成的實踐任務進行匯報描述,是一種報告性體裁,因此,文獻綜述章節基本沒有出現在語料庫樣本中。所采樣的60 篇實踐報告中,僅有一篇口譯實踐報告含有獨立的文獻綜述章節,其標題為Literature Review。這一特殊結果可能是由于該樣本作者在寫作中受到了傳統研究型學位論文結構的影響。
MTI實踐報告理論背景(Theoretical Background)單元的主要交際意圖是介紹用于指導口/筆譯實踐任務的翻譯理論和策略,以及闡釋實踐任務中典型案例所應用的相關翻譯理論、策略及技巧。就章節標題而言,Theoretical Background使用頻率最高,其他樣本傾向于將實踐報告中的理論名稱作為該章節的標題,如Relevant Theory。
過程描述(Process Description)這一宏觀語篇結構組織單元的交際意圖為描述口/筆譯實踐的過程,通常包括譯前準備、譯中活動和譯后事宜等。因其未出現在其他體裁中,該部分也是MTI實踐報告體裁特有的宏觀組織結構單元。研究結果表明,在60篇樣本中,章節標題使用頻率最高的為Process Description。其中有4篇口譯實踐報告采用Interpretation Process和7篇筆譯實踐報告采用了Translation Process和作為章節名稱。還有少數口/筆譯實踐報告采用了其他不同形式的章節名稱。
案例分析(Case Analysis)宏觀結構單元的交際意圖在于通過案例分析的方式呈現口/筆譯實踐中最具代表性、最典型和最有啟示作用的口/筆譯現象,包括翻譯問題、策略、方法及其他。這一單元也可以看作是MTI實踐報告體裁特有的宏觀組織結構,但在一定程度上該單元具有和研究型論文的結論(Result)相似的交際功能,即報告和總結研究結果[25],只是該單元強調以案例的形式報告實踐的結果。這個單元章節名稱使用頻率最高的為Case Analysis, 其中有9篇口譯實踐報告樣本和13篇筆譯實踐報告樣本都采用了這一標題。同時,筆者也發現該單元采用了一些描述案例分析主旨的章節名稱,如Translation Difficulties and Coping Strategies和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Project等。
MTI實踐報告結論(Conclusion)的交際意圖旨在通過回顧實踐任務的核心要素,陳述實踐所得,對實踐所采用的理論和策略做出評價及提出實踐報告的教學意義和存在的不足。因為研究型論文的結論部分也會對研究概況進行回顧,且陳述該研究的啟示意義以及將來的相關研究等[26],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翻譯實踐報告中的結論單元也具有相似的交際功能。就章節名稱來說,Conclusion 使用頻率最高, 有26篇抽樣的口/筆譯實踐報告分別采用了這一章節名稱。少數幾篇樣本中還使用了諸如Summary和Summary and Reflections等的章節名稱。
(二) 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在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的異同
因為一種體裁的各語篇組織結構單元在實現其體裁共同的交際意圖時使用頻次的不同,體裁分析中通常基于一定的臨界值(cut-off)來標注各語篇組織結構單元在該體裁中的功能地位(Status)。本研究的主體屬于報告體裁的一種,研究者采納了Parkinson在對學生的試驗報告體裁分析中的臨界值(cut-off)作為標注MTI實踐報告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功能地位的標準。具體為,如果一個語篇結構單元出現頻率等于或超過80%則標注為“必須的(obligatory)”,介于50%-79%之間為“常規的(conventional)”,低于50%為“可選的(optional)”。根據這一標準,本研究進而分析討論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在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的異同。
首先,如表2所示, Abstract,Case Analysis和 Conclusion3個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都100%出現在了30篇口譯實踐報告和30篇筆譯實踐報告中,因此這3個單元在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中具有相同的“必須的”體裁功能地位。對于Case Analysis 和Conclusion兩個宏觀單元來說,前者雖然是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呈現實踐結果,但因通過具體的口/筆譯案例分析證明MTI研究生已達到學位要求的口/筆譯實踐能力,故該單元是一篇實踐報告的核心部分。后者Conclusion則是對整個實踐的總結,因此,兩個宏觀語篇結構單元在口/筆譯實踐報告中都具有“必須的”體裁功能地位。其次,Process Description單元雖然沒有100%出現在60篇樣本中,但在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中都具有高出80%的出現頻率,因此該宏觀語篇結構單元在兩種報告中也是“必須的”的體裁功能地位。從這一點可以看出,MTI實踐報告的寫作,無論是報告口譯實踐任務還是筆譯實踐任務,其Process Description都是必不可少的語篇組織結構單元。再次,Introduction單元在30篇口譯實踐報告和30篇筆譯實踐報告樣本中出現頻次分別為60%和77%, 因此,其在兩個學科專業的實踐報告中都具有相同的“常規的”體裁功能地位。研究結果中有趣的是,Task Description單元在口譯實踐報告中呈現“必須的”的體裁功能地位,達到80%的出現頻次,而在筆譯實踐報告中卻是“常規的”,僅有53%的出現頻次。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在于口/筆譯實踐任務性質的不同。一般來說,口譯實踐任務大多是“合同項目”,而筆譯實踐任務較多為學生的“自選項目”。因此,口譯學生受市場導向影響傾向于用獨立的Task Description章節描述口譯實踐任務以突出任務的實際市場價值。而筆譯學生傾向于用Introduction 章節強調“自選項目”選擇的原因及其實踐的價值和意義。因此,造成了Task Description 宏觀單元在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中呈現不同的體裁功能地位。最后,值得一提的研究結果是,分析發現Literature Review 宏觀單元在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中幾乎沒有出現,僅有一篇口譯實踐包含這一章節。同樣,Theoretical Background單元在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語料庫中出現的頻次僅分別為27.0%和33.0%,因此Literature Review和Theoretical Background單元都是MTI實踐報告體裁中的“可選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以上就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在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異同的研究結果能為口/筆譯專業的實踐報告寫作提供有區別的參考。

表2 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在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的差異
五、 結語
本研究通過科學系統的抽樣自建語料庫,采用體裁分析理論和方法對采自全國16個省30個院校的60篇MTI實踐報告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進行分析,進而對比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在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的異同。研究結果主要包括:(1)MTI實踐報告共包括8個可能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即Abstract(摘要)、Introduction(引言)、 Task Description(任務描述)、Literature Review(文獻綜述)、Theoretical Background(理論背景)、Process Description(過程描述)、Case Analysis (案例分析)和 Conclusion(結論)。(2)在8個單元中,Abstract、Process Description、Case Analysis和Conclusion在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中都為“必須的”組織結構單元;Introduction在兩個專業學科的實踐報告中為“常規的”組織結構單元;Task Description在口譯實踐報告中為“必須的”,而在筆譯實踐報告中為“常規的”; Literature Review和Theoretical Background在兩種實踐報告中都為“可選的”組織結構單元。(3)根據各宏觀語篇結構單元在60篇樣本中的名稱頻次,歸納出頻次最高的標題命名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4)研究發現,由于口/筆譯實踐報告是同一個學科專業的學位論文,所以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在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單元上基本保持一致,但由于口譯和筆譯任務性質的不同使得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在各單元的使用頻次和體裁功能地位上表現出一定的差異。
希望通過本研究所得出的研究結果對MTI實踐報告這一新興體裁在宏觀語篇組織結構上提供有借鑒的教學參考。誠然,由于篇幅有限,本研究僅限于分析MTI實踐報告的宏觀語篇組織結構及其在口譯和筆譯實踐報告之間的異同,對于各單元的宏觀語步特征和微觀語言特征未能涉及。因此,希望將來的研究能進一步報告這些體裁研究結果,以期為MTI實踐報告的寫作和教學提供更為豐富的體裁知識,最終服務于我國翻譯碩士專業的教育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