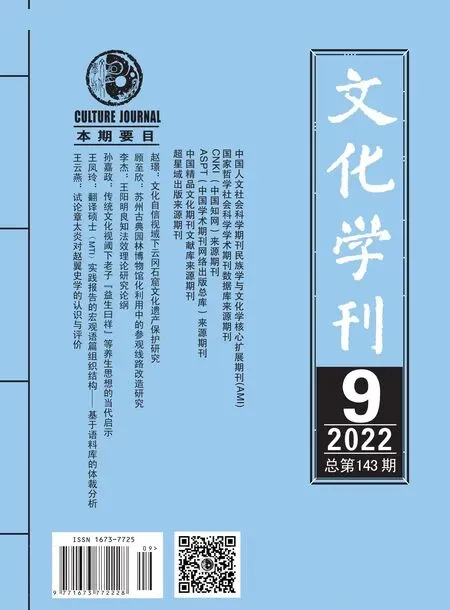社會語言學視角下的北島詩歌名稱
關林鶴
詩歌,作為一種語言藝術的存在,既傳遞著基本的語言功能,又有著區別于起到溝通、傳遞的實時語言的功能;詩歌這種文體,在寫作和表述時又有對語言的“反叛”和“升華”,正是因為詩歌語言的特殊,也使得詩歌名稱成為研究的另一角度。詩歌的名稱小到一個字符,大到十幾個字符不等,都包含了作者創作時的思想意圖。本文以北島先生的詩歌名稱為研究對象,從詩歌名稱的語言特點進行分析,尋覓其背后隱藏的社會語言學的特點。
一、 詩歌名稱的語音特點
由于漢語是一個音節一個漢字,想要表達一種意思需要不同音節的搭配組合來完成,因此,一首詩歌的名稱最少可以是一個單音節的漢字,多則七到八個音節以上的漢字來組配。為對詩歌名稱音節具有更直觀的分析,現筆者通過對來自中華詩庫203首北島詩歌的名稱進行整理,各音節數量如圖1所示。

圖1 北島詩歌名稱各音節數量柱狀圖
通過北島詩歌的音節數量柱狀圖,可以很直觀地看到北島的詩歌名稱中雙音節的詩歌名稱具有絕對優勢,占總音節數量的95.47%,這一數量上的優勢占據了詩歌的主體地位。數量第二多的是四音節的詩歌名稱,占總音節數量的37.18%[1]。
由此可以看出,詩歌名稱作為引起讀者興趣的第一層“面紗”一直以來傾向于言簡生動的屬性,這種“佳偶成雙”的音節排列形式一直深受作者和讀者的喜愛,雙音節的詩歌名稱也更能引起讀者的共鳴,如:《回憶》《路口》《期待》《歸程》等,這使得雙音節的詩歌名稱獨占鰲頭,而四音節的詩歌名稱地位也緊隨其后。
三音節和五音節這種非對稱形式的詩歌名稱相比于雙音節或四音節數量較少,這是由于三音節和五音節的詞語在結構上難以形成定式,其搭配往往表現為詞語的平列和黏合。但三音節和五音節的組合形式在一些意義上的靈動性和表達上的多樣性也得到了作者的青睞。同時六音節的詩歌名稱也占有一席之地,從六音節的名稱中可以看出,此類型的詩歌名稱大多是一句結構完整的短語,如:《我走向雨霧中》《藝術家的生活》《沉默的敲鐘人》,還有一些六音節的詩歌名稱將一些本無聯系的事物通過一首詩歌的名稱聯系起來,使這首詩歌變得神秘、富有深意,這也符合了詩歌本體作為一種藝術文化具有的超現實色彩。
十個音節及以上的詩歌名稱比較少見,但也有所出現,其數量之少也說明這種十個音節以上的詩歌名稱不能達到雙音節及四音節詞語那樣的使用程度。
二、詩歌名稱的詞匯特點
詩歌作為一種文學藝術,承載著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凝練,北島的詩歌更是將現實的感悟通過這種獨特的意象群表達出來,在他的詩歌名稱上這一想法更加得到證實。北島的詩歌名稱往往是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縱觀其詩歌名稱則多用象征性的詞匯,這樣的象征詞是作者為使內容和形式能夠完美結合而別出心裁設計的。由于北島詩歌名稱的構詞十分豐富,詞匯的搭配也十分多樣,可以分為以下幾類:[2]
(一)帶有傷感色調的名稱,如:《悼亡》《圍困》《遭遇》《憂郁》
(二)帶有顏色的名稱,如:《紅帆船》《紫色》《黑盒》
(三)帶有事物名稱的名稱,如:《船票》《古寺》《陽臺》《古堡》
(四)聯合短語的名稱,如:《蘋果與頑石》《結局或開始》《微笑 雪花 星星》
(五)帶有語氣詞的名稱,如:《真的》《睡吧,山谷》《是的,昨天》《你好,百花山》
從北島詩歌的名稱中可以發現,北島詩歌有其自身獨特的個性,其詩歌名稱中的“冷峻之感”“悲愴之情”似是在以不同尋常的手段進行的反思和批判,是在強烈的表達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巨大鴻溝,作者似是在用強有力的語言抵抗著一切不理想、不現實[3]。同時也可以透過詩歌名稱發現北島詩歌又極具新思潮、新主張,其詩歌名稱總是有意無意地流露出對集體、社會的關注,也注意對自我情感和自我意識的表達,如:《新世紀》《青年詩人的肖像》《在我透明的憂傷中》這幾首詩歌產生于特殊的歷史時期,歷經傷害的作者在創作詩歌名稱的時候有意地表達他當時的悲觀心理和憂患意識,也正是在這種憂患意識以及后來受到的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促使了北島的詩歌名稱具有濃厚的“自我感”和“人道主義”[4]。置身于當時的大環境下,北島的詩歌名稱折射出了當時北島對社會動蕩的悲哀、失望和對青年一代無法得到更好教育的疼惜,同時也使詩人堅定了在藝術創作上的批判精神。
三、詩歌名稱的語法特點
詩歌名稱都是由語素、詞、短語或組合或單獨使用的產物,目的是使這樣的組合能表達一定的意義且能夠符合詩歌名稱的特征和要求。在北島的詩歌名稱中可以發現作者依舊使用傳統的動賓、定中搭配,形式簡單易懂,可以說北島在詩歌名稱上并沒有運用太多的手法來吸引讀者,反而是運用常規表達來直述思想。
(一)動賓形式,如:《折疊方法》《呼救信號》《借來方向》
(二)定中形式,如:《港口的夢》《單人房間》《守靈之夜》[5]
還有一些詩歌名稱上的省略,這類名稱似是省略了后半部分尚未說完的話,這是詩歌名稱的一個典型特點,作為詩歌的名稱,既要達到簡潔、精巧的原則,又要新穎別致,以此作者在創作名稱的時候會用到省略的手法,設置一種懸念以達到名稱自身的引導效果。
(一)語句內容的省略,如:《自昨天起》《據我所知》《那最初的》
(二)主語的省略,如:《在歧路》《在天涯》《在路上》
這些名稱的省略,有關于主語的省略或是賓語的省略,省略的或是人或是一件事,我們不得而知,作者似是利用這樣的方式給讀者一種神秘感,使讀者充滿走進這首詩歌的好奇。
四、詩歌名稱的修辭特點
修辭即對語言的修飾和調整,是語言的一種綜合的藝術加工,在對語言進行交流思想、傳達信息時,不僅要表達得準確無誤、清楚明白,還應該生動形象、連貫得體、新穎獨特,盡可能給人以深刻的印象。在北島的詩歌中,比擬、夸張這幾類手法在詩歌名稱中使用頻率較高,使原本樸實的名稱有了更豐富的表達效果,使語言變得更加生動有層次,同時也側面地表達了主觀情感,使名稱語言上升到更具“詩感”的地位。如:《你在我透明的憂傷中》《在父親平坦的想象中》這兩首詩歌名稱中的“憂傷”和“想象”一個是形容詞,一個是動詞,這兩個詞的前面都用了形容詞來修飾,說明在這兩個名稱中這兩個詞語不再使用它們原本的詞性,而充當了名詞,即把其當作一件事情,從而賦予這件事情以狀態或性質,賦予“憂傷”以“透明的”狀態,賦予“想象”以“平坦的”性質。這兩個詩歌名稱運用的是擬物的手法,把本無形無狀的“憂傷”和“想象”變得更有意境,從而觸動人們的聯想功能,激發讀者共鳴,引起讀者興趣。
《睡吧,山谷》《冷酷的希望》《那淬火的斧子驚醒罷工的大海》這三首詩歌名稱都運用了擬人的修辭手法,《睡吧,山谷》中把本無實體生命的山谷看作有生命體征的人,對他進行“人格化”,使用“睡吧”這一語氣詞表達了對“山谷”的親切感,使得“山谷”帶有了情感的溫度。《冷酷的希望》中將“希望”進行“擬人化”,使希望具有了具體的“人物”性格,“冷酷的”一詞使“希望”變得形象、具體。概括地說,就是使“希望”變得富有生命力,同時也使讀者對作者關于這首詩歌的情感傾向一目了然。在最長的詩歌名稱《那淬火的斧子驚醒罷工的大海》中存在兩處擬人的手法:“斧子驚醒罷工的大海”和“罷工的大海”都運用了擬人的修辭手法,將本無生命的“斧子”和“大海”用強烈的詞語“淬火的”和“罷工的”來修飾,借助這些有強烈情感的修飾詞語,表達出“人物化”的情感態度,是作者情感的迸發式表達。總體來看,這種無生命的比擬和有生命體征的擬人都成為作者在詩歌名稱中表達情感的一大重要手段。
《被筆勾掉的山水》《積怨使一滴水變得渾濁》這兩首詩歌名稱將本無“功能”的事物,無限擴大,使之變得超越其本身的原始作用,如在《被筆勾掉的山水》中“筆”由原始的在紙上書寫、勾畫的功能擴大到能將動輒綿延千里的青山和奔流不息的長河“勾畫掉”的地步,如此可見其夸張程度的強烈。又如《積怨使一滴水變得渾濁》中“水變渾濁”原本是由外物、雜質的污染而形成的,而在作者的筆下“水變渾濁”是由于無色無形并且只存在于人心中的“積怨”形成的,這種夸張的手法把本來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積怨”這一情緒用強烈的描寫表現出來,加深了讀者對作者情感的認識,同時也加深了讀者對這首詩歌的感性印象。由此可見,夸張手法在詩歌名稱中的運用效果顯著,可以說,夸張的手法對于情感和意境的表達十分有效。
五、 影響詩歌名稱的因素
(一)社會文化因素
首先,北島的詩歌創作大多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這時期的詩歌名稱大多還有傳統文化的身影。無論是近代還是古代詩人創作時都較為喜歡借助傳統文化的語言風格來命名,一則可以使被命名之物擁有一個更具深度和厚度的名稱,二則也能夠使被命名之物變得更雅致,有內涵,從而提高整體的藝術水平和審美價值。如《候鳥之歌》《十年之間》《多事之秋》《告別之詞》大量使用的古字“之”,其作用相當于漢代漢語中“的”的意思,用于四字詞語組成的詩歌名稱中可以避免“的”字使用的語義平淡、結構簡單、缺乏美感等特點,從而特意營造出一種簡約、古樸雅致的風格,滿足中國傳統文化的莊重、整齊之感。
其次,北島詩歌名稱的音節數量有明顯增勢,作者在詩歌名稱的創作中已自覺使用通俗易懂的白話語言來作為名稱,不再為了追求“古典美”而故意斟酌用字,反而使用最直接、最簡單的詞語給詩歌命名,如《你在雨中等待著我》這一名稱句法結構和語義完整,直觀地交代了主要人物和狀態,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故事背景,不像其他雙音節或四音節的詩歌名稱那般“含蓄”“內斂”,極具“神秘感”。
最后,北島的詩歌分為早期詩歌和后期詩歌。早期的北島詩歌展現了人性的對抗性和對傳統的反叛性,后期的北島詩歌更多了些悲愴和堅毅,這是由于后期的北島遠離祖國,旅居外域,那種遠離祖國,猶如“浮萍”的漂泊、悲愴之感席卷其后期的情感表達,因此,在1989年以后北島創作的詩歌中無不透露出他的鄉愁、懷鄉之感,如:《回家》《過節》《鄉音》《局外人》這些名稱淺顯易懂,都可以展現當時的作者由于社會條件的原因而創作的詩歌名稱極具感情色彩[6]。
(二)心理情感因素
就北島自身的經歷而言,后期流亡在外的北島,切身體會到了流亡和居無定所,漂泊和孤寂,恰恰是這種獨特的生活經歷,練就了獨特的“北島式”人格。北島流亡在外期間,初到一個陌生的國家,環境、語言都成為他生活的巨大壓力,讓他這樣一位充滿詩情,極度追求精神世界的詩人不得不為了生存而奔走、憂愁。他流亡時期的生活與過去的生活完全的脫節,以至于北島的內心是極度空虛的、在精神上是極度壓抑的。
《在路上》這首詩歌名稱隱含的意義就是北島先生作為一個孤獨的漂泊者,無所皈依,只能一次次去漂泊,不斷地在路上[7]。《鄉愁》《毒藥》《在母語的防線上》也都體現了北島的痛苦源于對家鄉的思念。經過漫長漂泊生活之后的北島,已經變得從容、平靜、淡泊,多的是對于家鄉的遙不可及,他的詩歌名稱少了早期的那種盛氣凌人、凌厲尖銳,多的更是一份生活的苦澀和背井離鄉的艱辛。
六、結語
北島詩歌名稱風格上具有很強的主觀意識,使其創作的詩歌名稱大膽且具有批判性;名稱的表現形式上符合大眾對詩歌名稱的審美追求以雙音節為主,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新想法、新觀念,出現了八音節及以上的詩歌名稱。綜上可知,北島的詩歌名稱受到時代的先進思想的影響,不再追求名稱修飾的華麗,不再讓詩歌成為特定的“文人”才能解讀的作品,也開始向著通俗化、大眾化的腳步邁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