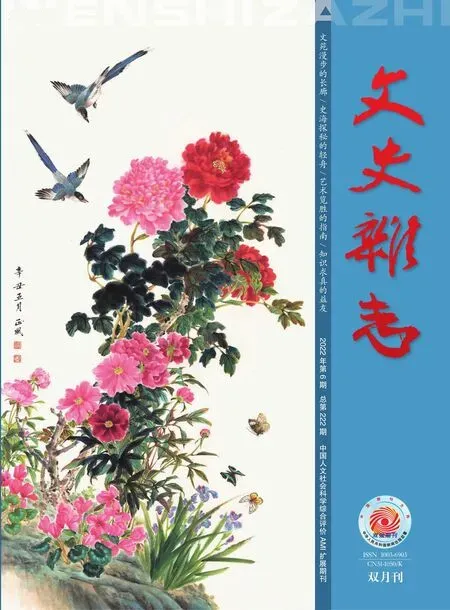《云中記》的地理關系與精神困境
郭鳳玲 周 毅
阿來的《云中記》是安多藏區災害文學的核心表達和卓越成果。在某種意義上,《云中記》集中地展現了后災害時期的藏地作為地方性空間的整體性和獨特性,釋放了藏地的空間內蘊。它以講述藏族故事的方式傳達與地震息息相關的共通性的人文關懷,并最終跨越民族與地域,借此“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
《云中記》通過祭師阿巴的講述與回憶描述了一個藏地古村落的興起與消亡。《云中記》以5·12大地震為著眼點,但不局限于地震給人帶來的傷害,而是結合傳統與現代的沖突與融合,展現了以祭師阿巴及其外甥仁欽為代表的民族精神困境。
在《云中記》中,人物的精神世界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以主要人物阿巴和仁欽為例,二人的精神世界在現代化進程中以及大地震前后都發生了變化,表現為在現代化進程與古老傳統信仰之間徘徊不定。它反映出像云中村這樣的古村落中的人們在經歷了現代化以及大災難之后,普遍陷入一種精神困境。而這樣的古村落則為《云中記》的地理關系與精神困境的闡釋提供了可能。
一、文地關系:《云中記》的地理背景與人物原型
阿來故鄉阿壩州地震、山地災害頻發,尤其是因為處于喜馬拉雅弧與緬甸弧交匯的地震帶上,20世紀后半期甚至幾乎每年都會發生1次4級以上的地震。2008年的汶川地震,激發了作家們表達情緒的創作沖動,但卻鮮有看到沉淀之作。
作為一部與“5·12”大地震相關的小說,《云中記》是在大地震發生十年之后才面世的。阿來說:“5·12以后,我一直在提防自己。警告內心里那出自一個作家本能的沖動。這個沖動就是急切地想寫點什么,表達點什么。”在別人爭先恐后趕在第一時間記錄災難,發表作品的時候,阿來卻將關于大地震的寫作計劃擱置。直到2018年大地震十周年紀念日的那一天,當聽到致哀的號笛長長的嘶鳴聲時,阿來“突然淚流滿面”,十年間的一幕幕如電影般在心頭閃現。他立即終止了其他寫作計劃,開始寫作《云中記》。
《云中記》是阿來獻給5·12地震死難者的“安魂曲”。阿來以一個祭師感知世界的方式作為寫作的出發點,創造了一個從一開始就注定要消失的村落。小說通過能夠照顧逝去之人靈魂的祭師阿巴的視角,再現了地震發生時刻地動山搖的毀滅性場景,看到了凡人看不見的生靈,構建了一個萬物有靈的世界。
祭師阿巴在云中村即將墜入岷江前,仍然堅守信仰、鄉情與人情,寧愿沉入江中也堅持在故地“安魂”。這樣一個人,一個村莊的設定,來源于多年前阿來的朋友給他看的一張照片。那是一個羌族的巫師獨自在村子里作法的照片。在整個村莊面臨搬遷之際,巫師為村子里死去的同胞送去了最后的安慰。羌族與藏族是阿壩自治州的兩大主體民族,但對于阿來來說,他更熟悉的是藏族的文化、歷史和生活,于是他把這個故事移植到一個虛構的藏族村落上。鄭少雄認為,《云中記》中的藏族祭師阿巴的原型“最有可能是”羌族釋比王明杰、楊貴生。
云中村的山川草木、小鹿旱獺、狐貍雨燕和貓頭鷹的夢境都牽動著作家的心弦。正如評論家程德培所言,阿來創作體現了一以貫之的“自然的力量”,其“最大的特點是關注人和自然的關系。在他眼中人和自然中間有一個巨大的鴻溝,這個鴻溝可能容納了人類以來的哲學,也容納了人類以來的詩歌和文學。”阿來自己也覺得《云中記》比“山珍三部曲”對自然與人的關系思考更加觸及到本質。他自認為《云中記》的貢獻“主要就是處理和提供了對死亡、對自然這兩個方面的新的書寫”,有助于人們意識到“人必須在這個充滿災難的大地上生存”,愛護自然“是一種更根本的宿命論的認識”。
二、人地關系:時空變化與身份悖論
時代賦予人身份。阿來說:“我們在談論人物的時候,要談人物和時代的關系”。時代的烙印會打在每一個身處其中的個體身上,個體無論如何也無法擺脫時代的影響。在《云中記》中,主要人物都因時代的變化而擁有不同的身份,這些身份蘊含著不同的精神傾向。
(一)云中村的地理位置與現代化狂歡
小說以云中村發展過程中的種種波折,體現出在現代化沖擊下村莊的生存困境:現代化的強勢進入給云中村翻天覆地的變化,也使人們陷入一種狂歡狀態。
小說從云中村的地理位置和歷史回顧兩方面表現了云中村從外至內的獨立與孤立。云中村是一個具有千年歷史的古村落,坐落在岷江邊上雪山半山腰的臺地上。小說通過阿巴重回云中村后的回憶,復現了村莊帶有傳奇色彩的千年歷史:祖先阿吾塔毗帶領子民由西向東,進入森林,消滅了森林里的土著居民矮腳人,從此云中村人在這里生息繁衍,并分化出云中村以外的六個村莊;但這六個村莊因為在宗教信仰上改苯教為佛教,便不再被云中村人認可。
從地理位置上來說,“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塊臺地上”的云中村,有著容易被忽視、被遺忘的意味。“半山腰上突出的臺地”這一設定也仿佛從一開始就注定了云中村終究要消失于滑坡中的命運。從演化歷史來說,從云中村分化出的六個村莊因為改變了信仰,云中村人就“不認為和他們同為一族”;小說中也多次提到阿巴與江邊村的云丹因為信仰問題而爭論。信仰上的不同從內部表現了云中村的人們在精神上自成一體的孤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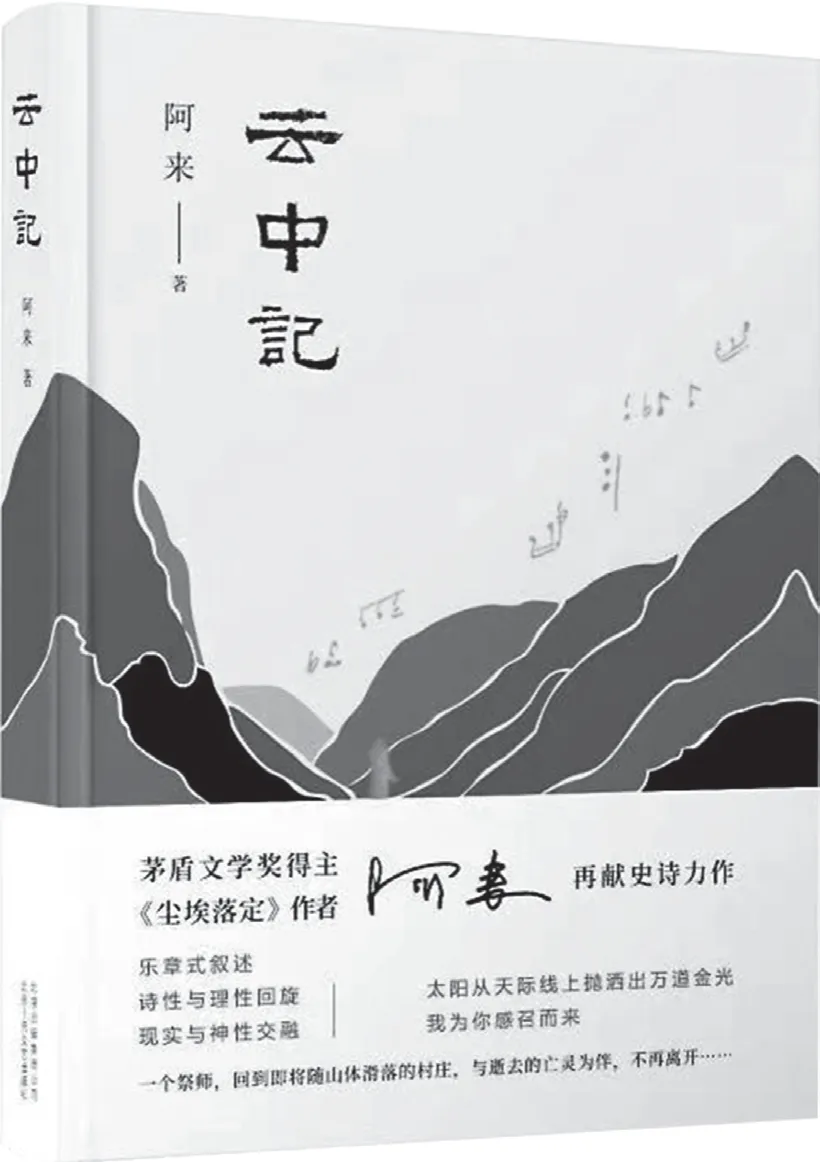
阿來著《云中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年版)
但云中村的孤立不是永恒的。現代化的到來對傳統造成沖擊,使得云中村這個原本相對封閉和獨立的整體,開始從外至內地被解構。現代化的到來給這個古老的村莊注入了狂歡的催化劑。這種狂歡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人們對現代化機器表現出興奮與狂熱以及電在云中村從無到有、失而復得的過程牽動著祭師阿巴的人生。
其一,當機器這一外來新事物出現在古老的云中村時,引發了狂歡式的反應:“肥沃的黑土在犁頭下波浪一樣翻卷。拖拉機聲響巨大。石碉發出巨大的回聲,紅嘴鴉群驚飛起來,驚惶地叫喚”。當人們處于興奮的情緒中時,眼里所看到的事物也披上一層興奮的外衣。“很重很珍貴的”水輪機在村子里停留了一天,面對這一新事物,大家“像敬神一樣繞著走了一圈又一圈”,而像警衛一樣的阿巴則因為享有擦水輪機的“殊榮”成為全家人的驕傲。他的一句“只許看,不許摸”如同口號一般四處流傳……在那個“凡是新的就是好的”的時代,機器就是現代化進程中的一面旗幟,插在了云中村的土地上,也插進了云中村人心里。
其二,電作為一種現代化的能源,在云中村經歷了從無到有,失而復得的歷程,而主人公阿巴的人生與其有著緊密的聯系。當他成為發電員時,“阿巴跟著奔涌的水流奔跑。身后,是云中村的少年和青年在跟著奔跑”。人們試圖用最原始的方式去丈量這種新能源的速度,而阿巴是那個跑在最前頭的人。他激動得“身體觸了電一樣震顫不已”。而阿巴的人生更是從此之后十幾年都與電難解難分:發電員是他引以為傲的身份,但正是由于這份工作,他在一次滑坡事故中隨水電站一同墜入了江中,人生進入了混沌期。巧妙的是,他從混沌中醒來的那天,正是受到云中村第二次通電的刺激,這可以看作是十幾年前狂歡的延續。
現代化的進入消解了云中村的自成一體。這個村莊越來越緊密地與外界聯系在一起,從而不再孤立,也不再完整。在“原先的‘共同體’向‘社會’轉化”的過程中,人們的精神除了要承受狂歡,還要遭遇身份決擇的兩難。
(二)阿巴:兩間徘徊的“上一代”
祭師阿巴是小說中最具典型性的人物形象。阿巴是發電員,是祭師,也是非遺傳人。在頗具傳奇色彩的一生中,阿巴變換著身份徘徊于現代與傳統之間。他的精神世界也糾結于傳統與現代之間。
第一,阿巴擁有現代化的身份。阿巴13歲時上了農業中學,后來成為云中村的第一個發電員。其“現代人”的身份在古老的云中村顯得獨特而令人振奮。阿巴所接受的現代化教育,所從事的現代化工作是他現代化身份的名片。
但現代化的身份并沒有一直在阿巴身上延續,他在一次滑坡事故中隨水電站一同墜入了江中,幾乎失去生命。當阿巴醒來時,發現“熹微的晨光是灰色的,周遭的一切也都是灰色的”。“他吃驚地看到自己身體上除了灰色細膩的泥漿,就什么都沒有了”。“阿巴赤條條地站在那里,身上居然沒有一道傷口”。阿巴如同回到了人類初始時的混沌時期,這也寓示著他將與之前的人生告別,試圖回歸傳統。
水電站的陷落暗示了傳統對現代的反撥。但阿巴醒來卻是受到云中村第二次通電的刺激:在醒來前夕,法鈴的裊裊余音在阿巴的腦海里亮起一團微光,“這燈把他里里外外都照亮了”,這說明阿巴作為一個個體,并不能擺脫現代化的影響。阿來這樣處理一方面弱化了傳統與現代的對立——他本就無意制造二者之間的沖突;另一方面則更深刻地表現了阿巴內心深處的困擾。

苯教經卷中的繪畫
第二,阿巴擁有傳統身份:祭師。阿巴作為云中村的一員,信仰苯教,敬奉云中村的祖先阿吾塔毗;此外,阿巴是祭師的后代,他在經歷了頗多曲折之后成為祭師。在云中村傳統的文化體系中,這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身份。在阿巴的這一身份背后,父親是一個頗具深意的存在。一方面,父親的祭師身份對于阿巴來說,代表著傳統的生命線得以延續的可能性——兒時來自父親的啟蒙是他后半生與祭師身份糾纏的源頭;另一方面,父親在云中村的現代化建設工程中意外死亡,則代表著現代化對傳統強勢的、殘酷的沖擊。這對于阿巴來說幾乎割斷了他作為祭師之子與傳統的直接聯系,暗示了傳統的生命線斷裂的危機,也為阿巴成為祭師的道路之曲折艱巨埋下了伏筆。
第三,“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這一身份,則是傳統與現代的融合。非遺傳人是阿巴的祭師身份在現代社會合理化的標志。這似乎意味著現代對傳統的接納與認可,但實際上卻充滿對祭師這一角色的合理性的懷疑。祭師的職責是安撫鬼魂,禮祭山神,但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培訓班里,人類學教授卻說對于鬼魂應該“揚棄”,作為祭師的阿巴“也沒有覺得這個揚棄有什么問題”。而這一培訓的目的,也只是作為一種旅游項目,阿巴依舊是在現代化的裹挾中被動前行。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的阿巴,終其一生都沒有把這個名稱說完整過。這在某種程度上表明阿巴內心對這一身份的不認可。這一身份與傳統祭師身份之間的差別與聯系使得阿巴陷入無所適從的困境。他以非遺傳人的身份作為回到云中村的借口,但他卻在回歸之后一直致力于脫離這一身份而成為真正的祭師。
在隨云中村一同滑落的過程中,阿巴腦海中浮現的都是與傳統身份有關的人生經歷。他在幻覺中看到了好多個自己:聽了鬼故事被嚇到的自己,第一次看見父親舉行祭祀儀式的自己,滑坡后死而復生的自己以及成為祭師的自己;但卻沒有作為云中村第一個發電員的自己——盡管那曾是他人生中為數不多的自覺偉大的時刻之一。這體現出他回到云中村以后在行動上對現代化的刻意回避而卻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實現了精神上的自覺。這是阿巴掙脫困境的方式。
(三)仁欽:出走——歸來的“下一代”
除了阿巴之外,《云中記》中還塑造了一個典型形象仁欽。仁欽的人生軌跡是一種出走—歸來的模式。出走是指仁欽作為個體在人生經歷上、思想上、心理上與傳統的云中村人有著很大差別。他接受現代化的教育,從事現代化社會的政府工作。這一點與阿巴是相似的,但現代化的程度不同。
仁欽代表的是與阿巴不同的一代人。他的童年沒有經歷過阿巴那樣“不怕鬼的故事到底意味著有鬼還是沒有”的困惑。他的困惑是既然門能從外面打開,為什么還要從里面鎖上——這是仁欽對云中村的古老傳統提出的疑問。他遠走求學,又以政府工作人員的身份回到云中村。在大地震發生之前,仁欽與云中村的關系都是若即若離的。
但無論如何,仁欽的出走都是不徹底的。阿來賦予了仁欽一個很特別的出身:私生子。這只有在古老的云中村才不被認為是有違常理的:“云中村不是東邊那些沾染漢人習氣更多的村子,仁欽也不是村里第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無論仁欽出走多遠,云中村的傳統都是他原始身份合法性的依托,這也為他之后的回歸提供了合理性。
仁欽的歸來開始于相信在地震中喪生的母親寄魂在一株鳶尾花上,并將其種子帶回工作的地方播種。這是超出仁欽的原有經驗的認知和行為。如果說阿巴是試圖回歸傳統,那么仁欽則是自覺走向傳統。也正是因為這種轉變,作為政府工作人員的他,逐漸能理解阿巴的選擇。他寧愿自己承擔處罰也不再強勢勸說阿巴離開云中村。
更重要的是,仁欽的轉變不只是作為一個個體的變化,而是指向傳統得以延續的可能。云中村消失后,仁欽發現鳶尾花已經“悄然飛翔”般綻放。這寄予了一切塵埃落定后的希望。云中村的消失并沒有讓這個村莊代代相傳的精神內核完全潰散,而是以一種心靈寄托的形式繼續留存;而仁欽就是承擔這種精神上的延續的人物之一。
三、災難體驗與神地關系
無意識的狂歡充分再現了現代化的新事物在古老的云中村那里所引起的翻天覆地的改變,甚至讓人們能夠足以把從前的歷史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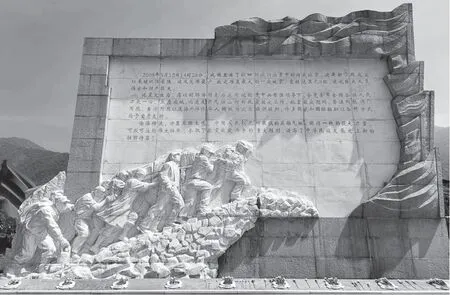
5·12地震紀念碑(在汶川縣映秀鎮)
(一)神性的失落
小說中寫到一戶多次被遺忘的人家謝巴家,這象征著云中村人離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故鄉越來越遠。小說三次寫到謝巴家被遺忘:因為麻風病而搬離之后;大地震發生后救援展開的時候以及阿巴回云中村安撫亡靈的時候。云中村人既追隨時代的變化,也留戀著“以前的真正的云中村人的生活”。一方面,“整個云中村都在向著未來的一百年而去”,另一方面,他們也對謝巴家那種返璞歸真的生活心向往之。而謝巴一家在地震中全部喪生尸骨無存,則使這種向往失去了可寄托的對象,意味著云中村人失去了一種精神寄托。
當人們沉浸在現代化的喜悅中的同時也與古老的傳統信仰漸行漸遠。當機器出現在云中村的時候,人們對它竟像敬神一樣充滿好奇與敬畏,這一方面說明現代化給云中村人的心靈帶來巨大沖擊,另一方面也體現了神性的失落。漸漸地,這種無意識地去神化變成了有意識地排斥。當老喇嘛要開口說話時,人們便開始猜測他是否會提議重新供奉苯教的祖師辛饒彌沃,并表示不贊同這種提議。實際上老喇嘛是想啟發阿巴成為祭師,但阿巴并沒有因此得到認可和尊重。
現代化沖擊造成的神性失落是一個被動的過程;但面對大地震的發生,人們認為這是被神拋棄的象征。當人們在慌亂和焦躁地等待中盼來救援的時候,并沒有將趕來救援的直升機的出現當做是“山神顯靈”。對神的信仰的失落讓云中村人在面對近乎奇跡的救援時,沒有表現出對原始信仰的忠誠,而是表現出對現代化的自發體認。
阿巴在回憶大地震發生時的場景的時候,產生了一個幻覺:他研磨出的祭神的香料迅速從沙漏滑落,時間已經變得沒有意義,“只剩下空間本身猛烈地顛簸搖晃”。這段描述也暗示了神性的失落。大地的劇烈運動帶給人強烈的不真實感。在阿巴的幻覺中,時間失去了意義,香料粉末變成了一股煙塵,就像云中村消失的那天,房屋廢墟在阿巴眼前騰起的淡淡煙塵一樣,像云中村消失后仁欽夢中的煙塵一樣,象征著毀滅、消散和虛無。
(二)神性的“回歸”
5·12大地震這場巨大的災難是人們精神上發生變化的轉折點,每個經歷了崩潰與無助的人都在嘗試尋找逃出困境的出路。《云中記》成功塑造了非遺傳承人阿巴、重拾信仰的仁欽、跳舞的央金、改過自新的祥巴以及移民村村民群像,展現了一個族群頑強的生命力。
對于阿巴來說,雖然在地震之前,他既是村里的祭師,又是政府認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關于信仰、宗教方面,他似乎很有話語權。但是作為祭師,他是個“半吊子”的不被云中村人認可者;作為非遺傳人,阿巴被賦予這一身份的初衷卻是為了發展旅游業。盡管阿巴在老喇嘛的指點下成為祭師的過程不乏神秘性,但是這一身份最初并沒有讓他在精神上與傳統信仰相呼應。
大地震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一方面,地震發生后云中村越來越多的人找到阿巴希望他能安撫亡魂,他的祭師身份突然得到認可與尊重;另一方面,阿巴既是幸存者,亦是受害者,災難引發了他對生命與自我的重新思考。阿巴雖然以履行祭師的職責為由重回云中村,但更多的原因是出自他自己:移民村潮濕的氣候,當地人熱情卻生分的稱呼,以及移民村陌生的味道都讓阿巴感到百般地不適應;與此同時,云中村消失的日子似乎越來越近,作為祭師的阿巴對那場未能如期舉行的祭山儀式念念不忘,希望能在云中村徹底消失之前彌補遺憾。
阿巴重回云中村有重述歷史的意味,這是神性“回歸”的一種表現。阿巴返回云中村后,多次反復言說歷史。他以祭師的身份在早已經變成廢墟的村落中舉行祭祀儀式,試圖重新搭建起與古老信仰之間的聯系。但他的每一場儀式都沒有得到來自神秘力量的呼應。在信與不信中徘徊大半生的阿巴最終也沒能解決困惑。
因此阿巴的努力從恢復整個族群的信仰層面上來講并沒有意義。他反反復復言說歷史,講述祖先的傳奇,試圖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口吻來消解當下的不確定性,這些都是為了對抗不可避免的遺忘與消亡。但云中村會永遠消失,幸存者們再也無家可歸的現實無法改變。在云中村最后的幾個月里,祭師阿巴不過是完成了一場自我說服,這帶有一種自欺欺人的悲哀。但對于阿巴自己來說,卻是一種逃脫困境的方式。
阿巴一個人在廢墟之上舉行儀式,與逝者對話的過程,使他覺得自己是一個真正的祭師了。這種從未有過的體驗,是他把自己的人生“提純”的結果。他的人生只剩下那些與傳統信仰有關的瞬間。這些時刻串連起來,使阿巴在生命的最后時光找到了一個純凈的自我。他終于從那些傳統或現代,信或不信的拉扯中掙脫,以付出生命為代價完成了一場悲壯的自我回歸。
對于仁欽來說,母親和舅舅阿巴是他與云中村最直接的聯系。大地震卻幾乎摧毀了這種聯系。地震發生之后,仁欽作為一名干部,奔忙在災區。等他從傷病中醒來想起母親的時候,母親已經喪生在巨石之下。
相信母親寄魂在一株鳶尾花上對于仁欽來說,是不可思議地轉變。大地震發生之前,在現代化程度更深的時代里成長起來的仁欽,在童年時代就會質疑傳統的仁欽。他與云中村的古老信仰是存在鴻溝的。仁欽一步步地遠走,無論是在現實層面還是精神層面,都與云中村越來越遠。當仁欽學有所成之后,也不愿意回到云中村工作,而是希望選擇上升更快的渠道……仁欽是自覺適應現代化的“下一代”人。如果沒有這次災難,他也許會一直繼續他的出走,但地震改變了他前行的軌跡。這場巨大的災難,使云中村的人們不得不搬離,而這個時候的仁欽,卻一步步在精神上回到了云中村。他開始相信母親寄魂在鳶尾花上,以此慰藉自己的內心。云中村消失以后,他與傳統、信仰的物質聯系也一起消失了;但在他內心深處,卻已經建立起了與傳統的精神上的聯系。
小說以仁欽看到鳶尾花開放,憂郁而鮮亮,像精靈在悄然飛翔作為結尾。這是新開始的象征。云中村憂郁的過去和鮮亮的未來,都在這花朵之上,也在仁欽心里。

阿壩縣安多藏寨一景
結語
從村莊過去到現在的變化中,人物的精神世界也經歷了相應的變化,即從尊崇古老信仰到在現代化進程中遺失信仰,再到大地震之后試圖重新建立與古老信仰的聯系。
狂歡、失落、“回歸”的模式,是《云中記》中民族精神困境的主要表現。這是具有普遍性的。云中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窘況是很多村落,尤其是少數民族村落在現代化進程中必經的陣痛;同時這種精神困境也具有特殊性,那就是遭遇大地震的創傷及其次生災害的毀滅性打擊,使得云中村人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故鄉雙雙失落,從而不得不轉向超自然力量,試圖通過與古老信仰重建聯系來自我慰藉。
綜上所述,《云中記》中所表現的民族精神困境是多方面的。這一狂歡、失落、回歸的模式,是傳統與現代拉扯的結果,也是人與災難對抗的結果。阿巴用生命獻祭,仁欽親近傳統,央金不再消費過去……文學無法給出一條適用于所有人的出路;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云中記》卻提供了一種如何背負著過去的憂郁而走向未來的閃亮的參考。
[1]曹順慶:《中國多民族歷史書寫與文學書寫——阿來的意義》,《阿來研究》,2014年第1期。
[2]阿壩州地方志編委會:《阿壩州志》,巴蜀書社2012年版,第49頁。
[3]阿來:《為〈幸存者說〉序》,見李瑾、何先鴻、唐法廣合著《幸存者說》,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4]阿來:《不只是苦難,還是生命的頌歌》,《以文記流年》,作家出版社2021年版,第16頁。
[5]行超:《阿來〈云中記〉:災難的安魂曲——訪作家阿來》,《文藝報》,2019年11月15日。
[6]阿來:《當我們談論文學時,我們在談些什么》,《美文》(上半月)2016第7期。
[7][8][9][10][11][12][13][14][16][17][18][19][20][21][22][23][24]阿來:《云中記》,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9版,第28頁,第166頁,第173頁,第75頁,第76頁,第74頁,第79頁,第77頁,第139頁,第140頁,第136頁,第215頁,第131頁,第387頁,第274頁,第152頁,第99頁。
[15]劉大先:《作為記憶、儀式與治療的文學——以阿來〈云中記〉為中心》,《當代作家評論》,2020年第3期。
基金項目:本文系川大學派培育項目“創意寫作理論與實踐”、四川省社會科學規劃項目“新世紀藏區災害文學地理研究(2001-2020)”SC20B058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