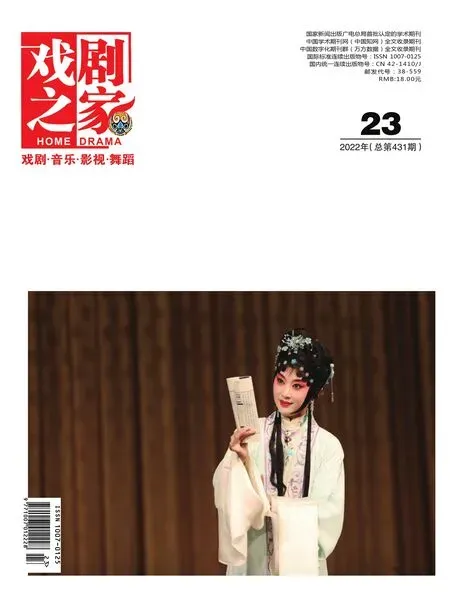歌劇史上的改革者
——以格魯克與莫扎特為例
徐 蔚
(河南大學 河南 開封 475001)
改革是一個事物進步的動力,社會的發展也離不開改革,而一場成功的改革離不開改革者們的不懈堅持和努力。在音樂歷史發展的長河中,也少不了那些推動音樂發展與進步的音樂改革者。以歌劇為例,格魯克與莫扎特同為西方音樂史中偉大的歌劇改革者,卻因所處時代的細微差異造成了創作理念上的巨大不同,分析二者歌劇改革的差異,我們可以發現其中的繼承關系以及相同點。
一、歌劇的發展歷程
17 世紀,歌劇誕生于意大利的佛羅倫薩。16 世紀70 年代“卡梅拉塔社團”的成員就人文主義和音樂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他們反對繁雜的復調對位手法,仿照古希臘悲劇創造出一種新的音樂表演體裁,其特點為:音樂不僅要表達語言,還要表現出人們真實的情感,作曲家們力圖為敘述性質的臺詞和情感宣泄的臺詞譜寫不同風格的音樂,即宣敘調、詠嘆調等,這些都為歌劇誕生奠定基礎。從威尼斯歌劇樂派的創始人蒙特威爾第提出“兩種常規”的歌劇創作思想起,歌劇中“形式與內容誰屬第一性”的問題就開始爭論不休。蒙特威爾第“以歌詞占主導,使音樂服務于歌詞”的創作理念發展到17 世紀晚期那不勒斯歌劇樂派的代表人物亞歷山德羅·斯卡拉蒂這里,他確立的返始詠嘆調的形式使優美抒情的詠嘆調占據了歌劇的主導地位,同時促進了閹人歌手的發展,音樂中的炫技成分越來越突出,音樂在歌劇中的地位明顯提高,并逐漸趨向另一種音樂風格——純音樂在歌劇中占主導地位,戲劇性則變得無足輕重。本來與歌劇融為一體的音樂,也開始與整體戲劇分道揚鑣。幾乎與歌劇同時誕生的閹人歌唱藝術在這一過程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閹人歌唱藝術既將美聲唱法的技藝發展到美輪美奐的境界,同時又使這種高技巧的演唱以過分炫耀的方式與整個戲劇情節嚴重分裂對立。由此,歌劇在形式脫離內容的環境中越走越遠,至18 世紀初期,歌劇成為一種夸張的藝術形式,淪為貴族宮廷節慶社交的裝飾品和背景音樂,無論是作曲家、腳本家,還是歌手、聽眾都沉迷于虛化浮夸的時尚之中。
二、格魯克的歌劇創作理念
(一)格魯克簡介
克里斯托弗·威利巴爾德·格魯克是德國歌劇作曲家。他早年創作意大利風格的神話歌劇。1750年起移居維也納,1754年任宮廷歌劇院樂長,開始創作法國喜歌劇。后來,他與意大利詩人卡爾薩比基合作,用其腳本創作了《奧菲歐與尤麗狄茜》《阿爾且斯特》和《巴呂德與愛萊娜》,對歌劇進行改革。1773 年,他來到巴黎,繼續歌劇改革事業。其代表作有《伊菲姬尼在奧利德》《伊菲姬尼在陶利德》《阿爾米德》等。
格魯克一生共寫了40 余部歌劇和5 部舞劇,他最大的藝術功績是歌劇改革。格魯克強調自然與真實,追求戲劇性的表現,強調對人物性格、情感和環境的刻畫。
(二)格魯克的歌劇創作理念
18世紀,佩格萊西(Giovanni Battista Pergolesi,1710—1736)的作品《女仆做夫人》在巴黎上演,引起了音樂史上著名的“喜歌劇之爭”,即意大利音樂與法國音樂到底孰優孰劣的爭論。由此,對意大利正歌劇進行改革的呼聲日趨強烈。但是由于喜歌劇之爭只提出了正歌劇所存在的一系列問題,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歌劇應該怎樣改革?是繼續走正歌劇的路,不放棄返始詠嘆調,還是來一次徹底的革命?當時還沒有確切的結論。格魯克在這個時代出生,在成長過程中受到了啟蒙運動“回歸自然”的思想熏陶。20 年后,第二次歌劇大爭論到來的時候,正歌劇改革的重擔自然地落在了格魯克等人的身上。
正是由于這樣的時代背景,格魯克對歌劇的“再創造”帶有改革性質。戲劇與聲音的高度結合才稱之為歌劇,但這一時期歌劇中的音樂發展正處于失控狀態,沒有人會從歌劇整體的結構布局去審視作品。為了迎合聽眾,歌劇創作者設計了許多滿足感官刺激的部分,完全背離了歌劇創立時的初衷。為了控制和挽回這樣的局面,格魯克以一個改革者的形象出現了。他提出了“戲劇在歌劇中的主宰地位,強調音樂要服從一切條件為戲劇服務”的歌劇創作理念。現在看來,這樣的歌劇創作理念好像是非左即右的。比如,我們現在去看格魯克的作品時,會感覺其過于樸實,有一定的局限性,他為了體現改革的理念,所以沒有辦法做到音樂與戲劇的完美統一,他的創作總是拘謹的、受限于劇本的。但是,這并不能說明格魯克就是缺乏音樂性的。只能說,他受限于歌劇改革的這個大環境。這就好像我國新文化運動時期,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人倡導全盤否定中華傳統文化,學習西方。這樣的理念至今還遭受著學術界的廣泛批評,被扣上矯枉過正的帽子。但實際上陳獨秀全盤否認傳統論也是有歷史背景的;首先,陳獨秀非常了解中國傳統文化,他怎么會不知道“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道理呢?只是因為當時的中國迫切需要改革,而傳統文化又過于根深蒂固,只能采取全盤否定這樣偏激的方式去尋找一個突破口。他與格魯克的共同點在于,他們都受限于改革者的身份。格魯克面對的是成千上萬人習以為常的錯誤觀念和審美習慣,所以他必須小心守護自己營造的理想陣地,在改革實踐中嚴格遵守自己所提出的歌劇創作原則。雖然格魯克迫于改革的壓力,無法隨心所欲地在他的歌劇中發揮音樂的職能,但是,為確保歌劇中的戲劇性和可觀性,格魯克會精心挑選劇本,這也是他的歌劇可以立足于當時社會的一個重要原因。總的來說,格魯克的歌劇改革對法國、意大利、奧地利、英國音樂戲劇的發展產生了顯著影響,是歌劇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
三、莫扎特的歌劇創作理念
(一)莫扎特簡介
沃爾夫岡·阿瑪多伊斯·莫扎特出生于奧地利薩爾茨堡,是維也納古典樂派代表人物之一。莫扎特在短短的35 年生活歷程里完成了600 余部(首)不同體裁與形式的音樂作品,包括歌劇、交響曲、協奏曲、奏鳴曲、四重奏和其他重奏、重唱作品等,幾乎涵蓋了當時所有的音樂體裁。莫扎特一生創作了22 部歌劇作品,如《費加羅的婚禮》《魔笛》等已成為歌劇經典之作。
(二)莫扎特的歌劇創作理念
僅比格魯克晚出生幾十年的莫扎特提出了與格魯克完全相反的歌劇理念,即音樂在歌劇中處于領導地位,詩歌需要無條件配合音樂。二人的差別為何如此之大?除了音樂家自身的個性化差異以外,最重要的便是年代背景的變化。我們從時間線上來看,18 世紀70 年代末,格魯克幾乎已經停止了歌劇寫作,而18 世紀80 年代,莫扎特的歌劇創作才剛剛進入成熟期。如果說格魯克將歌劇中不合理的各種關系理順了,那么莫扎特在此基礎上通過音樂的方式將歌劇的活力展現得淋漓盡致,使歌劇以更加鮮活的面貌呈現在世人面前。
他善用華麗的重唱來渲染歌劇氛圍,推動劇情的發展,比如喜歌劇《費加羅的婚禮》中第二幕的結尾處,莫扎特運用了重唱這一手法,音樂不斷增強,所有角色依次進入劇情,將原本伯爵與伯爵夫人的二重唱一直疊加至七重唱,將歌劇人物分為兩個陣營,費加羅、蘇珊娜,伯爵夫人為一組,伯爵、園丁、瑪采列那為一組,從而以重唱突出歌劇的戲劇沖突,將劇情烘托至整場的高潮,這是需要超高的復調對位技巧的。在《費加羅的婚禮》中,他還賦予了每個人物個性化的音調,歌劇中的幾個重要人物都有自己專屬的個性化詠嘆調或者獨立唱段。他將這種個性化音調貫穿歌劇的始終:費加羅的音樂速度快,剛健而幽默;蘇珊娜的音樂細膩而靈活,富有詩意;伯爵的音樂是滑稽、幽默的,帶有尖刻的諷刺精神;而伯爵夫人的音樂是猶豫、哀傷的,如第二幕中的《愛之神,請你來解救我的悲傷和我的憂愁》。莫扎特十分重視發展男低音的潛力:在那個歌劇中到處充滿華麗高音以及閹人歌手受到追捧的時代,莫扎特特立獨行地發揮男低音的潛力。最難得的是,他所寫的男低音詠嘆調十分符合人物的個性以及人物處境,例如,《費加羅的婚禮》中費加羅這一人物的出場音樂《如果你愿意跳舞,小伯爵先生》這一首詠嘆調,莫扎特就用了比較短小的音符去構成十分跳躍的旋律,再配上男低音的音色,非常吻合費加羅聰明、勇敢、善良的人物形象。這首詠嘆調明顯區別于同時代作曲家的歌劇中華麗流暢的高音詠嘆調。這也體現了莫扎特對于音樂天才的感知能力與靈活運用的能力。莫扎特與格魯克一樣,在歌劇中摒棄了那些與劇情脫節、嘩眾取寵的炫技表現,但表演他的歌劇也需要歌唱家發揮高超的演唱技巧,這種高超的演唱技巧是為音樂濃郁的抒情性和強烈的個性特征服務的。比如,歌劇《魔笛》中夜后的詠嘆調選段《復仇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燒》,其中的花腔女高音部分突出了高超的演唱技巧,更重要的是,華彩的花腔部分與夜后邪惡、黑暗的形象和復仇的處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其實,莫扎特努力發揮音樂的表現潛力,是為了用音樂表現人物形象,用或喜或悲的音樂烘托戲劇的氛圍。他從來不會濫用音樂,總是能憑借自己高超的音樂天分使歌劇中的音樂與戲劇完美地結合在一起。換言之,在某種程度上說,莫扎特歌劇中運用的音樂也是為了更好地體現戲劇。從這一點上來看,莫扎特和格魯克改革的初衷是一致的。
四、結語
綜上所述,表面上看,格魯克、莫扎特的創作理念大相徑庭,但實際上,二者都反對在歌劇中濫用與戲劇無關的音樂部分。前者在極端的時代背景下對歌劇中音樂至上的形式主義進行了力挽狂瀾的矯正;后者則在此基礎上,將音樂部分的正確運用發揮到極致,給世人做了最好的示范。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不論是音樂領域還是其他領域,改革始終是困難重重、道阻且長的。